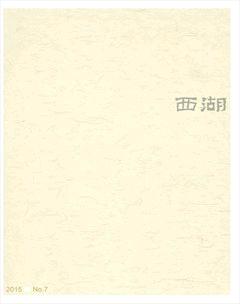老刘的尊严
蒋军辉
那个夜晚,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下,老马看见了小雅,她和几个男女一道,被警察从一家夜总会押了出来。她的衣着有些凌乱,显然是仓促之下的产物。其他男女都低着头,捂着脸,唯独她抬着头,一脸漠然地东张西望。一个民警走过去推了她一把,她愤怒地甩了甩身子。这时,她也看见了在人堆里瞧热闹的老马。
马叔。她喊道,不要告诉我爸爸。
老马吓了一跳,慌忙点点头。旁边的人都回头怪异地看着他,他用冷漠抵挡他们的目光。老马走出人堆时回了一下头,他看见小雅被推上警车时仍然很倔强。
老马回到了自己的旅馆,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霓虹灯的光披在他身上,旅馆门口的电子屏上,一行行红字在循环往复地走着:午夜钟点房每小时四十元,白天钟点房每小时二十元。旅馆地段偏僻,很少有住客找上门,生意全靠钟点房。以老马的老奸巨猾和老于世故,他当然能看出那些开钟点房的都是些什么人。只是老马没有料到,有一天小雅也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一个。每逢警察扫黄的日子,钟点房的生意就会一落千丈。今天,旅馆老板老马有些悠闲。
小雅是老马的朋友老刘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老刘现在已经带着他的老婆回到老家四川的一个什么坝上去了。老刘曾一次次向老马提过那个遥远的地名,但老马到现在都没记住。老刘如愿以偿地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去了,但他阴魂不散。在和老刘长达十来年的交往中,老马形成了许多生活习惯,老刘走了,这些习惯就失去了存在的依靠,让老马很不适应,如同把一个人培养成了烟鬼,却忽然断了他的烟,这叫什么事儿。老刘刚来这个小城时租了老马的房子,住进来的第一天,老刘在院子里炒辣椒,老马被呛得泪流满面,他赶到院子里骂道,你他娘的不吃辣椒会死吗,你想呛死我啊,再炒辣椒老子让你明天滚蛋。老刘笑笑,很无辜的样子。吃饭的时候,老刘笑嘻嘻地端着一碗辣椒进来了,说,尝尝。老马想骂他几句,又有些不好意思,尝了一口,辣得连忙跑到自来水龙头下漱口。在以后交往的日子里,老刘和老马常常会坐下一起喝几盅,老刘都会请老马吃辣椒。直到老刘走了,老马才发现辣椒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他的生活,没有辣椒的日子让他心神不定。他有时也会自己炒一碗,但总是吃不出老刘炒的口味,在每一个思念辣椒的日子里,老马总会想起老刘。他想,这个该死的老刘。
四十八岁的老马,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风烛残年了。他对自己只走了半截的人生评价不高,觉得除了攒下一大把年纪,什么收成也没有,哦,还是有的,他至少在老刘的怂恿和引领下,见识了黑夜里另一个世界的光景,睡了一堆各色各样的女人。如果说老马这半辈子干过什么坏事,那都是被老刘带的,由此可见,老刘不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没有老刘,他的人生将更加灰暗,更加不值一提。现在,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新的希望,如同一辆行驶着的汽车,是在依靠惯性往前走。他以前的人生是灰溜溜的,可以肯定,他今后的人生也不会光明到哪里去。
老刘刚来时租的是老马的一个弄堂。老马的房子在城市的边沿,自己建的,两间三楼,老马把一间三楼租掉,一间自己住。老马还拥有一间违章建筑,农村的房子和房子之间都有一条弄堂,老马把弄堂据为己有,在上面加个铁皮屋顶,在弄堂两端筑上墙,就成了一间屋子,长长的一条,用来堆放杂物。老刘来看房子,哪个房间都没看上,就看上那个杂物间。老马嘴角撇着轻蔑,穷人,没钱。老马不同意,倒不是他嫌贫爱富,而是杂物间堆满了东西,搬出来麻烦。老刘死缠烂打,非租不可。
一百块一月,怎样?
一百块?爷很穷,没见过!
大哥,行个好,我们初来乍到,没什么钱,您就当做善事,收留我们一下啦。老马这才发现院子外面还站着个女人,三十挂零,穿着鲜艳的红短裙,抹着鲜艳的口红,涂着鲜红的指甲,活像一只火鸡。女人长得有几分姿色。
内人。老刘文绉绉地说。
老马看看老刘,像一块又黑又粗的木墩子,又看看他那个漂亮的内人,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让你内人就住这儿?老马问。
后来老马就鬼迷心窍地把房子租给了他们。老马承认,自己后来走上嫖娼之路是有自身原因的,不能全怪老刘。老马是被老刘的内人迷住了,在他的潜意识里有某种邪恶的企图,似乎把房子租给他们,他就拥有了某种希望,某种可能。
老马和老刘最初的交往,就是因为老刘的内人。老刘的内人姓张,叫张玉凤,后来老马知道,张玉凤还有一个花名,叫露怡。张玉凤是原名,不公开,露怡是化名,公开的,大家都知道老刘的内人叫露怡,至于张玉凤是谁,估计没多少人知道。老马是一只喜欢腥味的猫,现在身边有了腥味,他当然像苍蝇一样,绕着腥味“嗡嗡嗡”地不肯走了。
老马有事没事地去老刘家表达一下关心,越来越表现得无微不至,但老马的注意力全在张玉凤身上,这点,老刘不会看不出来,但老刘没有点破。老马垂涎他老婆是可恶,但这也给老刘一家带来了许多方便,解决了许多问题。
老马哥——
什么事?只要张玉凤嗲声嗲气地一喊,老马立即屁颠屁颠地答应,所以,老刘有什么事找老马,都是让老婆出面。
老马的老婆刘小丽曾是个有名的悍妇,结婚这么多年,老马一直归刘小丽管,受尽刘小丽的压迫,苦大仇深。三年前,刘小丽突然变了性情,什么事情也不管了,虔心向佛,整天吃斋念经,梦想着来世投个好胎。老马像个刑满释放的犯人一样,结束了水深火热的生涯。可日子一久,老马发现这日子跟光棍没什么区别。现在,老马身边多了个风骚的张玉凤,时不时向他抛个媚眼,跟他发发嗲,这种情调,是在只会干活和骂人的刘小丽那里感受不到的。老马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的人生变得生动起来。刘小丽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可是她不管,老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
老刘夫妻俩的工作很神秘,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张玉凤的脸涂着厚厚的粉,如同油漆匠在墙上刷了一层老粉,脸上的皱纹被填平了,看上去有了虚假的青春。她的裙子总是很短,勉强能包住屁股,让人心驰神往,老马有几次产生猥琐的念头,想假装蹲下身系鞋带,看看这个风骚的女人有没有穿短裤。他从来没见过她穿长裙或裤子,哪怕很冷的天,冻得簌簌发抖也是如此。每一个傍晚,老刘骑着那辆五十块钱买来的破自行车,车后面坐着妖艳风骚的老婆,迎着夕阳的余晖,穿过一条条弄堂,去做他们的工作。金色的阳光勾勒出他们的剪影,剪影里可以读出恩爱、甜蜜和温暖,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但老马觉得他们形迹可疑。附近有许多失足女,好些都是夫妻档,老公老婆各有分工。老马怀疑老刘夫妇也是做这个的,他甚至怀疑他们并非真正的夫妻关系。他有时候会找些问题旁敲侧击,都被老刘搪塞过去了。有一次,老马闲着没事儿,戴了副宽边墨镜,像个高深莫测的老流氓,在湖滨公园闲逛。湖滨公园是本地“流莺”聚集的地方,名声不好,老马东游西逛,看着那些风姿各异露胳膊露腿的女人,时不时和一些主动凑上来的女人调戏几句。这时,背后有人说,大哥,要按摩哇?
老马回头一看,是老刘。老马说,你给我按摩?
老刘指指远处,说,那个,美女。
老马向他指的方向一看,只见张玉凤正站在一棵树下东瞧西望。老马笑了,摘下眼镜,叫了声,老刘。
老刘一愣,变了脸色,转身就走。老马获得了一种戳穿别人鬼把戏的得意。
第二天早上,老马正在吃早饭,老刘过来了,老刘以前都是十点才起床,今天起个大早,想必有事。老刘显然晚上没睡好,脸色蜡黄,眼袋下垂成两个兜。老刘说,老马,我打算搬走了,我现在去找房子。
老马说,为什么,还没到期呢。
你放心,房租我不会让你退的,是我违约。老刘说,话语里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老马这才觉得自己很不地道,人都是有面子的,老刘夫妻走上这条道,总归是有原因的,哪个男人愿意自己老婆干那事。现在,自己一把将人家的脸面撕了下来,让人家还怎么待在这儿?老马不知说什么好。整整一个上午,老马只看见张玉凤出过一次门,倒了一下垃圾,就快速地缩回屋子里了,仿佛她的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似的。
中午的时候老刘回来了,没提找房子的事,估计没找到合适的。老马提了一瓶老酒和一袋子花生,还有一些鸭舌头,来到老刘房间,冲老刘亮了亮手中的酒,说,喝两杯?老刘脸一红,讪笑一声,说,坐。又回头对躲进帘子后面的张玉凤说,弄俩菜,炒个辣椒。张玉凤低着头,打开煤气灶,弄菜去了,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骚气,像个过日子的良家妇女。
两杯酒下肚,老马的脸色就生动起来,话也多了。老马看着闷声不响的老刘,东拉西扯,眉飞色舞,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自己以前干过的一些破事儿。想不到老马平时看上去挺厚道的,却也是劣迹斑斑,龌龊不堪。老马说他十四岁时就从窗缝偷看邻居大嫂洗澡,一直偷看到十六岁。到了十六岁,不是改邪归正了,而是有了新的目标,看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同学,没事就跟踪那个女的,书读不下去了,老是盯着那女的屁股看,还在路上截过那女的,没得逞,有路人来了。二十多岁时,游手好闲,跟一帮混混朋友一道,拿几副牌,专门在人多的地方骗钱,他玩牌,那几个朋友是“托儿”,曾骗了一个小伙子给他爹看病的钱,小伙子输光了钱,一拳砸在了旁边建筑物的一块玻璃上……
操,隔壁的那个大嫂,现在都六十多岁了,一个肥胖的老太婆,想想自己对她干过那事,真恶心。老马说。
说着说着,老马就一把鼻涕一把泪了,老马说,老刘,我一见你就觉得和你投缘哩,为什么呢?咱俩都是苦命人,都干过一些自己不想干的事,你说,要是有个好混的地方,谁他妈的愿意当骗子。咱俩是一个粪缸里的两条蛆,是一个地洞里的两只黄鼠狼,怪不得我看见你这么亲切呢,原来是碰上自己人了。
老刘原本一声不吭,听着听着,弯着的腰也伸直了,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脸色也生动起来。老刘嘿嘿地笑。
老马忽然说,咱们是朋友是不是?你搬来搬去的有意思吗?别搬了,你总不能老搬家吧?这地方屁股那么大,什么事都瞒不住人。
老刘一愣,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想了想,对张玉凤说,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要不,不搬了。
张玉凤端上一碗炒螺蛳,眼睛不敢看老马,点了点头。
老马瞅着张玉凤,心里想以前费尽心思讨好她,靠近她,没料到却是个几十块钱就能到手的女人。现在,他的企图似乎唾手可得,但他又觉得,一切变得迷惘和遥远了。
两人都是好酒的人,喝得很投机。老刘酒一喝多,嘴巴就不关得那么严了,从老刘那一段段散乱无序、隐隐约约的话里,老马大概猜出了这夫妻俩的来路,原来张玉凤以前在别处的洗头房做事,老刘在一家建筑材料厂上班,听同乡说这里钱好挣,于是就赶过来了。一路上还抓紧时间赶了几趟生意。难怪初次见面,老马就觉得不对劲。
共同的爱好可以滋生友谊,老刘和老马由于喝酒走到了一起;这样的友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酒肉朋友。以前老马总是一个人喝酒,喝得寡然无味,他的儿子还小,他冲儿子晃晃酒杯,来一杯?儿子没理他,儿子更喜欢可乐。他想,生儿子有个屁用。现在有了老刘,旁边还有个张玉凤,老马的酒就喝得有声有色,情趣盎然了。他们三天两头在一起喝酒,张玉凤不管,她替他们烧好菜,就在一边看电视,电视机是老马从自己房间里给张玉凤搬过来的,老马说他不喜欢看电视。喝到下午两三点,老刘就把酒杯一推,说,不能再喝了,上班。
有一次,张玉凤逛街买衣服去了,老刘和老马又凑一块喝酒。老刘直盯着老马的眼睛,说,老弟,有一句话我说了你别生气,我看出来了,你他妈的真不是个好人。
老马问,怎么看出来的?
你对我老婆有企图。
老马笑了,说,你不是允许别人对你老婆有企图吗?
老刘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老马说,不是能一块儿喝酒吗?
朋友妻,不能骑,我的老婆,你不能打主意。老刘说。
为什么?凭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能!不就钱吗?
你老马真他妈不是个东西。老刘愤怒了,头发根根竖起,两眼滚圆,你……你也把我们当那种人,你压根没把我们当朋友,你看不起我们,你虚伪。说着要掀桌子。
老马连忙按住桌子,说,不就开个玩笑吗?你发什么酒疯。
不喝了。老刘说。两人不欢而散。老刘好几天不理老马,老马也不搭理老刘。那时刘小丽住到庙里去了,要半年才回来,儿子一去上学,老马就孤苦伶仃了。那时老马还没开旅馆,他在自己屋里开了一家小店,整天很无聊,眼巴巴地看着张玉凤进进出出,扭动着婀娜多姿的腰臀,老马看看抽屉里的几个钱,又看看张玉凤,还真有些向往。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老马还在睡觉,有人“砰砰”地敲门,老马揉着睡眼,打着哈欠,骂骂咧咧地开门,一看,是张玉凤。张玉凤进了老马的房间,说,大哥,你能借我三千块钱么?我的同乡回家了,我在这里也就认识你了。
怎么啦?老马问,老刘呢?
在派出所呢。张玉凤说,大哥,你能借我三千块钱么?我手上只有两千块。
怎么回事儿?张玉凤急,老马不急。
打架,他和几个小流氓打架,给抓进派出所了。大哥,你能借我三千块钱么?你,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不过你得快点儿。
老马原本不想借的,毕竟老刘夫妻俩是外地人,借了钱一拍屁股走人,他向谁要去?但听张玉凤这么一说,老马就有些冲动,他豪爽地说,妹子你说的是什么话,我老马能乘人之危吗,你等会儿,我去取钱。
老马于是取了钱,交给了张玉凤。两人一起去了派出所,把老刘领了出来。老刘被打得鼻青脸肿,左眼一块很大的乌青,使整个脸看上去有些怪异可笑,他的腰可能也受了些伤,走起路来斜着身子,屁股向右撅起。老马连忙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他扶上车,让他们夫妻俩先走。老刘夫妻俩一走,老马就后悔借钱给他们了,他对老刘夫妻俩的人品没有信心,他责怪自己色迷心窍,做事情太冲动,搞不好做了冤大头,如果真这样,就应该睡了张玉凤,好歹捞回些什么。他又开始琢磨怎么挽回可能的损失,他想,我得让他们写欠条,把身份证押在我这儿。
一回到家,老刘就过来叫老马一道去喝酒。老马找了一瓶女儿红,提着就过去了,张玉凤在煤气灶边忙,见了老马,妩媚地一笑。
老刘老马坐下喝酒,老马问老刘,怎么跟人打架了呢?强龙不惹地头蛇哩。
老刘说,我没惹他们,是他们先惹我。
怎么回事儿?
他们调戏我老婆。
老马费了好大劲才强忍住不让嘴里的那口酒喷出来,老马想,你老婆又不是良家妇女,睡都让人家睡了,还在乎别人调戏?
但老马什么都没说。
人都是有尊严的。老刘很严肃很认真地说。
老马又想笑,但他又觉得自己不应该笑,他收敛了脸上不屑的表情,直愣愣地看着老刘,然后庄重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老刘,咱们是朋友。
老刘说,我已经知道了。
老马知道,老刘是一个讲尊严的人,尽管他没有尊严,但是,他还是想尽力地抓住一些可怜的自尊,如同落水者死死抓住一根稻草一样,给自己一点尊严。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他的皮鞋被擦得锃亮,他说话文质彬彬,甚至拿腔拿调,除了对老马,他对四周的人不冷不热,敬而远之,这一切,其实都是老刘的“尊严”。
老刘第一次带着老马去找女人是在一次酒后,老实说要不是借助酒精的力量老马也做不成这种事,所谓酒后乱性,喝酒误事之类的,都是同一个原因。老刘诱导老马走上嫖娼这条道是有私心的,他知道老马对自己的老婆有企图,他也不信任老马的信誓旦旦,老刘试图通过别的女人来把老马对张玉凤的色心引开,提高张玉凤的安全性。
事后老马想,这是不是也他妈的事关他的尊严?
当时老刘对老马说你整天像个吃斋念佛的和尚似的,活着有意思吗?要不随我去长长见识?老马打着酒嗝说,也好,老实说,不下蛋的鸡我还真没见识过。老刘给老马介绍的第一个女人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有些胖,大饼脸,不好看。当时她坐在一间写着“理发店”三个字的破屋子门口,老刘叫了她一声,阿四,闲着啊,叔给你介绍生意。
刘叔好。女孩说。
老马,你敢进去么?老刘说。
老马被老刘这么一说,就进去了。女孩也跟着进去了。老刘于是坐在门口抽烟,他知道他这么一说,老马准进去,老马这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冲动,被人激不得,一激就冲动。老马这辈子,许多事就坏在冲动上了。老刘算是摸准了老马的脾气,只要顺着老马的脾气,老刘想让老马干什么老马就干什么。两人喝酒,喝到点了,老刘不想喝了,老马还想喝,老刘说,知道你馋酒,放不下酒杯,再来一瓶?老马说,谁他妈馋酒?不喝了。于是不喝了。
抽了两根烟的工夫,老马出来了。老刘说,还行,两根烟。
老马的酒有些醒了,脸就红了,挠挠头皮,低着头东张西望,似乎想在地上找一条缝钻进去。
这是阿四的男朋友。老刘指指角落里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
老马吓了一跳,他这才发现角落里还坐着个人,黑黑的,瘦瘦的,蔫蔫的,像有什么毛病似的。那人看了老马一眼,目光很灰暗,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老马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理发店,在门口绊了一跤,狼狈不堪。
老刘带着老婆“上班”去了,老马在屋子里躲了一天,连小店也不开了,仿佛他的丑行已经昭告天下。老马承认自己不是个好东西,曾经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事,碰上路边有失足女招引他,他也会心猿意马想入非非,可就是没那个胆;现在老刘成全了他,他又有些怪老刘,哪有把人往坏处推的呀,真要是朋友,就得往好处拉一把呀,这事要传出去,他老马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老马很生气,觉得老刘是故意把他推入了堕落的深渊。第二天中午,老刘喊老马喝酒,老马不理他,老马想质问老刘几句,可这话又说不出口。老刘连拖带拉把老马拉到了饭桌前,张玉凤热情地一张罗,老马就不好意思摆黑脸了。
谢谢你照顾了阿四的生意。老刘说,阿四长得不好看,人又病恹恹的,难得有个生意。
老马看看老刘,两只蛤蟆眼鼓着。
这也是做善事,老刘说,你给了别人一个活命的机会。
胡扯,老马说,真要行善,你还不如让我给她些钱。
这不一样,人不能吃嗟来之食,人得有尊严。老刘说。
老马想人都干上这事了还谈什么尊严,他总觉得老刘的想法哪儿出问题了,可又觉得老刘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老马不知道这个“嗟来之食”是个什么东西,老刘知道,可见老刘比他有文化,人一旦有了些文化,想法就多了,会弄出一堆的道理来折磨自己。老马可不想折磨自己,老马想反正事情已经干下了,再矫情也没意思了,这跟买菜卖菜一样,我要吃菜,你要挣钱,各有各的需要。老刘为老马的行为找到了高尚的理由,老马嘴上倔,心里的堕落感和羞耻感却在逐渐消解。对于像老马这样的人来说,有些事不去做,主要还是个面子问题,只要能找到面子上过得去的理由,这些事情都可以做。老刘给了老马一个理由,等于给了老马一个面子。既然现在面子有了,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
老马于是埋头喝酒。
善也不一定真善,恶也不一定真恶。老刘说。老刘的眼睛望着门外的天空,像一只望着井口的井底蛤蟆。
有文化。老马说。
小四的情况你看到了?老刘喝口酒说。我的小雅绝不会过这种生活。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老马瞅瞅老刘。
我女儿,我女儿叫小雅。
老马回头瞅瞅正在弄菜的张玉凤,觉得老刘的女儿年纪不会太大,要继承张玉凤的事业,为时尚早。
人得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老刘说。老刘说这话等于间接承认自己活得没有尊严,看来老刘的内心还是很脆弱的。
老刘说他们夫妻走南闯北,干过各种各样的事,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看过了别人的无奈、凄凉、得意和猖狂,也走过了自己的苦涩和无助,对人生却越来越感到惶恐,他们不想自己的女儿复制自己的人生,好在女儿还算争气,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我女儿在县城的学校读书,成绩相当好,她奶奶租了房子住在县城照顾她。老刘自豪地说,我们农村的小学,教学质量不行,在那里读书,没有出路。
他经常神经错乱,张玉凤说,他说他老担心在那种女孩子里看到小雅,这不是有毛病么?我们小雅还在老家好好读书哩。
入这行这么久,见过了各式各样做这种事的女孩子,我经常产生一种幻觉,担心自己的女儿将来也会和她们一样走这条道。老刘说。
真是不可救药。张玉凤说。
到县城读书要花很多钱的,我们的钱都花在小雅身上了。老刘没理张玉凤,说。
我跟你讲一件他发神经的事。有一回,他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看见了一个小姑娘,半天心神不定,说他越看越觉得那个小姑娘是小雅,难道是小雅自己跑出来了?然后他就跑到百乐门去找,结果被人家打出来了,你说这个人神经哇。张玉凤哭笑不得地说。
老马笑笑,老马想,看来老刘是很在乎这个宝贝女儿的。
我要让我的女儿活得有尊严,老刘说,我们不能让她在我们走过的路上再走一遍。
老马搞不明白他的这位朋友老是把“尊严”挂在嘴边有什么意思,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的,他倒是想起了他那位还赖在庙里不肯回家的老婆刘小丽,老是把来世啊、修行啊挂在嘴边,他想,要是刘小丽在家,让她和老刘谈谈,或许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老马做那种事,有了第一次,自然会有第二次,这叫破罐子破摔,一发不可收拾,到后来,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老马的事,老马臭名昭著。老马发现自己与老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老刘尽管把老马当朋友,但总觉得自己在老马面前低一等,说话都是低声下气,低眉顺眼,尊重得有些奴颜婢膝。现在不了,老刘现在敢冲老马大呼小叫、呼来喝去了,有时还拍拍老马的肩膀,老三老四的。一直被老刘尊重惯了的老马很不习惯,老马想,怎么回事儿?难道小人得志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老马想了好长时间,明白了,现在自己在老刘眼里,就是个嫖客,他和老刘已经扯平了。老刘把他老马变成了一个嫖客,就是为了给自己赢得平等。操,这难道也是老刘说的尊严?老马想,这才叫一失足成千古恨,活了一大把年纪,让老刘给黑了。
老刘在老马家租住了十来年,在这十来年里,老刘从弄堂搬到了老马家的三楼左间,后来又包下了整个楼层,老刘只要有些钱,对生活质量还是有追求的。老刘离不开老马,他是个讲交情的人,老刘说,朋友和酒一样,还是陈的好,好酒要放在身边。老刘的话让老马一阵冲动,一定要把老刘的房租免了。老刘坚决不同意,老刘说,交情归交情,房租归房租,两者不能扯一块。老刘手下有了十来个姑娘,他不让张玉凤做那种事了,专管这几个姑娘,用老刘的话说,叫“脱产”搞管理。在这十来年里,老刘的宝贝女儿逐渐长大,小雅这个名字在老刘的嘴里和老马的耳边萦绕了十来年,成了老刘和老马生活的一部分,老马从老刘的嘴里听到了小雅的成长历程,尽管没见过小雅,但他感觉小雅就在他的眼前,从一个梳着小辫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小雅的成绩是老刘的骄傲,老刘的每一次炫耀都让老马羡慕。老马有一个读书不争气的儿子,他总喜欢拿小雅做榜样,来教训自己的儿子。小雅让老马羡慕,却让老马的儿子痛恨。
在这十来年里,老马也有一些变化,他不开小店了,凑钱开了家小旅馆。尽管生意不是很好,但勉强支撑着。刘小丽彻底厌倦了尘世,或者说厌倦了他老马,出家做尼姑去了。老马独自呆坐的时候,也会想起刘小丽,想起她跳脚骂他、追着打他的情景,老马想人生真是件有意思的事。老马感到有些落寞。
两年前,六月末的一天,老刘慌里慌张地来旅馆找老马。老刘说,老马,出事了。
什么事。老马倒很淡定,问。
小雅要来看我们了。老刘说。
老马笑了,说,这不是好事吗?慌什么?
那,那……我们怎么能让她知道我们的情况呢?老刘说,我们都跟她说我们在做小生意的。
老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想起来了,小雅大学快毕业了,小雅读的大学,尽管不是名牌,却也是重点大学。让她别来不就得了。老马说。
我们说了,她不听,非要来看我们。
你没白养她,挺孝顺的。老马笑着说。
我们得想个对策出来。老刘说。
我这里你是暂时不能住了,左邻右舍对你都了解,万一漏个嘴什么的小雅受不了。老马说。去离我家远一点的地方找房子住段日子吧。
也只能这样了。老刘说,可我总得有个正当职业吧?
嗯,你们得把这几年来的经历编好。老马说,你的职业是什么呢?这样吧,我吃一次亏,这家旅馆就当是你开的,你是老板,我是店小二。
也只能这样了。老刘说,晚上我请你喝酒。
老刘很快找到了新房子,不知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居然把房子找在了离市区很远的村子里。老刘在临走前给老马的左邻右舍都送了礼,每户一坛绍兴老酒,说是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感谢大家的关照,真实的意思是让大家嘴上留德。老刘又请熟人们在小饭店吃了一顿饭,熟人们都知道老刘的女儿要来看老刘,吃了这顿饭,到时该怎么说话,都心里有数了。老刘雇了一辆车,把东西全搬了过去。老马也帮忙,老刘说,老马,小雅走后,我还搬回来,我们还一块儿喝酒。
你不是付了三个月房租吗?老马说。
管它呢,便宜房东算了,我付一个月房租他不肯租给我。
张玉凤忽然想起了什么,说,老刘,上次请朋友们吃饭,好像把小范漏了。
你怎么办事的,你是猪啊。老刘愣了一下,突然骂道。老马第一次听老刘骂老婆。
张玉凤说,你怎么全赖我啊,你自己怎么没记得。说着就委屈地抹眼泪。
老马连忙在一边劝解。老刘说,现在情况特殊,我们做事一定要周全,谁都不能得罪,晚上我去找小范,请他吃饭,给他赔个罪,否则,万一……
老马想,看来老刘这段日子神经高度紧张,都快成神经病了。
暑假,小雅来了,老刘和张玉凤带着女儿在这个小城四处逛,还带小雅来了老马的旅馆。
这是你马叔。张玉凤对女儿说。
马叔好。女孩很乖巧。
我是你爹的朋友,替你爹照看旅馆的生意。老马说。当这个耳熟能详的人站在老马面前,由抽象变为具体时,老马有些失望。小雅不如张玉凤好看,身材不如张玉凤苗条,眼睛细长,显然,老刘的那些劣质的遗传因子起了作用。
老刘带着小雅在旅馆马马虎虎地转了一圈,就要拖着女儿去逛郊区的一个人造旅游景点,小雅不想去,说是从今天开始,她要在旅馆里给父母打工。老刘急了,死活不同意,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开开心心玩几天嘛。
老马说,小雅,你在旅店里打工,那我干什么呀?你想让我失业啊。
小雅看着老马,笑了,乖巧地说,马叔,那我就不抢你饭碗了。
小雅玩了大半个月就要回校了,临走前,老刘在饭店请女儿吃饭,叫了老马作陪。老刘找的是本地一家特色饭店,点的菜也比较上档次,许多菜老马都没见识过,老马估计老刘也是头一回吃。老马知道这家饭店的东西挺贵的,老刘这回破费了。
吃完饭出了饭店,老马把老刘拉到一边,说,你是不是钱多得发霉了?
老刘说,在女儿面前我总得有个面子吧,我得让我女儿知道,他爹混得还不错。我得在女儿面前有尊严。
老马想,又是他妈的尊严。为了你老刘的这个尊严,张玉凤不知要躺倒多少回。
小雅的这一次探望,显然把老刘夫妻吓着了,小雅回校后,老刘夫妻决定回老家。
不能再待下去了。老刘说,否则小雅还会来找我们,迟早要露馅的。要是让小雅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绝对受不了,她会崩溃的。
在离开前一天,张玉凤来旅馆找老马。
马哥。张玉凤说。
老马有些奇怪,以前,张玉凤都喊他老马的。
马哥,我们要走了,以后怕是再也见不着了。
老马忽然就伤感起来,眼眶有些润湿。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张玉凤的脸上有一层羞涩。
张玉凤的话有些突然,老马一愣。老马说,没……没有,要不,拥抱一下?老马想起了电视里那些西方人之间的礼仪。
老马拥抱了张玉凤。然后,用手梳理了一下她的头发。老马想起了老刘的那句话,朋友妻,不可骑。
老刘夫妻回了老家,老刘有时会给老马打个电话,也会谈到小雅的事,老马知道小雅大学已经毕业。在老刘的话里,小雅有时出现在上海,有时出现在广州。看来小雅的工作不是很稳定。老刘的话里有一种焦虑。有一天,老马正独自一人喝酒,忽然接到了老刘的一个电话,老刘急乎乎地喊,老马,小雅来了!
什么!老刘吼道,什么来了?
小雅去你那儿了,去虞城了!老刘喊。
她到我们这儿来了?来干吗,她?
找工作!
啊!那,那怎么办?这里有你的熟人,她知道了你们的事怎么办?
听天由命吧。老刘说。老马可以想象,老刘现在一定是满脸的无奈和凄凉。
你别让她来啊,就说这里工作不好找。老马说。
晚了,她已经在路上了,她是在火车上给我们打的电话。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大人的话听不进去了。老刘说。
老马想这也只能怪老刘自己,在这十来年里,把自己在虞城的生活描绘得花团锦簇,小雅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都是虞城的美好,现在,在四处碰壁之后,小雅奔着这“花团锦簇”来了。
小雅到了虞城,来看望老马。
你爹把这旅馆盘给我了,我现在全靠它谋生。老马笑着说。
小雅笑笑,说,我不是来和你争财产的。
时间是观音菩萨,她把我们变成了老丑八怪,把你变成了一朵花。老马说,老马脑海里想起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在十来年里一直没怎么变老,那才是老马心中的一朵花。
小雅在老马家住了一段日子,后来说是找到工作了,搬走了。老马一直没见过小雅,只是常听老刘在电话里说起。
小雅现在在××集团做事,坐办公室。
小雅现在升职了,当主管了。
小雅看来混得不错,她汇给我们很多钱,让我们不要太节省,她会挣钱养我们。当然这钱我们不会花,留着给她做嫁妆。
老刘的语气里又充满了自豪,老马想着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一肚子的羡慕嫉妒恨。老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扫黄的人群里看见小雅。老马知道,老刘现在在那个没几个人的山村里很寂寞,过不了几天,老刘又会打电话过来跟他聊上几分钟,老马想,那时候,他该怎么跟这位老朋友说?
老马很苦恼,他搬出了小方桌,放在旅馆外面的水泥地上,屋里的灯光透出来,铺在了小方桌上。老马端出了几个晚上吃剩下的菜,然后,拿出一瓶酒给自己倒上。老马喝了几口,想起了什么,又拿来一个空碗,放在对面,倒满酒,端起自己的碗,和对面的碗碰了一下,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