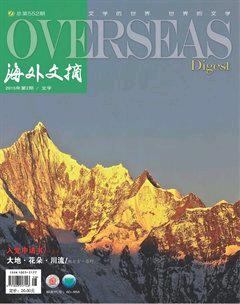入党申请书
徐伟成
入党申请书
狐狸沟村党支部领导:您好!
我叫那铜锁,狐狸沟社员,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12月,解放军攻打调兵山煤矿,屯兵狐狸沟。我家分得军粮5000余斤,我妈每天烙饼500余斤支援前线。当时我刚满月,不懂事,总是哭闹,我妈没有办法,将我放在烧热的炕上,不慎将我脑袋烫坏。长大后,因小脑受损严重,大小腿大小胳膊一边粗,行如灌铅,挥而无力。大脑也受到一定损伤,脑袋上细下粗,严重萎缩。是数不识,见亲难辨,但我对共产党认得死死的。听我妈说,杨团长临走时留下话口,如果我活下来,我就是党的人,党养我一辈子,我是为了解放调兵山煤矿而致残的,等同于残废军人。希望党组织说话算话,让我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此致
敬礼!
申请人:那铜锁
1969年7月1日
我姥姥把王先生为三舅代写的入党申请书放在支书马有田办公桌上的时候,他正装着一袋烟。他用手使劲按了按烟锅里的烟叶,瞥了一眼桌上的入党申请书,抬起头,乜斜了一眼站在门边流着鼻涕的三舅,眼角挂着讥诮的笑。他故意将嘴撇歪,重重地划着火柴,点上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干咳两声,朝姥姥说:“老那家的,今年是1974年,这个申请日期是1969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全国掀起当兵的热潮,你就是拿着这份申请带着你家傻三和老四来找我,非要傻三和老四去当兵,还要傻三入党……怎么着,老五也够岁数了?”说着支书从兜里摸出一毛钱,又拉开抽屉,找出几个钢销儿,冲三舅说:“过来,把桌上这些钱认全了,大小排出顺序,排对了,我认了,我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排不对,我就把这个申请给撕喽!噢,我不撕,你拿走,以后别来烦我!”
三舅瞧了瞧姥姥,瞟了瞟支书,姥姥没想到支书会玩这一手,她刚想说话,支书抢在姥姥头上说:“老那家的,就傻三这德性,我要替他把申请交上去,党组织真下来审查,非打我一个污蔑共产党员形象的罪名不可,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再有,你以为入党就能升官发财?就进了保险箱?错!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做群众的表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关满仓曾经也是党员,1960年老婆做小月子,他私自闪念,偷了队里还没发的救济粮。就20斤救济粮,怎么样,开除党籍,判刑2年。”
姥姥说:“我一直弄不明白,一个党员犯了法,本来是党内的事,不在党内处理,非要开除党籍再判刑?”
支书不屑地说:“当然要开除党籍了,因为他不配,他给党脸上抹了黑,玷污了党的纯洁性。别说一个关满仓了,现在有多少老革命,死的死,关的关,进牛棚的进牛棚……”
姥姥说:“我不听你讲那些,你说关满仓不配做党员,配当群众吗?群众的脸上可以瞎涂乱抹?群众的纯洁性可以随便玷污?”
支书把肩上披着的衣服向上掂了掂说:“你,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老那家的,村里对傻三怎样?你心里最清楚,出工干不干记八分。你说,他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不行,套牛让人帮着套,犁地犁不直,掰玉米掰一垄落半垄。我看他也就能和老娘们给砌堰的背背石头,扬场时扫扫麦糠。这么大了,三天两头还尿炕,共产党员有一个尿炕的吗?”
“呸!”我姥姥盯着支书眼睛说:“村里这三个党员,除了长顺岁数小,你们俩谁没踢过关寡妇家的门槛?你们干的事比尿炕臊多了!”
我姥姥几句话一出,支书不再言语,他低着头吧嗒吧嗒抽着烟,姥姥继续说:“当年杨团长临走时,怎么嘱咐你的?你又是怎么应的?你说!”姥姥的眼神从支书脑顶上移开,回头瞧着三舅,说,“好好一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招谁惹谁了!”姥姥回过头又瞪着支书说,“你说!老五想当解放军,难道是错误的吗?”
支书听了,使劲地摇头说:“那大嫂,我可没说有错呀!你可别给我扣这帽子,这帽子太大。”
姥姥说:“咱们村有多少土地,你比我清楚,每年地里产的粮食刚够吃,又来了十多个知青,天天不着调。”
支书说:“嫂子,关于知青的事可不好瞎说,也就是你,不过硬的说了要挨批的。”说着将烟锅里的烟磕在了鞋帮上,继续说:“我听说你家老五和知青混得不赖?还跟知青学吹笛子打快板,告诉老五别走得太近,前些日子双喜被几个知青打了,愣说双喜偷他们的钱,双喜娘找我说理,我一看双喜鼻青脸肿的也心疼,毕竟是本家的侄子,但我告诉他,小子,你就知足吧!这要是给知青打坏了,就得蹲大狱,我做叔的就得这么说。”
姥姥听了支书的话,忙说:“那是,那是!”她边说边从裤腰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说:“这是给你孙女扯的二尺花布头。”说完,放在桌上。支书推让着说:“放心,听说今年招兵的任务还是有的,就是招得再少,我想就凭你的关系也不是什么难事。过些日子我去武装部开会,顺便到孙部长那儿摸摸底。嫂子,咱可说好,我办事可不搭人情。”
姥姥听完说,“放心,这些日子,多上几趟山,多采一些蘑菇、榛子。”说着从支书手里接过入党申请书,给三舅使个眼色,自己先出了队部。
听姥姥说,1947年12月初,狐狸沟和赵铺驻满了解放军。当时老百姓称解放军为大军。我姥爷带着大舅二舅我妈我姨进了山,躲在狐狸庵,姥姥带着襁褓里的三舅和家里的一条狗老黑看家,解放军一进村先帮助老百姓担水、劈柴、扫院子,然后满墙刷标语,向有妇女的家里发放军粮,我姥姥看着外屋堆满的粮食,心里琢磨,听说过解放军打土豪分田地,怎么还送粮食?她把奶头放进三舅的嘴里,不知从哪儿开始高兴。马有田走进屋里,和姥姥打着招呼:“那大嫂,给孩子喂奶呢?”说着在屋里四下踅摸。
姥姥问:“这些粮食分给我家的?”
马有田听了噗嗤一笑,说:“我的那大嫂,你怎么说白话呀,这些粮食是军粮,让你烙成饼给当兵的吃。”他看着灶台说:“还不快把火点上,晌午都过了,当兵的还没吃呢。待会儿我把关寡妇找来帮你打下手。”姥姥将奶头从三舅嘴里拽出来,说:“有田兄弟,这大军到咱们这沟子里干什么?几晌走啊?”说着,姥姥将烟笸箩递了过去,马有田撇一下腿坐在炕上,捻上一袋烟,说:“还没落定就走?”说完他把烟点上,小心翼翼地说,“昨天给我们开会说得几天,看给你家这点面得住个十天半个月的。”他又压低声音说,“要打调兵山煤矿了,听说你大老伯子在矿上?”姥姥点点头,马有田说:“解放军头三天就把山口封了,今天又把进山的路封了,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地吸一口烟,两个鼻孔里像着了火一样冒着烟,沉默一会儿又说:“叫大哥带着孩子们回来吧!天寒地冻的,别给孩子们冻病了。”马有田站起来,边往外走边说,“还有好几家没通知呢,我先走了。”
姥姥把三舅往后背了背,送马有田出了门,临出院门问:“有田兄弟,你那两个侄女怎么办?”
马有田回过头说:“解放军和女人家不乱来,放心,出事算我的。”
姥姥望着马有田走远了心里骂,给我当姑爷,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性。姥姥把门掩好,看着老黑在窗底下晒太阳,回到屋里将灶锅里的温水舀到一个盆里,出门将温水加在带冰碴的狗食盆子里。姥姥巡视了一下,屋里垛着的一袋袋面粉,拿起灶木铲,掏起灶灰,把灶灰一点点扫进簸箕里,出门倒在前院的粪堆上,拿起旁边的铁锹,铲着旁边的残雪,将灶灰埋上。这时,关寡妇一转腰走进院门,她跟姥姥后面进了屋,说:“嫂子,马二愣让我过来帮你和面。”她低头看着灶,说:“我先坐锅开水。”她开始从缸里向锅里舀着水。
姥姥和关寡妇一个烧火,一个和面。一会儿,关寡妇的衣服就湿透了,她脱了衣服,上身只剩下一个胸兜兜。姥姥也不例外,她把头发全绾在了头顶,将布衫撸得老高,前襟大敞。姥姥一会儿给三舅喂奶,一会儿填着柴火,汗已经溻了布衫好几遍了,姥姥看三舅水捞似的在怀里,小腿乱蹬,前身红肿,她一下意识到,是自己的汗水将三舅的皮肤淹过敏了。姥姥和关寡妇说了句先弄弄孩子,走进西屋,从炕上随手抻过一个小被褥,把三舅放在上面,换了尿布,到屋外弄了盆温水,给三舅擦身子,然后换上一套干净衣服。此时,院里的脚步杂乱,五六个当兵的吵吵嚷嚷地拥进屋里。他们和关寡妇相互问候,几个人几个方言,大概的意思只有一个,他们一天没有吃饭,连长让他们收烙好的饼来了。
关寡妇看着几个当兵的,眼神有点乱,她双手向后捋着头发,尽量露出又白又细的腰身,白嫩的肚皮下面系着一条红布裤带,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兵说:“大嫂,你辛苦了!”
关寡妇说:“真不会说话,谁是你大嫂,我看你比我还大呢!”
当兵的说:“解放军规定,结过婚的女人都叫大嫂。”
关寡妇说:“你才结过婚呢?人家还是姑娘呢。”
当兵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说着嘴里流出口水。
关寡妇说:“这位大哥你贵姓,听你说话是本地人?你属啥?”
当兵的说:“我叫王有才,是喇叭沟的,我属蛇。”
关寡妇说:“巧了,我是北河套的,我也属蛇。”
王有才说:“你是北河套的,你属蛇?”王有才眼里闪着泪花。
关寡妇也来了兴致,说:“不信,瞧瞧我的腿。”说着将裤腿卷得老高,又把鞋子脱了,将三寸金莲放在垛起的面袋上,五指张开,王有才将身子探过去,翻着眼珠子来回瞅,腿上的皮肤像蛇纹,金莲缝里蜕着皮,五指一张一合一钩,活像眼镜蛇吐着芯子,王有才拍手惊叹:“姑娘真是属蛇的呀!”
我姥姥在屋里忙不迭地把胸襟系好,赶紧从里屋出来,她低着头,一声不吭,看柴火不多,到院子里抱了一大抱柴火,然后用烧火棍挑着火。关寡妇绕过姥姥到里屋取了衣服,披在肩上和几个当兵的聊起天。三舅在里屋哇哇大哭,关寡妇问这儿问那儿,几个当兵的抢着回答,一个问题出三答案。锅里冒出焦煳味味,姥姥将糊饼从锅里拿出来,在面板上摔着。关寡妇赶紧从灶里撤着柴火,用炊帚掸上水刷着锅降温。她抬起头,对王有才说:“晚上到家里去,我给你做好吃的,我家就住在村西头,门前有棵大桑树。”
关寡妇不是寡妇,正像她说的还是个姑娘。
关寡妇名字的由来是跟她所住的屋子有关。1938年村里闹瘟疫,一下死了二十多口人,包括姓关的全家四口。日本投降那年,这个关寡妇通过别人介绍来到这个村,买了姓关的这处房产,因为她跟村里人很少接触,没人知道她姓甚名谁,村里人就以屋代名了,村里姓关的族人觉得不吉利,又因关寡妇门前有一棵大桑树,院中有一棵杨树,关姓人就叫她桑杨家的。她还有一个名字叫浮水蛇,这个名字是她和村里的邻居吵架吵出来的。她说:“你到铁岭火车站打听打听我浮水蛇!”村里人才知道她有这么一个绰号。
关于她绰号的来历,经过外面人的谣传,和本村人的开发,才弄出个大概,她这个名字敢情和床上的事有关。据说,她跟男人做那事时,身子软得和面条一样,能把男人盘起来,干那事越能的男人她盘的匝数越多,听说,她盘过一个苏联老毛子三匝。我听了这事半信半疑。有一次我让媳妇盘过我,也搭着她胖点,半匝盘着都费劲,后来我明白了,可能是村里人说她干那事特能的意思。她还有一个更能的是在水下干那事,她能将男人吸浮在水面上,听说她把铁岭火车站一个日本少佐给吸服了,那个少佐在水里直叫“摇希,哈拉硕,故的……”高兴得一下说了七八国语言。关于在水面上干那事,我没敢跟我媳妇试,一是这个技术太综合,二是让她上次出过洋相,三是她见水就晕,有时洗脸还呛水呢,要试肯定有风险,这事出点意外,无法示人。这些传言,我想可能是农村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成了村里人炕上灯下的荤段子。
听村里老人说,浮水蛇跟村里人接触比较少,很少出屋,只有听见杀猪冯、剪刀王、豆腐刘、蒋炉匠的吆喝声和一些暗号,才从屋里嗑着瓜子扭着腰走出来,她斜倚在院门上和他们搭讪,谈不拢把门一摔,谈拢了就一块进屋,晚上村里就有几个光棍到她屋檐下听叫床。听光棍们说,浮水蛇的叫床声因人而异,碰见杀猪冯,那叫声和杀猪声一样惨烈;碰到剪刀王,那叫声和闹猫的一样那么难受;碰见豆腐刘憋闷得就像一锅豆腐大开不起来。几个光棍特别盼着蒋炉匠来,只有碰到蒋炉匠才能传出女人那迷人的呻吟声,才能传出娇滴滴的一段段酸曲:爱美的我呀不穿棉,寻情的炉匠窜村来。再肥的土地怕懒汉,薄情的……
关寡妇把饼糊的地方掰下来,夹在摞起来的饼中间,她分完摞,让当兵的往外抱,几个当兵的美得甩着屁股走出屋。王有才红着脸和关寡妇说:“大妹子,刚才听说你是北河套的家?”
关寡妇“嗯呢”一声说:“我就是北河套的。”
王有才说:“我跟你提一个人,你认识不?”
关寡妇说:“你说吧!”
王有才说:“我们村马洪檩,马大哥。”
关寡妇自豪地说:“当然认识,他常去我们村找我四哥,我四哥就是闸北门派出所警卫韩永龙。”
王有才说:“韩永龙是你四哥?”
关寡妇说:“他奶奶是我爸爸的亲姑姑,这亲戚远吗?”
王有才说:“不远不远,你有空回去就提我,我刚从国军那边投诚过来一个月,解放军哪都好,就是纪律严点,要是在国军,今天晚上向连长请个假,借一匹战马送你回家看看。”
关寡妇说:“自从母亲一死,家就不想回了。”关寡妇说得越来越低沉。
王有才转了话题,说:“晚上没有警卫任务去你家认认门。”
两个人越说越近乎,说得关寡妇脸也红了,手上的面直起皮,聊得老黑扒开门朝他俩直汪汪:“滚蛋操!滚蛋操!”
老黑用牙咬着姥姥的袖子往西屋里拽,姥姥使劲掰着老黑的嘴,举着白烟袅袅的烧火棍,照着老黑的屁股就是一棍子,老黑瞪着火星飞溅的烧火棍没有松嘴,口里呜呜地流着口水,并继续把姥姥往西屋拽,姥姥趔趄着跟老黑进了西屋。姥姥嘴里不停地骂:“你疯了,狗东西,别把我衣服扯坏喽!”老黑松开嘴,蹿到炕上,用嘴叼着三舅,姥姥这才注意到三舅小脸焦黄,双手举在胸前,像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似的,一抽一抽地打着拍子。姥姥一步赶上去,赶紧将三舅从炕上抱起,她手摸了一下三舅的后脑勺,手立刻就分开了。
后来听姥姥说,当时她就感到不妙,三舅非死即伤,她的心筋狠狠地抽了一下,当时就晕了过去。
姥姥醒来的时候,屋里挤满了人,有一个穿军装的男医生按着三舅,两个女护士给三舅后背屁股腿上抹着药,三舅后面烫得满是大泡。关寡妇上下左右打着下手,三舅的嗓子早已哭哑,张着嘴一声不吭,手还是指挥的动作,但比刚才抽搐的动作小了许多。
屋里人看我姥姥醒了,围了上来,问这问那,姥姥谁都不理,哭声让所有人无法止住,医生和护士在一边小声嘟囔半天,不知是商量三舅的病情,还是商量怎么推卸责任。一会儿,一个姓周的女护士向我姥姥开了腔:“大嫂,孩子刚才我们检查过了,生命体征暂时还没有出现异常,不知以后脑部会留下什么问题,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这几天为了更好地观察孩子的病情,准备将卫生队设在你家,你放心,我们将尽全力治好你孩子的病。还有,我们马上向团部汇报你孩子的情况。”我姥姥跟没听见一样地哭着。
听我姥姥说,第二天中午真来了一个三十来岁当官的,出出进进的人都叫他杨团长,周护士给他介绍了姥姥,介绍了三舅的病情,杨团长听着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嘬牙花子,他看我姥姥侧身躺在炕上,用木讷的眼神看着三舅,一声不吭。
杨团长侧过身和一个当兵的说:“去把这个村的马同志请来,我有话要对他交代。”当兵的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走出屋门。杨团长又对一个当兵的分派着工作,说:“解放战争已经打两年了,怎么到哪儿那里的老百姓还是躲躲藏藏,这么冷的天,你告诉陈连长,让村里老乡带路,兵分几路,进山把乡亲们都请回来。”杨团长正吩咐着,马有田走进屋,杨团长看见马有田主动上前握手,两个人互相寒暄,杨团长朝姥姥说:“大嫂,叫马同志来,就是想当着面将您的事托付给当地政府。马同志,”杨团长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这个孩子是为了解放调兵山留下的残疾,他跟我们战士在战场上负伤是一样的,都是光荣的,我们党会管他一辈子。我把话放在这儿,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一定联系地方政府,将孩子照顾好。”杨团长冲姥姥说,“大嫂,这回您放心了吧?”
马有田点头哈腰连说:“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他转向姥姥说,“大嫂,杨团长都说到这分儿上了,你应一下呀!”转身向杨团长表着忠心:“杨团长,只要我马有田不离开这个村子,这孩子就是我的亲侄子……”
家里出事的第三天,姥爷大舅二舅我妈我姨从山里被解放军劝回了村,他们看三舅昏昏沉沉的样子,看三舅身上裹满纱布,看卫生员无微不至地照顾,别提多别扭了,但大家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只有我妈我姨忙里忙外。
马有田这几日在村里忙得不亦乐乎,到处串联做工作。他要和赵铺的人联合起来,成立担架队、运粮队。可在那个年代,就是你说得再好,家里能喝得上稀粥,也没人跟你去当兵,谁乐意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活着呀!何况又不是国军,马有田说得满嘴起大泡,就是没人去,只有本家的两个表哥不好意思驳他面子,说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马有田到姥姥家和大舅说:“冬天有的是剩力气,又管吃管住,出去见几天大世面,革命真的成功了,还是个功臣,就是革命不成功,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马有田说得天花乱坠,他看三舅一声不吭地躺在炕上,好像有了什么重大发现。
第二天晚上,马有田把村里二十几个青壮年请到自己家里吃饭,搭上赵铺六个背枪的,一共办了四桌,这顿饭吃了足足三个小时,席间说了什么,我没向大舅细致问过,无非是一些亲兄热弟的话。酒足饭饱后,马有田说了话:“刚才大家聊了半天,也知道我们什么意思了,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赵铺这次运粮抬担架去四十人,咱们村至少也得去十个,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都是乡里乡亲,我也为难,这么着吧,待会儿吃完喝完咱们都坐在炕上,谁屁股先离炕,谁就算同意去。”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马有田说的这个办法也没针对某个人,大家又没有别的好办法,年轻人又喝了点酒,吵吵嚷嚷都说这个办法好,“谁他妈扛不住活该,算他倒霉。”二十多人呼呼噜噜进了屋,有人问中间尿尿怎么办,马有田说:“上了炕,只要屁股离开炕,就算同意去。”上了炕的人又稀里呼噜找鞋下炕,到外头尿尿,大舅二舅跟着也出了院,在当街向天上滋着尿,大舅尿完还抖搂抖搂,抖得二舅脸上全是。大舅看二舅用手擦着脸说:“怎么,嫌弃我?”二舅迟疑片刻,说:“没有,我想抹匀点。”他笑着将擦脸的手指放在嘴里嘬着,大舅自豪地搂着二舅的肩膀走进屋里。
二十多人坐了一满炕,起初以为是比谁憋尿时间长,没想到马有田让人在外屋灶台点起火,没过一个时辰炕上的人全脱了棉衣,有人就穿一个坎肩,屋里二十几双鞋,二十多双脚,借着屋里上来的温度,挥发出咸臭咸臭的味道,让人脑浆子拧着疼。上头熏底下烙又搭上吃的喝的多了点,有不少人开始坚持不住了。我二舅用双手垫着滚烫的屁股。有一个赵铺的人看二舅两只胳膊肘往外背着,问马有田:“手垫着屁股算不算离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