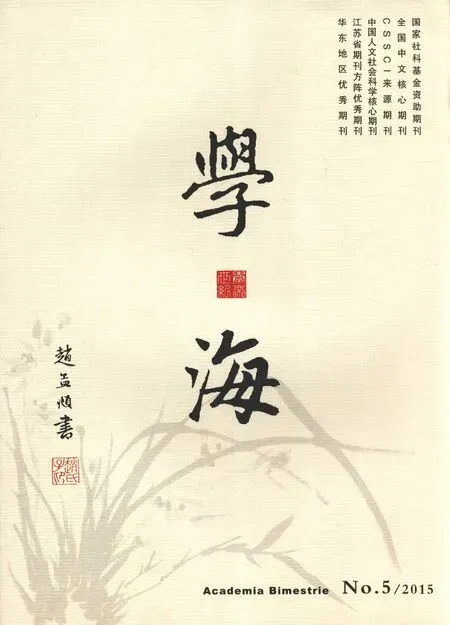《论语》“君子不器”涵义探讨
李 宁
《论语》“君子不器”涵义探讨
李 宁
“君子不器”是揭示《论语》中对于“君子”的规定的关键,它昭示了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使命应是修德、弘德,而非局限于某些专门的才能。由于孔子对君子使命的这一规定,历史上儒门子弟基于“君子”的士阶层社会特征,认为只有从政和治(儒)学这两条路才是正途,其他如农、工、商、医、卜等等都是“小道”。士阶层是以“务德”为本,不崇尚专门化才能训练的,这与孔子对周代兴衰的反思、与其对政治制度的思考有关。但当受教育人群大大扩充、“君子”概念逐渐下移之后,如果仍然从“务德为本”、鄙视“小道”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器”,则会造成空谈流行、“实学”不彰的后果。
《论语》 孔子 君子 不器
“君子不器”是《论语·为政》(以下只称《论语》中的篇名)中独立成段的一句话,由于缺乏上下文背景,其阐释历来存在诸多争议。然而,“君子不器”对于理解《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规定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对“君子不器”的具体涵义进行探讨很有必要。以朱熹为代表的传统解释认为“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①“用无不周”、“无所不施”、“非特为一才一艺”逐渐被引申阐释为君子应“多知多能”,即“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应该多才多艺,无所不能”。②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君子不器“与其说是主张多才多艺,不如说是倡导提高道德水平和境界。”③笔者认为,仅仅从“才能”和“道德”等某一方面诠释“君子不器”,未免失之单薄。要阐释《论语》中“君子不器”的涵义,首先要厘清孔子对“君子”的界定,其次要结合孔子心目中“君子”的定义及君子的使命,对“器”与“不器”的涵义作出梳理,如是,才有可能在阐释“君子不器”时尽可能接近孔子本意。
何为“君子”
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指统治者和贵族。虽然有的文献中也出现对“君子”道德修养的赞美和规定,如“君子所其无逸”(《尚书·无逸》),即君子不贪图安逸,但春秋之前,由于只有地位高的人才能受教育,才能更多的关心“公德”而非私利,因此君子之“德”与君子之“位”密不可分,论及“君子”时,主要是指政治、社会地位高者,而非道德高尚却没有高位的人。与之相对的“小人”、“民”,主要是就政治和社会地位而言,一般没有道德上的贬义。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出现了大批虽然“无位”却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人。与此同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各为其利,战乱四起,贵族阶层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出现了大批虽然“在位”却无道、无德的人。有的人有君子之“位”却无君子之“德”,有的人有君子之“德”却无君子之“位”,“德”、“位”一致的“君子”内涵于是发生了变化,“‘君子’一词逐渐由表示统治者或贵族男子身份地位的概念转变为表示德性修养的‘有德者’。”④孔子被认为是将君子概念从“位”向“德”转化的关键人物,在孔子看来,不管是否有政治地位和贵族身份,能够承载道德理想、躬行道德规范的人即是“君子”,与之相对的“小人”往往有道德上的贬义。是否“有德”是孔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主要界限,但这不意味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毫无关联,只不过这一阶层不一定是统治者或贵族阶层。
《宪问》中的一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孔子对何为君子、君子应承担何种使命的阐述:“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病诸!’”在集中体现了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中,孔子对君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君子应遵循什么样的“礼”、应当如何学习以成为君子等都有阐述,但总的来说,孔子认为君子应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并且能够以自身高尚的道德感召人,如果君子还能以德治国,使国家安定、百姓幸福,则更佳。不过孔子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病诸”,因为要使百姓“安”,除了君子自身的道德修养要高,还要等待良好的时机。孔子多次指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国家无道时君子应隐居或离开、国家有道时君子应出仕,他非常不赞同君子在无道之邦做官。孔子认为“天下有道”、“邦有道”是“仁治”能够得到实施的前提,君子是将“道”、“德”的潜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人物。但如果这一前提不存在,即“天下无道”、“邦无道”,君子靠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这种局势的,即使其自身再有德也无可奈何。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最重要的规定性是“有德”并能够有恒心躬行道德,这是君子的本分。君子应以“立志”、修身养德为第一要务,至于能不能“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君子应尽力而为,“不可则止”。如果不顾时势和自身能力去强行“安人”、“安百姓”,会有“降志辱身”的危险。比如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微子》)伯夷、叔齐坚持自己的原则,隐居避世,宁可饿死也不出来做官,孔子称赞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在一个“无道之邦”做法官,多次被罢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柳下惠坚持不离开那个无道的国家,认为无论在哪里,“直道事人”都会被罢黜。按理说柳下惠是一个能够坚持原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君子,但孔子却批评他“降志辱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天下和国家的有道无道是人力不可改变的“命”,以君子的力量无法使一国变无道为有道。在无道的国家做官,如果君子坚持自己的原则,必然会遭遇打击,招致“降志辱身”。如果他的仕途很顺利,那么,他必然要“枉道而事人”,沦为道德卑下之人,也就不再是君子了。所以,虽然孔子重视君子出仕,孔子的学生子路甚至批评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指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不仕无义”(《微子》),但君子从政做官的前提是“邦有道”,在无道之邦做官拿俸禄是可耻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有学者认为“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任务是‘学而优则仕’,‘仕’就是从政做官,协助朝廷治理民众。”⑤这是不确切的,孔子心目中“君子”的本务并不是做官,而是修德、弘德,能够造福百姓当然更好,不能的话也可隐居起来养志修德,如果君子在无道的国家做官的话,则会损害君子之德,这与君子的本分(立志修德)有违。
既然认为君子与“德”密不可分、立志修德是君子的本务,那么,如何成为君子、君子所承担的使命必然都与“德”有关,而妨碍修德、行德之事,或与修德、行德无关之事,都非君子所应为。从这一原则出发,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追逐私利,不应学习、从事普通百姓所做的“鄙事”,或专精于某一项技能。君子之学,不是学习农、医、卜等专业化技能,也不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孔子主张君子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有别的陶冶教育。如果所学与匡正人心、涵养德性无关,则被孔子认为是“小道”、“小人之学”,最典型的是《子路》中的一段:“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的弟子樊迟向老师请教种田、种菜的学问,被孔子认为是“小人”。显然,孔子认为种田种菜是“小人”、“民”干的事,不是君子所应当去关注的。其实樊迟问种田种菜之事,也不是为了个人谋利,从孔子接下来所说的“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来看,这里的“稼”与国计民生有关,樊迟讨教稼、圃之学,是为了“安百姓”。可见,孔子说樊迟是“小人”,并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批评樊迟是只知追逐小利的小人,而是说樊迟不懂得治国的关键所在。关于君子为什么不应从事“小道”,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夏也从另一方面作出了说明:“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种田、种菜的本领,和医、卜等才能一样,与行义、知礼等君子的“大道”相比,只是“小道”、“器”,如果陷于此,会妨碍通达仁义大道。
另外,从事“鄙事”总是与追逐私利相关联的,德国学者韦伯指出:“孔子本人并不鄙视对财富的追求,但财富又似乎靠不住,会破坏高贵的心灵平稳,一切本来的经济职业工作都是庸俗的匠人的活儿,在儒家眼里,匠人即使借助他的社会功利价值也不能提高真正积极的尊严。”⑥君子不一定是有政治地位的统治者、贵族,但君子不从事“鄙事”,以立志修德为务,这就决定了君子要么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人,或者像不事生产的僧侣阶级一样,总之只可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而不可能是所有的人。因为社会要运转,包括君子在内的人们要生活和繁衍下去,总得要有人从事“鄙事”。所以,孔子虽然完成了君子“德”与“位”的分离,但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仍然不是后世儒家“人皆可为君子”的单纯有德者,而是专以修德、弘德为务的一个特殊的阶级,也就是“士”的阶级。有学者认为“孔子对于君子所做的创造性诠释,使得君子从表示地位和身份的社会精英的尊称,转化成大众可以追求的理想人格目标(道德精英)”⑦,这一论断并不确切。笔者认为,君子“德”、“位”彻底分离的转变并非在孔子那里完成,要等到宋明之后,“君子”的队伍不断扩大而下移,“君子人格”成为普通百姓人人皆可追求的目标,君子的内涵才发生了由“位”向“德”的彻底转变。孔子对“君子”人格的阐述,就其本分、使命来看,针对的是“士”这一特殊阶层,而非普通大众。只能说,孔子心目中“君子”的部分道德规范,如仁爱、坚毅、守信用、有恒心等,是人人都可以追求的目标。总体而言,在孔子那里,“君子”的“德”与“位”仍然有密切关系,只不过这里的“位”并不一定是统治者、贵族之位,而是“士”这一特殊阶级的社会地位。厘清这一点,对于理解《论语》中的“君子不器”有着重要作用,因为“不器”对于仅就“德”而言的“君子”,与“德”、“位”相配的君子,有着不同的涵义。
何为“器”?何为“不器”?
“器”的本义为“器皿”,引申义有工具(器具)、生物体的构成部分(器官)、人的气度(器量)、重视程度(器重)等。此外,“器”也被用来指称“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论语》中提到“器”的地方只有六处⑧: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里的“器”指工具,工匠要做出好的作品,光有想法和技能还不够,还要有好工具,孔子在这里把“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比作“实行仁德”的工具。
“‘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瑚琏”是祭祀用的礼器,这里的“器”,指的是器皿,也可以解释为“有具体用途的物品”。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君子让人做事,不像小人那样求全责备、吹毛求疵,而是根据这个人的能力、专长等实际情况来衡量他,不拿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里的“器”与“备”即完备、完美相对,指的是有限性。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有大恩泽于百姓,建下了非常伟大的功业,孔子数次称赞其“仁”。但在这里,孔子说管仲“器小”,是说管仲虽然功业成就极大,然而“不俭”、“不知礼”,在道德品行上有亏,因此做人的格局还是狭小了一点,算不上“大人”。
“君子不器。”(《为政》)由于这句话缺乏上下文,对其中“器”的理解历来纷争很多。除了“君子不可气量狭小”、“君子不能把别人当作器皿”等过于浅显或一望即知谬误的解释外,结合孔子对“君子”的阐释及《论语》中其他各处“器”的涵义,对于“君子不器”中“器”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对“君子不器”中“器”的第二种解释,是将其解释为“形而下者”。“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与“道”相对,指的是物质生活和物质财富,泛指整个凡俗世界。在这里,对于君子“不器”即指君子应追求形而上之“道”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于什么是“道”、什么是孔子心目中君子应追求的“道”,又有不同的意见。
《论语》中多处提到“道”,如《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吾道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雍也》:“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等。那么,《论语》中的“道”究竟指的是什么?



对“君子不器”的解读
孔子心目中君子的任务是在天下有道、国家有道的时候,协助君主治理国家,其施政的重点不在实际的政务,而是匡正人心,即内以高尚的道德素养感召百姓,外以“礼”的约束来保证国家社会在正轨上运行。这里所体现的“君子不器”,除了上述涵义外,还包含了“以德治国”、“仁治”的儒家政治原则。




②王大庆:《“君子不器”辨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④林贵长:《孔子与“君子”观念的转化》,《天府新论》2008年第2期。

⑥[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8页。






〔责任编辑:吴 明〕
李宁,哲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成员,zizi98@sina.com。南京,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