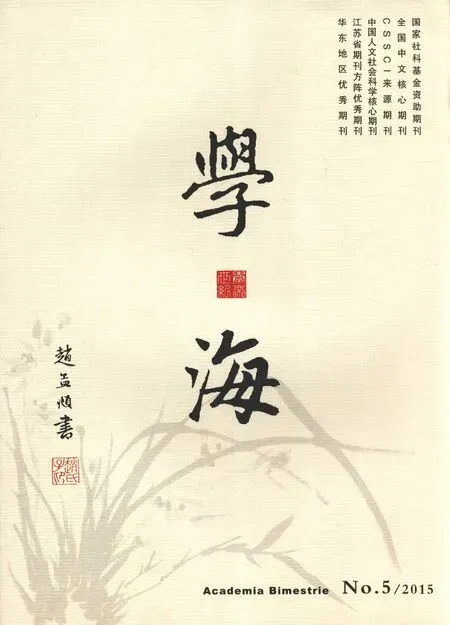道德失范时期良善行为何以可能:兼论阿伦特的良知理论*
张云龙
道德失范时期良善行为何以可能:兼论阿伦特的良知理论*
张云龙
由传统而现代的社会转型,解构了形成已久的传统道德规范,从而将人所依据的法则从外在的律令转向了内心的良知。经历了社会严重失范的阿伦特,认为良知所唤起的记忆与思考,将会形成正确的判断进而做出善的行为,因而是人类危机时刻最为可靠的东西。然而,危急时刻唯有少数人才能坚守的个人良知,能否承受这一重负显然值得怀疑。唯有健康而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个体的良知免于煎熬与折磨,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正确判断,最终实现个人的“良善生活”。
道德失范 良知 判断 思考
英国19世纪文学家狄更斯在其著名的《双城记》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其实,狄氏所谓的这个令人纠结不已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转型期”。由于旧的规范已然解体,新的尚未形成,道德失范就成为这一时期极其突出的症候,作为个体的自我因此面临着严重的道德挑战。中国目前也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毒奶粉”、“地沟油”等令人窒息的问题无不拷问着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底线。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个体的自我能否不做坏事,或者进一步说,能否成为一个好人,也即“良善行为何以可能”,就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切身问题。
一
狄更斯的那段话,是“现代性症候”的文学化描述,实际上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标准搞乱了,新的尺度未能及时形成。这时候,人的欲望就缺乏节制,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在合理要求与异想天开之间,这一切的界限,都变得模糊起来”。①即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出现“道德失范”。
从历史上看,在与现代相对的传统社会之中,人们总相信“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对或错、善或恶、美或丑的标准,通过运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来阐释我们的世界。没有超验存在的支撑,价值就不再有牢固而不容置疑的基础”。②正是“天”、“道”、“上帝”等这些专属形而上学的话题,让我们相信某种非我们人类的智力可以把握的力量才是“自然的法则”、神圣的法则,从而支配着我们的善恶观念。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等西方哲人就将人视为不完善的存在,只能追求而不能拥有智慧,因此应该怀着谦卑的心理对待世界万物。同时,希腊诸神的战争也告诫人们,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超验的、唯一的神,世界将永无宁日。于是在希伯来文化传入之后,基督教定于一尊,免除了西方人思想与信仰上的混乱。中国,从秦“大一统”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逐步形成了古代中国的伦理纲常。“天不变,道亦不变”,虽历尽沧桑,但“三纲五常”却已扎根于中国古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人们日常行为不可逾越的教条。显然,无论中西,正是由于这些奠基于超验存在之上的道德规范,保证了人类的文化血脉得以存在与延续,期间虽有战乱或者朝代的更替,但人们的心理结构与价值观念却依然稳定不变。
然而,在人类社会由传统而现代的过程中,超验存在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在现代性的视域中,超验存在不过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幻象”,真正值得依靠的不是外部的、无法经验的存在,而是我们内在的理性。随着把个人粘结在一起的超验存在的终结,因之而形成的共同世界也因此变成了碎片,不复存在,人们从而失去了其最为熟悉的世界,最终“退缩到了其自身之内”。③这被尼采形象地表述为“上帝死了”。上帝的“死去”,标志着传统道德崩溃。“上帝死了,做什么都是被容许的”,成人、成圣还是成兽,都取决于自己,其后果就是每个人都成为上帝。这种人的地位的极端高扬,固然有解放思想、鼓励创新的意义,但也会因敬畏感的消失而使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诸神并起、无法无天的局面。其原因在于,传统的解构使人们失去了其最为熟悉的、与他人共在的“共同的现实”,从而生活于一个令人陌生的、异己的世界之中。在这一极其虚无、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之中,个人只有自私自利、独善其身,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必然成为社会的常态。神圣感的消失势必使人们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但人类的形上冲动又使其不得不寻求一种根本性、终极性的东西,以安顿其惶惑不安的心灵,金钱于是成了唯一能给人们带来安全感的“神”。其结果是,金钱成为衡量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唯一标准,一切都成了可以“物化”的东西,人完全堕落为追求利益的动物,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等等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的“上帝”,但有着与上帝同等地位的圣人,圣人形象的倒塌在中国也确确实实地上演过。在西方以枪炮迫使古老的中华帝国不得不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以“科学与民主”为表征的现代性终于为中国人全面接受。故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现代性的“革命”和“创新”已经理所当然被赋予了正面价值,而“保守”和“传统”已经成了退步的代名词。其结果是,民国以降,一次一次的政治革命接踵而至,这些激进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古代的传统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游魂,完全失去了可以依附的基础。那种关注公共幸福、“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气质已经荡然无存,独善其身则成为最佳的选择。可以说,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的生活世界完全割裂,人们失去了规范其行为的道德法则。在法律失位、道德解体的情况下,我们的食品、医药卫生、工程、教育等领域无不出现了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这些突破道德底线现象的出现,无不昭示着我们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之严重。
在这种境况下,作为个体的自我该当如何?我们如何才能不随波逐流,依然有善的行为?退一步说,即使不能行善,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能否独善其身而没有道德上的过失?对于这一问题,有着比我们的经历更为惨痛的阿伦特的回答可能更能引起我们的思考。
作为一位犹裔哲学家,在20世纪的纳粹德国度过了青春岁月的阿伦特,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在这一过程中,她看到了“伟大之思者”海德格尔的“伟大的迷误”——政治上的失误与道德上的冷漠无情;也感受到了雅斯贝尔斯这位西方“现代圣贤”的伟大人格——坚守良知,忠于爱情以及坚定的反纳粹立场;同时还在战后看到了艾克曼这位纳粹刽子手的平庸。对阿伦特而言,她所关心的既有狂热的反犹分子,或者被希特勒洗脑的人,更有那些如艾克曼一样普通的德国公民,而后者在其心目中更有研究的价值。因为,究竟为什么,这些如你我一样普通的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会成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而少数如雅斯贝尔斯一样的人,为何又能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坚守自我?这种种完全不同的面相究竟是如何铸就的?在《责任与判断》一书中,阿伦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如果你关注一下少数人,他们在道德崩溃的纳粹德国不受触动,并且没犯有任何罪过,你将发现,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道德冲突或者良知危机这样的事情,……如果那是他们的良知,那么,其良知没有义务特征,它说‘我不能这样做’,而不是‘我不该这样做’。”④显而易见,在阿伦特那里,这些不受触动的人,就是能够坚守道德底线的人,也就是有良知的人。在危机时刻,他们的良知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防止了恶行的发生。良知比道德规范能更有效的防范道德危机的出现。
二
阿伦特断言,当规范崩溃的时候,道德上可靠的人,就是那些说‘我不能’的人。说“我不能”的人,就是依据良知行事的人,这与说“我不该”的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阿伦特看来,道德命题,类似于真理命题,或者为自明的,或者得到了严格的证明,从而就有一种强迫的或者说义务的性质,通常可以被表述为“你应该……”或者“你不该……”的命令。从道德与伦理的发展历史来看,其“最初的名称,即mores和ethos,暗示着它们只不过是风格、习俗和习惯”。⑤如此看来,道德伦理非常重要,因为人们常常根据已有的道德规范或者标准来辨别是非、区分善恶,或者判断自己行为的合理性,然而,它们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它们不过是一套习俗,能够像改变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餐桌礼仪那样轻易地被改换。阿伦特因此明确指出:“不是在罪犯那里,而是在普通人那里,道德瓦解为一套孤立的风俗——一些可以随意改变的风格、习俗、传统。”⑥如果说,在传统时代,那些道德规则与标准因其权威性而获得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话,那么,在超验消退的现代社会,一切均已失去了永恒的价值,道德律令也因此被理解为可以随意改变的习俗。因而,道德标准既重要,又充满风险。
在未见到艾克曼之前,阿伦特将其想象为穷凶极恶之人,但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见到阿克曼之后,阿伦特却大跌眼镜。这样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竟然是一个懦弱、胆怯、没有自信的平庸之人,那么,毫不手软地屠杀了数万犹太人的罪恶,如何会发生于这样一个平庸之人的身上呢?阿伦特因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庸人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在阿伦特看来,艾克曼的罪恶并非源于康德所谓的“根本恶”(radical evil),即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人心的邪恶。⑦与之相反,“庸人之恶”乃是非常普通的人,或者说既不残暴也不凶恶的一般人犯下的罪恶,其关键在于“无思”(thoughtless)。阿伦特认为,“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者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经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⑧艾克曼也会夸夸其谈康德的“绝对命令”以及其他的道德箴言,当他第一次杀人之后,也曾短暂的内疚和痛苦过,但在纳粹特别鼓吹的新观念——即大规模杀人乃是一种英雄行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对元首的忠诚,并且能够忍耐身为行刑人的痛苦——的影响之下,“他的良知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运行了四个星期,随后开始反其道而行之”。⑨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后,艾克曼的内疚感荡然无存,因为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被纳粹的国家新道德全然取代,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重新找到了极具合法性的道德根据,完全可以视人命如草芥而无动于衷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罪恶并非仅仅发生在那些天性罪恶的人的身上,即使在那些平庸之人的身上,也可能产生令人吃惊的恶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克曼对于你我而言,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他的影子——我们可能也会见死不救,我们也曾在利益与正义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见利忘义,我们可能也会造假卖假,我们可能也会为虎作伥,如此等等的失范行为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每当此类事情发生于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或者感慨一番,或者袖手旁观,但却未必会做出积极的行为。我们可能曾经为之而短暂地挣扎过,但总会找到一个原谅自己的理由——世风如此,我能奈何?在这样一个规范错乱的时代,还有什么是可靠的呢?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三


但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良知,这样的洞见显然令人不安。我们知道,在社会失范的时代,要求人们像正常社会那样坚守道德原则,显然期望过高。在正常社会中,道德规范的可靠性保证了一般行为的正当性,但在失范时期,标准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们无规可循,从而只能退缩到自身,寻求自己的利益。一个人如此,其他人也会以“像他人一样”的“常人”心态,做出见利忘义的行为,群体性的道德失范也就在所难免。依靠少数人的良知不可能纠正整个失范的社会,能在危机时刻坚守良知的少数人,尽管为我们树立了道德典范,但这远远不足以拯救整个病态的社会。良知无法承受如此之重。




①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②陈家琪:《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础教育”》,《文汇报》2013年1月14日。



⑧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前言。







〔责任编辑:蒋秋明〕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基金“人权现象学研究”(项目号:2013JK0028)与国家社科基金“工程与社会正义研究”(项目号:11CZX026)的阶段性成果。
张云龙,哲学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