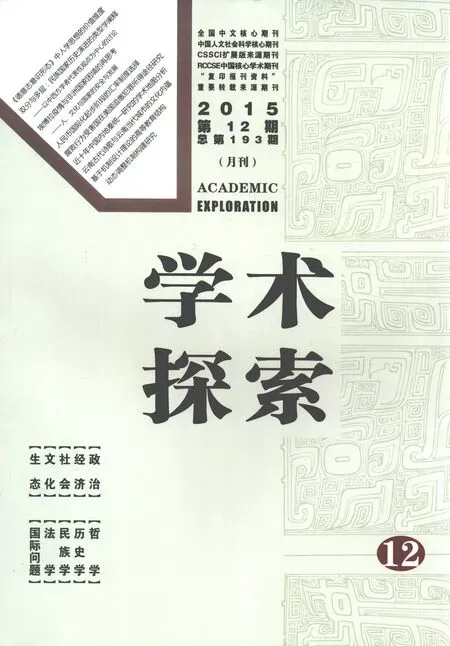当前南海安全局势与美国角色选择
——基于美国主流智库近期听证会的文本分析
李忠林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当前南海安全局势与美国角色选择
——基于美国主流智库近期听证会的文本分析
李忠林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近段时间以来,南海局势的发展引起美国国内激烈讨论。为此,美国国会举行主题为“美国在南海的安全角色”的听证会,邀请美国主流智库的学者参加。听证会围绕“当前南海安全局势”和“美国的政策选择”两部分展开。整体上,他们赞同美国政府采取对华示强的政策取向,同时希望中美关系和地区稳定得到保障。他们认为,中美南海争夺的核心是秩序和规则,中美围绕南海的博弈及带来的紧张局势将持续下去。
美国智库;南海局势;政策选择;听证会
一、前言
进入2015年以来,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迅速引起各方强烈反弹。特别是自2月份以来,中国的岛礁建设成为美菲等国炒作的焦点。美国高层多次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表示关切,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强硬要求中国停止岛礁建设。同时,美国军方派出军机和军舰赶赴中国岛礁周围侦察,扬言派出舰机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领海领空。中美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急剧增加。
在美国内部,各方就南海的局势和美国的政策也展开激烈的争辩。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23日举行听证会,以“美国在南海的安全角色”为题进行听证。[1]有四位来自美国主流智库的学者参加了听证会: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和高级总监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Erickson);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 (AMTI)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 Hooper);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斯韦因(Michael D.Swaine)。上述智库均为美国著名智库,学者均为美国知名中国安全问题专家,代表着美国主流智库对南海问题的认知水平。
美国国会曾多次举行关于南海问题的听证会,其主题具有高度连贯性,均是围绕南海形势和美国角色展开。如2009年7月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在南海地区“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潜在的“亚洲争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应当扮演的角色。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开关于中国与南海问题的听证会,其目标是推动南海周边海上领土争端的和平与合作解决。
美国主流智库与美国政府之间联系密切,其通过多种途径对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分析与制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就认为,“美国智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示器和风向标。”[2](P41)比如,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2014年10月就南海政策为美国政府提供11项建议,与当前美国的南海政策举措高度吻合。[3]因此,全面了解和掌握美国主流智库对当前南海局势与美国角色的认知,对中国有效判断未来美国的南海政策以及做好战略应对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南海安全形势评估
在过去的几年里,南海已经进入一个竞争加剧的时期。四位学者对此看法高度一致。就紧张局势产生的原因,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的岛礁建设上。众所周知,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并非最早,也非唯一。胡珀也指出,“南海的填岛和建设并非开始于中国2014年的工作。南海声索国在南沙群岛开始设立前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家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进行这种努力。”[4]但是,他们对同样的岛礁建设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对中国严加批判,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类似行为视而不见。
他们的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的建设速度和规模过于显著,远远超出其他声索国。马来西亚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在同一地点开垦了大约60英亩,越南过去5年在同一地点开垦了50~60英亩。然而,中国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在七个不同的地点开垦至少2000英亩,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和。第二,中国是唯一将水下礁石完全转化为人工岛的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增加那些已经露出水面的岛礁的面积。换言之,菲、越仅是在已有的岛礁上建设,而中国则通过填海作业制造人工岛。第三,中国建设活动的时机比较特殊。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国家的建设多是在2002年以前,而中国则是在2002年以后,因此中国违反了文件精神。第四,中国建设的飞机跑道超出了民用的范畴。埃里克森指出,中国在永暑礁修建的3000米飞机跑道在支持人员疏散、医疗救助、紧急天气时对于民用飞机来说是没有必要的。“这样的跑道只能用来支持全方位的军事选择……显示了高节奏、高出动率军事行动的计划。没有其他南海声索方在任何它所占领的岛礁上建有这样的跑道。”[4]

表1 各方飞机跑道对比
资料来源:http://amti.csis.org/airstrips-scs/
基于上述分析,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活动只有一个逻辑解释:军事考虑。比如,支持在南海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他们认为,引起其他声索国对中国在南海意图严重关切的,不是建筑物本身的纯粹事实,而是极快的速度和广泛使用的吹沙造陆和建设,他们指责中国正在通过切香肠策略增强战略地位。克罗宁将中国此举的动机概括为三点:一是大规模地进行军事和非军事部署,旨在对其邻国实施更大的控制;二是意在国际法律诉讼进入程序之前改变地面上的事实;三是对邻国实施恐吓。加之中国在南海主权声索方面的模糊性——比如九段线以内水域法律地位,以及中国近年军事实力的增长趋势,特别是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引起了地区邻国的强烈不安和美国等域外国家的严重关切,他们认为这是南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对目前南海紧张局势,克罗宁认为不会很快缓和,也不应期望紧张局势完全消退。这种趋势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各国关系仍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之下。他还预测,进入下一届美国政府后,中美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中间地带上航行。斯韦因也认为,这种情况不只是当前的昙花一现,而是将在中美关系中起伏。埃里克森甚至主张中美应当适度地、可管理地摩擦,“考虑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我们的力量和决心,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有界限的战略摩擦和争论的区域”。[4]
南海局势在过去一年多发生明显的外交和军事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各方对中国的回应和制衡。对此,四人整体上均表示了认可和赞同。其中,胡珀具体回顾和论述了有关各方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平衡行为”,认为存在南海声索国、域外美国盟友以及多边机制三个层面上的努力。[4]
南海声索国的“平衡行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自身的建设作为回应。2015年初,马来西亚宣布将在弹丸礁安装防空系统。菲律宾决定从2015年3月修复和翻新中业岛的军事设施,同时将增强在仁爱礁的军事前哨。其次,区域各国寻求新的军事能力,增加了军事演习的频率。自2014年初,南海声索国投入巨资购买新军事能力,其中大部分有明确的海上目标。随着地区紧张局势上升,南海声索国增加了新的演习训练以增加防卫准备。这包括与新的军方合作伙伴的演习,以及在海洋领域进行明确专注于防卫的演习。再次,在区域内推进新的政治伙伴关系。胡珀认为,区域国家以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寻求平衡中国并不容易实现。中国的军事预算是东南亚军事能力六倍还多,中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数量超过其他声索国总和。因此,各声索国致力寻求外来援助。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都在追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除域内国家外,还包括域外的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
其他美国盟友和伙伴也在实施平衡中国的努力。日本一直反对中国的南沙群岛建设活动。日本官员,包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重申日本承诺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地区争端。自2015年初,日本一直频繁地公开讨论参与南海空中巡逻的可能性。澳大利亚的外交和防长一直反对中国在南海前哨的吹沙造陆和军事化。堪培拉的高级官员明确表示,他们将反对中国干扰南海航行或飞行自由的任何努力,包括抗议南海防空识别区。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还考虑在中国的人工岛附近进行航行自由的演习。澳大利亚最近已与菲律宾举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它还和河内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未来将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印度参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印度官员强调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国际法的重要性。2014年9月,印度和越南发表联合公报,反对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和使用强制手段。2014年9月和2015年1月,莫迪和奥巴马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确定了南海的共同利益。
该地区各国已经通过多边机制对中国的自信做出反应。在马来西亚的领导下,2015年4月的主席声明,东盟对中国的岛礁建设活动表示严重关切,称后者已经蚕食信任和信心,并可能破坏南海的和平、安全和稳定。该声明重申东盟各国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利益,敦促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这是超出许多专家预期的更坚强和更团结的声明。东盟之外,有关利益方正在考虑他们关系的多边化,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在南海的挑战。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已经讨论签署部队访问协定的可能性。据报道,越南、印度和日本私下达成了三边框架下协调安全政策的协议。
他们在认为通过这些途径可以抵消中国“自信”的同时,也对其制衡效果表示怀疑。原因基本包括三点。第一,许多区域国家实施搭车行为,并没有专门寻求平衡北京,他们对保持与中国的积极战略关系感兴趣,包括在安全问题上和南海争端上。比如,2014年年中的中建南事件后,越南和中国10月在一份高调的协议中承诺修复他们的关系,更好地管理他们的海洋和领土争端。第二,台湾和中国大陆复杂的政治关系增加了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尽管两岸之间仍有许多未解决的争议,但是台湾和中国大陆共享南海主张。美国政府官员已敦促台湾澄清或放弃不透明的主张线,但它拒绝这样做。第三,中国有关政策的吸引和消解作用。南海各声索方有可能参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成为基础设施援助的接受者,参与中国的泛亚铁路,并有可能继续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比如,许多国家还参加了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因此结论是,地区声索国共享许多美国对南海安全保障的关切和利益,但是他们反对北京活动的立场既不十分明确也不完全统一,其根深蒂固的担忧并不必定转化为一个协调的政策反应。[4]由此,反思美国的安全角色是为必然。
三、美国的南海角色认知与政策选择
对美国在南海角色的认知源于美国对自身在南海利益的判断。埃里克森和斯韦因一致认为,美国在南海的利益主要包括:反对使用武力和维护航行自由。[4]所谓反对使用武力,就是可能无端使用武力应对其他声索国来解决这些有争议的主张,这样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更高级别的地区紧张。实际上,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中国而言的,斯韦因明确指出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在他们看来,中国试图强行威胁或者将其他声索国从争议领土清除,是一种“无端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这种没有任何明确地诉诸自我防卫性的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破坏和平并产生强烈的地区和国际反应。所谓维护航行自由,一方面,美国不承认任何对人工岛声称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企图,认为此举将会违反国际法,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自由出入岛礁周围任何合法设立的领水之外水域,包括专属经济区,坚持它有权利以非敌对的方式(包括正常监视活动)行动。这一点也是针对中国而言。
其实,无论是反对使用武力还是维护航行自由,背后折射的都是美国地区秩序主导权和控制权受到所谓中国的潜在挑战后的忧虑。正是如此,使用武力以及限制航行自由是美国竭力要反对的。正如克罗宁所言:“规则和秩序仍然是美国在亚洲和南海利益的核心。”[4]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东亚地区长期保持存在带来了稳定与秩序,后者给中国和亚洲带来了卓越稳定与繁荣。目前,中国强硬的立场、模糊的政策和持续的活动已经腐蚀了地区稳定和国际规范。为此,“现在美国需要调整思维和政策,以稳定局势以及平衡中国的行为和影响力负面前景”。[4]
规则和秩序之争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和期待。美国的重视和决心被质疑,是“已经糟糕的事情”,而且“可能变得更糟”。[4]美国在南海上的政策取向事关美国对地区盟国伙伴的责任与承诺,已经大大超出中美双边关系的范畴。按照其逻辑,一旦地区盟国或伙伴对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和决心产生怀疑,有利于北京最终利用其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创造有损美国利益的势力范围。
因此,上述因素“证明美国重视在南海发生的事件,以及一系列旨在确保航行自由,防止或减少紧张局势,并支持和平和依据法律管理地方争端的政策是正当的”。[4]只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言论和行动都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围绕这些议题产生的日益紧张局势正以一种不必要的方式威胁和严重破坏重要的中美关系”。[4]
至于美国如何有效地应对南海局势的发展以及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各位学者竞相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胡珀的多边机制论,克罗宁的综合框架论,以及埃里克森的范式转变论。就具体政策而言,他们的建议整体上高度保持一致,但就个别领域也存在尖锐的分歧,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美国原则立场。首先,美国应该定期强调对南海的原则。美国应视南海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将努力加强法治,维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政府官员应该坚持和阐明美国对充满包容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的美好愿景。要求充分尊重国际惯例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在一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和无害通过权。此外,不应该使用武力解决争端。虽然美国应该在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它有责任确保不通过使用武器、威胁使用武力或胁迫等手段解决或管理纠纷。其次,美国应该澄清会引起反感的行为。美国应该澄清它反对并呼吁停止一切在整个南海某些特定类型的活动:封锁任何被其他声索国占领的岛礁;夺取或侵占任何其他声索国占领的岛礁,及其领海;通过拒绝其他声索国进出的方式夺取任何未被占领的岛礁;建立和扩大人工岛;对低潮高地的主权声索;基线主张以及基于领海基线对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不符合国际法的主张;对不符合国际法对海洋空间的过分主张;伪军事戒备区和在争议区域建立防空识别区。[4]再次,在政府最高层讨论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应该是9月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议程,及相似档次级别活动的议程。这种讨论不应该是再一次交换彼此的正式立场,而是应该努力取得更清晰和更细致的对担忧、意图和后果的理解,承诺采取相互保证措施,以避免螺旋式升级。
第二,强化信息搜集传播。首先,增强东南亚海事感知(MDA)能力建设。通过该透明机制,收集和公布情报,以及在政府内部及政府之间处理并分享情报。在最广泛的层面,通过支持提高南海问题发展透明度,帮助声索国形成南海的共同愿景。其他声索国将更好地协调他们的反应,方便各国即时做出预警和应急响应。其次,建立东盟简报机制。美国应该利用海事感知网络创建东盟简报,作为一个论坛,通过它分享有关中国岛上设施的信息。简报应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会议提交,让地区国家理解中国的岛屿项目的性质和影响,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来协调应对。再次,对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进行风险评估并定期公布。此举应将中国的警告和其他国家的反对承诺等事件充分记入档案,有关各方之间共享,并定期公布。“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以判决美国和地区国家的利益是否被中国的活动危害,并且通告将在该地区采取后续行动。”[4]
第三,扩大对东盟的支持。首先,美国需要深化并拓宽对东盟的实际支持。克罗宁认为,东盟中心已经成为美国对地区多边框架进行探讨的基本原则,美国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东盟团结和强化东盟共识,至少在四个层面上推动建设以东盟为中心的制度:东盟整体、东盟主权声索国、东盟成员国以及海上盟国和东盟内外的合作伙伴。其次,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美国应该继续呼吁利用行为准则来管理南海争端,但是应该鼓励东盟国家自己起草文件,然后向中国提供加入机会,而非目前的谈判模式。胡珀认为,正是由于当前的模式下中国-东盟谈判没有时间限制,致使中国已经减慢这一进程,同时逐步“修订”对其有利的领土现状。
第四,加强伙伴能力建设。首先,加强合作伙伴军事能力建设,实施对华“对冲战略”。美国应继续使用国防部4.25亿美元的东南亚保障基金为其他南海声索国的海岸警卫队和海军提供急需支持。同时,华盛顿应与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一道建立机制以协调东南亚的合作伙伴能力建设,使培训和设备支持相互促进。另外,将美国与菲律宾等地区国家防务关系的提升等级与中国的承诺和反应挂钩,美国将视情况暂停或重启上述措施。其次,美国应该帮助东盟声索国达成共识,为实现一个对所有国家都公平的共同目标而努力。促成这些国家减少分歧,制定共同的行为预期,并建立外交及安全合作方式。与此同时,美国应该通过提供外交以及法律专业知识等,来帮助东盟声索国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关于有争议主张的谈判,美国应努力促成菲律宾-越南和越南-马来西亚之间的双边解决。尽管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却有助于减少声索国之间在双方层面上和中国的分歧,以及能够反映这些国家坚持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有效遏制中国利用东盟声索国之间的分歧阻止这些国家形成共识的企图。
第五,保持强大军事存在。首先,保持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这将强化美国对亚太稳定的承诺,并深化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参与。关岛及马里亚纳群岛虽在南海之外,这里的美国驻军也可以为地区范围的海上、空中和海岸警卫队演习及训练提供良机。这些步骤同美国亚洲再平衡军事层面的意图是一致的。其次,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威慑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为了防止美国的目标和能力之间差距的出现,美国需要投入更多军事资源,包括核潜艇、巡航导弹等,维持美国的显著优势。因为这种威慑的目标不是战争,因此要竭力“避免相互战争”,“保持稳健的威慑。”[4]但是,斯韦因在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他建议华盛顿应该停止强调军事威慑的方法来阻止改变现状,扩张的声明和含蓄的威胁,以及呼吁更多的军事行动起不到任何用处,只会导致立场强硬和加倍双边对抗的努力。这有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加对抗性、零和博弈方向以及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
第六,构建地区多边机制。首先,建立海上多边联盟。美国应该利用东盟的召集力量汇聚更多海上强国,结成更广泛的联盟,主要成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从东盟部长级会议到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峰会等外交机制以及东盟防长会议上,美国都应该坚持把南海问题提升到最高优先级上。更广泛的海上联合演习可以定期开展,在南海展开空中和海上巡逻,密切审视最近的发展以及增强应对所有危险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斯韦因认为华盛顿不应该鼓励日本自卫队加入美国在南海的巡逻。日本改进美国的东南亚盟国和朋友的海岸警卫队能力的努力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南海部署日本自卫队将加剧美日联盟和中国之间新出现的安全困境,带来不稳定”。[4]其次,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需要强化支持海洋法创建和支持全球性机构,这将增强美国的力量,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机构和平解决争端。其中,美国必须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此举会进一步支持以规则、规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后者正是美国正在试图培育的,借此美国可以再次对其规则和规范的发展实行“直接领导”。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将消除长期以来中国偏见性的批评。总之,“美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个伟大的想法”。[4]
第七,加快TPP谈判进程。美国应该投资长期的经济实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可经由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及发展关系实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完成,可以证明美国有能力构建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架构。美国需要吸引包括菲律宾、韩国等更多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可以利用该协议获取关键的影响力,在未来贸易规则的问题上与金砖国家一较高下。
同时,美国还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想象力以及资源,为美国自己打造一个多边发展倡议。美国国会应该要求当前和未来的美国政府制定一个包括提出新倡议的新发展战略,建立一个重要的国际公私合作关系,推动亚洲人文发展。在这方面,美国无须效仿中国推动当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而应更关注新知识经济、人力资本和教育、科技、卫生和能源等美国更具竞争优势的领域。
四、解析美国主流智库对美国南海角色认知的评估
参加此次国会听证会的四位学者均来自美国顶尖智库,也都是著名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其观点基本代表着美国主流智库对南海安全局势和美国角色的认知。正因为此,是他们而不是别的智库学者,被邀请参加此次关于南海问题的听证会。美国智库以其独立性、非营利和权威性而著称,但是上述四家智库学者关于南海安全局势和美国角色的分析评判和政策主张在整体保持一致的同时,在局部问题上也存在显著的分歧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主张——尽管他们都是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这背后,深刻反映了美国智库自身的背景与特点影响其政策偏好。同时,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东亚地区格局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使得他们对南海安全局势和美国角色的认知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中国发展强大的激烈争端,其中也包含他们深刻的内在矛盾和焦躁不安的情绪。
第一,智库与学者自身的背景特色影响其政策偏好。美国智库擅长标榜自身的独立性,但是一般而言他们具有自己稳定和固定的资金来源,比如政府、军方、利益集团等,而有的智库则有自己的隶属单位。因此,美国智库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其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助单位的影响。从而,“智库的政策倾向有了很大程度的区分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政策偏好”。[3(P48)]比如在此次听证会上,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洋研究所的埃里克森来自军方智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利益。因而,埃里克森的发言通篇以军事为主,态度相对强硬。他特别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美国军事力量的式微,以及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问题,主张加快美国军事威慑能力建设。他坚决要求对华实施军事威慑,主张中美南海军事对抗长期化,为此要求接受适度摩擦。相对而言,另外三位学者的观点相对中立,克罗宁强调包容,胡珀主张多边主义,特别是斯韦因的立场比较温和。斯韦因对军事高压政策持有异议,认为“美国和中国必须超越激烈的言辞和信号”“美军没必要在南海进行高水平的信息侦查搜集活动”。[4]事实上,斯韦因所属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其政策观点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和合作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这也决定了斯韦因发言的整体基调。
第二,充分体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美国智库及其学者在南海问题上秉持双重标准,充分体现在南海岛礁建设方面。在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上,他们的焦点聚集在中国所谓的军事建设,对其他国家先于中国开展此类活动有意避开。其一,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中国南沙岛礁上进行非法建设在前,中国在本国的岛礁上进行建设在后。其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岛礁建设增加岛礁面积,和中国此类活动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其三,事实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经”在非法占据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建设,而中国只是“可能”用于某些军事考虑。可见,军事考虑并非问题的关键,即便中国的规模、速度并不突出,也会被他们视为威胁和挑战,问题的关键是双重标准。双重标准使他们忽视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性质维度和政策逻辑。
在他们看来,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所采取的系列举措,只是对当前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活动的合理反应,是处于平衡中国的正当行为。这一认识显然是将中国的南海活动视为局势紧张的根源,而忽视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是对其他国家类似活动的回应与平衡。从表面上看,美国及其伙伴炒作南海问题是南海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的原因。而从深层次看,根本原因在于菲律宾、越南等国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和宗旨,在非法占有的中国岛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岛礁建设,以强化实际占有。这种行为不仅违反国际法,也打破了2002年以来的地区平衡。因此,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是推动南海局势平衡而非打破平衡。美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若干年来进行的大规模岛礁建设活动视而不见,反而将中国为扭转局势而进行的被动岛礁建设视为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源,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的本质。
第三,折射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心态。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中,这些学者建议美国政府更多地利用国际规范、多边机制以及地区国家等第三方因素来制衡中国,凸显了美国传统离岸平衡手角色的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力不从心,逐步开始强调潜在成本和责任分担,要求他国承担更多的防卫负担以减轻美国压力。美国在继续推动传统的“美国+盟国”联盟体系双边互动模式的同时,开始强调“盟国+各盟国”的多边互动模式。即便如此,胡珀也不得不承认,“单独多边方式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的增量机会主义”。[4]
他们在建议对中国示强甚至是进行军事威慑的同时,也在强调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中美合作问题。对华“适度的摩擦”必须是有限的、可管理的,中美必须要避免战争,威慑的目的只是防止中国的某些行为而已。同时,还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从而形成一种竞争加合作的双边关系。可见,对华强硬政策仍受到国内外诸多要素的制约,使用武力不是美国应对南海问题的首要选择,慎用武力仍是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
对华实施政治高压和军事威胁也表明,美国以其他手段应对中国发展的乏力和无助。态度最为强硬的埃里克森也无奈地表示:“我们必须接受基本现实,即我们不可能把中国从现在占领的岛礁上击退。”[4]在论及中美军事差距时,他的话语中透露着深深的危机和忧虑意识。
然而,美国一边是一味对中国示强,一边又寄希望中美“在短期内承诺提供相互确保,同时致力于长期形势的稳定”。[4]这折射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心态。这种困境下,美国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通过军事威慑和联盟体系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而是如何理性接纳中国影响力的外溢和如何实现中美良性互动。否则,当前的行动就会产生更危险的难以扭转的局势,那将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加对抗性、零和博弈方向以及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美国在竭尽全力对华遏制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对华遏制无效的后果,尽管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他们却显然低估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1]“Subcommittee Hearing: 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DC, Jul 23, 2015,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hearing/subcommittee-hearing-america-s-security-role-south-china-sea.
[2]CAN, The South China Sea: Assessing U.S. Policy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October 2014. 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SouthSeaOptions_CNA.pdf.
[3]卢静.美国智库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评析综述[J].现代国际关系,2010,(7).
[4]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50723/103787/HHRG-114-FA05-Wstate-HooperM-20150723.pdf.
〔责任编辑:左安嵩〕
The Current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merica’s Security Role——A Text-based Analysis on the Recent Hearings of Mainstream Think Tankers in America
LI Zhong-l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nt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caused heated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the US Congress held the hearings of “US security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viting the scholars who come from American mainstream think tankers. The hearings focused on two topics, “the current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merican policy options”. Overall, the scholars agree with the US government to take strong policy toward China; meanwhile they hope that Sino-US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be guaranteed too. 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 core of Sino-US competi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for the rule and order. Hence, the Sino-US game and tension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continue.
US think tanker;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cy options; hearings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CW201409)
李忠林,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南海问题研究。
D815.3
A
1006-723X(2015)12-00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