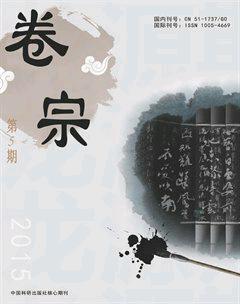日本不动产侵夺罪之历史沿革
曾德康
摘 要:盗窃,是对非己财产的直接侵犯,尽管社会危害性较小,但时常发生。动产作为盗窃的对象已成共识,然而,对于不动产能否被“盗窃”却争议不少。在面对不动产亟需保护的情况下,日本《刑法》以“不动产侵夺罪”的形式,搁置理论争议而先行保护之实,这对我国刑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刑法;不动产侵夺罪;盗窃;中国刑法
盗窃罪属于侵害他人财产性权益的犯罪,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于盗窃物的定义往往与物之可移动性相联系:成立盗窃需以被盗财物脱离所有人的支配范围,并发生非法占有为条件。故而,不动产不属于盗窃罪的保护范畴。然而,随着社会交互行为的复杂化,当发生自有耕地被他人私自耕种,且获利巨大等情形时,传统的刑法观念则在不动产的保护上爱莫能助了。
关于盗窃罪的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日本刑法学界亦存争议,通说与判例均以不动产不可移动为由予以否定。1960年,日本对刑法进行了修正,“不动产侵夺罪”被增设其中。笔者认为,由于学界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仍存在争议,所以,罪名中“侵夺”二字并不是对不动产能够成为盗窃对象的否定,相反,这体现出立法者从法律层面给予不动产保护以肯定。
1 日本刑法的发展与相关盗窃规范的特点
作为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间的岛国,日本从古至今灾害频发,这客观地造就了大和民族感恩自然又极力争取生存的民族特性,故而,对舶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方式。可以说,日本法律是倚靠中国而蹒跚起步,借助欧美而独立行走,它的发展是一个兼收并蓄的过程。
明治维新开始后,1868年至1873年间,明治政府相继颁布了《假刑律》、《新律纲领》和《改定律令》,作为刑法典的铺垫。由于受到清王朝法文化的深刻影响,三者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性质上都属于“中国法系の律の系統(中国法系之律类体系)”。1880年,日本的第一部刑法典编纂完成,日本国内称之为“旧《刑法》(明治13年太正官布告36号)”。旧《刑法》以法国刑法典为基础,参考比利时刑法、德意志刑法和意大利刑法,并在博瓦索纳德(Gustave ?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的支持下完成。
由于“盗窃作为最古典的犯罪形态,是具有高犯罪率的常见型犯罪行为1”,因此,旧《刑法》在第二章财产性犯罪的第一节,便开门见山地详述了“窃盗罪”(盗窃罪)。
第366条 窃取他人之物者,以盗窃罪之名处2月以上4年以下监禁。2
第367条 洪涝火情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乘人之危而盗窃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监禁。
第368条 破门越墙或者私开他人仓库行盗窃之事者,以第367条定罪处罚。
第369条 二人以上共犯前三条所列之罪者,各罪加一等处之。
第370条 携带凶器进入他人住所行盗窃之事者,处以轻徒刑3。
第371条 偷盗他人田地中五谷果蔬者,处1月以上1年以下监禁。
第372条 偷伐偷盗山林中的树木矿藏,或者偷盗他人养殖于海河湖泊中的养殖物,或者其他有关经营活动的物品者,以第371条定罪处罚。
可见,在日本的旧《刑法》中,对于盗窃罪的定义是采取列举的方式,立法者欲穷尽犯罪之各种形式,却实为难事,因而流弊甚多。
旧刑法实施后不久,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兴盛,各种犯罪现象也极具增加。明治23年(1890年)以后,诸如富井政章、勝本勘三郎等法学学者在研习欧洲新派刑法理论后,开始批判旧刑法在打击犯罪方面的软弱无力,故而,一场以1871年德意志刑法(以后期古典派刑法理论为基础)为参照,以新派刑法理论为指导的刑法修改活动开始了,18年后(明治41年),第二部刑法——现行《刑法》(明治40年法律45号)正式实施。
较之于旧《刑法》条款冗杂、言多必失的弊端,日本现行《刑法》则显得条理清晰、内容简练,特别是在盗窃罪的认定上,极度简明,并且独具特色地区分了“动产盗窃”与“不动产盗窃”。
第235条 盗窃
窃取他人财物者,以盗窃罪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35条之2 不动产侵夺
侵夺他人不动产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日本现行《刑法》第三十六章规定为“窃盗及び強盗の罪”(盗窃罪、抢劫罪),该章共12条,包括“第235条之2”。其中,第235条、第235条之2分别规定了“动产盗窃”和“不动产盗窃”,第242条、第243条、第244条以及第245条则分别从盗窃的角度就“他人的财物”、“盗窃未遂”、“亲属间犯罪之特例”以及“电力资源”的属性进行了解释。有关盗窃罪的条文在现行《刑法》中所占数量虽大幅减少,但实则扩大了该罪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范围。
2 不动产侵夺罪之设立背景
日本现行《刑法》中之所以区分“不动产盗窃”,是源于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内社会更是破败凄凉。疾病、饥饿和自然灾害导致社会动荡不堪,加之警力的缺乏,致使以生存为目的的偷盗行为崭露头角,直到黑社会等暴力组织的顺势介入,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暴力犯罪活动,其中就包括侵占有主或者权属不明的不动产。4
经历战火侵袭的日本,部分土地的权属已不甚明朗,这为无家可归的日本民众寻求自救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于是,大批的简易棚屋搭建其中,甚至连公共场所也难以幸免。这样一种非法状态随着棚户的激增与商业化,而于人的意识中显得理所应当,并逐渐地被渲染为一种“合法”的存在。兜售食品、定做工具、买卖服饰等等,棚户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生存。权贵们逐步将这类非法占有推向城市的中心,希望通过修建建筑物的方式永久地占有他人土地,从而将之合法化。由于当时的司法力量薄弱,土地的合法所有人只能通过雇佣暴力团体发起反抗的方式实现私力救济。于是,人身伤害、财产损害案件不断增长,虽然大部分人都以损坏建筑物罪为名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法院终以成立正当防卫而宣判其无罪。
尔后,立法者意识到,仅靠民事救济并不是快速遏制这种违法状态的万全之策,不论是从制止暴力犯罪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古往今来国家对盗窃罪的惩治上看,对不动产盗窃行为的处罚都势在必行5,因此,1960年的刑法中,增加了“不动产侵夺罪”一条。
3 不动产侵夺罪的构成要件
3.1 主体
日本学界认为,不动产侵夺罪的犯罪主体与盗窃罪之主体并无差异。因此,从盗窃罪的角度去理解本罪的主体是恰当的。
日本通说指出,窃取他人占有之物者即为盗窃罪的主体6,但是,在适用日本刑法的过程中存在两种主要限制:“自己占有物”和“亲族相盗”。而河上和雄指出,不动产侵夺罪的主体尽管没有特殊限制,但是适用“亲族相盗”所规定的例外7。
日本刑法的形成与发展受中西方影响很大,明治维新时期,《假刑律》、《新律纲领》和《改定律令》等刑事法律中就融入了“亲族相盗”的规定,旧《刑法》在第337条明确规定:“祖父母父母夫妻子孙及其配偶,或者同居一室的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窃取财物的,不入盗窃之列”。后期草拟的新《刑法》,也直接受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瑞士等国刑法的影响。因此,日本现行《刑法》在第244条就“有关亲属相犯的特例”做出了具体规定:
1.配偶之间、直系血亲之间,或者同居一室的亲属之间,犯第235条、第235条之2之罪,既遂与未遂犯均免予刑罚。
2.有亲属关系,但不属于前项所规定的亲属的,犯以上同等之罪,不告不理。
亲属间犯盗窃之事而特别处理的规定,源于日本社会“法律は家庭に立ち入られない(法律不入家庭)”的传统思想。通说亦认为,亲属相犯应当由家族内部固有的处事规律进行解决,不能过分使用国家的刑罚权力加以干涉。故,亲属亦不构成不动产侵夺罪之主体。
3.2 主观方面
构成侵夺,除了需要具备实施侵夺的故意外,还必须具有“不法领得”的内心意思。此处的不法领得与动产盗窃下的概念相一致,意指行为人排除他人占有而将不动产当作自己所有物,进而依照其属性加以的利用或者处分的行为,并不需要行为人以自己所有为最终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对他人之不动产短暂性的使用,则不成立不法领得,不构成本罪。例如,在他人的空房中留宿一晚,或者擅自在他人的空地中搭建舞台开一场演唱会,均不构成不动产侵夺罪。
此外,日本福冈县高等裁判所的判例还指出,没有履行相关道路法规的法定手续而擅自填埋道路周边的土地用作驾校场地的,由于市政府知悉该行为,因此无法构成不法领得;而周围的居民将其视为普通道路加以使用,也就具有正当性了,亦不构成侵权。(福冈高判昭44·3·18高集22卷1号46页)
3.3 客体
立足于设立不动产侵夺罪的社会背景,可以明晰其保护的法律关系是,不动产所有人对该不动产享有的合法权利。由于不动产包含的价值往往较大,一旦对其行使处分全能,将引起复杂的社会关系变动。因此,不动产侵夺罪的设立有利于保障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行使,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3.4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对他人不动产的侵夺。
首先,他人的不动产,是指除自己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国家或者地方团体所有的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为他人所占有,或者被公务机关指定由专人看管时,亦属于他人之不动产的范畴8。此时,他人占有不动产虽然不具备法律上的所有权,但是由于其存在法律需要保护的独立的法益,因此所有权人也不得侵犯。
其次,该罪还要求行为人基于不法领得的内心意思,在排除他人的占有后,将不动产置于自己或者第三人的支配之下。积极主动的侵占行为是必要的,而是否具有公然性,是否被被害人所知悉,在所不问。对于判断是否成立侵夺,应当“综合考虑具体的案件情况,不动产的种类,占有侵夺的方法、状态、程度,占有时间的长短,恢复原状的难易程度,排除他人占有并设立自我占有意思的强弱,以及是否给予对方损害等情形。9”
此外,生活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行为人对不动产不存在现实的管理和占有事实,而仅在房屋产权登记簿上做了虚假登记。将这一行为断定为“排除他人的占有”是不合适的。不动产侵夺罪惩罚的是对于不动产的事实侵占行为,它要求以存在实际且积极的侵占行为为要件。因此,对于这一类违法行为,“文书伪造罪”足以规制,无需刻意归至本罪。
四、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我国刑事法律对于不动产是否属于盗窃之对象并无规定,换言之,我国刑法在保护不动产问题上缺乏细致的规范。正因为立法态度的不明朗,导致学者对该问题仍未达成共识,从而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盗窃罪的对象仅限于动产,因此,从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角度出发,也不应刻意将不动产排除在外10。而且,“窃取”行为并非成立盗窃罪所必须的最终样态,而是意指,通过窃取行为最终达至排除原权利人占有财物而转为自己占有或者第三人占有的事实状态。尽管不动产无法窃取,但是可以实现“窃占”,而这两者于效果层面是一致的。此外,还有学者补充,某物是否发生物理上的位移,与其能否成为盗窃之对象并无必然联系。例如,“甲发现乙的皮包里有巨额现金时,便起了非法占有之意,当乙把皮包放在一旁时,甲用自己的衣服把皮包盖住,自己坐在上面,乙发现自己的皮包找不到后便去报案。这时甲已经实现了对皮包的控制支配,成立盗窃罪,而这时皮包的位置并未发生位移。11”
支持否定说的学者则列举如是理由:首先,刑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约束国家刑罚权力行使的规范,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入罪,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具体条文加以确定。其次,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完成物权登记为要件,纵然行为人实施了窃占行为,权利人仍旧能够依据产权登记簿享有所有权,其并未丧失对不动产的控制。再次,从社会成员朴素的观念出发,将不动产纳入盗窃的对象范围是难以理解的,而且,“现代的刑法价值观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12”
笔者认为,当一行为具有可责罚性时,行为人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的数量,全然取决于其违反的法律规范的种类。刑法与民法并非对立,在惩罚违法行为上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民事上的侵权行为仍具有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性。刑法的谦抑性不应被过分解读以至于滥用。如今,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均价值不菲,因此,窃占后所获得的利益不可谓不大,然而,在盗窃价值2000元的财物即可认定为符合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情形下13,窃占不动产却仅给予民事上的苛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外,将所有权是否转移,作为盗窃成立与否的判别标准是不恰当的。笔者承认动产盗窃罪的既遂形态下,行为人是完成了窃取行为的,且大部分动产业已发生位移。然而,这种排除原权利人占有,自己给予动产控制的状态并不能导致所有权发生移转。刑法对这一行为的制裁,终究在于其破坏了原权利人占有的事实状态,而非夺取了所有权(于民法上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以不动产产权登记未发生变更,来否认不动产侵占所带来的、与动产盗窃同等的危害,从而将其排除于盗窃对象之外,是不符合逻辑与法理的。
我国刑法在盗窃不动产问题上没有具体规定,这会导致一些现实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例如,农户私自更改土地地界标示,侵占他人暂未耕种的土地用于珍贵中草药的种植,获利数万元。针对这一行为,若只追究其民事上的侵权责任,由于违法成本较小,该类案件不仅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会持续增长。因此,刑法应当加强对不动产的保护,在相关概念的争论尚未得到平息的情况下,可以借鉴日本《刑法》的做法,暂以“不动产侵夺罪”的罪名形式来规制对不动产的窃占行为。
参考文献
[1][日]中山研一,刑法各論の基本問題 [M].東京:成文堂,1986:113.
[2]本文所载日语文献与刑法条文之内容均为笔者所译。
[3]轻徒刑:“軽懲役”,指日本旧《刑法》第22条第2款规定的6年以上8年以下有期徒刑。
[4][日]大塚任,川上和雄,佐藤文哉.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9巻)[M].東京:青林書院,1991:290.
[5][日]大塚任,川上和雄,佐藤文哉.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9巻)[M].東京:青林書院,1991:290[川合].
[6]日本《刑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責任年齢]14歳に満たない者の行為は、罰しない。(对于未满14周岁的行为人不予以处罚。)
[7][日]大塚任,川上和雄,佐藤文哉.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第9巻)[M].東京:青林書院,1991:291.
[8]日本《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条。
[9]大阪高判昭40·12·17高集18巻7号877頁――高村達美·捜研179号87頁。
[10]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1]陈宁. 不动产盗窃行为入罪问题之研究[J]. 政法学刊,2009,03:31-35.
[12]张颖杰. 略论不动产窃盗[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03:4-6.
[13]记者 肖春燕 王勇. 山东调整盗窃罪入罪数额标准[N]. 人民法院报,2013-07-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