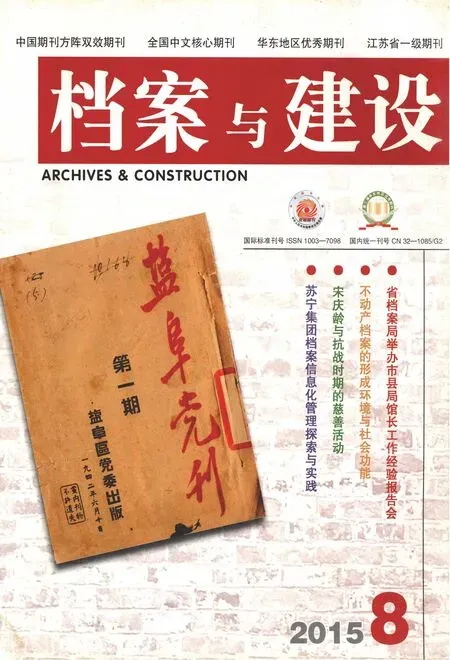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
沈慧瑛
(苏州市档案局,江苏苏州,215004)
自2012年起,苏州市档案馆陆续将苏州古典园林怡园、过云楼主人顾文彬(1811—1889)及其后人的档案征集进馆,其中顾文彬日记、年谱、书信、《吴郡真率会图》等颇为珍贵,弥补了馆藏档案历史文化内涵的缺憾。《过云楼日记》是顾文彬从同治九年到光绪十年(1870—1884)15年间宦游生涯与归隐故里的实录,涉及家庭生活、社会交往、诗词创作、怡园修造、过云楼收藏、官场活动等情形。2015年5月,《过云楼日记》由上海的文汇出版社出版。
一
顾文彬,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湖北汉阳知府、武昌盐法道、浙江宁绍台道,词坛名家。顾文彬属于懂得生活情趣、懂得艺术欣赏的一代词家,朋僚往来频繁,一同诗酒唱和、游戏玩乐、鉴赏字画、寻访名胜,怡情自乐。因此日记的语言虽是简洁的,内容却是丰富的,有事则多记,无事则一笔带过,其间夹杂不少诗词。
作为过云楼的第一代主人,有关收藏字画、玉器、钱币的活动是日记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中可以一窥过云楼是如何崛起的。顾文彬在同治九年三月到京城等待复起的十个月里,跑遍了琉璃厂,成为博古斋、松竹斋、论古斋、德宝斋、润鉴斋等20余家古玩店铺的常客,或观赏、或购买、或请他们代售,黄公望、文征明、唐伯虎、仇英、沈周、王时敏、王石谷等名家的作品都是他收藏的目标,其中讨价还价、鉴别真伪、欣赏过程等细节都被一一记录下来。特别是当以低廉的价位获得珍品时,其心情无比舒畅,日记中经常出现“狂喜”、“快心”等字眼。
顾文彬在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八日记道:“与论古斋议定《宋拓定武兰卷》、王石谷《十万图册》,价银八十两。近日快心之事,除军机进单外,此事为最……平心而论,即石谷册已值此数,《兰亭卷》只算平空拾得,论此卷价值,即三百金不为贵也”。松筠庵的心泉和尚雅好收藏、精于鉴赏,两人经常相互观赏书画作品,鉴别真赝。当心泉看到顾文彬新得的上述两件宝贝时连说“值三百金”。京城十月,顾文彬隔三差五光顾古玩字画店,精挑细选,反复鉴别,文征明的《秋林闲眺图》、唐伯虎的《墨石菖蒲盆立轴》、沈周的《长江万里图卷》、王石谷题王鉴《碧云山海图》、金冬心人物画册、董思翁山水小册、明贤诗札四十家等大量名家字画、旧拓流向过云楼。

顾文彬在日记中说“物之得与不得,洵有一定,不可强求”。无论在京城还是在苏州,抑或宁波,他不时因为“价昂”而放弃心仪的书画。从第一次见到心泉和尚所藏释永《真草千文墨迹卷》就惊为“奇宝”,后数次观赏,两人一度谈好价格150 金,顾氏也拿回寓所,终因“客囊窘涩,舍之而出,中心耿耿,未尝一日忘”。直至第二年他已就任宁绍台道,嘱咐在京城的女婿朱研生以当初议定之价,再向心泉求购。面对失而复得的释永《真草千文墨迹卷》,顾文彬写下这段话:“窃叹历来见此卷者,岂无好而有力者,顾皆弃而弗收,迟之又久,而卒归于余,固由翰墨因缘亦有前定,究由真鉴虽逢,因循不决,如此奇珍,失之交臂。假使余出京后,此卷竟属他人,悔将何及,既自幸又自愧也。”日记中详细地记下了初见时的惊奇、鉴赏时的喜悦、放弃时的无奈,以及最终收藏的全过程。失之交臂的遗憾也时常在顾文彬的笔端流露,多数是书画商或者藏家的出价超过了他承受的能力范围。
收藏书画的过程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拼眼力、拼实力,但最怕拼到最后还是买到赝品。顾文彬日记中屡屡出现“亦疑为伪,可见真识之难”,“审定书画之难如此,总不宜掉心轻心耳”,“作伪者千奇百怪,稍不经意,即受其欺”,“书画介乎疑似者便是伪作”这样的文字,感叹辨别真伪之难。就如翁同龢见到顾文彬出示《定武兰亭》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不敢定也”。朋友送来秦淮名姬柳如是的《五柳高隐卷》和顾横波的《梅兰竹菊图》给他鉴赏,前者由钱谦益、袁枚题跋,后者由龚芝麓题引首、吴梅村题七绝于卷尾,对方要价二十八金,顾文彬只肯出十二金。之所以没有成交,价格不是主要问题,就如顾文彬所说:“即二十八金亦不为贵。余因无可印证,未给灼然无疑,故姑舍是。”面对一幅作品,往往从纸张年代及生熟(有纸本、绢本、绫本之别)、印章新旧、作者生卒年份、笔迹、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证。即使顾文彬小心求证,也有上当的时候,他曾在京城以二十金的高价购买黄公望的作品,这是唯一一次“在京出重价而误收伪迹”。
从《过云楼日记》有关书画作品收藏的记录,可以发现收藏家除了需要财力支撑外,更重要的还须具备深厚的书画修养。顾文彬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与鉴赏能力,而且身边不乏志同道合者,及时提供各种名家书画信息,相互品鉴讨论,提供参考意见。更为幸运的是,顾文彬的三子顾承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与鉴赏家,涉猎广泛,眼光独到,经手不少精品。可以说过云楼是顾文彬、顾承父子合力的产物,而顾承过硬的鉴赏力确保了过云楼收藏的品质,使过云楼名扬天下。
二
北宋年间,司马光官场失意后,与故交至友成立真率会,规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由北宋到晚清,皇帝不知换了多少个,缙绅名士的风雅不减当年,吴郡真率会就是光绪年间已归隐苏州的官绅们的小圈子。他们以真诚坦率为相处之道,以私家园林为活动场所,以书画鉴赏、诗文唱酬、品茗饮酒为主要内容,雅集频频,自娱自乐,俨然成为引领苏州时尚的文化沙龙。《过云楼日记》中有关真率会的记录与《吴郡真率会图》,复原了晚清士绅交游的图景。
吴郡真率会初期的主要成员为吴云、沈秉成、李鸿裔、勒方锜、顾文彬、潘曾玮、彭慰高七人,或名门之子,或封疆大吏,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都是当时的名流耆旧,更因机缘巧合与吴门结下深厚的渊源。顾文彬、潘曾玮、彭慰高是地道的苏州人,吴云、李鸿裔在苏州做过官,罢官后又息影吴门,而勒方锜正在苏州任上。彼此关系颇为密切,来自归安(即湖州)的吴云与沈秉成既是同乡,又是亲戚;而吴云、顾文彬、彭慰高三人同岁,且有姻亲关系,其中吴云之孙娶了顾文彬的长孙女。这些学富五车的名流擅长书法,精于鉴赏,爱好收藏。情趣相契的他们轮流作东,时而品茗喝酒,时而吟诗作对,时而鉴赏字画,从城南李鸿裔的网师园到城中顾文彬的怡园、吴云的听枫山馆,再到城东沈秉成的耦园,来来往往,风流自在。顾文彬的日记中有关真率会雅集达20次以上,且策划与导演了真率会成员们的集体照——《吴郡真率会图》。此图呈现了这些热衷林泉生活的官绅们的交游场景,那份悠闲与风雅让后人羡慕不已。
光绪五年(1879)九月初九,顾文彬邀请真率会的朋友们在怡园举行雅集,特地请来常熟籍画家胡芑孙为他们集体画像,每人各持一幅作永久纪念。图成之后,顾文彬发现朋友们的POSE(姿态)摆得太一本正经,“不能顾盼生情,致令补景者难于措手”。于是他与另一位著名画家任阜长商量,在画卷中补画三个童子,“一摘阮,一抚琴,一吹笛”。两个多月后,顾文彬将画分送给好友们,先到李鸿裔处,再到听枫山馆。谁知吴云看后,嫌自己脸上“瘤太大,玉泉(即潘曾玮)面色太红”,有损老帅哥的光辉形象,要求顾文彬让画家重新美化一下。第二年秋天顾文彬为此图题跋,对画卷中的人物相貌神情及其所坐位置逐一描述:“其浓眉秀目,面皙髭白,以手掩胸而坐于右者中江李鸿裔香严也;面圆髭微白,其容蔼然,以手按膝而中坐者奉新勒方锜悟九也;面颊若被酒,白鬚飘然,袖手抱膝而坐于左者吴县潘曾玮养闲也;方面浓髭、笑容可掬,屈膝而坐于方椅者归安沈秉成仲复也;凭椅背而立,面清臞、鬚疎白,有海鹤风姿者归安吴云愉庭也;面长鼻直,美鬚髯望之伟然,凭几而坐者长洲彭慰讷生也;方面微髭,坐于几侧,以手作按曲状者元和顾文彬艮庵也。”点评一番之后,又描述真率会的主旨:“坐无杂宾,肴止五簋;位以齿序,酒随量饮;礼数不拘,弗流放诞;庄谐并作,弗涉讥弹。酒阑之后,继以品茗,各出法书名画,互相欣赏。”
同年,李鸿裔应顾氏之请为其真率会图抄录了钱饮光的诗,第二年又题咏。而“《吴郡真率会图》怡园藏卷”几个字则由吴云题写,时间为光绪八年六月。这一年为此卷题咏的还有彭慰高、沈秉成、潘遵祁。彭慰高以一手漂亮的隶书题写长诗:“真率斋中载酒过,闲云天际意如何,往来人侣沙鸥孰,更比城南雅集多……我本沧浪旧钓童,而今衰白已成翁。数椽老屋堪延客,分付园丁种早菘。”沈秉成也以长诗题跋,巧妙地将六人的名字嵌进诗句,写出他们的经历、性格及兴趣,如“钝舫少小绍其裘”指彭慰高,“延陵好古无与俦”指吴云,“养闲洵可傲五侯”指潘曾玮。吴云则题诗感叹“各抱平生志未酬”,40 多年岁月的磨砺早使朋辈们当年的豪气荡然无存了。由于吴云体弱多病,经常由其作东在听枫山馆举行真率会活动,有时勒方锜、潘曾玮也借此雅集。光绪六年四月初四,吴云在听枫山馆召集真率会活动,参与者沈秉成、彭慰高、李鸿裔、顾文彬。此时吴云在听枫山馆的院中新筑茅亭,“枫树下环筑假山,移石笋三株”,请顾文彬撰写楹联。顾氏的书法一流,诗词也不错,平时喜欢集苏东坡、辛稼轩等名家的词,当即集辛稼轩词相赠:“今古几池台,新茸茆斋,倚栏看碧成朱,揩试老来诗句眼;风月一丘壑,醉扶怪石,有客骖鸾翳凤,横斜削尽短长山。”那年十一月初九日,吴云又邀作蝴蝶会,实则是真率会之“变局”,参加者即真率会中人,唯一增加江苏布政使许星台。或许是初次活动,许星台带菜肴请大家品尝。
真率会人员并不固定,最初吴云、勒少仲、沈秉成、潘曾玮、李鸿裔、顾文彬六人经常相聚,到光绪五年九月初二在李鸿裔的网师园聚会时,彭慰高开始加入,之后勒方锜开始到福建等地任职,至光绪六年七月初七日潘谱琴作为新成员加入。顾文彬在光绪八年、九年的日记中并无真率会活动的记载,究其原因:一是勒方锜、吴云相继过世,沈秉成离开苏州再度进入官场,朋友们聚不起来;二是这两年顾氏家中丧事接二连三,先是最钟爱的儿子顾承突然过世,接着二孙、大孙病亡。直至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顾文彬的日记中再次出现真率会的记录,说“七老真率会”雅集在潘遵祁的三松堂举行,参加者有顾文彬、潘遵祁、蒋心香、彭慰高、吴引之、吴语樵、潘曾玮。真率会是一个风雅的朋友圈,而今早已成为过眼烟云,惟有文字让我们触摸到历史的余温。
三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减少不少繁文缛节,及至1949年之后,“破四旧”的活动使不少传统项目随之消失,人际交往也更为简单,除了婚丧生子大事外,一般鲜有礼金的支出。但在顾文彬生活的年代,传统节日多,朋僚交往多,大至祭祀神灵先人,其中涉及不少礼仪礼节,尤其是礼金名目繁多,花样百出。
顾文彬自同治九年三月初一离开苏州,到闰十月二十日接到补授浙江宁绍台道员的官职,数月的等待总算有了结果,而且这是个肥缺,到那儿任职,顾文彬十分满意。按清代官场惯例,地方官员离京时都要给京官别敬,别敬之意即离别时的赠送,实则也是一种贿赂的雅称。顾文彬的同学、好友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夏天送的礼金叫冰敬,冬天送的礼金称炭敬,这三敬在当时的官场是一种合法行为,低收入的京官靠此养活全家老小。顾文彬按习俗到各处辞别,顺便奉送别敬,仅十一月十三日,他拜访了夏同善、沈桂芬等32 位,送给25 人别敬,但沈桂芬等4 人“仍璧还”。第二天顾文彬又“往各处送别金”,共送朱茗笙等8 人别敬,只有李鸿藻未收。另外顾文彬还送给18 位小军机每人别敬“十二金”。离京辞行之时,顾文彬共送了53 人别敬,仅7 人退回,可见接收别敬属于正常之事,但退回别敬或许要看彼此关系的疏近与交情的深浅。
恭亲王奕䜣对下属管教甚严,当顾文彬到恭王府拜访时,恰巧恭亲王不在,接待他的是恭王府回事处穆尔庚额号。顾文彬照例拿出红包送给他,不料对方婉拒,说“近日王爷不准收此,得日到寓来取”。据之后的日记,这位门房似乎并没有去取红包,恭亲王的“反腐”力度还是蛮大的,虽然管不了整个朝廷的大小官吏,至少他的手下不敢造次。别敬之外,节敬、水礼、贽仪、程仪、赆仪等礼金名称出现在日记中,贽仪是为表敬意所送的礼品,赆仪是送别时的礼品,程仪就是路费。古代上级、亲友要出远门旅行,作为下级或亲友,送给他一笔程仪用作旅途花销。赠送礼金既体现了当时官场的陋习,也反映了个人的品性。顾文彬经常以赠程仪的方式帮助别人,其日记中记载的最大的一笔程仪是500元:老师之孙从四川到宁波“求借千金”,顾文彬赠以程仪500元。有一位叫张的旧相识生活贫困,顾文彬经常以赠送礼金的方式给予帮助。
除礼金外,他们互相赠送的礼品范围极广,有生活用品、食品、酒席,也有高雅的书画、古玩等。但一般对方收礼不照单全收,总要退回一部分,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礼节。同治十年二月,顾文彬就任宁绍台道,先到杭州拜会浙江巡抚等人。拜会上司和同僚时都送礼,送给浙江巡抚杨昌濬“京货八色,配以尺头十二端,仅受缙绅、京靴”,“送午峰礼,受缙绅;送子垣礼,未受;送子颖,受绣货、缙绅、干果”。第二年春节,顾文彬到杭州拜会上司,送给杨巡抚“礼八色,收五色”,这五件礼品中除鱼肚四片外,其他都是名家字画作品:唐伯虎画屏四幅、金冬心的《梅花卷》、吴云刻《双钩虞恭公》一本及刘石庵、梁山舟字册各一本,这些字画放在当下都是稀世珍品。有时送名人字画有真迹,也有赝品,如顾文彬送给连绪斋将军的绢本米元章山水立轴、唐伯虎人物卷都是真迹,王烟客山水六页册、恽南田山水十二页册皆赝品。当时的读书人都有一定的书画知识与修养,为官者基本上以功名起家,文化素养较高,因此书画、拓片、古玩等也作为普通礼品出现在人际交往中。
除了送实物外,还流行送戏助乐。同治九年二月十六日,顾文彬与盛康、吴云、李鸿裔、潘季玉及苏州织造德静山等人借湖南会馆公局演大章班。当天的聚会由潘季玉操办,正厅两席,女眷在里边设一席,费用公摊。大章班与大雅、鸿福、全福合称苏州四大昆剧老班,遇到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生日、乔迁升职等都要请戏班演出。宁波也以昆剧为主。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为庆贺顾文彬生日,“幕友、帐房友送戏,辞之不获,传老庆丰班来演”。第三日顾文彬自己出钱,“仍请老庆丰班,还请幕友、帐友”。因此无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宁波,昆剧作为高雅的流行艺术活跃在大江南北,从中可以看出士绅们的文化生活与取向。
《过云楼日记》内容包罗万象,它不仅是一部反映作者文艺修养、兴趣爱好、宦海生涯的私人日记,更是研究晚清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与官绅交游的原始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