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与芭蕾
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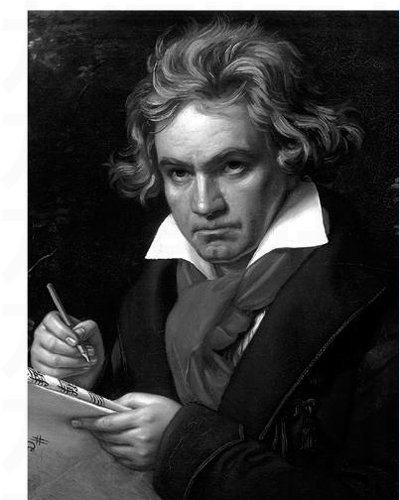


假如我们谈起词汇搭配,“纽约与摩天大楼”、“纽约与股票交易所”,似乎是最适当的配对,至于“纽约与芭蕾”,在不了解纽约的人看来,那简直是把两个异义词硬拽在一起。本文要说的偏偏是纽约与芭蕾的配搭,纽约与芭蕾之间的情缘,一个商业社会与一种高雅艺术之间的默契:
当华尔街的晴雨表预报经济天气,让股民们知道明日是晴或阴、该笑或该哭的时候,在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宏伟的大都会歌剧院,纽约客正陶醉在《吉赛尔》或《天鹅湖》动人的音乐和舞姿之中。
当洛克菲勒中心竖起全市最高的云杉圣诞树的时候,在林肯中心金碧辉煌的大卫·科克剧院,《胡桃夹子》开演了,那一段段舞曲,从糖果仙子舞到中国茶舞到雪花圆舞曲,把全场二千五百多名观众一个个都迷住了,其中有很多是中小学生。
当一群群顾客涌进梅西百货的时候,许多参观者正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欣赏法国画家埃德加·德加的一幅幅作品:《芭蕾课》、《芭蕾舞女》、《十四岁的小舞蹈家》、《芭蕾舞台下的乐团音乐家》等等。
多元化的纽约,既有错综复杂的商业史、金融史,也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史,其中包括芭蕾舞的历史,尽管其芭蕾史要短于罗马、巴黎和圣彼得堡。
在欧洲,芭蕾舞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意大利,被称为balletto,传到法国后被简称为ballet。十七世纪中期,这种综合音乐、舞蹈、哑剧和舞美来表演戏剧情节的舞剧,在法国进入兴盛时期,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 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舞蹈学校。十九世纪,法国先后出现多部浪漫芭蕾经典作品,如塔里奥尼编导的《仙女》、亚当作曲的《吉赛尔》、德利布作曲的《葛蓓莉娅》和《西尔维亚》。十九世纪初,法国舞蹈家狄德罗应邀去彼得堡,在后续三十余年期间对俄国芭蕾艺术革新作出重要贡献。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间,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写了《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的音乐,使音乐成为芭蕾的灵魂,使这些舞剧成为世界经典剧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艺术家们又为世界芭蕾舞坛增添了多部力作: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灰姑娘》,阿萨菲耶夫的《巴黎的火焰》和《泪泉》。
芭蕾舞在纽约虽是个迟到者,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正式的芭蕾舞剧团,但一旦出现,纽约便与芭蕾结下不解之缘,既传承古典芭蕾,又开创现代芭蕾,为这个商业大都会增添了亮丽的艺术色彩和浓郁的诗情画意。一九三四年,纽约第一个芭蕾舞剧团成立,初名美国芭蕾舞学校,一九四八年改称纽约市芭蕾舞团(NYCB),至今仍是西半球最大的芭蕾舞剧团。当初,曾在哈佛大学专攻现代艺术的林肯·柯尔斯坦一直怀有创建芭蕾舞团的梦想,一九三三年,他去伦敦会见了巴黎俄罗斯芭蕾舞团大师乔治·巴兰钦,成功地说服他移居美国,翌年两人就开始在纽约创业,先建校后办团,为现代芭蕾事业大力开拓,其重大创作成果对世界芭蕾舞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舞团重要成员后来还包括另两名舞蹈家和编舞家:纽约当地人杰罗姆·罗宾斯和来自丹麦的彼得·马丁。罗宾斯另因导演百老汇音乐剧《国王与我》、《西城故事》和《屋顶上拉小提琴的人》而享誉艺坛。女演员帕特里霞·麦克布莱德在该团表演近三十年,二○一四年荣获由奥巴马总统颁发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荣誉奖。
作为杰出的编舞家,巴兰钦的贡献在于用舞蹈来表现古典音乐,体现音乐的内涵, 更要让芭蕾舞在古典音乐伴奏下跳出画境、诗意和情韵。他根据柴科夫斯基音乐编排的芭蕾,如《小夜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组曲》、《钻石》、《活跃的华彩》、《双人舞》和《莫扎特集选》等,都是久演不衰的上乘之作。他也致力于改革芭蕾语言,注重舞蹈形式、肢体技巧,使动作更快捷、强烈,意象比较虚幻、抽象,从而开创了鲜明的美国特色。
一九三七年,纽约第二个芭蕾舞剧团成立,初名莫尔德金芭蕾舞团,后改名为美国芭蕾舞剧院(ABT)。莫尔德金原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演员,十月革命后离开俄国,一九二四年主持《天鹅湖》在美国的首次演出。该剧院初期的重要编舞家、舞蹈家包括杰罗姆·罗宾斯、来自英国的安东尼·图德。主要演员包括俄裔舞蹈家娜塔莉娅·玛卡洛娃、亚历山大·戈东诺夫。俄国独舞演员米哈伊尔·巴里希尼科夫脱离彼得堡基洛夫芭蕾舞团之后也加入该剧院,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该剧院艺术指导。二○○八至二○一四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前艺术指导阿列克赛·拉特曼斯基担任该剧院首位驻院艺术家。如今该剧院主要演员来自好几个国家,除美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阿根廷、古巴、巴西和韩国。二○○六年,美国国会宣布该剧院为“美国国家芭蕾舞团”。
NYCB和ABT这两个芭蕾舞团的历史,显示了美国芭蕾的渊源、所受俄罗斯芭蕾的影响,也显示了美国芭蕾对俄罗斯音乐和芭蕾的传承和光大。纽约人对俄国两大芭蕾舞团因此也情有独钟,经常邀请彼得堡基洛夫芭蕾舞团(也常用原名“马林斯基”)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简称“大芭蕾”)前来纽约演出,并详加报道、评论。圣彼得堡的埃尔夫曼芭蕾舞团也受到纽约人欢迎,该团带来的剧目不一般,如有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有用柴科夫斯基音乐编排的《柴科夫斯基》。
有一次,大芭蕾带来四部大型舞剧:《堂吉诃德》、《斯巴达克斯》、《法老女儿》和《明亮小河》。首席明星斯维特拉娜·扎哈洛娃既演《堂吉诃德》中的吉特莉,又演《法老女儿》中的阿斯皮霞,一个是西班牙女郎,一个是古埃及国王之女,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舞姿, 她以多姿多彩、爐火纯青的技巧跳得活灵活现。《斯巴达克斯》由哈恰图良作曲,大芭蕾三十年的艺术指导格利戈罗维奇编舞,笔者曾去观看,觉得斯巴达克斯的几段独舞相当感人,舞剧结尾极为悲壮:先是奴隶主官兵的许多根长矛把斯巴达克斯的尸体戳起来,聚光灯打在矛头密密顶刺的尸体上,四周一片黑暗;后来是奴隶和牧羊人的手臂把斯巴达克斯的遗体举起来,聚光灯打在很多很多手臂高高托举的遗体上,四周是黑暗一片,全场先是持久的静默,然后是持久的掌声,来自莫斯科的芭蕾艺术家们向纽约观众一次又一次谢幕。
纽约观众喜欢把NYCB和ABT作比较,也喜欢对比“马林斯基”和“大芭蕾”。这四个芭蕾舞团各有不同的创作方向、保留剧目和表演风格,互相竞争,也互相借鉴,甚至演员也互相流动。马林斯基有更多典雅的贵族气派,对十九世纪古典芭蕾作品精益求精,现在也排演很多巴兰钦作品;大芭蕾则有率真奔放的气质,以演出专为该团创作的作品为主。NYCB发扬巴兰钦的创作传统,仍然保持用舞蹈表现古典音乐作品的特色;ABT既重視古典芭蕾舞剧的演出,也不断邀请著名编舞家、作曲家创作新作品。
巴兰钦与俄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合作,也许可进一步说明美国芭蕾与俄国音乐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兰钦与斯特拉文斯基就于巴黎由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创办人狄亚基列夫(一译佳吉列夫)撮合认识,并于一九二八年联合创作芭蕾舞《阿波罗》,初次搭档即成功,给两人留下了难忘印象。一九三九年斯特拉文斯基移居美国后,便与巴兰钦在纽约进一步合作,创作了《三乐章交响乐》、《奥尔菲斯》、《阿贡》等名作。
评论家们在分析其合作成功的原因时指出,首先,他们俩各自在舞蹈和音乐上都是行家里手。巴兰钦,作为舞蹈家,爱上舞蹈之前先已爱上音乐,他父亲是作曲家,他五岁时父亲就开始要他学钢琴,少儿时代在圣彼得堡帝国芭蕾舞学校上完八年学之后,又去国家音乐学院修读钢琴、音乐理论和作曲法。而斯特拉文斯基,作为音乐家,很早就熟悉芭蕾舞,因为他父亲是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剧演员,所以他常去剧院看芭蕾演出,欣赏芭蕾之美。后于一九○九至一九一三年期间,他在巴黎与俄罗斯芭蕾舞团合作,成功地创作了三部芭蕾经典作品:《火鸟》、《彼得卢什卡》和《春之祭》,既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又有强烈的原始表现主义色彩。他自己也爱跳舞,熟悉芭蕾舞步,在纽约参加舞团排练时,常向巴兰钦和演员们示范他自己构想的动作。
在创作手法上,巴兰钦和斯特拉文斯基不谋而合,两人都重视舞蹈和音乐结构的严密、精致,注意两者在空间和时间、速度和力度上的均衡,不以舞蹈“压倒”或“遮掩”音乐,也不让音乐喧宾夺主超越其背景伴奏作用。巴兰钦的“宁少勿多”的编舞原则恰恰适合于斯特拉文斯基的往往是错综复杂而又完美无瑕的音乐。两人长期愉快合作,成了终生朋友。一九七一年斯特拉文斯基病逝,翌年,巴兰钦举办“纽约市芭蕾舞团斯特拉文斯基节”,演出了他和作曲家合作的芭蕾作品:《小提琴协奏曲》、《二重奏》和《三乐章交响乐》。
巴兰钦,这位纽约舞蹈界大名鼎鼎的“B先生”,根据其自己的以及与作曲家合作的经验,对芭蕾舞作了如下通俗概括:
芭蕾把我们的自然冲力调动起来,形成姿势,使我们自己尽可能的优美、高雅,变成某种全然不同的状态。芭蕾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十分熟悉的动作—跑和跳,举和抱,旋转和平衡—以及由这些动作形成的姿态变为令人欣赏的景观。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旋律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自然杂音—撞门声,溪流声,林间风声—很不一样。旋律是人工的,由人创作的。芭蕾也同样是人工的;其根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芭蕾从生活中摄取东西,并变换其形式。
纽约市芭蕾舞团十分重视这一高雅艺术的普及工作,每次演出都要向观众散发有关知识的材料。如有一份《芭蕾艺术》就包括很多内容:芭蕾舞历史(起初是一种男性舞蹈,故现有男子版《天鹅湖》就不足为奇),芭蕾艺术风格(轻盈、舒缓、优雅),脚部五个基本位置,三种基本舞姿(其中“阿拉贝斯克”类似金鸡独立),脚尖艺术的形成(19世纪初芭蕾演员开始以脚尖点地),尖头舞鞋的制作(NYCB的54名芭蕾演员一年要用12,000双舞鞋),独舞的直立、踢腿、跳跃和旋转动作,双人舞的扶持和托举,芭蕾演员练功的艰辛,等等。笔者读此材料时,不禁想起俄罗斯芭蕾舞艺术家乌兰诺娃说过的话:“芭蕾是美的艺术,也是青春的艺术”,又是“一门严酷的艺术,要求付出最艰苦的体力劳动”,“舞蹈演员的身体天生就是用来表现人的心灵活动的唯一的乐器”。她在自己的记事本上除了记下演出剧目、日期和合作者名字外,也常写道:“脚疼。”
美好而艰辛的脚尖艺术始终吸引着一代代新人。在纽约有好多所芭蕾舞学校,有专业的,也有课余的,不论白人、黑人或亚裔,许多家长都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让他(她)们小小年纪就开始在大镜子前扶着把杆学练芭蕾语言。NYCB的学校名“纽约市芭蕾舞学校”,ABT舞校以已故总统夫人的名字“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命名。纽约大学有附属舞蹈学院。朱利亚音乐学院舞蹈系设有芭蕾舞专业。纽约以前的另一个重要舞团—成立于一九五六年的乔弗莱芭蕾舞团,一九九五年迁往芝加哥后在纽约保留其舞校。
乔弗莱芭蕾舞团原在纽约与ABT、NYCB平起平坐,如今在美国中西部独占鳌头。在全国许多城市,如亚特兰大、旧金山、波士顿、代顿、塔尔萨、明尼阿波利斯、费城、密尔沃基、盐湖城,都有处于显赫地位的芭蕾舞团。
所谓“脚尖舞”的艰难、辛劳,其实不仅仅表现在芭蕾演员们要付出“最艰巨的体力劳动”,而且也体现在社会不断商业化、文艺不断通俗化和娱乐化为这门高雅艺术造成的困境。从这一点上来说,纽约有愧于芭蕾,华尔街有愧于百老汇,当政府和大公司缺乏责任感,不扶持严肃艺术,不多赞助高雅文艺团体的时候,编舞和跳舞的艺术家们只能感到失望和沮丧。美国芭蕾舞剧院有一阵子就不得不采取许多措施来解决财务困难:裁员,冻结工资,放无薪假,取消开销大的节日外地演出,等等。《纽约时报》报道说:“整个舞蹈界在为钱而挣扎,许多团体常生活在厄境。”
有才华、有闯劲的艺术家往往能在厄境中闯出自己的路来。如今在美国舞蹈界享有卓著声誉的人当中,米哈伊尔·巴里希尼科夫是格外引人瞩目的一个。
巴里希尼科夫一九四八年生于拉脱维亚里加一个俄罗斯家庭,少年时代显露舞蹈天才,在国际芭蕾比赛中获奖,不到二十岁就加入基洛夫芭蕾舞团,在《吉赛尔》中最先跳农民双人舞,后演主角阿尔贝特伯爵。《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家巴恩斯当时看了演出就说:“ 他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最完美的舞蹈家。”但巴里希尼科夫不满足于当时苏联文艺界墨守成规的保守气氛,渴望能与更多有创意的艺术家合作,一九七四年在随基洛夫芭蕾舞团到加拿大演出时“叛逃”,先加入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团,后很快移居纽约,先任美国芭蕾舞剧院主演,后任纽约市芭蕾舞团主演(B先生破例接受了他这个客座艺术家),八十年代则一直担任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艺术指导。
巴里希尼科夫是一个善于虚心学习、吸取新事物的艺术家。他曾与许多不同风格的编舞家和导演合作,不论成败都很高兴,他说:“每个芭蕾成功与否并不重要,新经验总使我受益匪浅。”如通过与黑人舞蹈家、编舞家阿尔文·艾利合作,他学到了不少把古典舞蹈技巧与现代舞技巧结合起来的经验, 所以他后来一直兼任芭蕾舞和现代舞编导和演员。作为演员,他以舞蹈为生命,到国内外四处频繁演出,人到中年一直在跳,年逾六旬仍然在跳。年纪老了,腿可能踢不高了,对此,他说:“你的腿能踢多高,这并不重要,舞技要求的是清晰、简朴和真挚。”他德艺双馨,频频得奖,受人爱慕,还被邀请演戏演电影,成了影戏明星。他当年滞留美国的新闻,像一九六一年鲁道夫·努里耶夫(他被视为俄国继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之后的芭蕾“超星”)叛离基洛夫芭蕾舞团时一样引起轰动效应,但两人走了不同的路。努里耶夫后来主要活跃在欧洲,曾任巴黎歌剧芭蕾剧院编导,一九九三年因艾滋病逝世,因曾主演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有人痛惜地称他为“被毒死的彼得鲁什卡”。
为进一步开拓舞蹈事业,为让更多艺术爱好者有更多机会欣赏艺术,巴里希尼科夫通过其基金会于一九九○年在佛罗里达创办白橡树舞蹈团,二○○五年在纽约建成巴里希尼科夫艺术中心(BAC),并开办舞团,因其所在地旧名“地狱厨房”,这个舞团也就起名为“地狱厨房舞蹈团”,演员大多来自朱利亚音乐学院舞蹈系和纽约大学舞蹈学院。对巴里希尼科夫来说,地狱厨房其实是天堂舞厅,在其高雅的艺术殿堂里,他和他的舞伴和学生们翩然起舞,显示着生命的活力,体现着真善美的魅力。
巴里希尼科夫艺术中心拥有各类艺术所需要的场所:剧场、舞厅、 音乐厅、电影院和美术馆,总面积五万平方英尺,现已是纽约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之一,吸引成千上万人去唱歌跳舞,去观剧听乐,去欢度快活而有意义的业余、课余和退休生活。
社会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十分钦佩巴里希尼科夫为美国艺术事业作出的贡献。她曾于二○○三年采访他,支持他在纽约建艺术中心的计划,称赞这个计划“勇敢、重大而必需”,因為她觉得,这样的计划在纽约常被认为既无意义也无可能,因而遭冷嘲热讽,遭泼冷水。可惜她第二年病逝,未能见到最后竣工落成的巴里希尼科夫艺术中心。
桑塔格在采访时对巴里希尼科夫说:“我说你的计划是勇敢的,指的是你敢于挑战那种广泛传布的感觉,似乎真正的好东西、一种文化性质的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纽约是不可能产生的。在这儿,生意经,官僚作风,没兴趣,或仅仅是老一套的风凉话,就可以抹杀一个理念。当然,说这种话的人也为现状感叹,所以我想,要证明那些风凉话是错误的,要创建你的艺术中心那样的东西,对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嗤之以鼻,这实在令人高兴。”
巴里希尼科夫答道:“你知道,人们现在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不懈。”
桑塔格说:“对,只要你坚持做下去,这就已经几乎是乌托邦了。”
巴里希尼科夫说:“纽约是美国城市中最具世界性的,应该也能够吸引和发现在此出现的天才。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把他们送给那些有能力、也更慷慨资助艺术的国家,而每失去一个艺术家,我们城市的精神生活就变得更可怜。就如一个人,一个没有艺术的城市也是很可悲的。”
纽约与芭蕾,纽约与艺术,不就因为有了巴兰钦、巴里希尼科夫这样的芭蕾舞艺术家而联系得更紧密,成为更合适、更令人心旷神怡的搭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