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狱与江湖
李庆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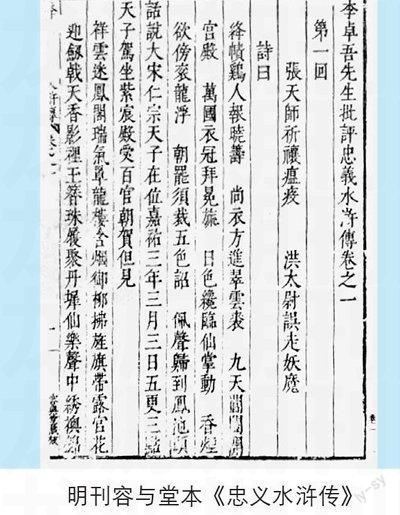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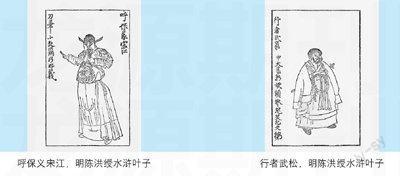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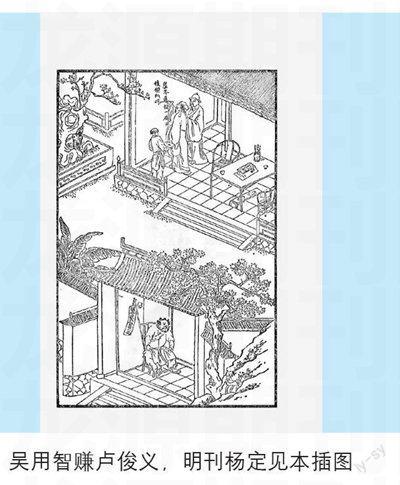
《水浒》一书中,牢狱是一个重要场景,书中最重要的个人叙事几乎都包含一段牢狱经历,像林冲、杨志、武松、宋江、戴宗、解珍、解宝、雷横、关仝、柴进、史进、鲁智深、卢俊义、石秀这些梁山好汉都先后身陷囹圄,权力法网中的挣扎无疑生成意味无穷的叙述张力。其实,黄泥岗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七人本来也难逃牢狱之灾,是宋江及时通风报信才得以走脱。其中唯独白胜遭厄,那是之前就被拿在济州大牢里了。白胜之被捕,恰恰凸显《水浒》语境中的法网森严。
书中第十八回,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领命往郓城县侦破生辰纲一案,最初获得的线索虽说有其偶然性,却是一种必然结果。谓之偶然,是何涛偏巧有个赌徒弟弟何清,因筹措赌资在城外客店意外发现案犯踪迹。其必然之由,则是官方颁行的旅店入住登记制度,早已布设了一张大网。书中藉何清之口有详细交代:
为是官府行下书文来,着落本村,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要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哪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
何清曾替店家填写旅客登记簿册,记得六月初三来了七个推着江州车儿的客人,自称从濠州来贩枣子,为首却是东溪村晁保正,这未免让他心生疑窦。次日与店主去村里赌博,又遇担桶过路的白胜……这些线索拼凑到一起,成为何涛侦案的突破口。如此详尽的旅客登记备案,辅以群众专政的“首告”律例,完全不输于现代社会的治安/反恐监控机制(所差只是技术设备)。这并非小说家臆构,是熙宁变法以来实行连坐切结的“保甲法”的衍生制度。北宋末年虽是奸佞柄国,整个国家却以申韩之术为治道,各级政府防盗维稳自有妙招。小说中的郓城县实是一个模范典型,为打造平安祥和的法治社会,在奉法循理的知县时文彬治下,俨然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态势。
关仝、雷横二人原是郓城县里专管擒拿贼盗的都头,时文彬上任后连乡村治安也要他们管起来,不许有絲毫懈怠。第十三回写朱、雷夜间带领士兵出城巡逻,时文彬指挥二人出东西二门“分投巡捕”。为防止敷衍塞责,又命往东溪村采撷山上特有的红叶来县里呈纳,以证明确曾巡逻到该处。赤发鬼刘唐来投奔晁盖,夜宿村外灵官寺就被雷横逮住(其实只是“齁齁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如此风声鹤唳,足见防盗反恐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当然,郓城县左近有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加强本地治安力度并不奇怪,可是再看小说其他各处描述,官家的法网绝不止是郓城县格外严密。
譬如第二回中,王进不奈高俅欺压,携母逃离东京,高俅得知,“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官方通缉的惯例是“画影图形,明写乡贯年甲,到处张挂”,简直就像公安部A级通缉令。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如此行开诸州各府,需要调动充足的警力和包括街坊大妈在内的综合治安力量,而书中的描述无疑显示当局法治手腕和执行力。随后第三回中,鲁智深在渭州打死镇关西,逃窜到代州雁门,那十字街口已张挂捉拿他的榜文。第四十三回写李逵上梁山后回沂水搬取老母,行至县城西门外,一簇人正围观捉拿他和宋江、戴宗的布告—如果不是让朱贵拦下,这莽汉“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几乎自投罗网。
伴随着“画影图形”的通缉令,往往是辖区内大范围搜捕。第三十一回中,武松逃出孟州城,在张青家里将息数日。可是眼看风声渐紧,张青只得让武松乔装行脚僧人出逃,去投奔二龙山宝珠寺。有曰:“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排门挨户……”这里所谓“排门挨户”就是拉网式搜索(刑侦术语曰“排查”),至今仍是警方追缉逃犯的常用手段。再看第一百三回,王庆杀了牢城管营,越城而逃,官方即从城里搜到城外,乃至“各处乡保都村,排家搜捉”。王庆后来横行淮西,被受了招安的宋江给灭了,先前亦颇受缧绁之苦。
最倒霉的是宋江,杀惜之后在江湖上东窜西躲已流落大半年,青州村店途遇寄书的石勇,竟误信老爹已殁急急回家奔丧。不料前脚刚进门官军后脚就赶到,“四下里都是火把,团团围住宋家庄,一片声叫道:‘不要走了宋江!”本来,宋太公寄书诓宋江归家,是听说朝廷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以为法网松弛而心存侥幸。这下被逮个正着,结果刺配江州。在江州宋江还另有一劫,就是浔阳楼上题反诗,让黄文炳举发(法网之中更有文网)。由刑事犯搞成政治犯,事情更麻烦,宋江要被押往东京。吴用劫囚车一计不成,后来闹出江州劫法场一幕。其后的情形更见雷霆手腕—第四十二回,宋江上了梁山即回家搬取老父,不料郓城乡下的宋家村已被当地警方监控。他潜入村子伺伏到夜里去敲自家后门,宋清拦住说,“你在江州做了的事,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待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于是,未进家门又被一路追杀。
江州一出事,二千里外的郓城即刻响应,跨区域警务联动机制果然厉害。
决杖,黥面,配役—按《水浒》叙事,这便是判处重犯的固定套餐。比之凌厉的刑侦和缉捕手段,大宋王朝的刑狱之法似乎显得窳败和混乱。通览《宋史·刑法志》记述的种种案例,实在是极度繁琐,且朝三暮四,宽严甚远,鞠狱并无刑名之理。宋初制定折杖之法,流刑犯人以脊杖折抵流徙,配役一年至三年不等(“折杖”之配役通常并不远配);而徒罪只以笞杖解决问题,一般决而不役。但熙宁新政后重施重典,像林冲、武松、宋江、卢俊义、王庆诸案,即便不是发配远恶军州,也在千里以远。不过这几位罪名大抵属于“贷死”(免于杀头的死罪)或“加役流”(流刑中最重之例),其量刑曰轻曰重亦难以分说。
高俅设局制造了林冲误闯白虎堂的冤案,本拟杀头治罪,只因当案孔目有心回护,结果脊杖二十,刺配沧州牢城。这个判决没有给出服刑期限,似乎遇赦才能回家,可是看情形倒未必就是永刑。林冲上路之际,其丈人张教头安慰道:“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老汉家中也颇有些过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锦儿,不拣怎的,三年五载,养赡得他。”所谓“三年五载”并非漫无期限,却是没个准确日子。同样,杨志、武松、宋江、朱仝、卢俊义的刺配也都不提刑期,量刑轻重在于脊杖多少,流配一千里、二千里还是三千里。
林冲“手持利刃,擅入节堂”大不了是“行凶未遂”,而杨志、武松、宋江都确有命案在身。杨志在东京杀了没毛大虫牛二,本来是死罪,因天汉州桥下街坊怜其为民除害都为之申述,办案推司将款状改为因斗殴而“误伤人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开封到大名府不过数百里,从流配距离来看,这桩命案判得最轻。之所以轻判,除了民意求恕,牛二是光棍一条,家里没有“苦主”也是一个因素。
武松是两度被刺配。前一回因杀了西门庆潘金莲,被判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武松杀人轰轰烈烈,搞得很有仪式感,自有街坊同情。县官和府尹念其仗义刚烈,亦将招稿卷宗改得轻了,两条人命都改作斗殴致死,府尹还通过刑部熟人关系保其性命。后一回情形完全不同,武松在孟州被张都监设局陷害,按了盗窃银器的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比之自己上回,比之杨志、宋江等人,想来盗窃银器与杀人行凶未可等量齐观,但判下来的结果亦庶几相埒。孟州的轻罪重判自有原因:一则他已有罪在身,属于“罪上加罪”;二则是张都监那一干人要把他往死里整。如果不是施恩使着银子上下打点,当案孔目有意回护,很可能定为死罪。其实,那时盗窃亦是重罪,唐末五代对此罪量刑尤为苛峻,宋初趋向宽弛,但太宗时定下的规矩是“(窃盗)十贯以上乃死”(《宋史·刑法一》)。张都监往武松的柳藤箱子里塞入的“赃物”足以抵得一二百两银子,让他死上十回也够了。这样掂量过来,武松发配到恩州倒是轻判。
宋江一案也是知县和府尹做了手脚。不但是因为他名声好,满县人都替他去说情,而且宋太公不断往衙门里赍送银两,金钱更是左右司法之力。因而,知县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依准他“误杀”的招供,案情背后一切都未予追究。脊杖二十,刺配江州,对宋江来说已是最好的结果—他老爹说,“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鱼米之乡,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作为从轻量刑之依据,“误杀”自然是最好的托词。不论从当日人情或是司法角度看,武松杀西门庆潘金莲是为兄报仇,楊志杀牛二自有为民除害之社会效果,都有可宽宥之理。但宋江杀惜就没有这些说道,因为被害人并非十恶不赦。实情是那婆惜捏着晁盖书信大肆要挟,弄得宋江一时杀心顿起,此中原委只是不能拿到衙门里去说—暗通梁山泊本身就“担着血海也似干系”,透露出去更是个死。
人家为兄报仇、为民除害,都有社会认可的正当性,但宋江的正义性恰恰不能言诸于理,只能编造一个“误杀”的理由。这无疑生出一个悖离的命题:一方面是与官方法理相对立的江湖道义,一方面是竭力掩盖案情真相的弥天大谎。后来浔阳楼“题反诗”被押在牢里,宋江又企图以装疯规避法网。面对国家伦理与司法体制,正义或道义只能包裹在谎言之中,这种叙事策略之合法性在于一个是非颠倒的现实语境,也就是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所谓“冠屦倒施”之义。所以,宋江手刃一个弱女子(尽管刁钻泼辣,也还是个弱女子),却并不有损其仁义形象,因为许多道理都要倒过来看。所以,在《水浒》语境中,谎言是恪守道义,造反是忠君报国。
所有这些卷入官司的好汉中,最无辜的是卢俊义。他被吴用施计赚上梁山,虽不肯落草却被管家李固告了官府,一回到北京就落入囹圄。卢俊义的冤案是梁山/官府/奸人三方共谋与互动的结果。宋江、吴用是想断其后路,逼他上山,这是利用法网广开江湖之门。李固是想让卢俊义死,买通押狱要在牢里动手。岂料柴进花更大价钱搞定上下关节,留得卢俊义性命,判了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这量刑竟比林冲、杨志、武松、宋江等人都要重,只因为牵扯到梁山敌对势力,便成了弥天大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么说,没掉脑袋已属轻判—后来押解途中燕青救主未成,官府拿获卢俊义便要当街开斩(这又引出石秀劫法场和众好汉攻打大名府,自是后话)。
从林冲到卢俊义,这一系列官司案牍书写了“逼上梁山”的完整注脚。
无论轻判还是重判,《水浒》诸案无一例外都以刺配处置,总须留下当事人性命—小说中这些重要人物自然不能过早出局,人家后边还有戏码。
但是不杀头并不等于真的是从轻发落,毕竟远途流配本身就是极为严酷的刑役。至于其法之酷烈,《宋史·刑法一》有称“道路非理死者十恒六七”。卢俊义被流配沙门岛(今山东长岛县大黑山岛),其实就跟死刑相差无几,按《刑法三》说法:“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沙门岛所能收纳的囚犯有限,岛上以“逐旋去除”的办法控制数额,如嘉祐间京东转运使王举元呈报:“登州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如计每年配到三百人,十年约有三千人,内除一分死亡,合有二千人见管,今只及一百八十人。”可见抵达岛上也只是缓期的死刑。所谓“逐旋去除”,据说是将超额的活人扔进海中,如宋人周《清波杂志》卷二:“旧制:沙门岛黥卒溢额,取一人投于海。”
即便是九死一生,徙配的判处仍不能让高俅、张都监、李固这些人放心,所以他们都买通差人在途中动手。这种私刑几乎也成了国家司法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漫长的押解路途确实提供了买凶害命的便利,但反过来说也是逃脱或获救的机会。林冲在野猪林几乎丧命于董超薛霸的水火棍,却让鲁智深给救下;武松配往恩州,途中不等差人动手就先把对方给干了。流徙之途是牢狱与江湖的双重空间,难免出现搅局和翻盘。
进入流配程序意味着法治权力的多元化。董超薛霸既代表国家法度,又兼营黑道勾当,这是体制与体制衍生功能之集合。可是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开始,董薛之辈已被解除权力,流徙者的命运逐渐由另一种力量所掌控。宋江解往江州途中,经过梁山泊被晁盖款留一日,虽不肯上山入伙,实际上已是人在江湖。此后的行程跌宕起伏,真正将宋江抛入杀人越货的山林草泽。揭阳岭上在李立店里险遭暗算,揭阳镇上被穆家兄弟追杀,浔阳江上又遇张横打劫……这一路步步惊心,又是步步逢凶化险。宋江此际尚不肯出来混,却有另一种力量将他推上老大的位置,那就是江湖上人称“及时雨”的美誉,这名声就是一种道义,托付着救赎的责任。因而在抵达江州之前,宋江已将道上的散兵游勇整合规饬,如李俊、李立、童威、童猛、薛永、张横、穆弘、穆春等人纷纷投其麾下,还有后来结交的戴宗、李逵和张顺。
其时梁山势力已经渗入江州牢城,戴宗就是吴用的眼线。
经过艰难困顿的长途跋涉,只有少数犯人能够抵达指定的刑役地—牢城。
书中先后出现的沧州、孟州、江州和陕州牢城,就是宋代流配罪犯的囚禁之地。所谓牢城,亦称牢城营,是宋代厢军之一种。沿五代之制,宋代流配犯人通常编入军伍,故曰“充军”。《宋史·兵志三》所列“熙宁以后之制”,厢军建制中就有“牢城”一目,在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淮南、江南、荆湖、广南、四川等各路诸州均有设置(惟两浙路和福建路不设牢城)。可以说,这是一种混合牢狱与军营性质的管制方式。
观察《水浒》人物的牢城生活,那里边似乎不像是监狱模样,至少是监管松懈。林冲被安排在天王堂内烧香扫地,行动并不受限。宋江进了抄事房做文书工作,重操胥吏本业,时不时还跑去江州街衢酒肆消遣。武松在孟州牢城的待遇显然更好,因为管营的施家父子看上他的好身手,要用他对付蒋门神。当然,别的犯人并非都有这份待遇,林冲和宋江是用银子买通了人情。差拨得了林冲的银子便来向他卖好,“你看别的囚徒,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拨他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第九回)
武松每日被好吃好喝伺候着,竟纳闷别的囚徒为何不像他这么自在—
武松那日早饭罢,行出寨里来闲走,只见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担水的,劈柴的,做杂工的,却在晴日头里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这热。武松却背叉着手,问道:“你们却如何在这日头里做工?”众囚徒都笑起来,回说道:“好汉,你自不知,我们拨在这里做生活时,便是人间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热坐地?还别有那没人情的,将去锁在大牢里,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铁链锁着,也要过哩!”(第二十八回)
根据这里描述的情形,牢城大抵就是一种劳改营,囚犯中各色人等待遇不一。有的在露天里做苦役,有的被关在土牢里,像林冲、武松、宋江这样的大概只是少数。还有,王庆在陕州牢城也能自在出入,那是龚正替他贿赂了管营。不过,王庆在里边过得相当窝囊,姓张的管营每日差他买办食用供应,却不支付现银,他赊不了账,回来只能挨打(两腿都打烂了)。不堪欺凌的王庆后来将管营给杀了,就在人家内宅门口下手,这情形差似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犯人能有行凶之便,自然是有其活动空间。王庆的凶器是一把解手尖刀(如今应是管制刀具),当初林冲杀陆虞候也是用的这家什—都是从街上买的。
林冲、武松、宋江还有王庆,能够自在出入牢城,自然是为了铺展故事的需要。不过书中对此有充分提示—林冲是有柴大官人照应,武松被施恩认作兄弟;宋江更有戴宗等人维护(背后有梁山泊)。唯独王庆没有强势后援,好歹不受人身限制。应该说这些都是个例,但文学偏是以个例吸引读者眼球。林冲、武松复仇行义也好,宋江酒后孟浪也好,以及王庆窬墙的月黑之夜,真是大开大阖而扣人心弦。所以,事情难免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好像牢城不存在强制性的封闭管制。
也许,套用福柯的说法,牢城真正是一种“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尽管这不是边沁设计的那种带有中心瞭望塔的环形建筑,似乎也缺乏监视功能—在这里金钱与人情往往模糊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界限。然而,就活动空间而言,《水浒》描述的牢城很像是福柯所讲到的规训体制的普及状态,即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三章)。
其实,即便不是强制性的封闭管制,也并非不存在规训与纪律。譬如,林冲在野猪林遇救时就能逃脱,却依然载饥载渴远赴沧州服刑,而武松和宋江也是甘愿伏法。原本谁也没有想利用出入方便逃脱司法制裁,如果不是陆虞候、张都监、张管营们非要置人于死地,林冲、武松、王庆们绝不会反抗与逃逸。《水浒》没有越狱的故事,倒是有梁山泊两度劫法场,一次是江州救宋江,一次是大名府救卢俊义,而宋江和卢俊义恰恰是最不愿意与国家体制对抗的恂恂之士。宋江是“自幼熟读经史”,包括忠义节孝在内的一整套儒家祖训正是其日常功课,早已成为内心之戒律。当初宋江被押往江州时,他老爹千叮万嘱:“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这类细节足以说明,规训体制并不仅限于权力与牢狱,很大程度上依仗于乡绅、宗祠、村塾、乡规乡约和保甲制度所行使的职能。从《水浒》叙事中可以看出,十二世纪的大宋王朝已经形成“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而福柯认为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才进入所谓的“规训社会”。
韩非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诚是法治精髓之义。
不管怎么说,《水浒》描述的牢城显然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叙事要求,也带有隐喻性的暗示:牢城不一定就是实体的集中营,其边际模糊,形廓不定,可以无限普遍化而无限延伸,甚至江湖草泽亦在其覆盖之中。
宋代是否没有封闭式监狱,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水浒》书中经常出现“收在监内”、“押在牢里”的言语,是指衙门临时监押未决犯人的牢房(犹似看守所),而长期服刑的犯人通常是远途押送至某地牢城。不过,《宋史·刑法三》提到神宗时一项狱政改革方案:
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道路有奔亡之虑。苏颂元丰中尝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则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时未果行。崇宁中,始从蔡京之请,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行之二年,其法不便,乃罢。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
苏颂元丰初曾权知开封府,断狱聪察,吏治精敏。他动议设置的“圜土”,就是古时的监狱。《周礼·地官》:“比长各掌其比之治。……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郑玄注:“圜土者,狱城也。”《释名·释宫室》:“狱,确也。……又谓之圜土,土筑表墙,其形圜也。”很难说这种圜形监狱是否具有“全景敞视”功能,但相比牢城,显然是一种封闭式监管。此法后来两度施行两度罢置,所谓“其法不便”,似乎难以解释。在州府本地设置监狱,至少比远途流配便于操作,又大大节省司法成本(《水浒》中押送一个流配犯人须两名差人,司法成本更是离谱)。也许弃置“圜土”的真正原因是规训机制已经无限扩展,而且治安權力已经渗透整个社会机体。既然全体国民已处于自律和互相监控状态,封闭的监狱自然意义不大。刺配一千里、二千里或是三千里,更使司法的规训与惩罚获得广袤的空间意义,这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注解。
开放式(或是半开放式)的牢城何以不怕囚犯逃逸,除了全社会的监控网络之外,也有另一种技术手段作为保证,那就是刺配犯人都有黥面印记。黥面又称“金印”—第八回中说:“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不过所刺并非金色字样,而是涅以黑色。金印本指官府之印,这是表示官府的判决。黥面之法古已有之,但作为防止逃逸的手段,大约缘自五代军营。苏洵《兵制》有谓:“及于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因为牢城纳入军伍编制,流配的犯人自须照此办理。洪迈《容斋续笔》卷五“唐虞象刑”条亦称:“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
既是“望而识之”,这种脸上刺字的人就很难在社会上行走。武松去投二龙山时,孙二娘将他打扮成行者模样,就是要使头发遮住脸上的金印。宋江去东京看灯之前,早让神医安道全将其脸上的涅墨都点去了,书中第七十二回于此有详说,其法似亦麻烦。那些黥面者用这种医术去除脸上斑痕的,除了宋江,只是一个王庆。
有趣的是,领命侦破生辰纲一案的何涛脸上也被刺了字,刺了“迭配……州”字样。府尹限时破案,留着空白等候发落(其实府尹知道自己脸上同样留着空白,若此案不破,“我非止罢官,必陷我投沙门岛走一遭”)。可见警匪一体,陷于无限普遍化之法网。
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山泊也是一处“全景敞视”的牢城,这里聚集了林林总总的逆法之徒。梁山众多好汉最生动的叙事皆纠缠于“罪”与“罚”,或是“义”与“法”。其中有林冲、卢俊义这样的冤主,有鲁智深、武松一类以暴制恶的行义者,更有宋江、柴进、花荣、朱仝、雷横诸辈甘为江湖道义而徇情枉法。如果说晁盖等人是以不法手段取不义之财,那么也有不少人干着毫无道义的犯罪勾当,像李立、张横、张青孙二娘夫妇这些人平日里就专事杀人越货。所有这些戴罪之身集于山寨,起初只是逃避官方缉捕。山寨里虽说尽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后来亦有“替天行道”的精神自慰,却是困于一个封闭的乌托邦。
宋江决意要去东京赏灯的时候,他内心的躁动流露着重返社会的渴念。自上山以来,宋江一直申明“权居水泊,专等招安”,是要给弟兄们指一个方向。他深怀救赎的心愿,要为弟兄们寻找一条体面的出路。诚然,宋江的“替天行道”可以说是一个行动纲领,是对官僚体制(不是皇帝)合法性的否定,更是申明重建伦理秩序的政治诉求。可是,宋江并没有任何改造社会的新思维,就连改朝换代之念亦丝毫不存。结果“替天行道”成了“替天子行道”,实际上则是苟且于官僚体制。他与体制的合作非但不能改变任何官场积弊,而回到王道秩序还必将消解自身的合法性。譬如招安之后,梁山大军奉诏伐辽,中书省派员在陈桥驿发放酒肉,那些谗佞之徒依然克减朝廷恩赏,结果惹怒了项充、李衮手下一个军校,把那厢官给杀了。这样的反抗,本是梁山聚义的合法性所在,但此时回到法治轨道的宋江已不能容忍部下的“旧时性格”。
“陈桥驿”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地名。当年赵匡胤正是在此发动兵变,而有大宋三百年江山;现在宋江却于此地挥泪斩小校,且将自己的队伍带入无边的牢狱之国。
中国小说中講述司法公案和民间造反(教科书多谬称“农民起义”)之事,以《水浒》一书最为出色,所描述江湖势力也最浩大。书中以北宋末年为背景,跟实际历史情况形成有趣的反差,真实的宋江和方腊都不成大气候,远远不逮陈胜吴广、黄巢、红巾、李自成和太平天国,甚至不抵绿林、赤眉、瓦岗一类。说来大宋王朝“攘外”不行,“安内”却很有一套,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唯一未由内乱导致垮台的王朝,即如两晋藩王门阀之乱亦不曾有过。这就让人奇怪,文学叙事中声势最大的民间造反竟来自一个相对和谐社会的历史原型。
文学未必是现实的直观反映。旧籍中“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之说,只是语焉不详的虚夸之辞,而小说将梁山军事力量极度夸大,这使得反抗的意义在接受层面上又被无限放大。可是如果忽略了《水浒》的救赎之道,实在不能解读作品真义。反抗,在这里首先要联系个体命运去理解,整个官场腐败不等于全社会已是干柴烈火。其实,这部小说并未着意描述民间疾苦,反倒不时渲染民丰物阜、祥和安定的社会景况(仅宋江元宵赏灯就写了三次:清风寨、大名府和东京),这种《清明上河图》式的画境不能说是有意粉饰太平,“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胜市井何尝不是王道秩序和规训机制的肌理与织体;而从另一方面看,如此描绘跟江湖社会相对应的生活之景,亦恰恰映衬着局外人的悲凉。作为一种“反抗—绝望”的叙事模式,《水浒》是以不能实现的救赎表达中国人陷于心狱的心灵挣扎。
小说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隐喻,后来凑齐一百零八将的石碣天书又将他们一网打尽—不管他们是星宿还是妖魔。这个类似犹太传说的所罗门瓶子的故事,以幽扃者的双重身份,在聚散交替中暗示中国人的精神轮回。
谁还记得,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三句口号(就写在真理部大楼外墙上)?其中“自由就是奴役”一句用于《水浒》最是契合。或者,不妨另外结撰两句,凑成“替天行道”的联句口诀—
造反就是忠君
江湖就是牢狱
自由就是奴役
写于二○一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