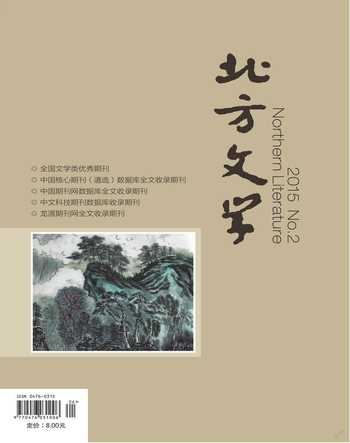浅析鲁迅的父亲情结与创作心态
摘 要:“父亲情结”贯穿鲁迅一生,他对父亲既爱又恨,父亲去世等童年遭遇影响到创作心态,坚定了他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决心,使得“父亲”这一意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父亲情结;创作心态
在鲁迅的文本中,“父亲”是一个若即若离的话题,他很少在作品中涉及自己父亲,却有意无意塑造出形貌不一的父亲形象,并承担起不同的文化内涵。究竟是怎样的童年历程导致了他言而半隐的叙述策略,影响到他的创作心态?
鲁迅出生于绍兴一个封建大家族,童年时其父周伯宜卧病不起,身为长子的他每天出入于药铺与当铺之间,为父亲的身体操劳,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然而父亲还是离去了,享年36岁。丧父之后家道衰败让幼小的鲁迅饱受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于是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早年丧父的经历对鲁迅后来的创作道路影响很大,成为他观照传统文化的窗口。他的作品中充满对父亲矛盾的情感:既爱也憎,既敬又怕。
鲁迅对父亲的爱主要定位于血缘关系的父子之爱,在《我的种痘》(1933年8月1日上海《文学》月刊)中他就曾写道:
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
时隔近50年,鲁迅在回忆起他最初的种痘经历时仍然历历在目,而父亲送他的万花筒也成为他心爱的玩物。在洋文化初传中国,遭受国人抵制的那个时代,敢为风气之先率先为爱子种痘的父亲,思想之开明舐犊之情深,也可见一斑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也构成了鲁迅对父回忆中相对温暖的场景,“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须到长庆寺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
然而鲁迅表达对父亲喜爱的文字较少,更多的是对父亲的批判。在鲁迅的文化体系中父亲是父权文化的代表,要进行国民性批判就要反抗父亲权威,而这一切是从对自己父亲的批判开始的,收录于《朝花夕拾》中的《五猖会》,写出了鲁迅的父亲专制保守不近人情的一面: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逛庙会事件反映出父子态度差异,父亲浸染封建传统文化,他与鲁迅形成了尖锐的“父子冲突”,这种代际文化鸿沟的形成是进入现代以来典型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新旧文化的冲突与变革不可避免。当父亲的形象与旧文化相联系起来,就更多的反映出鲁迅对其“父”的憎恶之感,其实鲁迅对父亲的憎,是出于两个立场,两种文化的对立。归根到底,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抗在家庭中的体现。
父亲的去世还让他看清了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弊病,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父亲的病》,似乎用更多的笔墨去暗讽为父亲看病的那些昏庸中医,久治未愈的父亲在聆听庸医阐述之后更多的是无奈: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不能医好父亲,甚至不能让他平静地离去,父亲去世就像一个咒语,让鲁迅背负着内疚捱过一生。李欧梵和日本学者竹内好都认为鲁迅的创作是来自某种赎罪感,但鲁迅在事情已过去二十五年以后选取这样一种心理的角度来写,本身就很有意义,说明父亲的病和死一定向青年鲁迅的头脑里带来他儿时世界的全部“黑暗力量”,从而促进了他的心理危机。[2]
鲁迅对父亲的回忆着重在他的疾病上,“久病”和“孱弱”是父亲带给鲁迅最大的印象,而这样的境遇与当时的中国国情不谋而合,封建儒家文化破烂不堪,沦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枷锁,积贫积弱的中国早已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了。
父亲去世对鲁迅创作心态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形成冷峻的性格与文风。因为父亲的病死,鲁迅奔走忙碌,饱受冷眼。他成年之后形成的泼辣犀利的文风,对敌人不留情面的嘲讽谩骂,与年少丧父过早接触社会也有关。那时为救治父亲家庭拮据几乎到了举债无门的地步,仰人鼻息艰难度日。正如鲁迅自己所言:“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3]李长之就看出:“从小康家庭而堕入困顿,当然要受不少的奚落和嘲讽,这也是使鲁迅所受的印象特别深的。在他的作品里,几乎常常是这样的字:奚落,嘲讽,或者是一片哄笑。”[4]
第二,长子心态的形成。鲁迅承担起了父亲去世后家里的重担。对于两个幼弟他亦父亦兄,对于寡母他极尽孝道。正如李欧梵所说,“鲁迅作为家庭的长子,按照习俗,已经被置于一种负有责任的地位,被期望去完成祖、父辈的未竟之志而重振家声。在父亲死去之后,他更等于是充当了两个弟弟的年轻父亲角色。”[5]而孤儿寡母在宗法家族中被边缘化,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鲁迅在父亲去世后便遭到了族人的排挤,“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6]这样的人生体验让他看清人生的真面貌,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人生阅历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等多方面支撑。
第三,洞察到包括中医在内的封建文化的虚伪与脆弱。鲁迅在对父亡的沉痛反思中把目光射向整个中国,由想医好父亲的病扩大至去医好国民的苦痛。鲁迅的学医经历也与父亲疾病和死亡的深刻记忆有关,1904年鲁迅前往仙台学医,学医的目的很耐人寻味:“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7]而“幻灯片事件”则更让他清醒,“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8]。这深深刺伤了鲁迅的心,他痛感国民性的愚昧,精神上的疗救比身体上的要来得更紧迫,愤而弃医从文,从医治人的肉体走向医治人的精神。
第四,文本中“疾病”隐喻的大量出现。鲁迅作品中某些作为核心情节的“病”的描写,这些都间接或直接地跟父亲的肺病扯上关系。《药》中对华小栓的描写就是对“肺痨”的独特表述“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洋文的‘八‘字”,“两手按住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吃的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明天》中的宝儿“绯红里带一点青,热,气喘”也是肺炎的症状。《弟兄》中的弟弟是“猩红热”,它极易引起肺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到一个多月前,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后来就躺倒了;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也有人说有些生痨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由此可知,仍然是肺痨。并不是鲁迅偏爱肺病,而是父亲的病和年少的记忆对他影响太深,在文字上找到了排遣的出口,对中医的厌恶、对父亡的执着、对生死的叩问,潜意识里已融化为情感体验和创作素材。
对鲁迅来说,“父亲”是一个充满痛苦与依恋、悲伤又排斥的复杂矛盾的意象。无论在价值理性上对父权文化的批判,还是在感性层面上对父亲深沉的思念,父亲情结都无比回避,这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内化为鲁迅的处世哲学,映射在文本中则有更为深沉的表达,并在潜意识中决定了他文本的基本走向,影响到他的创作心态。鲁迅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多从家庭变革入手,这其中鲁迅父亲的影响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8]鲁迅:《呐喊·自序》,漓江出版社,1999.
[2][5]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鲁迅:《父亲的病》,《朝花夕拾》,漓江出版社,2001.
[4]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
[6]林非、刘再复:《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高梦菲(1993-),女,滨州人,鲁东大学文学院2011级本科生;秦彬(1983-),男,五莲人,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