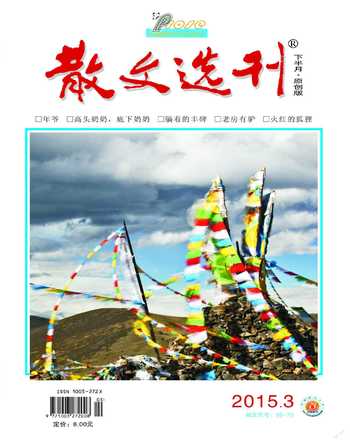我的华容河
王艮庆
一条平平仄仄的小溪白隋唐的斜阳与轻雾中,缓缓走来。
小溪来自湘鄂边界的桃花山中,挟带远古的体温与千秋万代的梦想,挟带呛人的硝烟与春夏秋冬的暗伤,挟带遍插两岸红旗切割夜幕的风声与成千上万喉咙撕破冰天雪地的号子……一路走来。
终于有一日,这历经磨难抱成团形成势锁定目标滚滚东流的水啊,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不仅仅属于长江的调弦口,选择了石首与华容与钱粮湖百余华里母性十足的河床。走过五田渡,走过石矶山,在容城玩了一道小小的魔术,再往南走上高桥与轭头湾,往北走珠头山与南堤拐,准时深情约会罐头尖,一起扑向浩浩荡荡的东洞庭与日新月异的年代……
这,就是父老乡亲魂牵梦萦的华容河。
长江宛如奔涌不歇的大动脉,华容河无疑是洞庭原始意义的一条脐带,一条吸天地之精华的通道。长江每朝每代的律动与振荡,总会激起华容河流域甚或洞庭湖区历史的嬗变与生灵的超越。
华容河,岂能忍住深处的青春再次喷发。
虽说,这只是江南最常见的一条河。
这河来自远古的水,饱含着浓浓的墨汁与思想,交汇着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灿烂光辉的基因。
在车轱山遗址流连,与隔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贴面耳语;在章华台遗址驻足,楚灵王及其细腰们忘我地欢愉依稀可辨;谒刘大夏墓与黎淳墓,仿佛目睹两位明朝先贤分别走向兵部尚书与礼部尚书的足迹和背影;至于范蠡西施结伴泛舟、元代美女夭折厚葬、大禹治水过境、岳飞操练水军等神奇美妙的故事,仍于坊间自由自在地发酵与繁衍。
华容河还是一条红色经典之河。你我熟知的蔡协民、何长工、方之中等老一辈革命家,豪饮一口华容河水就背井离乡,头也不回,去追索人类最先进的理想与信念,直至生命画上句号。一些难忘亦根本不应忘记的日子,华容河滩依稀可见抗日的壮烈场景,华容河水依稀可闻醒人头脑的刺鼻血腥。
掬一口,你的魂灵从远古的人文之源踏歌而来。
一条束腰抑或结发的深绿的轻绸。
先前的乌篷船、机帆船、鸭划子、拖驳子、货轮、客轮……早已彻头彻尾消失在沿河的梦中;纤夫的号子、车水的槽歌、渔翁的吆喝、马达的轰鸣、汽笛的嘶叫、捣衣女子水淋淋的嬉笑、龙舟男汉硬邦邦的呐喊……大多已渗透于渐渐抬高的河床;往日人流涌动的东门水码头,古朴热闹的四牌楼,船来船往的潘家拖船道,还有那些有名无名的古渡口古闸口……一一凝成了华容河珍贵的底片及两岸浓浓淡淡的怀想。
大桥,一座一座,举头相望,虹飞两岸。沱江广场、华容道广场、沿河风光带、护城大港风光带、高楼阔街闹市……有点、有线、有面装潢着这条流经古老文明繁华城池的内河。青翠欲滴的黄湖山、马鞍山、牛桊山……一不小心就染绿了深深浅浅的河水与湖水及两岸朦朦胧胧的相思。
于华容河漫长的浸润与精心的呵护中,岸边的城镇一日一日长高了、变靓了,湖乡特色与现代风采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岸边的乡村一日一日褪去了守旧的色泽与理念,墙之白瓦之红或深蓝及农人满脸的红润构成了乡村永远的主色调,谷黄、棉白、豆青、椒红、柳绿、杨翠……以及鸡鸣犬吠、欢声笑语……着实把江南描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华容河,永远年轻的华容河,北纬30度一条不朽的风景线。
貌似温顺的华容河,亦曾发疯地袒露过罪恶与报复的邪念。高洪、干旱、血吸虫、生态污染……企图将两岸的风景屏蔽,企图将两岸的生灵涂炭。
不屈不挠的华容儿女将连年经略华容河的战旗插上了高高的海拔。一眼望不到头的河堤,在锄头土块的博弈中,在扁担肩膀的较量中,在血泪的浇铸中,在日月的见证中,在几十万颗心之期盼之祈祷之自强中,渐高渐壮,渐行渐远。
在华容河温柔舒适的臂弯里,成群结队的纱锭与车轮正大胆放心飞转,忽如成千上万的螺旋桨纷纷着陆异国他乡……一群群红男绿女,或学唱京剧、花鼓戏,或演绎《蚌壳精》《竹马戏》,或同奏《华容夹叶点子》,或齐舞长刀短剑,把喜悦写在脸上,把自信烙在心中,把欢乐献给他人……
华容河,我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