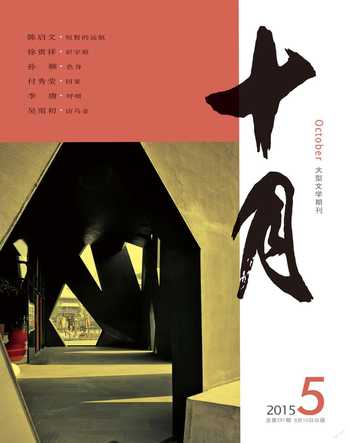回家
付秀莹
一路上,小梨都在跟乃建赌气。
已经下了高速,前头就是滹沱河了。窗外是大片的田野,偶尔夹杂着树木,也不知道是钻天杨,刺槐,还是别的什么树。今年因为闰月的缘故,过年晚了。立春是早就过了。眼看着就要进七九。七九河开,八九燕来。这个时节,地气蒸腾,隐约有一种躁动。空气里也雾蒙蒙的,像是软软的烟霭。麦田里的绿,还有那么一点犹豫,却终究是渐渐明朗起来了。阳光一晃一晃的,在窗玻璃上跳跃,车子里便被弄成了两个世界,一半是明的,一半是暗的。
妞妞塞着耳机听歌,摇头晃脑的。再不像小时候,见了什么都一惊一炸的,尖着嗓子,指给大人看。乃建却慢悠悠的,跟那司机没话找话。反腐啊,环保啊,房价啊,时局啊,说的都是天下大事。听那口气,好像他刚从国务院开完会出来。滔滔不绝的,有时候愤激,有时候无奈,有时候长叹一声,是冷眼热肠的气势,却都是心中有数的。小梨素日里早听惯了,那种语调,叫人不由得就心思走远了,走远了,远到自己也认不出的地方,却忽然又被某一句惊醒了。就像眼下,乃建在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冲着小梨问一句,是不是?嗯?对吧?小梨只是不理他。
乃建也不觉得尴尬,照例是笑眯眯的,跟那司机聊得火热。司机可能是石家庄郊区的,口音挺重。这时候,乃建正跟人家聊着马上就要召开的两会,说起某个大老虎,又笑又叹的,不想那司机冷不丁问了一句,大哥在北京,有房不?乃建愣了一下,有啊。司机仍不死心,多大?乃建迟疑了下,仿佛是有点吃惊,也有点拿不准,半晌才说,还行,凑合住呗。司机却没有追究,只自言自语道,妈的北京那房价,吓死个人。乃建说可不是。过一会儿,司机又问,有车不?乃建说没,没买。北京那交通!司机说噢。就听乃建抱怨起北京的交通来,又顺便谈起了著名的雾霾。小梨正被触痛了心事,气得喉头硬硬的,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本来,小梨是想着借一辆车开回家的。可是大过年的,借人家谁的呢。又想到租,反正租车也方便了,一个电话的事儿,乃建也有本儿,开回去就是了,不过是四五个小时的车程。乃建却不肯。说坐动车多好,要么就高铁。又环保,又省心,何苦呢。小梨听出他话里的意思,气得咬牙道,我就是好面子,怎么着?
转眼已经进了县城了。阳光越发明亮了,照得满街都是红尘扰扰的。路边店铺的招牌一掠而过,叫人来不及细看。街景也是新鲜的,有一点熟悉,更多的是陌生。好像是这么多年的光阴,哗哗哗哗地倒退着,倒退着,倒流河一样。想起来,都恍惚得很。在这个县城,她曾经读过三年书。那时候,是初中,就在城北,附近有一条河,叫作木道沟,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一下车,家门口早有人迎着了。爹立在台阶上,穿着她给买的羽绒袄,烟色绒线帽。姐姐姐夫过来,帮着拿后备厢里的东西。见了妞妞,都说长高了长高了,这一晃。乃建付了车费,打发那司机走了,过来同大家打招呼,又拉住爹的手,问寒问暖,赶着叫爸。爹一辈子没有儿子,哪里经过这个,早被叫晕了,呵呵呵呵地笑着,露出一口白瓷瓷的假牙。乃建今儿个穿了一件铁锈红皮夹克,围着黑色羊毛围巾,皮鞋锃亮,很是扎眼。小梨从旁冷眼看着,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乃建的那一口京片子,平日里觉得顶烦,现在听来,却是十分的顺耳好听。又打量乃建的衣着,觉得还算得上体面,便暗暗后悔,光顾着怄气,倒忘了叫他换上那件新买的衬衣了。
男人们在北屋里喝酒。女人和孩子们在东屋,嗑瓜子,说话。屋子里有暖气,还特意开了空调。暖风薰薰的,吹得人头昏脑涨。妞妞照例是手机不离手,忙着刷微信。大姐慌得给她抓糖不是,抓瓜子不是,抓花生不是。她哪里要这些。地下早已经摆了一张低桌子,大家围坐起来。姐夫和外甥们一趟一趟的,先是冷碟,再是热炒,大鱼大肉,大荤大腥。小梨看着一桌子的七大碟子八大碗,心里不由得怨爹太费事,乃建又不是外人,也不是头一年上门的新女婿,何苦这么费事呢。大姐一个劲儿地往妞妞碗里夹菜,嘴里用芳村话劝着,叫她多吃点多吃点。妞妞也听不懂,只是皱着眉,克制地笑一下,依然埋头玩手机。大姐着急道,你看这。这孩子啥都不吃,你看这。小梨肚子里有气,说甭管她,还是不饿,饿了就吃了。大姐又忙着给小梨夹菜,直把她的碗里堆得小山一样。小梨一面把一只鸡腿夹给旁边的孩子,一面笑道,我又不是且(客),甭光顾着我,你们倒是动筷子呀。
正说话呢,又端来一盘煎饺子。芳村的风俗,娘家大年初一的饺子,是一定要吃的。吃了好。出嫁的闺女回门,这是必上的一样饭食。究竟怎么个好法,小梨也说不清。总之是,命好运好,添福添寿吧。爹撩帘子进来,立在一旁,看着小梨吃饺子。大姐笑道,我说要割羊肉的,爹不让。如今羊肉也是忒贵。转脸跟小梨说,早些年,娘还在的时候,最爱吃羊肉馅儿。小梨见提起娘,忙看了爹一眼。大姐笑道,也怪,我就偏不服那股子味儿。又夹了几个饺子,放进她碗里。
爹摸摸索索的,从兜里摸出几张钱来。一一分派给孩子们。一个孩子二十,妞妞呢,却给了一百。小梨想拦下,却晚了。回头正瞥见外甥媳妇,盯着妞妞手里的票子,脸上似笑非笑。小梨赶忙也掏出压岁钱,给孩子们分。大姐忙笑道,啊呀呀,小孩子家,有这么点意思就行了,给这么多干啥!又低声跟小梨说,傻。都落进人家腰包里啦。拿下巴颏指了指她儿媳妇。小梨就笑。
院子里有人说话,青嫂子撩帘子进来,哎呀一声,叫小梨。小梨赶忙起来给她让座。青嫂子在床沿上坐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直把小梨看得都臊了,才又哎呀一声,叹道,几年的小梨呀。果然是北京城里来的,硬是不一样。小梨笑道,青嫂子你笑话我吧。青嫂子说,哪敢笑你呀。你如今是金贵人儿。比不得我们这些庄稼主子。青嫂子说梨呀,嫂子问你,在北京,一个月挣多少钱呀。小梨没料到她这么直接,心里一惊,脸上却笑道,我呀,反正够花了。青嫂子哪里肯依,笑道,那到底挣多少呀?大城市里不比芳村,花销可忒大。小梨笑道,省着点儿花呗。青嫂子伸出几个指头,说有这个数?小梨摇头不是,点头也不是,只是笑。大姐端着瓜子花生过来,让青嫂子,青嫂子抓了一把,一面咔嚓咔嚓剥着吃着,一面笑道,你看你,还藏着掖着,又不是外人!还有你家她爸,挣多少?小梨正不知道该怎么招架,然婶进来了。高声音大嗓门的,要借外甥的车用一下。大姐说,怎么,又去相媳妇?然婶叹道,可不是。见天相他娘的媳妇!光相媳妇就把家相穷了!狗日的没出息,天天上网,就不会从网上勾搭一个?急了我叫他打一辈子光棍儿!小梨忙问是谁相媳妇呀?青嫂子撇嘴道,她那二小子呗。青嫂子说没车就别臭显摆。好意思呀,老借人家的。费车不说,这油钱怎么算?
午后,整个村子都懒洋洋的。阳光亮亮的,有一点风,是春天的意思了。大街上挂着彩,花红柳绿,在风里招摇着。人家门楣上都贴着春联,挂着大红灯笼。一地的鞭炮纸屑,红彤彤的,空气里有淡淡的硫黄的味道。街上却不怎么见人。胡同口,大门前,还有街边上,停着一辆一辆的汽车。有车不断地从街上开过去,开过来,腾起细细的飞尘,半晌不散。也没有唱戏的,也没有说书的,就连孩子们也不多。不像她小时候,穿着新衣裳,在街上玩耍。鞭炮一声起一声落,把空气炸得新新的,更清澈凛冽了。衣兜鼓鼓囊囊的,满满装着花生瓜子。糖在嘴里一点一点融化,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去。芳村的年味儿,真的是不比从前了。
周围的房子都盖得气派。楼房,大多带着车库,平房呢,宽敞的院子,高高的围墙,铁桶一般。正看着呢,听见汽笛响,赶忙往路边避一避。不想那车却停下了。正诧异呢,车窗子摇下来,里面探出一个男人的脑袋,叫她的小名。小梨见那人穿了件浅米色休闲西装,深蓝衬衣,也不怕冷。知道是村里人,却一时叫不出名字来。那人笑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呀。老同学都不认识了?小梨脑子像是冻住了,一时转不过弯来。那人见她怔忡的样子,大度地哈哈一笑,说好啦好啦,还是早先的性子,一点儿都不改。装一装都不会,老叫人下不来台。一面说,一面把一张名片递过来。车里开着空调,夹带出来一阵暖香的风。小梨看那名片,失声叫道,哎呀,是你呀。小宾就笑。小梨笑道,都大老板了,春风得意啊。小宾笑道,笑话我是吧。谁不知道你是大城市来的。两个人就一个车里,一个车外,说起话来。阳光照在车窗子上,有一道光白亮亮的,正好把他们切割开来。小宾的一只手在那交界处搁着,手上一枚硕大的金戒指一闪一闪的。
小梨指一指那戒指说,要把人眼睛晃瞎了。小宾说,又笑话我。看了看小梨光秃秃的手,笑道,你们城里人都戴钻戒是吧。小梨脸上一窘,正不知该说什么,小宾却又岔开话题了,说起了别的。又说起了当年的一些个同学,如今大都在芳村,都儿女成行了。有的都当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小宾感叹道,真快呀。我们都成了小老头了,你还是小姑娘模样哩。小梨笑道,少笑话人吧你。谁比谁小呀。正说话呢,大姐远远地叫她。小宾说,说句正经的,那个谁,你那外甥,你大姐家小子,如今干啥呢。小梨说,也没有细问,好像是闲着吧。原先在李家庄厂子里干,后来不知道怎么不干了。小宾沉吟了一下,说那啥,你要是不嫌弃,就叫他到我厂里来吧。就在城南这边,离家也近。小梨笑道,那我问问他,怎么谢谢你这老板呀。小宾说,谢啥谢。自家的厂子,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回来把这事跟大姐说了。大姐十分欢喜,一面感叹,一面骂人家势利眼,成天价在一个村子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早先怎么不肯呀。小梨知道她的脾气,也不理她。姐夫说,不愿意去就不去嘛,犯得上这样。大姐气道,你这么有骨气?我怎么不知道?你有骨气,你也去开工厂呀。叫你家小子当阔少爷。在人家屋檐下打哪门子工!小梨见她这样,情知又有一场大闹,生怕爹听见,赶忙吓唬道,你看,我多管闲事,倒管出一堆不是来了。再闹,再闹我可不管了。摔帘子就出来了。
大门口的台阶上,有几个闲人坐着晒太阳。见她出来,都跟她爹说,啊呀老木,亲人来啦。她爹就笑。人们七嘴八舌的,问小梨一些个北京的事儿。有人问她住在哪儿,离天安门近不近?有人问她是啥单位?挣钱多不多?她女婿哩?看样子像是个当官的吧。一个远房大伯,劈头就问她,现在是啥官儿,要是在早年间,算是几品?小梨知道是躲不过了,只好如实说了。人们嘴里咝咝哈哈的,嘬着牙花子,像是不相信,又像是惋惜。她爹也脸上讪讪的,一时不知道该说句什么才好。小梨臊得满脸通红。恨不能找个地缝儿,一头钻进去。那大伯叹口气,半晌才说,梨呀,从小你就念书好,脑瓜儿灵。怎么反倒越念书越傻了呀。不是非要为官做宰的,可自古以来有一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呀。大伯说你看你爹,供你念恁多年书,腰都累断了……四叔在旁边笑道,梨那女婿可厉害呢,北京人哩。那根根蔓蔓的,深着哩。众人又都问起了乃建。乃建是啥单位?官儿做到了哪一级?手底下管着多少人?乃建他爸妈,退了没有?一个月多少退休金?几乎来不及多想,小梨就信口胡诌起来。
太阳光煌煌的照下来,竟然背上就热辣辣的出了一层细汗。到底是七九的天气了。田野里雾蒙蒙的,给阳光一照,好像是笼着一重薄的金烟。有一点风,软软凉凉的,把满街挂的彩吹得索索乱响。远远的,有一个人走过来,一迭声地问,小梨?是小梨不?哎呀呀,小梨?小梨赶忙答应着,也不管那些人一箩筐的问题,趁机溜了。
傍晚回来,乃建的午觉已经醒了,正坐在沙发上喝茶。小梨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恶气,三步两步过去,端起他的茶就泼到院子里了。乃建见她脸色不对,也不敢多问。跑过去看了看门外,把门掩了,才小声道,怎么了这是?要吵架也别在这里吵呀。小梨恨道,谁跟你吵?我懒得跟你吵。收拾东西,立马走人。赶紧的。乃建纳闷道,不是住两晚么?怎么说变就变呀。小梨气道,住两晚?你是不是还打算在这儿住上一辈子?七大碟子八大碗的,被人伺候着?乃建忍气道,这人,怎么不讲道理?一面穿外套,一面嘟嘟囔囔地收拾东西。妞妞本来窝在电脑前,见这架势,才把耳机摘下来,雀跃道,怎么,要回去啦?欧——耶——
晚饭的时候,爹一个劲儿埋怨,怪小梨把乃建他们爷俩儿撵走了。爹说回来一趟容易吗,一年才一趟。爹说都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呀。小梨说冷么。他们怕冷么。暖气屋里待惯的,冻得跟什么似的。爹就不说话了。半晌才说,叫你公公婆婆怎么看呀。连夜赶回去。小梨笑道,看你,操心也忒多。亲闺女守着你还不够呀。趁机岔开话题,说起明天去看姥姥的事。爹果然叹气道,阎王老了不拿鬼。你姥姥,一辈子刚强厉害,年前生日,五六个闺女,谁都没有来看一眼。爹说九十二了,还能有几个生日呀。小梨说,我姨她们,都没来?爹说,没来。还是你小姨,买了几个蒸碗端过来。都说忙,忙……小梨见爹感伤,也不敢多说,只好胡乱打岔,说一些个妞妞的趣事。爹果然渐渐喜欢起来。忽然又问,乃建的事,不是你编的吧?小梨愣了一下,撒娇道,哎呀,您看我哪一句像是编的呀?
晚上在外甥的新房子住。新房子有暖气,又干净,洗洗涮涮也方便。外甥媳妇刚添了孩子,才满月。二姐就住在这小后屋里,伺候月子。新房子装修得不错,面积又大,比小梨北京的家还要气派。虽说有暖气,可小梨还是觉得不暖和。也不敢大洗,只简单洗漱了,就钻进被窝里躲着了。二姐忙进忙出,总算是里外收拾妥当了,才躺下来。姐妹两个挤一张床,说了半宿的私房话。不外是芳村的一些个人和事,还有亲戚之间的是是非非。还有婆媳之间的疙里疙瘩。埋怨姐夫懒,儿子不懂事,儿媳妇呢,更不行了。隔着一层肚皮哩。半夜里,忽然孩子就哭起来了。二姐一下子就坐起来,张着耳朵听了听,见越哭越厉害,便赶忙胡乱披了件衣裳,趿拉着鞋跑过去敲门。再过来的时候,小梨都要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听见二姐抱怨,便说,人家爹妈都在哩,还巴巴跑过去,真是劳碌命。二姐叹口气,小声说,可也是,怀里揣笊篱,捞(牢)不着的心。二姐说要是不过去吧,就又是事儿。这一声奶奶呀,可不好应哩。小梨就笑。
早晨起来,一家人围桌坐好,预备吃饭。外甥媳妇却迟迟不过来。再三再四地叫,仍是不见人影儿。二姐小声说,八成这又是有事儿。果然,外甥过来,吞吞吐吐的,半天也没有一句囫囵话。二姐恨道,我知道今儿回娘家,钱不是早给你们了吗。外甥说,还有压岁钱哩。二姐说,压岁钱?给她娘家七大姑八大姨出人情,也活该我们出呀。外甥也是听惯了,只是不说话。二姐叹道,上辈子欠你们的!回头冲二姐夫说,还愣着干啥,去吧,去借吧。小梨起身要去小后屋里拿包,被二姐摁住了。二姐冲着她摇摇头,使了个眼色。小梨只好坐下了。
正说着呢,二姐她婆婆来了。二姐趁机就诉苦。大姐一进屋子,见这情势,使眼色叫小梨出来。小梨就出来了。大姐撇嘴道,看吧,又是一场好戏。你也是,这时候还待在这儿干吗?他们刘家的事儿,咱少掺和。
这是村子东头。再往东,就是野外了。先前,这一片都是庄稼地,到了秋天,郁郁苍苍的,一直蔓延到天边去。再往东,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就是大河套了。当年,那可是一个神秘好玩的所在。早晨的太阳怯生生的,却到底是有一点泼辣的意思了。远远近近的村居,被笼上一层软软的烟霭。这个季节,田野空旷,安静,只有停下来仔细听一听,才能隐约听见,泥土深处骚动的声音。人家的院墙上,歪歪扭扭写着,打井,13832105561。专业烫房顶,13703215042。上瓦,18032097599。旁边的一面白墙上,是中国电信的巨幅广告。几只麻雀在地上蹦来蹦去,活泼极了。小梨指着后头的一栋楼,问是谁家的呀,这么阔气。大姐说,兔子家,老庆叔的三小子。大姐小声说阔啥阔,还不是反穿皮袄,外光里不光。做买卖赔了,要债的不离门。过年都不敢回来。他媳妇要跟他离哩。正说着话,见一个闺女拎着一个垃圾袋出来,染着金黄的头发。大姐拿胳膊肘碰碰她,小声说,看看,这是他闺女——不想那闺女回头看见她们,明晃晃一笑,赶着叫大姑。又眯起眼睛,迟疑了一下,笑道,小梨姑呀,看我这眼拙的,都不敢认了。小梨见她穿一条小短裙,露着两条黑丝长腿。上头只穿了一件桃粉薄毛衣,两颊冻得红红的,领子却低低的,十分惊险。大姐蝎蝎螫螫的,叫道,哎呀,就一层丝袜呀,不冷吗?跑过去真的就捏了捏人家的大腿。那闺女笑道,看着薄,可厚哩。大姐嘴里啧啧的,看了人家的丝袜,又看人家的胸口。那闺女说,来家里坐会儿呗。小梨忙说不了不了。心想这闺女倒是长得俊俏,又伶俐。看着她进了大门,大姐才叹道,这闺女,刚硬着哩。为了帮家里还债,把自己都豁出去了。小梨心里一惊,刚要问一句,却见几个人影影绰绰过来,在土地庙前头停下了。
大姐说,这是烧香许愿的。咱们还是绕道走吧。这种事儿,都不愿意被撞见。小梨说,晴天大日头的,难保不撞见人。怎么不天黑了来呀。大姐说,恐怕这不是咱芳村的。甭小看了这土地庙,名气大哩。才一会儿工夫,庙前头那个大香炉里,就点上香了。几缕青烟,在晨风里静静地升腾着。太阳光照下来,那几个人跪在地下,一拜,两拜,三拜。远远看去,红尘霭霭,有一种不似人间的错觉。那几个人的影子,也像是金箔纸剪出来的,孤零零的,仿佛是浮在茫茫的日光里。
大姐碰碰她,笑道,怎么,你不想烧一炷香,许个愿?小梨这才醒过来,笑道,我才不信这个哩。大姐吓得赶忙说,甭乱说话。都听着哩。又赶紧冲着土地庙拜了拜,双手合十,嘴里念念叨叨的,也不知在说什么。小梨也不敢笑了。一阵晨风吹过来,头皮一炸,只觉得脊背上簌簌地起了一层小粒子。不远处,那几个人影还在地下跪着。香烟丝丝缕缕的,缭绕着他们。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劝说。半晌,大姐才埋怨道,可不敢乱说话。三娃子媳妇,就是说了一句啥话,也不知冲撞了哪一路仙家,闹了大半年。疯疯癫癫的。请小别扭媳妇看了,也不大好。又请了城北那个大仙,许了愿,家里也请了神,才慢慢好了。你说怪不怪?
门前的台阶上,照例有几个闲人坐着。小梨见了,心里不由得有点慌乱,想赶紧躲进屋里去,大姐哪里肯。那些人正闲得蛋疼,见她们姐儿俩过来,老远就笑道,这可是远且(客),得好好待一待呀。大姐笑道,她呀,有啥好待的,又不是啥且(客)。人们说,那可不,人家平日里大鱼大肉早吃腻啦。还稀罕个啥。大姐笑道,可说呢。梨说啦,就想吃个素净的。小米粥咸菜,家常饭想得慌哩。他们大城市里的,肥鸡大鸭子的,就想这一口呢。大姐说她家那妞妞,嘴刁着哩。一大桌子,愣是没有她的菜。吓。大姐说我急得不行,看把个孩子惯成这个样儿——人家城里人么。小梨扯扯她袖子,她只当看不见,抓着小梨的手,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听那口气,好像小梨就是中央的,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小梨又臊又恼,拉着大姐就往屋子里走。大姐没能尽兴,悄悄咬牙骂道,怎么啦?我说说怎么啦。这帮势利眼,就得镇镇他们!小梨气道,你吹够了没有?
屋子里倒是暖洋洋的。水壶开了,滋滋滋滋地叫着。大姐一面往暖壶里灌水,一面叹道,你不在村子里,你知道啥?念书都念傻了。大姐说如今呀,哪里还有啥人情,人心凉着哩,薄着哩。小梨说,那也不能瞎吹呀。真是。大姐叹口气道,梨呀,不是姐说你。心眼子太死。在外头混了恁多年,混了个啥?连个车都混不上。你看看,就咱芳村,一年里添了多少辆车了?恨不能,是个长脑袋瓜的,就有车——小梨脸腾的就红了,一时却说不出话来。大姐说,咱家里倒没啥,外人都看着哩。那些个势利眼们,狗眼看人低。人这一辈子,不蒸馒头争口气呀。小梨说,房子都买了,一辆车算啥呢。大姐说,说的是呀。房子在北京,搬不动扛不动,谁看得见呀。汽车可是脸面哪。你看那个谁,大老黑家的老二,开车回来,好威风呀。他那车叫啥来着?小梨哭笑不得,也不理会她。心里却把乃建恨得要死,骂了他祖宗八辈一遍。
正说着话呢,二姐过来了。说起儿媳妇回娘家的事儿,唉声叹气。大姐把嘴一撇道,就你这性子,怎么能够拿得住人家?一辈子叫人家骑到你头上,拉屎撒尿吧。二姐说,你是没听见人家骂你,还觉得美哩。眼下人家用着你哩,白天黑夜,给人家看孩子。往后你老了,你再看。大姐说,我就是图眼下,痛快一天是一天,痛快一晌是一晌。眼下的火焰山都过不去,我还顾得上往后哩?小梨见她们两个又要吵嘴,心里不耐烦,转身就出来了。
正月里,人们忙碌了一年,都趁机歇一歇。打牌的打牌,推牌九的推牌九。也有串亲戚的,待且(客)的。也有说媒的,相亲的。平日里人们都忙,忙得四脚朝天,哪里有这些个闲心。这条东西街,算是芳村的大街。再往西,就是小辛庄了。村委会的小白楼,在大街上的正中央,早些年威风得很,如今,四周的高楼大房都盖起来了,相比之下,倒有些寒酸了。临街的门脸,是秋保家的超市。芳村的超市倒有好几个,这个算是最大的了。位置又好,秋保呢,又灵活。生意就特别的好。人们进进出出的,也有买东西的,也有来交电费的,也有来拿快递邮件的。秋保两口子忙得手脚不停。还是秋保眼尖,见小梨进来,赶忙招呼道,梨回来了?几时回来的呀?小梨也笑着叫他哥。他媳妇国欣过来,说了一会子话。小梨说你们忙着,我挑几样东西,去串门儿。秋保忙说好呀好呀。又吩咐他媳妇,帮着梨挑几样好的,多挑几样儿。小梨说甭管我,你们忙。秋保媳妇冲着她挤挤眼,小声说,我给你挑,这里头道道多着哩——你不知道。小梨见拦不住,就由着她挑。她一口气挑了一大堆,一箱六个核桃,一箱蒙牛鲜牛奶,一箱露露,一只烧鸡,一只鸭子,一大块咸驴肉,半个酱肘子,两盘鸡蛋。小梨忙说够了够了,国欣哪里肯听,又把一些个酸奶火腿杂七杂八的零食塞过来。小梨只好拿出钱包结账。秋保见了,就骂他媳妇,梨妹子是外人儿?真是混账娘儿们。吩咐国欣把小梨送回去。小梨哪里肯。打架似的,撕扯了半晌,秋保骂他媳妇,小梨北京来的,差那几个小钱儿?真是的,丢人现眼。小梨见四周人多,心里不耐烦,把钱扔在地下,拎着东西,跌跌撞撞就跑了。后头秋保媳妇还在说,梨呀,有空过来玩儿呀。
一进门,大姐就叫起来。小梨就说了方才的事。大姐听了破口大骂。小梨说算了算了,你这嘴真脏,骂人家这么难听。大姐就火了,你是有钱人?你有钱怎么不救济一下你亲姐姐呀。打肿脸充胖子。我就看不惯你这做派。小梨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秋保这两口子,穷疯了,见谁都想咬一口。六亲不认,狗日的。惹急了我,堵着超市门口我去骂他个三天三夜。小梨见劝她不住,只好道,我正想着去亲戚本家看看哩,这些个东西恐怕还不够。大姐笑道,好呀,你是城里来的,礼法长,回来自然要各家走走。打算整个芳村都走一圈?小梨知道她动了气,笑道,你看你,不就是到亲戚本家去看看么。大姐冷笑道,你翟小梨欠他们的?啥时候欠下的?我怎么不知道?每一趟回来,都要上赶着去给人家送东西。你开着银行哪?大姐说我在村子里待着,我什么不知道?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就懂人情世故啦?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没啥好东西。一帮势利眼。你今儿个要是敢出这个门,就甭认我这个亲姐姐。小梨见她眼睛里亮闪闪的,好像是有泪花,一时也吓住了,正不知怎么办好,二姐过来了。见这个阵势,冲着小梨使个眼色。小梨赶忙说哎呀姐,我听你的还不行呀。又软声劝了半晌,大姐才叹了一声,道,我活了半辈子了,我不懂人情世故?我还不是心疼你呀。白喂了那些个白眼狼们!
芳村的夜,说来就来了。
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了,好像是一只一只眼睛,一闪一闪的,也不怕冷。天是那种深的黑蓝,月亮就在天边,浅浅淡淡的半月,缺了一块,像是谁不小心咬了一口。星星们却稀稀落落的。只有仔细看的时候,才像是忽然间跳出来似的,一颗一颗,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竟是越来越稠密了。同街灯混在一起,到处都闪闪烁烁的。
小梨穿着高跟鞋,一崴一崴的,一面走,一面埋怨这路难走。大姐说,让你穿我那平底鞋,你嫌难看。活受罪。大姐说黑灯瞎火的,谁看呀,真是。小梨说都走到这儿啦,还说这个。远远的,影影绰绰过来一个人,逆着光,也看不清模样,只见一个瘦瘦的轮廓,像是浮在昏黄的夜幕上,一游一游的。快走到跟前了,只听那人叫她,小梨仔细一看,才犹犹豫豫叫了一声,果子?
卫生院门前,停着各种各样的车。里头灯火明亮,人影一高一下的,投在落地玻璃窗上。有几个人正在治疗室里输液,还有一个小孩子,大约是哭累了,躺在他妈妈的怀里,时不时抽泣一声。诊室里有几个人在排队。会开穿着白大褂,正在给一个妇女把脉。那妇女嘴里絮絮叨叨的,诉说着病情。会开半闭着眼,似听非听的。把完脉,又拿起听诊器,那妇女把毛衣撩起来,会开的听诊器一下子就伸进去了。小梨的一颗心忽悠一下,就蹦到了嗓子眼儿。果子在一旁碰碰她胳膊肘,她这才醒过来,听果子说话。日光灯白茫茫照下来,屋子里面好像腾起了大雾,灯管偶尔咝咝咝咝叫两声,过一会儿,又咝咝咝咝叫两声。果子的脸更加苍白了。眼睛下面,有两块青色的阴影。果子的嘴唇上起着白皮,嘴角边爆起了几粒小水泡。
会开开完药方,一抬眼看见小梨,哎呀一声立起来。小梨笑道,忙啊。会开一面搓手,一面结结巴巴地,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住几天,怎么来了也不吭一声,是谁不好了,还是——小梨看了一眼排队的人们,小声道,我就是来问问我爹的事儿,是不是输输季节水。这不,碰上果子了。你忙你的。我这倒不急,果子这,你给她好好看看。会开答应着,看了果子一眼,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说。
晚上说起闲话来,才知道果子的事。果子的一个奶子被切掉了。另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果子的男人去外头打工,再也没有回来。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已经是深夜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偶尔有谁家的狗,好像是被惊扰了,忽然叫两声。小梨睡不着。摸出手机,想给乃建发个短信,想了想,又罢了。好像是起风了。风掠过树梢,呜呜呜呜地响。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看见果子朝着她跑过来。蛋黄的小衫,红喷喷的一张圆脸,肉嘟嘟的,鼻尖上有星星点点的细汗珠,胸前有两个小兔子一样的东西,跳啊跳。
果子。小梨叫了一声,一下子醒了。二姐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