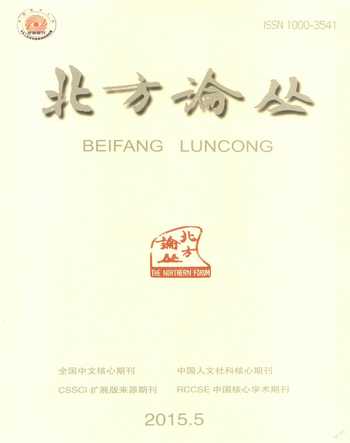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的“解释学”
杨子飞
[摘要]施特劳斯并没有一套普遍的解释学理论,但有细致精巧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预设了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永恒根本问题的整全的存在。经典文本是对整全的模仿,对文本的解释就是一个通往整全的起点,解释的过程就是在与被解释者交往对话的过程中追问这个根本的问题,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共同向整全开放。因此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就是一种哲学实践,解释并非仅仅是达到理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解释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解释的过程就是哲学化的过程。像施特劳斯那样读书,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被看成是在践行哲人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解释学;哲学实践;经典文本;整全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131-06
Abstract:There is no universal hermeneutics theory belongs to Strauss, but he do have meticulous and ingenious hermeneutics methods. This methods presup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y, the existence of the whole as eternal and essential questions. The classical text is an imitation of the whole, and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is that both of the reader and the author search for the essential questions during their dialogue, and their final end is that they open to the whole together. So Strausss hermeneutics methods is an philosophical practice, the interpretation process has its own value, because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ocess of philosophize. So reading like Strauss can be seemed as a practition of philosophers life.
Key words:Hermeneutics; Philosophical Practice; Classical Text; The Whole
[收稿日期]2015-07-13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被称为“海德格尔之后最重要的释义学大师”[1](封面),但施特劳斯的“解释学”对于他自己的意义可以说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长期以来,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都是广为争议的话题。批评他的人最肤浅的就是认为这是一种“书虫英雄主义”(bookworm heroism),嗤之以鼻,一笑而过[2](p.105)。深入到思想根基里的批评来自德鲁里(Shadia Drury),她认为,施特劳斯的解释基于一种危险的神秘主义,它与施特劳斯暗地里主张的哲人的秘密统治是同一个逻辑[3](pp.98-102)。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则指责施特劳斯只是“没有秘密的狮身人面像”,表面上神神鬼鬼,骨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4](pp.30-36)。还有人讥讽施特劳斯“整个哲学生涯都把古典著作涤荡于唇舌之间,仿佛品尝陈年白兰地似的,而这么做几乎不可能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5](p.290)。
当然,赞许他的人也不在少数: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一篇著名的文章《作为政治的解释学》注重的是施特劳斯解释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在共同体内部,任何解释都是一个政治行动[6](p.192)。坎特(PA Cantor)则赞扬施特劳斯为西方当代解释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施特劳斯的成就是对当代解释学“鲜明的对比和健康的矫正”[7](p.166)。国内也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他赞扬施特劳斯的解释学不同于传统的普遍的解释学理论,“它虽然相对而言简单但是却不教条”[8](p.18)。
一、解释的基础——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
解释可以被看成是写作的一个反向运动,写作是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而解释则是从文本中解读出意义来。因此,一个人怎样解释,取决于他认为作者会怎样写作;解释的方法取决于写作的方法。要讨论施特劳斯解释学的正当性,就必须首先讨论施特劳斯关于写作技巧的论述,而这必然就得直面施特劳斯备受诟病的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区分。但这种区分的基础何在呢?
施特劳斯指出,在写作中区分“显白的教诲”与“隐微的教诲”是一个历史事实。古典哲人认为,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哲学只关心真理,是对万物“原则”的毫无限制的疯狂追寻[9](p.83)。这种追寻必然始于对哲学所处的政治社会所遵循的一整套意见的质疑,而这套意见恰恰是政治社会所赖以存在的根基[10](p.299)。因此,哲人一方面要向普通大众隐藏自己真正的观点,“不只是现在,而且是任何时代”[11](p.34)。他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保护哲学免遭迫害,还是为了保护社会免于哲学的伤害。这就是所谓“显白的教诲”。另一方面,哲人又必须向潜在的哲人透露一些真理,以吸引他们进入哲学的行列,这是为了哲学事业的传承。这就是所谓的“隐微的教诲”。可以说,“显白教诲”是真理的必要外衣,学会编织这种外衣是哲人成长为政治哲人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认为“显白教诲”除了保护哲学和社会免于互相伤害的作用之外,本身并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说相比于“隐微教诲”,施特劳斯更重视的是“显白教诲”,理由是这样的:哲学是从意见到知识的一个升华过程[9](p.125),因此,意见并非是应该被废弃的毫无价值的,相反它是哲学的自然起点。那么“显白教诲”作为一种意见也就一定是“隐微教诲”的自然起点。“显白教诲”表面上看来是通往“隐微教诲”的一种障碍,而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桥梁。之所以是一种障碍,是因为它要把大多数普通人排除在外,同时还是借此对潜在哲人的甄别和考验。而之所以是一种桥梁,是因为它首先具有足够的诱惑力,其次它也是借以上升的阶梯。
因此,真正的哲学写作是“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杂糅在一起的,而这样的杂糅就是所谓的“修辞问题”(literary question),亦即哲学在社会面前的言说问题。施特劳斯认为:“修辞问题研究就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修辞问题,恰当地来理解,就是社会与哲学关系的问题。”[12](p.52)修辞问题是事物的表层现象,是读者直接面对的对象,而在施特劳斯看来,事物的表层就是事物的核心[13](p.64)。解释因此就是从“显白教诲”到“隐微教诲”的升华过程,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升华过程。因为如果哲学并不是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那么解释也不是“隐微教诲”,而是追问“隐微教诲”的过程。
但是,正如罗森所质疑的,施特劳斯致力于揭露西方传统中隐微教诲的存在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一方面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换来的只不过是英语学界的冷嘲热讽。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化的努力似乎破坏了隐微教诲本身实践的道德和审慎原则[6](p.192)。这个质疑非常有力,因为表面上看来,解释学是隐微写作技术的反技术,旨在把被隐藏了的东西揭示出来。所以,施特劳斯运用解释学公开了隐微写作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之作为传统是被隐藏的,那么施特劳斯是否就违背了他所颂扬的传统原则,并因而成为了现代人了呢?[6](p.226)他是不是公开了本不应该公开的东西了呢?
施特劳斯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他寻找理由,似乎只能是这样的:存在着两重意义上的解释,第一层是施特劳斯解释经典文本,这是一个纯粹内在的并且私人的思想过程;第二层是我们解释施特劳斯的“解释”,此时我们所面对的“解释”实际上又变成了文本。也就是说施特劳斯的写作是同时融合了解释与书写的两个过程。因此,施特劳斯在书写他的解释过程中,极有可能又运用了隐微写作的技巧,他在解密了之后又重新设置了新的秘密。新一轮解释的任务已经落到了施特劳斯的读者身上。
如果这样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施特劳斯的解释学定位在纯粹内在的思维。解释首先不是写作,也不是言说,因为不管写作还是言说都是实践性质的。而解释首先作为纯粹的思,是理论性的。思的过程也就是从显白教诲向隐微教诲升华的过程。因此解释具有哲学生活的首要性质。
二、解释的对象——作为整全之模仿的文本
解释的对象是文本,而施特劳斯所说的不是普通的文本,而是堪称经典的文本,它是伟大的思想家精心雕琢出来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思想家才有资格和能力如施特劳斯所描绘的那样写作。我们怎么定位文本,我们也就怎么对它做出解释。
在施特劳斯眼里,经典文本不仅仅是经典作家的言辞,更是对整全的模仿。这是因为,言辞作为书写的媒介有着本质上的局限性,书写一旦完成,就已经死亡,因此,只能针对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表达同样的东西[12](p.52)。与之不同的是对话,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场景做出灵活的调整与适应。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的活动,因此,柏拉图哲学总是以对话的形式。但柏拉图却是记录苏格拉底的对话,哲学要用对话录(区别于苏格拉底的对话)的形式出现,这就必然要受到言辞的限制。
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呈现他的教诲:“柏拉图不仅运用了其作品的内容(众多角色们的言辞),也运用了其作品的形式(总体上的对话形式,每篇对话的特殊形式。每篇对话中每一部分的特殊形式,情节,人物,人名,地点,时间,场景诸如此类)。”[14](p.225)这些形式正是整全的构成要素,它们旨在恢复对话所赖以发生的情境,就像戏剧场景一样。我们发现柏拉图的对话是戏剧的,因此,为了能够真正理解它,我们就必须像戏剧一样去阅读它。正是这些形式的补充,才使得柏拉图的对话具有了口头交流的弹性和适应性[12](p.53)。因此,对对话作品的透彻理解就是根据“形式”来理解内容。比如,对于《理想国》著名的开场情境的解释就是利用了“形式”来理解内容:苏格拉底与格劳孔从雅典来到比雷埃夫斯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极其简单的叙事介绍,在施特劳斯看来却孕育了极其丰富的信息。首先,比雷埃夫斯港是民主政治的大本营;其次,苏格拉底来到这里并非是为了讨论有关正义的话题,而是为了参加祭祀诸神的活动。从中施特劳斯解读出这是哲人从阳光明媚的理念世界下降到昏暗的洞穴内的过程,整部《理想国》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哲人下降重返洞穴的故事[12](p.62)。
文本作为对整全的模仿,它表面上是死的,而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它是一场形象的、生动的在剧情推动下的运动过程,读者的解读过程就是在全程参与到剧情运动的过程之中。文本的运动就是整全的呈现,而解释就是交往或者说对话。在此过程中,读者与剧中人物开始共同面对相同的对话情境。既然任何的交往都只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那么对交往的解释(也是一种交往)就只能也是具体的了。
总之文本作为整全的模仿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施特劳斯的解释以寻求与被研习的思想家们进行交往对话为旨归[15](p.8),解释的过程无疑就是一个交往对话的过程,在交往与对话的过程中,整全向双方逐渐地呈现。而哲学的本意是对整全的追问[10](p.344),解释作为对整全的追问,因此就具有了哲学生活的意涵。
三、解释的目的——作者的意图
如前所述,解释是在纯粹内在思维中“完成”从“显白教诲”向“隐微教诲”的升华,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的目的就仅仅在于寻找“隐微教诲”,“隐微教诲”并不是真理的全部。施特劳斯的“解释学”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像作者理解他自身那样去理解作品”[16](p.209)。作者的自身理解,显然不仅仅就是指隐微教诲,它是“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综合,这种综合就是作者的意图。
施特劳斯一再强调,要从流俗所谓哲人对“哲学史”的“贡献”,返回到哲人之“意图”[17](p.183)。所谓“贡献”指的是对推动哲学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是用“哲学史”来度量哲学家的思想。而所谓“意图”指的是哲学家自身写作时的意思,他只是对人类永恒根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施特劳斯其实暗示,只有理解了作者的意图,才是真正理解了作者本身。难怪施特劳斯及其信徒们的很多文章都是以某某人的意图做题的。
但历史主义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它认为所有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都受到思想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同样任何人也都只能从自己时代的立场出发来解读过去的思想,并且认为这种解读超过过去思想家对自己思想的理解[18](p.149)。历史主义因此而否定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可以说,历史主义否认了哲学的可能性,把我们的视野牢牢局限在了当下,把我们的思想束缚在人造的历史洞穴之中。
而施特劳斯之所以坚持认为“像作者理解他自身那样去理解作品”是可能的,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像他本人那样去理解他,只有一种方式。”[19](p.33)这是因为“学说之创建者理解其学说的方式是惟一的,倘若他本人是清醒的话”。这就意味着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终极的解释,它符合作者的真实意图。
这样的宣称难免令人觉得过于霸道,但施特劳斯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坚持存在不受历史影响的永恒的问题,尽管人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解答,但这些问题本身是不变的[20](p.75)。问题之所以不变,是因为整全之作为整全是不变的。意识到了根本问题的存在,也就是意识到了整全的存在。因此,施特劳斯解释学的根本目的应该被理解为像作者那样,认识到根本性的永恒问题即整全的存在。
因此,可以说解释学是消除历史主义带来的认识障碍的一种方法,在施特劳斯看来,在我们的时代进行哲学思考主要在于“倾听伟大的哲学家们之间的对话……也就在于研读一些伟大的著作。”[21](p.7)它的目的就是要寻回前科学的或前哲学的自然理解[22](p.343),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它们敞开着对于我们的自然世界的自然理解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根本性的永恒问题的意识,恰恰正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哲学精髓所在[20](p.32)。在其原初的意义上而言,哲学是探寻的,或者说是怀疑的,相比于对问题的答案来说,问题本身才是更加确定的。因此,如果说哲学的实践是向整全的开放,那么解释学的实践也是向整全的开放。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解释学所面对的整全不是古典哲人所面对的整全,而是由伟大思想家所模仿的整全。在我们的时代,人正是通过对文本的解释,通过意识到整全的存在,才把自己的心灵从历史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的。感受到从当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是哲学生活实践的意义之所在。
施特劳斯说苏格拉底教导我们,目的是理解整全的关键[23](p.138)。我们也可以说作者的意图是理解文本的关键,因此,也就是理解整全的关键。因为如前所述,文本就是对整全的模仿。解释者正是借助对文本的解释才获得了对整全的理解。而这实际上就是哲学的工作,“解释学”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实践。
四、解释的原则
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作者的意图,进而把握作者所呈现的整全性的问题呢?施特劳斯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学理论,施特劳斯也非常怀疑一种超越于“形式的”或外在经验的普遍解释学理论是否可能[7](p.103)。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解释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基本原则,我们将发现,这些原则无一不是哲学精神的体现:
一是读者必须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心态,必须相信古人能够教会我们一些我们在其他地方无法学到的知识。施特劳斯认为,要理解一种真正的学说,必须对它怀有真正的兴趣,兴趣越大,充分理解它的可能性就越大。还必须认真对待它,也就是说,必须愿意考虑这一可能性:它就是真理[19](p.34)。对于真理的热爱就是哲学最原始的含义,没有这种热爱,就没有解释的动力和毅力。
二是心智的完全开放,让文本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坦然面对和接受所有来自文本对我们既有观念的挑战。因此,对经典文本的解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的过程。“必须克服自我去聆听他们,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质询。”[24](p.51)首要的就要求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问题强加在作者身上,而是要把作者有意识地提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他的材料[18](p.151)。认识到无知是哲学生活实践的正当结果,而自我的开放就是哲学的恰当姿态。哲人永远不能在确定性的温床上睡懒觉。
三是坚持从表面出发。施特劳斯不断强调,表面是解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表面并不是需要被克服、被撕裂的“面纱”。正如罗森所说:“表面不能被毁构,因为不管我们从何处开始,表面总是作为开端。”[6](p.192)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充分尊重作品的表层结构。因为哲学是从意见到知识的升华,因此表面就具有了桥梁的重要意义。
四、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出于前述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和对政治迫害的考虑,一个谨慎的思想家会在其写作的时候字斟句酌。因此,我们在阅读这样的著作时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反复推敲作者遣词造句的良苦用心,而不能只专注于作者提出的结论和教条。这是对哲人的必要磨炼。对于具体的、个别的、细枝末节的关注和理解,在布鲁姆(Alan Bloom)看来正是哲学教育的方法和目的所在。因为抽象的观念在将世界条理化的同时也遮蔽了事物,它使得经验世界日益枯竭[24](p.56)。哲人不应是干枯的,他必须对于经验世界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培养潜在哲人对枝节的关注,就是要让他不要忘记哲学借以出发的自然起点。
总之,施特劳斯“解释学”不仅是一种方法,即不仅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它还具有存在论维度上的意义,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哲学精神的体现,对文本的解释犹如哲人的生活,就是一趟不知目的地的航行,“他开始踏上了一条他并不知晓其目的地的征途。他不可能毫无改变地回到他所出发的地方,即他所处的时代”[18](p.133)。难怪布鲁姆在评价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书时,近乎夸张地声称像是踏进了漫无边际的沙漠。“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沙海中长途跋涉,满目黄沙,枯燥乏味,了无生意”[13](p.80)。而这对于哲学生活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
五、解释的技术——“字里行间”阅读法
要能够“像作者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作者”,要能够紧紧抓住文本本身的运动轨迹,就必须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方法,施特劳斯把这套方法称为“字里行间阅读法”。具体来说,这套方法可以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运用:
(一)留心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当我们发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以至于连聪明的中学生都知道的错误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作者一时疏忽所致。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我们与其认为他(马基雅维利)也具有常人的弱点而掉以轻心,等闲视之,毋宁相信他始终是在字斟句酌,一丝不苟。”[13](p.55)我们有理由认定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如果作者是在讨论故意犯下写作错误的可能性,情况就更是如此[11](p.30)。我们要去追问他用这种方式在隐藏什么观点或者提示读者思考的方向。
(二)注意互相矛盾的地方
施特劳斯发现,马基雅维利处心积虑地以某种精巧微妙的方式,蓄意自相矛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两次提到了佛罗伦萨对皮斯托亚的政策,第一次认为皮斯托亚这个城市自觉自愿地接受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是因为佛罗伦萨人对皮斯托亚人一贯以兄弟相待。而仅仅在四章之后,又认为这其间的奥妙在于“和平秘术”,是佛罗伦萨人对皮斯托亚人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导致的结果。施特劳斯借此告诉我们,第一个说法与普遍观点和谐一致,认为道德应该也可以支配政治生活;而第二个说法则建议我们对上述普遍观点产生疑虑[13](p.49)。那么哪一个才是马基雅维利的真实观点呢?施特劳斯说,我们倘若在某类作品中发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我们就有理由假设,那个更隐秘的论点传达了作者的真实观点[25](p.166)。也就是说,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利的第一种说法明显是针对普通大众说的,是显白的教诲,而后一种观点则是针对哲人或潜在的哲人说的,因此就是隐微的教诲,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真实观点。
(三)比照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异
这种比照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第一种是比照文本与文本对象或者说是作者与作者处理的原作者之间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差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对于李维所叙述的历史故事,不事声张地做出改动。施特劳斯认为,这证明了马基雅维利开始质疑李维的权威[13](p.179)。
第二种是比照同一个作者在不同文本中就同一个问题论述上的差异。施特劳斯发现,法拉比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全然不谈神和神们,而在《概要》中却频频地谈到了神和神们,甚至有十四次之多[26](p.190)。
第三种是比照同一个作者在同一个文本中的不同部分就同一个问题论述上的差异。比如,施特劳斯分析了阿尔法拉比在《法义概要》中是如何分配“神”(God)和“神们”(gods)的。在前言和整个第一卷中,或者一定程度上更准确地说,在前面六页中,提到“神”是提到“神们”的三倍,即“神”提到了三次,“神们”提到了一次。往下就只提到了“神”一次[26](p.190)。
(四)注意特殊的沉默
这是施特劳斯经常运用的方法。“智者的沉默总是意味深长的。这不能用遗忘来解释”。他发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与《李维史论》两部书中都没有提及世界的此岸与彼岸的区别,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我们的灵魂。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通过在普遍观点,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沉默向读者显示出,这些题目对于政治来说并不重要,亦即普通人的观点是错误的[13](p.31)。而作者之所以不直接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不仅仅是考虑到了哲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通过隐藏自己与流行观点的对立来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样不同寻常的沉默,变相提醒深思熟虑的读者领会到他的特殊观点。
以上几点只是施特劳斯经常运用的几种解释手法,还有许多我们不能一一罗列。但可以肯定的是,运用这样细致灵活的解释手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解释者永远处于文本的征途中。这与哲学事业的永无止境是相一致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相比于形形色色的解释学理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看起来是简单而朴素的,它没有太多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可以阐发。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施特劳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解释学”,他只有具体的解释技巧,最多也就是一些解释的原则。而一旦我们真正进入施特劳斯所展开的解释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甚至枯燥的旅程。
而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在于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根本上是服务于哲学的目的,或者干脆说“解释学”就是哲学实践的一部分。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注重解释的目的,但也注重(甚至更加注重)解释的过程,这个解释的过程就是哲学化的过程。解释的过程培养的就是“一种适度的脾性,一种既勇敢无畏,又谦逊审慎的习惯”,而这就是施特劳斯心目中理想的哲人品质。而且解释过程的复杂与艰辛,恰恰构成了一道门槛,它将粗心大意的大多数人排除在哲学的大门之外,同时又为极少数潜在的哲人开了一扇隐蔽的小门。
[参 考 文 献]
[1]刘小枫,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古内尔(John G. Gunnell).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M]. 香港:明风出版社,2003.
[2][美]斯蒂芬·霍尔姆斯. 反自由主义剖析[M]. 曦中,陈兴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加]莎迪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M]. 张新刚,张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4]Myles Burnyeat,Sphinx without a Secret[J].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5(30).
[5]Brian Barry, Political Argument[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6]罗森.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C]// 宗成河译.刘小枫. 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坎特·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C]// 程志敏译.刘小枫,陈少明. 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2003.
[8]郑兴凤.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J]. 现代哲学,2004(3).
[9][德]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7(3).
[11]Leo Strauss,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2]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13][德]列奥·施特劳斯.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M]. 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4][德]列奥·施特劳斯.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C]//彭磊译.刘小枫.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5]Thomas L.Pangle. Editors Introduction[C]//Leo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6]Leo Strauss,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7][德]迈尔. 隐匿的对话——施密特与施特劳斯[M]. 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8][德]列奥·施特劳斯. 评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C]//余慧元译.刘小枫.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9]列奥·施特劳斯. 政治哲学与历史[A]. 洪涛. 什么是思想史[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0]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1]Leo Strauss,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2]古涅维奇. 自然正确问题与《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基本抉择[C]//彭刚译.刘小枫.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3]Leo Strauss,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Socrates[J]. Interpretation. Ed. David Bolotin, Christoher Bruell, Thomas L.Pangle: Wickersham Printing Co., Lancaster, PA, 1996(2) .
[24]阿兰·布鲁姆. 文本的研习[C]//韩潮译.什么是思想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5][德]列奥·施特劳斯.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C]//林志猛译.刘小枫.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6][德]列奥·施特劳斯. 阿尔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法义》[C]//阿尔法拉比. 柏拉图的哲学. 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