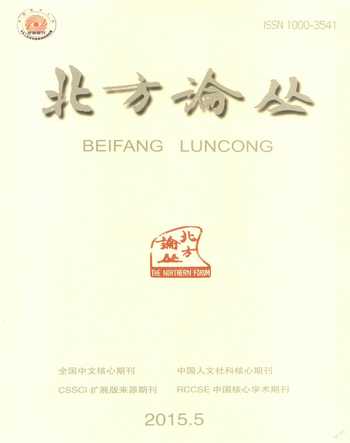晚清的词与物: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
[摘要]晚清域外游记出现诸多对西方现代事物的“命名”,从“无名”的谜面式描述,到“有名”的词语指称,从颇具模糊性、想象性的自造词命名到客观精确的词语命名,命名活动既是一种词语运动,意味着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多音节的现代汉语词汇纷纷登场,也是一种精神衍变,表征了命名者精神结构,以及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
[关键词]晚清;域外游记;命名;精神图式
[中图分类号]K207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040-06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eon how strange, fresh, “unknown” Western things bring into travel writing,How to give the names and thus achieve a clear statement of the other state,The ferry between namenand thing surgethethe control power of the main body, showing the writers spiritual change,Be worthy for us to get an important schema aboutthe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t the same time, word naming, reveals the mental turmoil, for the text itself, also means that heterogeneous intrusion, has brought the new change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overseas travel notes ;the late Qing Dynasty;naming;mental schema;language
[收稿日期]2015-07-06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课题“晚清域外纪游诗歌文献整理与研究”
名与物,名作为一种被强加于物之上的符号,它控制着事物被想象的边界,凸显了命名者的认知限度与主体意识,当作为“名”的词语成为“物”固定的、被普遍认可的,并具有历史性的符号时,名与物似乎合二为一了,但是,当“物”以一种溢出历史认知框架以外的方式出现、并亟待命名时,如何去命名它们,在还不可靠的命名过程中,名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种考古式的追问或许能够让我们发现对异“物”的命名如何让这些“物”丧失了它初始的透明性,并成为主体欲望与意识集合物的展开过程。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当晚清域外游者乍然进入现代西方,面临溢出认知范式之外的西方事物时,他们捉襟见肘的命名活动,往往集中体现了晚清域外游者意识衍变的展开过程,譬如,照相机、电梯、避孕套、自行车这些内化于我们认知架构中的现代名词,以及它们所指代的“物”,对于彼时初见它们的晚清人而言,是陌生、新鲜、“无名”的西方事物,将它们纳入游记书写时,如何命名,并由此达到一种对于他者的清晰的表述状态,往往折射出命名者的主体意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写过程中所发生的命名的转变,如从“肾衣”到“避孕套”,从“木马”到“自行车”的名称变化,背后涌动的则是主体的操控力量,呈现了书写者的精神变动与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可堪为我们追踪晚清士人的思想嬗变提供重要图式;与此同时,词语的变迁,既彰显着精神的动荡,对于语言自身而言,也意味着蜕变与更生,随着旨在考察西方这一目标的日趋坚定与清晰,那些颇具想象性、模糊性的命名逐渐转化为相对客观、平实的符号,英译外来词成为不少书写者的借用方法,单义性的、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多音节的命名新词纷纷登场,不自觉地冲击了固有的语言范式,带来了古文的语言新变。
一、 自造词命名:观念衍变与制词方式的迁徙
当晚清游者面对传统知识架构中未曾被概括,原有生存体验中未曾被经验的西方事物时,择取词语对它们进行命名,犹如为新生儿命名,充满了新鲜感与创造性。翻阅这批记录了异域见闻的域外游记,许多洋溢着奇思异趣的名称跳跃入眼,甚至让我们忍俊不禁,将它们与已成规则的命名做对比,会发现晚清域外游者的命名洋溢着蓬勃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如林针将照相机这一“物”命名为“神镜”,张德彝将橡皮擦呼为“擦物宝”,把望远镜称为“千里眼”、避孕套称为“肾衣”;斌椿将自行车呼为“木马”等等,不一而足。这类充满想象与联想、颇具主体能动性的命名,不仅涉及词与物的复杂的牵涉作用,还涉及命名主体的操纵力量与观念变迁历程。
以照相机的命名为例。林针在纪游诗草中以诗兼文的形式讲述了他所命名的“神镜”:
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形(有神镜,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顷刻留模,余详其法)。
照相机因为是中土前所未有的事物,并没有一个赋予它的强制性的语言符号,所以,我们看到林针在肆意地行使他的主权,表达他的感受与观念,它们集中体现在对“神”的表述上,“神”指涉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难以为人掌控的力量。林针初见照相机,惊羡于它能“指日留形”而呼为神镜,充沛地表达了他对这一现代器物的想象与向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以一种目瞪口呆的表情,观看超出他经验范畴以外的事物,“顷刻留模”让中国画家需要经历千辛万苦、精雕细琢方能成形的传统形构方式被颠倒了,现代相机在林针面前宛如神器;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进化的时差,使得处于西方文明序列中的林针成为仰望“神器”的观看者,而忽略了照相机的具体模型、构造与使用方法,林氏仅仅指出它能“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然后就跳过不提了,除了表示惊叹,他似乎丧失了进一步阐释的能力。
这种想象的、夸张的命名方式很快随着志刚的命名而消失,对照林针的“神镜”,奉命出使、旨在探究西洋利弊的志刚对照相机的命名,以及论述已经俨然上升到客观、研究的层面。志刚在文中以近乎科学的手法论述了他所见的“照像之法”:
照像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所谓化学之药者,西人率以硫黄、焰硝、盐碱等物煎炼成水,以之化五金,为强水。而各视其强力之水,化所能化之物,如磺强水能化金,硝强水能化银之类。[1](p.321)
被神秘化的“神镜”在这里被志刚赋予一个相当朴实的命名:“照像”,对照像法的追本究源,有关原理的枯燥分析,以客观、务实的现实力量颠倒了林针笔下的神话,照相机在此通过硫黄、盐碱等毫无感情色彩的词语说明被还原成为一种普通的、可以被认知的事物,它似乎在历史的隧道中嘲笑林针的“山川人物,镜中指日留形”的空疏和想象。此后,郭嵩焘等游者均沿袭了这一名称,改呼为“照像机”。这是命名演变并逐渐被固定的过程,它的固定方式与索绪尔分析的人造语一样“人造语只要还没有流行开,创制者还能把它控制在手里;但是一旦它要完成它的使命,成为每个人的东西,那就没法控制了”[2](p.114)。自从“照像机”的命名在志刚手里开始固化后,我们对照相机这一“物”的称呼就无法进行控制了,它成为再也拉不回来的符号。
针对照相机的不同命名方式充分展示了命名初始阶段,名与物之间的任意关系与命名者主体的操控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下,符号与事物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在没有成为社会固定规范时,有着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任意性?为什么志刚之后,对照相机这一“物”的命名的任意性便消失了,除了有个人的偶然性的命名缘故,它显然部分地与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历史相连。林针出洋是在1847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兵戎相见头一遭,但《南京条约》的签订,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中华帝国以“抚”代“战”的轮回。日本学者加藤祐二指出:“即使缔结了南京条约,清朝也不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们理解是为了施予恩惠而缔结了这个条约。”[3](p.362) 对于大多数晚清人而言,鸦片战争的西方冲击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反应,1840年到1860年之间,大约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指出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4]。从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语境而言,西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仍是一个遥远的、惯性认知下的对象,作为一名依靠在洋商处担任翻译以“谋菽水之奉”的下层士人,林针显然并未有着关于战争的刻骨触动,更无从自强、师夷的角度来观看西方的眼光,西方的零零总总,对他而言不过是“耳闻奇怪多端”[5](p.39)。
这便是林针命名的场域,是他得以依靠的社会总体意识,也是他只能勉为其难地以“神镜”这一富于想象性的名词对之进行命名的原因。
考究的、客观的笔法只有当明确意识到“西方”成为探究的空间与考察对象时,才可能会产生。志刚随蒲安臣出访美、英、法、普等国是在1868年到1870年之间,彼时已经过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清朝王室鼠奔热河。这一时段,朝廷上下对西方的认识正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晚清多数士大夫到1860年以后,开始觉察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来未曾见过的变局。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54—155页)统计,从1861年至1900年至少有43位士人认识到这种变化,并评价了这种变化的巨大意义,王韬把这叫作“创事”,丁日昌、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则称之为“变局”,随着对“变局”的接受,师夷长技等致用思潮成为诸多士绅探究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道路,西方器物与技术被看成足以挽中国之衰败的核心力量,可以说,1860年成为一条重要的界线,“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6](p.109)。正是在变局的忧患下,志刚奉命出洋。他处于朝廷惶恐不安、“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经世意识力量暗涌的语境下,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八旗世仆”,求国定、求自强的欲望溢于言表:“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者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1](p.253)更何况,在他背后是充满期待的朝廷的眼睛,“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1](p.384)。
这已经是一个旨在求强、师夷、亟须对西方进行了解的时代,志刚的行文内容与林针的奇闻搜录必然产生相当距离,对西方的观奇在此演变成一场精细的旨在有用于大清帝国的社会考察,它天然地反对不合实际的、想入非非的命名法,对照相机的命名,呈现的不仅是志刚个人的书写方式,还是他背后清廷睁眼看世界的诉求与师夷长技等经世思潮的凸显。 对照相机的命名考察,让我们看到了纵深空间中因社会意识变迁而导致的命名的衍变,呈现了背后观念变动的力量与社会总体意识的权力机制。
从词语层面而言, 志刚之后,域外游记中的“异”物命名渐趋客观化与描述化,基于想象并蕴含多种可能性的命名词语似乎消遁了,域外游记中的“异”物命名,如“照相机”“织布机”“缝纫器” “自行车”等,都是基于实际功能的单义性的命名,它们身上不再负载文言文中约定俗成的意义元素,也收拢了富于个体想象与文化象征意味的羽翼,而成为指向单一、含义明确的语言,这一变化固然部分地与非语言因素相关,如上述所言的社会总体意识的变迁、人文精神的嬗变等,但是,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命名方式的迁徙首先是狭义层面的词语制作方式的迁徙,即从多义的、模糊的构词集体迁向单义的、明确的构词,这是呈现于晚清域外游记中一类普遍的词语运动,颇具一致性的、日趋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新词的大量出现,显然表征了一种现代汉语的形构方式正在集体形成,也有力证明了汪晖有关现代汉语形态及其形成的论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而言,评价现代语言、进而现代文学的尺度显然是:恰当、精确和真实。”“宇宙、自然和人自身在这种精确的语言中只有一种展现方式,从而古代语言所展现的宇宙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日渐地消失了。”[7](pp.1136-1142)
从“神镜”到“照相机”,从“木马”到“自行车”,诸如此类命名的人为转换,不正意味着存在大量模糊空间、足以展示事物多种可能性的文言文开始被摈弃,一种单义性的、明确指向现代事物的新词逐渐成为普遍的词语形态吗?此段论述参见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14年版第5期。
二、 音译词命名:多音词与欧西文思的传达
晚清域外游者在把握全然陌生的西方事物时,勉为其难地因袭固有语言对之进行命名,这种命名方式毕竟是危险的,一不小心,词汇就会成为惯性思维的产品,反而让读者步入被误导的迷途。如何相对准确而客观地传达“异”者,将命名的另一种方法提上了日程,即尽量沿袭异域语言,以音译或者半音译的方式力求准确地命名“异“物,这种类似直译的命名方式,不但以最直接的方式传达外来意义,而且它背离文言词汇的形态,往往会让文言文显得格外触目,带来了古文语言层面的新变。
梁启超曾从新名词的现象来归纳语言的变化“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万流汇还、群族分孥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可如何者也……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8]语言体系并非自足、平静的同质系统,随着世易时移,语言往往会发生相应的变异,新词的出现则是语言运动的重要成分,带来文体日日新的音译词在域外游记中层出不穷,呈现了古文的语言新变,典型如黎庶昌在描述热气球时所使用的语言:
球皮用布缝成……其大径三十五买特尔,围圆一百五买特尔,容轻气二万六千建方买特尔,空中压力每建方买特尔重一百吉罗。司球者云,若无绳可升至四五千买特尔,再上则人不能呼吸。[9](p.487)
上述短短的引文便引入了买特尔、轻气、吉罗等西方名词,而且这些名词并未经过作者的特意解释,而成为直接侵入文言文的语言成分,它们似乎与前言后语连成了一片,成为作者自以为然加以运用的词语。与黎庶昌类似,一向固执守旧的刘锡鸿在面对西方大量的新事物与新观念时,也迫不得已大量援引外来词:
西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克莱斯参司衣符(即耶稣降生之前一日),西洋各国以此为令节。先期十余日,饴糖果、饵玩具器物……如中国之贺新岁。至期,官学给假, 雇佣停工,商贾百艺,咸各休息,或游猎,或宴会,或结队诵经礼拜堂,熙熙如也。[10](p.224)
上述引文中“买特尔”“吉罗”“克莱斯参司衣符”(圣诞节)等西方名词的引入,不但对固有语言层面造成了触动,而且作为“能指”的符号,这种词汇内部的组合方式出现了从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王力先生曾指出:“中国语向来被称为单音语,就是因为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词,现在复音词大量地增加了,中国语也就不能再称为单音词了。这是最大的一种影响。”[11](p.339)文言文多为单音词,几乎每个字都有自己独立的意义,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足体,并衍生出文言文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意蕴,这就使得古人津津乐道于“炼字”,可以为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上述种种均表达了文言系统对单音词的倚重。而通过半音译、音译等方式被纳入书写的外来词,则多为复音词,必须在字与字的整体勾连中才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如果将词分开,则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比如,“买特尔”三个字连在一起,表达了对西方测量尺度的一种描述,相当于现在所指的“米”,但是分开来,组成词的三个字基本上失去了语境中的意义,成为无指涉的、无根的字的漂浮。同样,“克莱斯参司衣符”如果分开,更成为各奔东西的字符,这种必须连在一起方能体现意义的复音词的出现,正是现代汉语思维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趋势。黎庶昌、刘锡鸿于游记中大量引入这类音译词,并且将之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成分,显然冲破了文言文雅顺的固有面目,在文言向现代语言的转变上起到了开化的作用,而背后引入的西方的度量理念与宗教观则可谓随着新语言的进入而潜在产生影响的西方观念。
黎庶昌、刘锡鸿笔下中西杂糅的语言变动至梁启超的游记书写则更为明显,甚至是有意为之了。早在书写《新大陆游记》之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便于《汗漫录》提出了文界革命:“其文雄放隽快,乃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2](p.604)
梁启超冀图效法日本的文学改造,期望通过对现代理念与西方新名词的引进来构造新文,为此,梁启超为他所倡导的新文体做了如下定义:“启超素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条例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13](p.70)从上述倡议,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所言的文界革命便包含了对古文的自觉反叛、对西方语法以及词汇的积极引入等,反映到他的游记书写上,也多呈现为一种半文半白混杂外国词汇、夹杂现代语法、语义的过渡形态:
托辣斯者,原文为Trust,译言信也。其用之为一特别名词者,自一八八二年,其大盛于最近之五年中。托辣斯者何?以数公司乃至数十公司之股份之全数或过半数,委托之于所谓“托辣斯梯”Trusty者(即可信之人之意);而此“托辣斯梯”(或一人或数十)发回一证券于股东。自此以后,此托辣斯梯有全权管理各公司之营业,或分析,或合并,或扩充,悉听其指挥,而以所得利益分配于股东。托辣斯者,以政治上之现象譬之,则犹自各省并立而进为合众联邦也,自地方分治而进为中央集权也;质而言之,则由个人主义而变为统一主义,由自由主义而变为专制主义也。[14](p.20-21)
显然,在曾为文之大宗的散文写作上,梁启超并未如小说实践一样,大量运用俚俗和口语,而是保存了文言的典雅与规训,这种貌似具有文言躯壳的文体与俗化的古文又截然不同,其字里行间既有铿锵的韵文排列,又有欧化的长句,西化名词更是层出不穷,证券、自由、公司等外来新词直接入文,所阐释的道理则远远凌越古文义法之外,譬如,“证券”不仅是一个西化的舶来词,其内涵及其意义也均隶属于西方现代经济理念,大量这些颇觉生硬、刺眼的外来语在当时“规范”的文言文书写中是不可兼容的,但它们被梁启超杂糅一体,形成恣肆、浅白的文章新“范式”,如今这些被当时人讽为“野狐禅”的语言,绝大多数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惯用语,直接引用“trust”这一英文原文,这在古代散文中也是从未见过的语言现象,因此,这种半文半白、半中半西、长短相间的文字纠缠,充分显示了过渡形态语言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除了语言躯壳上杂有西语与外国语法,梁启超在使用英译的新名词时,还不自觉地将“欧西文思”传达于读者:“公司”与“股份”之间的关联,“证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托辣斯”作为全权管理机构的权力行为等,它们所附属的是西方现代工商体制,所遵循的也是现代管理理念,与梁启超所言的“合众联邦”“自由主义”一道,都属于“欧西”之思,梁以此现代理念与现代词汇入文言文,势必使得从理念到语言躯壳均发生变化的游记文本无法被纳入到传统古文范畴之中。
对于约定俗成的语言,索绪尔认为,如果不遭遇重大革命,往往只有微妙的嬗变,一旦语言开始呈现日趋强烈的变化,往往与外部环境的变动有关,“如果民族的状况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态,继续它的合乎规律的进程”[2](p.210),晚清域外游记所发生语言裂痕显然与晚清这一动荡时代相符合,可谓合乎规律的自我更生的变化诉求。
三、命名的反面:谜面式书写
以自造词、音译词对域外“异”物进行命名,这可谓晚清域外游记中一类普泛的书写现象,然而,除此之外,晚清域外游记在面对“异”物时,还存在一类特殊的书写情势,即面对超出经验范畴的“异”物时,游者无力寻找词汇对之进行命名,而权宜采取一种对事物特性进行列举与强调的方式来暗示“那个”将生未生的词,或许并不能把这种书写情况归于命名层面来进行讨论,但是,这一书写过程展示了一种制造命名或者新词汇出现之前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它们有着因果关系,与最初走向世界的那批晚清游者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书写某个具体事物时,让读者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名称,已经成为我们描写的惯性,不然,作者与读者就会处于一种沟通断裂的状态,如一名作者在描述“梅花”时,如果他只道“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不在标题上表明是《山园小梅》,那么读者可以理解他所描述植物的是荷花、水仙或者栀子花,甚至有可能联想到风华绝代的美人,正是因为有了“小梅”的命名,上面清丽的诗句才被历代奉为咏梅绝句。因此,如果作者在描述中并不道明这个事物被指称的代号时,对于“物”的匿名式描述便可能成为类似于谜语的叙述。
初出国门,乍然进入西方现代文明世界的晚清游者,面对让他们眼花缭乱的异物,他们往往选择一种大赋式的方式对之进行铺排、描绘,对这些未曾被经验、未纳入认知框架的事物,迟迟不给予一个具体的命名符号,当我们读到下面这些对于“异”物的文字编排时,不免进入猜谜的状态:
“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之详)。”[5] (p.37)
“ 初患无水,故沿开至百里外,用大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且积水可供四亿人民四月之需。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而平地喷水高出数丈,如天花乱坠。”[5] (p.37)
“ 客寓楼七层,梯形如旋螺。登降苦劳,则另有小屋可容六七人,用火轮转法,可升至顶楼。屋有暗消息,手一按,则柜房即知某屋唤人。”[15] (p.107)
上面所引录的三段文字,如果我们忽视惯有的现代经验,从一种陌生的眼光来进行观看,可能变成一次无穷尽的猜谜之旅。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道:“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之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谜语,特别是在打一物的谜面书写中,往往是“或体目文字,或图像物品,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对作为谜底的“物”进行穷形尽相的描写,让人在欲隐中追溯它的“显”。上述所引录的几则描述,它们俨然遵循了“打一物”谜面的表述形式,即从形状、构成、作用等层面对隐藏背后的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说明,第一段引录不但说明此物的构成成分,而且对构架的距离、字母的数字都有着细腻的呈现;第二段引录部分甚至从事物兴起的缘由讲起,对该物的功用以及外在形态无不予以详尽的描述;第三段引录对小屋的空间形态、内部机关以及功用都有着清晰的说明,它们与谜面一样有着形象化的表述,甚至不乏纤巧的构思,但是,它们是不向读者公开谜底的谜面,谜底永远藏在书写者的意识中,他“知道”是什么样的事物,他见过这样的事物,但是,他不告诉你它是“什么”。
以我们现代经验与常识,我们可以从容地猜出上面三种描述指向的是电报、自来水和电梯等三种现代器物,但是,如果从晚清读者的眼光出发,因现代经验的匮乏,便会陷入与猜谜所类似的状态,比如,“巧驿传密事急邮,支联脉络。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到底指的是什么,似乎与驿站、邮件有关,但“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却是晚清彼时固有经验中未曾拥有的东西,虽然林针在诗句后面又做了细致的描述“每百步竖两木,木上横架铁线,以胆矾、磁石、水银等物,兼用活轨,将廿六字母为暗号,首尾各有人以任其职。如首一动,尾即知之,不论政务商情,顷刻可通万里。予知其法之详”,这类描写愈细致只能愈加促发读者的想象 ,读者可能因此把它想象为由水银等物质制造的蛇一类的东西,因为作者并没有在描写背后如谜语一样给予谜底,此类描述就更成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形象了,因为缺乏一个归纳性的命名,甚至会成为各类奇奇怪怪的想象物。
这类谜面式的、匿名式的对“物”的书写显然并非出自作者本意,恐怕更多源于书写者西方经验的匮乏。我们可以先来考察一下斌椿等游者的境遇与可能拥有的知识经验,斌椿曾在诗中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16](p.189),他可谓鸦片战争以后,因缘际会出洋的首位使者,彼时,国门乍开,西方的身影已经浮出地平线,但如何走近乃至走进它显然还来不及计划,面对这么一个陌生而强悍的文明实体,晚清士大夫对于它的主动认知,仍停留于纸上谈兵,此时,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姚莹编撰了《康车酋车酋纪行》,徐继畲刊印了《瀛环志略》,有关西方的地理的、文化的知识开始为知识精英们所探究,但这类好奇终究是过眼烟云,西方具体的人与物仍旧是一团混沌而遥远的庞大存在。林针、斌椿作为西游的先行者,他们处于这么一种西方经验严重匮乏的时空场域下,当他们乍然需要来把握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现代事物时,显然还不具备对之进行清晰命名的能力,斌椿为此慨叹这种无力感:“其国人之官爵姓字,以及鸟兽虫鱼草木之奇异者,其名多非汉文所能译,姑从其阙。”[15](p.144) 更何况,林针、斌椿出洋时,帝国天下的中心文化意识,依然是他们不容置疑的真理,异域之旅于他们更似一种搜奇揽异的经历,林针在《西海纪游草》结尾吐露心迹:“山海奇观,书真难罄……生逢盛世,岂甘异域之久居;略叙游踪,思补职方之外纪。”斌椿于《天外归帆草》谈及他此行的观感是“言语重译通,人物具奇致;鸟兽与虫鱼,大半多怪异”[5](p.187)。对于林针、斌椿而言,所置身的西方现代文明世界不过是山海奇观的异域,是异于自我的并且在文化层级上低于中土文明的他者,这种对于文明层级之下的他者所关注的是“奇”与“异”,对“异物”的概括与归纳自然成为不需要费心的事情,于是,“无名”的描述成为西方事物片段式的蔓延与展览,它们以无名的、纷繁的状态共同构筑了林针、斌椿们的山海奇观,而这种谜面式的书写情况,在日后志在探其利弊、“以期有所知者贡于祖国”[16](p.419)的游记书写中几乎消遁了。
四、结语
舍勒曾说:“词语意义还有一种力量——确定我们在自身体验和他人体验上所感知事物的力量。”[17](p.196) 词语的发生、衍变与陨落往往与书写主体的个人经验与意识变动紧密相连,而于命名活动中显露痕迹的词语,有关它们的出现、变化乃至零落,自然绕不过命名主体的操控力量,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肯定,晚清域外游记中所发生的命名活动,始终与晚清游者的主体意识与域外经验紧密相连,其中所呈现的命名词语的衍变清晰地展示了晚清士人在面对西方他者时,如何调整观看视域、更新认知图式的意识变迁历程,成为我们触摸晚清文化心理嬗变的一条有效线索。
[参 考 文 献]
[1]志刚.初使泰西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瑞士]费南迪尔·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日]加藤祐二.讨论日本文化与江户时代[C]//依田憙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4]黄钧宰.金壶七墨[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5]林针.西海纪游草[M]长沙:岳麓书社,2008.
[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7]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梁启超.新民说[C]//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9]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4]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5]斌椿.乘槎笔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7][德]舍勒.自我认识的偶像[C]//舍勒选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