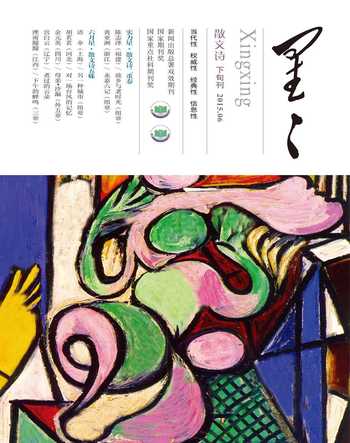另一种城市(组章)
语伞
门的可能
我抚摸满身透明的颗粒。“你好……”一扇门,迫不及待地邀请你。空气中有花瓣的微毒,我逐渐升高的体温,忍耐着切割掉多余的热度,只是在原地,跳起了小步舞曲。
在敞开心扉之前,我虚掩脸颊。没有谁引导我,无数个我宿命的基因,就在城市的子宫里孕育。拜认钢铁为父,竹木为母,辨认玻璃、塑料为同胞兄弟姐妹。最后,我只成为用唯一的胎衣包裹着的,那个我。
这个我,深藏安全感和秘密,只接受你冥冥之中的一次驻足,你凌驾于玄奥之上的脚步,只接受你,偶尔也曾有过的,一瞬间绝望的眼神。
为了获得那个确曾是我的自己,我把身体藏了起来。
为了看清迎面走来的空旷的你,我又穿上影子的长袍。
第一道反光是面孔。第二道反光是年龄和性别。第九道反光,是一双具有魔力的手。推,或者拉。打开,或者关闭。我在你对面,或者你早已经过了我。你重复经过我,或者所有人重复经过所有人。
天花板上的城市
无法抵达两个相同梦境的时候,我低于,房间的另一种结构。
躺在床上,认真地注视天花板,仿佛我失眠的眼神得到了某种特别的眷顾。
一个城市在天花板上说话,眼睛上面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我必须重新组合我与天花板的关系。
望着满街倒立行走的人群从各自的门里出发,他们的姿势像银河里的星辰,飘移,飞奔,或者冒险,被无垠的天空所诱惑。我把赤裸的手臂从被子里伸出来。我想接住他们,比接住自己未来的影子更迫不及待。使他们平安,使他们从我手中再次打开门的时候,能在脚下储藏更多的光芒,从此不惧怕漫漫长夜的黑。路上隐约可见一些鞋子和石头,鞋子和石头有时为了一毫米的地面打架,没有人低头去捡拾它们。缓解一场刻意的闹剧,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最终将归于平静。
天花板骄傲起来。一个城市骄傲的样子其实很美。或许她应该有一个演奏霓裳羽衣曲的广场,有一座庄周梦蝶的花园,有一片十面埋伏的绿地,有一幢没有主人的高楼……或许,它们应该像房间里的床一样,时刻等待困倦的人归来。
软月亮
城市的正上方,月亮将脸谱高悬。
我坠入悬空的蜘蛛网。这座城市有闪光的格子线条,她结实的桥墩和螺旋状的道路,是图案中颜色最深的那几笔轮廓。我抓住天空与高楼之间的那点想象,爱得迫不及待。
你在纸上活着,活在我的整个城市里。
我的眼睛是你的展厅,一道敞开的门,供你精密的思维兑现文字,让他们适宜观看、收藏,最后,你残留在我的心脏上,像充满艺术气质的碎片。
那些在出生和成长中都伴随着我的旧东西——棉布、稻谷、房子、炊烟、忍耐和无休无止的游戏,正从我身后返回,比抢占战争的阵地更加激烈地,抢占着我的记忆。
你知道城市里,有我便于搜寻自我的望远镜。
一枚月亮的脾气和态度,就是促使望远镜把放大的生活细节又重新粘连在一起,使我落在阳台上的手指,搅动月色,成为霜、雪、雨、露、血液和眼泪的替代物。
所以月亮是软的,渗透在我的身体里。而你,看到了她尖利的光亮。
花瓣里的城市
“我只把香气赐给月亮的圆缺……”
你捧起脸,比早晨醒得快,从天空的格子抽屉里取出一些高楼,把谋生的人群装进去。
而我不能准确地说出我还看见了些什么,人们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接近花朵含苞的样子。你在我的表象里绽放,这人间的深层涵义,就在你的花蕊里隐居。
我朗诵一株美人蕉就是在朗诵你,我朗诵花瓣里的你就是在朗诵一座城市的爱情。我见证这微醺,这袭来的美和孤独,仿佛我的芳香也沿着空气的纹路扩散,柔软的星子的余光,在一个清晨,漫过我的身体。
一座城市住在一朵花里,就像一个人住在另一个人的心中。
暗喻的城市
那时几何形状离我很近,有建筑般突兀的喻体高高矗立。
我把我当成几何形状的一部分。
我在你的脸上,认出了一把熟悉的钥匙。我危险的名字说起我们的生活,秋天的舌头上,就结满了暗喻的果实。
我抱着光洁的想象上班,写诗,与饥饿妥协,寂静无声地经过人群,经过你身体的缓慢和匆忙,偶尔驻足,偶尔穿梭在你创造的本体中,取下另一个遥远的城市,做我的喻体。
简单的手,简单的嘴巴,简单的眼泪和痛,简单的思维和安于简单的心,简单得像一幢刚砌好的不懂人情世故的砖墙,拒绝了水泥和石灰粉的巴结。
没有意外的玻璃割疼我,没有多余的火焰燃烧我,我可以脱去一身潮湿的噪音,行走在命运干瘦的沙粒上,听你读整个世界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