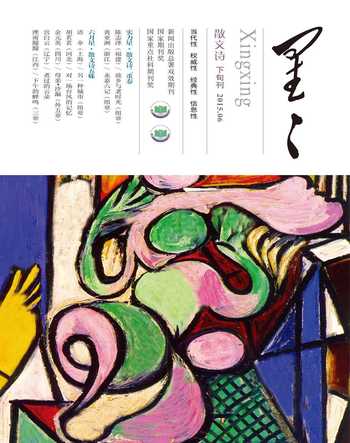母亲·沙漏(外五章)
余元英
如果一定要描出母亲的形状,我宁愿相信她就是一个沙漏,她用牵挂把自己紧勒,一头是儿女,另一头还是儿女。
自母亲生下我们三姐妹,本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却能精准的把自己的心等分成三份,女儿,女儿,还是女儿。
长大后,母亲是重力之下的细沙,一会儿流向带娃娃的姐姐家,一会儿流向坐月子的妹妹家,一会儿挂念着一个人在外的我。至于她自己,她更喜欢把自己留在沙漏的狭窄的细颈,甚至伤痕累累。
母亲说,只有这样,不管我们飞得再高再远,我们都不曾离开她的身体,她的心。
选择玻璃球的封闭,就注定失去一片沙漠的广袤。
母亲,我无法想象你用了多大的勇气,拒绝娇艳的仙人掌以及被风吹远的驼铃声,义无反顾将生活过成奶奶的浓茶、韭菜的嫩绿、我的小脾气。
母亲,我可以想象,要是你不在了,我就认每一粒沙子为母亲,只要我轻轻地呼喊你,整个沙漠都会替你唤着我的乳名。
离去,是我的温柔,也是你的
我转身的那一瞬,是否已将我灵魂里闪光的萤火虫放逐到你的夜?
当一些微光义无反顾地泛起,我们谓之为黎明。我来时和离开时,你的表情是那样的相似,就像日子本身复制了日子。
别怪我用车轮描绘远方。离去,是我的温柔,也是你的。只是我将老屋粘贴到我的诗行时,有些歪斜。
你时常说及玉米接近阳光,说及小侄儿开始开口喊外婆,说及年迈的父亲还能背起一袋大米健步如飞,也说及我离开时,风吹了一粒沙子在你的眼里。
可你雨天就要疼痛的风湿,却忍着不说。
好久不见
人们常说,走着走着就散了。的确,走着走着就散了,散了就再找不到向心力了;笑着笑着就流泪了,流着流着就忘了,忘了就又开始义无反顾地走着走着……
没有风的时候,我喜欢站在湖边,看水鸟盘旋,从未停止飞翔,也从未找到走失的自己。如我,从未停止流浪,也从未见过远方。
湖面泛起涟漪时,我将自己交给风,随它起飞,跌落,再起飞。循环往复中,我从未停止点亮自己,因为我不想让你伸出的双手在夜里失落。
对于爱情,我只想做那个傻傻的农夫,背靠着我愿用一生守候的树桩,等待我一直等待的那只小笨兔撞上我的柔软,我的心,然后说一句“好久不见”。
等待下一个春天
未曾触摸春天,我们就已将各自的码头交给春风,为百花腾宽追逐硕果的路。
阵阵花香,我却不敢回望繁花似锦的场面,如春运的车站,每一朵花都在用生命挤拼,用储蓄一个冬季的力量,把自己尽情的开成鲜血的红,铮骨的白,等待生活这只蜜蜂疼痛而又幸运的一箭,救赎一片花瓣过早地凋零。
春天,我不做采花的人,我只要做一个隐者,像蝙蝠悬挂在柱头,让黑夜掩藏花瓣盛满了的遥远以及我酒杯的虚空。只是我脱口而出的沉默还能在下一个春天喧嚣吗?
花开,是诉说,是静默
梨花开了,是心碎,洒满天。
云朵向着太阳飞翔,从未抵达太阳。蜜蜂向着花蕊诉说,从未让一朵花儿孕育出静默。
我不敢随意牵扯一抹风,我怕飘落的花瓣会成为伤害你的刀具,留下深深浅浅的血红,成全漫山的桃花。
我不敢轻易招惹一只鸟,怕它的悲鸣让我接近你的码头,从一只破旧的渔船感受到墓碑的冰凉,以及悼词里抹不掉的悲怆。
你说过通往灵魂坟茔的暗语是白色,正如梨花开时,死去的人期待在这无与伦比的白中醒来,活着的人渴望带着这份纯洁的白睡去。
而我呢,还猜着半梦半醒之间谁会与我对白?
怕黑的人,站在最深的暗里
夜追随夜,昏黄的路灯与黑对峙,偶有经过的车辆或是破碎的酒瓶,才会打破这僵持的局面。
黑,是一块海绵,柔软。柔软成父亲的轻咳,母亲的呼吸。我喜欢用乡音这滴水饱满黑这块海绵,黑就家乡一样沉甸甸了。
夜里,我憎恨蛐蛐儿的假慈悲,一声两声,试图把村庄搬进月光,让漂泊的我误以为还停留在儿时看守过的玉米地。
我是一个怕黑的人,可我始终站在最深的暗里,抱着温暖或者疼痛的黑,抵挡酒杯中虚拟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