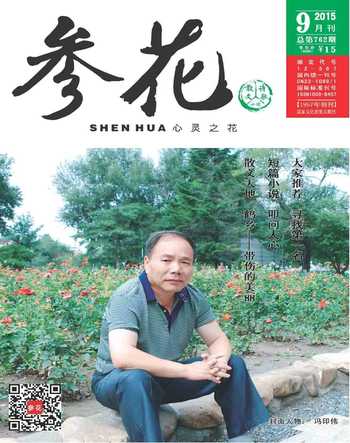简论荀子哲学中的“天”“学”“礼”三个概念
吴尚志
一、荀子哲学中的“天”
《四库全书总目》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持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于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1]
此段话道出了荀子之学的大体,即“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如果再加上‘化性而起伪这五个字,就是对荀子精确而全面的理解”。王博此论虽“精确”但不“全面”。他忽略了中国哲学主要问题中的第一大问题:天人关系问题。宋志明提出了中国哲学所包含的四大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两一关系问题、知行关系问题和义利关系问题[2]。“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讨论犹为激烈,也正因此而引发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天道学进路和人道学进路。前者以道家为代表,而后者的当然代表则是儒家,荀子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学巨匠,当然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哲学立基,展开恢弘论述。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3]306-307
荀子在《天论》开篇即对“天人关系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天的运行有其常道,无关人事的吉凶祸福,而人事的治乱也有其法则,应不以人事的殃祸而怨天。因此须明了天人各有其道,天人的运行应治也各异其则。同时,他还说:“治乱天邪?……治乱非天也;时邪?……治乱非时也;地邪?……治乱非地也。”[3]311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3]311
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荀子想天人相分之道。因此,荀子所论之天可看作一种自然之天。冯友兰先生对此亦有论述。然面对这强大的自然之天,荀子并非无能为力的,相反,荀子更加强调,尽管天行有其常道,而君子应自强不息。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物理而勿失之?愿于物之所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3]317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荀子的儒家人道学进路,他讲天,最终的根本还是落实到人上,因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人更应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如此方能“天地官而万物役矣”。
二、荀子哲学中的“学”
“学”是荀子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他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3]443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彊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3]439
荀子一方面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又道出了现实,突出了“学”的重要性。“由学以致圣”的思想路径,在《论语》中已见端倪,到了荀子则表达得更加显豁。《劝学》之所以安排在《荀子》各章之首,由此可见“学”在荀子哲学中的地位。“荀子论述的角度,主要的不是和知识相关,而是和德性与生命密不可分,在荀子看来学习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塑造和提升的过程,或者一个道德生命成就的过程。”此道出了“学”的意义,即在荀子中,“学”更重要的功用在它能以“伪”来“化性”。而具体的“学”的内容主要是经典所代表的先王之遗言。
因此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后止。夫是之谓道德之极。”[3]11-12
荀子对经典学习的重视,强调“学至乎礼而后止”,因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是荀子“由学至圣”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人之性恶”的遏制,是荀子对当时社会的下层民众所给予的希冀和开出的药方。由“学”以至于礼义并以礼义之道来规范身心,除去性中之盈满和泛滥,使其中的不正以归于正并长期积习,进而成圣,这即是“学”和“积伪”的过程。正如《劝学》篇的首句:“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矣。”此学即修身,而修身亦学也。
三、荀子哲学中的“礼”
荀子哲学的另一基本范畴即是“礼”。在荀子看来,这关乎整个学问的宗旨,隆礼才能知其统类,得其经纬。同时“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所以“古者圣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和于道也”。故国家之治理应遵先王之道,实行礼治。荀子对“礼”的思想的论述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治理层面。因此,他在《礼论》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346
不难看出,荀子认为,礼起于欲,而礼的最终作用又是养欲。人皆有好利穷欲之心,顺是,则必将起争乱,故先王制礼以度量分界,使物和欲“两者相持而长”。“礼”的首要作用是“分”,“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定“礼”行“义”,并以此来规范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所有行为,使“分”得以顺利实施……既能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求,又能使人们各就各位来保证社会安定有序。因此,荀子才会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3]490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3]178
纵观《荀子》全书,“礼义”“礼治”实际是圣人“化性而起伪”以治理天下的核心内容,并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礼义”的兴起源于人欲,是对人欲泛滥的节制。与此同时,荀子把“法”置于“礼义”的从属地位,在荀子看来,礼是法的纲领,法在礼的基础上产生,“礼义生而制法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此即荀子治理社会的“隆礼重法”思想,荀子对礼法的特别重视,是源于他当时的社会实际境况和他由此而得出的“人性恶”的判断,因其对“伪”的重视使得他想以礼法由外而内地对人予以规范和教化,这与他重视学的思想目的是一致的,即范围人心,消除纷争,而使社会归于正理平治。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统观荀子的思想,他从“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视角出发,进而着重论述了人世,运用“学”以修身,“隆礼重法”以教化,从内的方面正理人心,而从外的方面平治社会,使之归于善政,恢复周孔之教。
参考文献:
[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770.
[2]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4-50.
[3](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作者系云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学术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 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