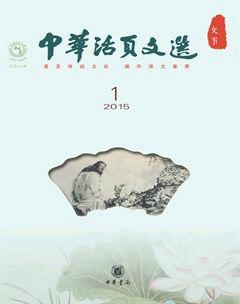炼出一颗丹来
蒋平
互文关系,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关系。新的文本,总是在旧的文本或历史文本的基础上发生,因此互文性写作的每一个碎片,呈现为一个“虫洞”,读者可以穿越它而抵达另一时空。《文心雕龙·隐秀》所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用互文性理论来表述,就是任何文本都处在一个巨大繁复的意义网络中,无法摆脱从“隐”、“奥”的源头“派生”出来的多义或歧义。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学文本相当于一个能指、一个词,它是对某个所指、某个对象的表达。她首先从语词之间的反射与交织看到了文学文本之间的反射与交织。
也就是说,现实文本中都有一系列“寄生的”东西,即存在着对以前作品的模仿、借喻,乃至存在着以前作品的某些主要精神。而对已有文本的词句、引语、“镶嵌”进行解读剖析,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借此认识到作者言说的意义指归。因此,在语言创新上,互文性是大大增强语言和主体地位的一个扬弃的复杂过程,一个为了创造新文本而摧毁旧文本的“否定的”过程,这是一次语言的升华与蝶化,是新的话语在已有的语言文化的基础上的纯粹。
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一文中存在着大量的互文性现象,本人试图通过对互文性语言进行剖析,以揭示语言生成的文化线索,还原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
首先,文中有较多的引语,有的明引,有的是暗用。暗引如“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其中的“杏花,春雨,江南”六个字,在语言形式上与元代散曲作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的意象组合方法一致。马致远廖廖数语,便将人在天涯的羁旅游子之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语言形式,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这首小令,引发遐思。然而在内容上还是有来历的,唐代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诗记叙了行人(出门在外的路人羁客)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情景中,孤身一人,在他乡异地赶路回家中的情景,表现了他的孤独、凄凉、烦乱、惆怅之情,行在路上,忧郁愁苦,简直要断了魂似的,内心十分凄迷哀伤。行人自然想:最好在附近找个酒家,歇脚避雨,饮酒解寒,借酒驱愁。于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的回答以行动代替语言,行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盛开的杏花遮掩着一处村庄。清明节,传统有与亲友结伴踏青、祭祖扫墓的习俗。
这六个字,三幅画面,引发作者无限的乡愁和对故土的深深眷恋。春天杏花盛开,以美景衬哀情;而春雨纷纷扬扬,潇潇未已,这“雨纷纷”,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着实令人惆怅;那大陆的江南,那故土,这是清明祭祖,告慰已故亲人的时节,“我”已无法回到那边,只在台海之隅悲念。那凄冷的雨点点滴滴在“我”这游子的心头。
赵涵漠在《回家的路》一文中写高秉涵“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旅居台湾”的菏泽同乡老人“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文中强烈地诉求了在台湾的大陆人渴望回家的情感,身在台湾,心眷念故乡。而于右任《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表达了对大陆的无限思念。这种乡愁情结在余光中先生的《乡愁》“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与《招魂的短笛》“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等诗篇中都有吟唱。
“杏花,春雨,江南”这句所浓缩的三幅画面承载的正是这种厚重的情感。
“引用”在本文中表现为:
①直接嵌入式,如: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作者直接将杜甫《望岳》诗、姜夔《点绛唇》词、王维《终南山》诗中的有关“云”、“雨”的意象融入自己的文本之中,表达在异国他乡是无法看到那么美丽的雨趣云意的境界的,如果要看,仍然要回到大陆那头才能见到。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认同。
②诗化散文式镶嵌,如: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这里作者巧妙引用了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在语言上作了扬弃: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这种笔法,较之于词而言更趋散文化,而诗词之神韵犹在,只不过借此来言自己的情感,于今回味起那大陆的秋雨不仅“凄凉,凄清,凄楚”更有一层“凄迷”了!古今映衬,抒发对那冷雨的独特感受,那种隔海之痛!而同时也表达了十年之前作者的丧子之痛、生死之无常之叹。1963年冬,余光中、范我存夫妇唯一的儿子诞生仅仅三天即夭折。悲欢离合总无情,作者于1963年12月作《鬼雨》一文,其中写道:“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雨在海上落着。雨在这里的草坡上落着。雨在对岸的观音山落着。雨的手很小,风的手帕更小,我腋下的小棺材更小更小。小的是棺材里的手。握得那么紧,但什么也没有握住,除了三个雨夜和雨天。潮天湿地。宇宙和我仅隔层雨衣。雨落在草坡上。雨落在那边的海里。海神每小时摇他的丧钟。”这就是作者自己所经历的“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从《鬼雨》全文来看,情感已超越了个人的悲痛,具有浓重的宿命意味。
③意引式镶嵌,如: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这里概括了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中的有关语言碎片:
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一方面作者借此来抒发家园之思与文化恋慕之情,另一方面难道不是古人古事以证“恬然自安”之情吗?
④意象呈现法,如: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这里作者用“布谷咕咕的啼声”这一文学意象来呈现,布谷鸟即杜鹃鸟、鹧鸪,古诗词中的杜鹃常常是凄凉、哀伤的象征,诗人常常用以表达思亲之情,归家之念;“杜鹃啼血”常用以表现环境之凄凉,白居易《琵琶行》中“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句,就是借“杜鹃啼血”来渲染江州的荒凉,表达自己被贬江州的哀怨之情;也有用“杜鹃啼血”来比喻忠贞的,如文天祥《金陵驿》“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而余光中先生用“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来传达出那种无限哀愁之感,布谷咕咕的啼声里有思家之念,有离愁,有凄凉,有哀怨……抒写的是一种渴望。
其次,在语言形式上,大量叠音词的运用,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词汇形式上的推陈出新。《听听那冷雨(节选)》有五十多处用了叠音词,叠音词的运用,使语言有了音乐的节奏感,同时突出了事物的形象特征,有助于表情达意。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有很好地说明:“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暳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也有的是双声叠韵词的运用,如“……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句中“忐忐忑忑忐忐忑忑”七字的双声联绵复词,“摹拟出大雨滂沱的声音以及作者雨夜倾听雨势而随之起伏不定的心情”。
《听听那冷雨》又融入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仿佛作者在雨中沉思回忆,是作者的心理世界、记忆世界、隐秘世界的显性呈现,以冷雨为意象中心作心理散点式透视。因为我国的古文是不用标点的,所以作者在文中个别地方也有意地不加标点,如: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
事实上可以断句为: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
而原文的佳妙之处在于:语言如连珠一般,一气呵成,不可阻遏。
所以这个文本无论在语言的文化内涵方面,还是在语言形式方面,既有纵的继承与创新,沿袭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血脉,又加以新的创造;同时又有横的移植,借鉴西方现代小说创作的手法,凸显人的心理情感意识和回忆闪现。
余光中在散文集《逍遥游》的“后记”中指出:“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又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
《听听那冷雨》确实非同凡响,是余先生的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全文如同一首交响乐,或昂扬激越,或低沉悲凄,融铸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人生感悟,表达了游子对祖国对故土的依依眷恋,对传统文化的慕恋与追怀,是作者在中华民族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的一粒赤诚之丹!
一个新文本是由无数个前文本的交织、映射、叠加、组合而形成的,文本是互文的时空,其中又深刻地融入了作者的生命!
参考资料:
1.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陈蒲清校订,阙勋吾、许凌云、张孝美、曹日升等译注《古文观止》,岳麓书社。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附词语简释》,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