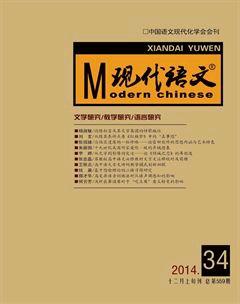论中国方言写作文学传统对陈忠实文学语言的影响
摘 要: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大量撷取方言土语,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域色彩,他的文学语言受中国文学史上方言写作传统沾溉甚深。他把当代由柳青、王汶石等老一代作家所奠定的方言书写经验吸收、改造和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中,走出了一条既承传前人,又超越前人的独特创作道路。
关键词:陈忠实 方言写作 文学语言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大量撷取方言土语,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地域色彩,他的文学语言受中国文学史上方言写作传统沾溉甚深。古今中外文学史上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方言写作传统,陈忠实在改革开放后阅读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但是外国作家运用方言取得作品成功的经验却很难被陈忠实所借鉴。因为陈忠实并没有读外文原著,而读的是翻译作品,翻译作品使用的是欧化语言,作品经过翻译的欧化语言中介之后,其中的方言韵味大打折扣。陈忠实读外国作品更多着眼于借鉴作品的思想视野、结构布局和艺术手法,如果在语言上受其影响,也是受欧化的翻译语体的影响,对其方言写作经验借鉴不多。
中国文学史上方言写作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十五国风”展示了各诸侯国方言的风姿,战国时期的《楚辞》则是楚地方言的记录。秦代开始,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逐步形成,用口语方言写作的作品很少被记载和留存于世。唐宋以后,方言成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词、曲之中。到明清时期,随着白话小说的兴盛,方言大量进入文学作品。“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言文一致,方言写作被大力提倡;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众语讨论将方言运用和革命文学的阶级意识联系起来并付诸艺术实践。在延安边区,凭借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政治之力,知识分子不是“化”大众,而是大众化了,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了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文艺大众化真正得以实现。建国后,随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定位,文学文本逐渐走向民间文艺化、通俗化。方言写作作为追求通俗化与民间文艺化的重要途径而被许多作家重视。陈忠实运用方言土语的文学书写与中国文学史上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陈忠实曾深情地回忆自己的父亲:“我当时就回忆起从小见惯的这种姿势,雨天和冬天的不能下地干活的日子,父亲躺在祖居的土炕上,头下枕着一块他自己从灞河滩上捡回的方方正正的河卵石,读着书页残断的《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古董。”[1]父亲酷爱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癖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儿子,陈忠实从中学时代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他最初所受的文学熏陶中古典小说无疑占有重要的份额。清代小说《说岳全传》的作者钱彩是浙江仁和人,出于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他的小说从刻画人物形象、抒发思想情感到描写事态情节,都渗透着浓浓的吴越文化气息,其中还巧妙地插入了较多的吴越方言,如“家堂”“登时”“交关”“做人家”“杀坯”等等,更增强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清代石玉昆所述《七侠五义》虽然经过俞樾的修订润色,但依旧保留了较多的方言俗语和诙谐幽默、贴近日常生活的口语。《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山西,作品中有大量的太原清徐一带所特有的方言俚语,如时时出现的“甚”字,表示“什么”“不大”“早该”的意思,至今留存在晋语方言中。古典小说浓郁的方言韵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入陈忠实的文学库存,成为他可资借鉴的语言资源。陈忠实在《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中回忆自己平生阅读的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是《静静的顿河》,“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快乐和悲伤竟然牵动着我的情感,而我不过是卖菜割草的一个尚未成年的农村孩子。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喜欢阅读欧美小说的偏向,就是从此发生逆转的,从‘说时迟那时快的语言模式里跳了出来。”[2]“说时迟那时快”的语言模式显然归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尽管作家在外国作品的熏染下,从这种语言模式中跳了出来,尽管这种文学储备不见得会立竿见影地体现到小说创作中,但却会在某个时机以井喷之势源源不断地涌现。
比古典小说更直接地影响陈忠实进行方言写作的是来源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创作经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向大众化转移,这是作家、艺术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式的文学变革,未能实现与民众真正的结合。到了1930年代后期,大众语和文学大众化运动不仅获得了新意识形态的表述,还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1940年代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路线。围绕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标,解放区文学对民间文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作家们都学习民间文学,特别是向民歌、民间故事、谚语学习,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四十年代的赵树理、李季、阮章竞等一批作家,自觉实践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陈忠实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老师就是赵树理。
赵树理的小说语言以让老百姓喜闻乐见为目标,尽力营造明白如话的效果,叙述尽量少用形容词和修饰成分,常用的句子结构是某处有什么,谁做什么。句子十分简短,结构简洁,主谓分明,突出谓语,强调人物的行为。叙事不仅以农民为主线,组织叙事也是从农民的视角。不仅人物的对话语言用方言,叙述语言也用百姓口语方言写作,这样就实现了叙事者的大众化。2009年上海书展期间,陈忠实的新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正式发布。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无意识里的盲目,却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3]赵树理山西味很醇的口语方言写作给予长期生活在西安东郊乡土世界,熟悉关中人的语言和民间艺术形式的陈忠实建构文学世界以深深的影响,成为他写作道路上最初的语言典范。
在文学创作层面对陈忠实影响深远的中国当代作家还有柳青和王汶石。柳青、王汶石与陈忠实都来自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地域上的亲缘关系,黄土高原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陈忠实在生活和创作上自然会对两位前辈产生亲切感。柳青和王汶石作为力求忠实于生活的作家,对文学事业的那种挚爱和忠诚使陈忠实非常钦佩,他在创作初期就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柳青和王汶石。在《从感性体验出发的生命飞升旅程》中陈忠实回忆:“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文革中的1974年我到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规定要带的《毛泽东选集》,我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在窑洞里渡过了半年,那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性阅读。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能让评论家和读者产生这种阅读感觉,起码标志着不低不俗的起步的基点。”[4]
王汶石和柳青用关中原生态的方言叙写着关中乡村生活的艺术成就,给予仍处在文学起步阶段的陈忠实以深深的感染和启发,陈忠实说:“柳青的《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的最直接的启示,是把小说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距离完全融合了。尤其是我生活的关中农村,那种读来几乎鼻息可感的真实,往往使人产生错觉,这是在读小说还是在听自己熟悉的一个人的有趣的传闻故事。我对创作的迷惘和虚幻的神秘幕纱可以撩开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就在我的左邻右舍里生活着。”[5]可以想见,作品中如果缺少了方言俗语,这种“鼻息可感的真实”就会立刻消失,无从寻觅。虽然陈忠实的早期创作中还没有萌发自觉的方言写作意识,但他对柳青和王汶石的刻意模仿以及对真实可感艺术效果的追寻,使他不自觉地利用方言资源丰富着自己笔下的艺术世界。
随着陈忠实创作风格的成熟,他确立了艺术自主意识。他在《关于<白鹿原>的答问》中说:“我决心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荫影,彻底到连语言形式也必须摆脱,努力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我当时有一种自我估计,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决心进行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白鹿原》。”[6]陈忠实努力摆脱的是被政治话语拘囿的柳青,他并没有为此对方言弃而不用,而是小心地将政治话语同方言分离出来,让方言恢复到民间话语的本真立场,成为建构自己的话语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当代由柳青、王汶石等老一代作家所奠定的方言书写经验吸收、改造和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中,走出了一条既承传前人,又超越前人的独特创作道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1JK02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忠实:《自己卖书与自购盗本》,贾玉民主编:《对话:与当代文艺名家面对面》,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陈忠实:《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从模仿赵树理开始》,广州日报,2009年8月29日。
[4]陈忠实:《精神“剥离”引发的创作新机》,商洛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陈忠实:《为了十九岁的崇拜——追忆尊师王汶石》,《陈忠实文集》第6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6]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王素 陕西西安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71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