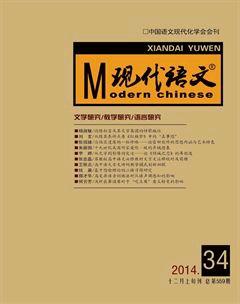政治文化视野中的乡村民间世界
摘 要:浩然的农业合作化小说《艳阳天》在政治文化视野的观照下,将特定时代乡村民间世界的乡村人物设置为正、反、中三种人物类型,隶属不同谱系。在塑造正面人物时存在后来“文革文学”创作中“三突出”的创作倾向;在塑造反面人物时则有丑化、漫画化的趋势;在塑造属于中间派别的落后人物时因创作者的乡村民间生活经验而使其显出鲜活真实、丰富复杂的生命力。
关键词:《艳阳天》 政治文化 民间世界 人物类型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许多农村作家的农村题材创作成为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其中,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它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京郊一个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围绕土地分红、闹断粮、倒卖粮食、抢粮库、退社等事件,在政治话语的规约下,浩然将文本中乡村民间人物设置为不同的序列,呈现出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政治权力斗争图景。以当下目光审视《艳阳天》,故事发生时间前后不过短短十几天时间,作家则用近一百五十万字的篇幅来叙述结构文本,集中精力、浓墨重彩地涂抹出一幅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的“阶级斗争”风暴,并赋予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农民只要走社会主义之路,农村就是风光明媚的艳阳天。小说将特定时代乡村民间世界的乡村人物设置为正、反、中三种人物类型,隶属不同谱系,这样原有的乡村民间世界中“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1]从而使原生态的民间美学因素几乎消解殆尽,正反面人物之间只剩下严峻的你死我活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争夺,这使得文本呈现出一幅政治化的田园乡村图景。
一、理想化、崇高化的正面人物
在文本中政治话语占强势地位情景下,作家塑造出一群坚决走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面英雄群像。他们性格各异:党员主任韩百仲生性耿直且固执,农村妇女焦二菊火爆脾气快人快语,团支部书记焦淑红立场坚定。此外如风风火火的马翠清、积极向上的韩小乐、风趣幽默的焦克礼、满脑子政策条文的焦振茂等形象也都栩栩如生。这些正面形象体现出强烈的爱社如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是农业社的先进积极分子,公而忘私,坚决与那些反面人物和落后人物做斗争。韩百仲是萧长春的左膀右臂,面对复杂、诡谲的政治风云变换,他和萧长春共同研究对策,是萧长春忠诚可靠的革命战友;农村妇女焦二菊生性泼辣豪爽,为了阻止焦庆媳妇不与弯弯绕、马大炮等人瞎起哄掺合,她情愿分麦子后把自己粮食送给她;作为团支部书记的焦淑红,在年轻的积极分子中很有号召力,全力协助萧长春的革命工作,主动积极维护萧长春的声誉;风烛残年的饲养员马老四与落后不争气的儿子马连福决裂,自己没有粮食,情愿吃难以下咽的野菜也不向萧长春要救济粮,当马之悦、弯弯绕等一伙强拉饲养场上的牲口时,他口吐鲜血决不退步,用生命来保卫着集体财产。小说极力渲染其崇高无私的精神境界、豪迈的革命激情和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外在的言行举止到隐秘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没有任何的私欲和杂念,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每个人都自觉将自我消融到集体的“大我”之中,无论男女老幼在思想境界上惊人一致。在农业社内部他们亲如一家,如人们梦想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在对待反面人物马之悦之流,他们同仇敌忾,与反面人物势同水火。如果谁有了不单纯的政治思想,就不再是农业社的积极分子而被划为不属于同一阵营的另类。如曾是队长的马连福,仅因为在干部大会上针对萧长春发了一通牢骚,就被清除出去,免去队长之职,并令其作深刻的反省,对他进行严肃的政治教育和“拯救”。萧长春和焦淑红为积极分子排名站队的依据就是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表现。无疑地,这个标准也是浩然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中为其小说中的人物站队、排名、归类的标准。
正面人物的典型代表是东山坞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他是以严格的政治标准来塑造的高大全形象,也是故事浓墨重彩塑造的充满神性和理想化色彩的英雄形象。他高大伟岸,健壮英俊,精明深沉,充满智慧和魅力,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心力挽狂澜,显出革命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东山坞发生秋季大灾荒的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稳住大局,受到人们拥戴,初步在东山坞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反面人物马之悦强有力的政治对手。萧长春一心扑在工作上,妻子死了三年也不续弦,心中装的全是集体事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前程,关心的是贫下中农里的积极分子马老四、哑巴、五婶等人生活的苦与乐,随时保持警惕的是马之悦之流的阴谋诡计,全力维护农业合作社的利益,努力争取的是那些落后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在与马之悦、马小辫方面进行权力斗争过程中,萧长春在上级领导指导下精神思想不断成长进步升华,时时、事事以阶级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随着萧长春政治眼光和斗争艺术不断提高,他身上的理想化色彩也愈来愈浓。马之悦黔驴技穷之际,利用水性杨花的孙桂英精心设计“美人计”以达到让萧长春身败名裂、自己大权独揽的卑鄙政治目的。面对风流成性的孙桂英的引诱和挑逗,萧长春义正词严地宣布“你把心安错了,萧长春不是这种人!”并努力劝说,让她走光明大道,“只有跟大伙儿一起劳动,只有给集体出力气,把东山坞建设好,那才是真正的快活!”显出一个英雄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为了彻底让孙桂英醒悟,萧长春不计前嫌,让焦淑红等人动员她参加集体劳动,亲自到她娘家为她母亲修缮门楼,并把她母亲接到孙桂英家里。受到感化的孙桂英决心与“地主的闺女”马凤兰彻底决裂,皈依集体,重新做人。在“美人计”较量中萧长春的思想境界更加崇高,表现出宽阔坦荡的胸怀和正人君子风范。在麦收过程中,地主马小辫怀着对农业合作社和萧长春的深仇大恨,残忍地将萧长春活泼可爱的六岁儿子小石头推下山涧。为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保卫合作社胜利果实,痛失爱子的萧长春坚决不让大家放下打麦工作寻找儿子,并说服悲痛欲绝的父亲坚强起来。在整个敌我权力斗争过程中其完美无瑕的道德品质,公而忘私的政治信念,充满智慧机智的政治斗争艺术,他的“金钱买不了,刀枪吓不倒,困难挡不住,刀抹脖子不变颜色,永远当革命的硬骨头,不干到底不罢休”的革命宣言,使这个有着革命理想主义的高大完美英雄形象放射出神圣耀眼的光芒。
二、漫画化、丑化的反面形象
与光辉高大的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面人物马之悦、马小辫、马立本、马凤兰等。他们无论从外貌还是思想言行举止都被涂上“阶级敌人”的政治色彩。马之悦的人生历史和轨迹展示出他是一位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脑瓜灵活,能说善讲,心多手辣。东山坞的庄稼人,十个八个捆在一块儿,也玩不过他的心眼”。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日本人与八路军之间玩得转,脚踩两只船,“四面玲珑,八面叫响”。白天应付日本人,晚上接待八路军。他用性命保住了全村人的生命财产时,人们对他感激涕零,这使马之悦改变了原来发家致富的梦想,“一心一意要往‘官势上靠。他认定这是一个金江山,只要靠上,省心省力,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见风使舵、权衡利害,最后彻底倒向共产党。他因救了伤员——区长李世丹,趁机混进党内成了一名党员。土改时期,他玩弄心机,他在开斗争会头天晚上和马小辫在一起喝酒,到了开会时他第一个上台提出清算马小辫并将其踢昏在地来迷惑人们,暗地里却救了马小辫一条命。土改之后的马之悦投机钻营,处处表现自己,逐渐在东山坞的政治舞台上成为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这与萧长春的人生和政治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强烈的对比,使这个反面人物的反动行为有了历史依据,为其继续反动作了有力铺垫。在东山坞灾荒中,马之悦因失职受到党内撤职处分,他不甘心权势的失去,梦想击败政治对手萧长春,以图东山再起重新掌权,以恢复昔日荣光。因此,他处处暗里与萧长春作对并施展一系列阴谋诡计。在闹土地分红、闹断粮、倒卖粮食、抢粮库等故事中,都有他或明或暗的支持。他抓住富裕中农急切想单干求发家致富的自私心理,鼓动、煽动他们故意和萧长春为首的农业社作对,以达到自己打倒对手重整基业的政治目的,这些卑鄙伎俩与萧长春的光明正大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谋深算的他一计不成,就采用卑鄙下流手段,设计“美人计”企图让萧长春身败名裂。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被捉奸的马凤兰、马立本逮个正着。他还玩弄提拨过自己的乡长李世丹于股掌之中,利用他不明东山坞实际形势喜好被拍马奉承的心理,在东山坞兴风作浪,妄图搞垮农业社,以使整个局势陷于混乱之中,方便自己混水摸鱼。马之悦作为萧长春的对立面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的反面形象,其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正是其性格类型的证明。
另外两个反面形象是地主马小辫和被称为“地主的闺女”的马凤兰。马凤兰的阶级出身注定她必然有着丑陋的面貌,“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女人,早就开始发胖了。本来就不大好看的脸上,两个大胖腮帮子往下嘟噜着,细眉毛,三角眼薄得像张窗户纸儿;头发用一个铁丝卡子卡着,家雀子尾巴似地搭在脖子后边。浑身肥肉,越肥越爱做瘦衣服,瘦裤腿绷得紧紧的,随时都有绷开的可能。这个女人整个看上去像一只柏木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行动的时候,“她移动着两只肉滚滚的脚”。从类似漫画式的人物塑造可以看出作家对其深深的厌恶、强烈的讽刺和揶揄。这个女人积极为丈夫马之悦出谋划策,几乎在萧、马为首的双方所有权力争夺中,都无可例外地充当了反面人物的中坚分子。她积极鼓动、挑唆、拉拢落后人物“弯弯绕”之流站到马之悦一边。“美人计”中她把孙桂英拉入陷阱;收麦子时她挑唆落后妇女罢工;抢粮库中她煽动马大炮之流抢粮。与坚决支持萧长春的积极分子焦淑红、焦二菊、马翠情等正面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两极。对地主马小辫的刻画同样是漫画手法,他日日夜夜想着盼着“变天”和报仇,把自己昔日的荣耀夺回来,是一个反动的“恶魔”形象代表。这正反两种人物类型形成两个鲜明的、不可调和的极端,有些类似雨果所倡导的浪漫主义的美学对照原则: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下,也像王蒙曾指出的那样苏联文学的基木模式常是真善美与假恶科之间的斗争,“在苏联文学中往往真善美一方面的人是胸怀宽广的、无私的、伟大的、善良的、正直的、淳朴的,另外相反的一些人是懦弱的、奴颜婢膝的、自私的、虚伪的、阿谀奉承的、八面玲珑的……苏联文学中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但它的这种文学模式、思维模式往往并不符合,或者并不特别深刻地反映生活,另外,人们常常把感情、无私、爱都放在正极,相反把恨、自私、保守都放在负极,但人类的生活并不是这么简单。”[2]作家以强力政治话语超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性,简化、忽略以致遮蔽了人物的复杂性和自然人性,使得反面人物漫画化和丑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三、人性化、民间化的中间人物
小说的第三种类型是处于正面和反面之间的中间人物,这里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弯弯绕”、“马大炮”、韩百安等人。这类形象的设置在文本强势的政治话语中显出其固有的朴素和鲜活性,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衬托正面人物。作家对这些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情感又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作家以政治标准用嘲弄和批判的目光衡量出这群落后人物与农业社发扬的集体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突出其自私、落后和刁钻的劣根性;另一方面,作家又从自身乡村民间生活经验出发,写出其自身的梦想、愿望和追求。这些人在思想上比农业社的先进分子落后,他们对农业社不满和反面人物不同,没有政治野心和政治动机,而是他们的本性使然。他们和反面人物之间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各自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有着精明、狭隘的自私本性,“谁主张多分给他们麦子,谁就是天大的好人”“有奶便是娘”正是其自私心理的写照。在一场场土地分红、倒卖粮食、多分麦子等政治风波中,他们一切行为的背后动机都源于其一心想靠自己单干实现发家致富的光荣梦想。但是,现实的政治环境只能让他们老老实实参加合作社,将他们的土地、牲口归入集体,无法单干的束缚与限制令他们对农业社充满了不满。又由于他们投入的土地多,便感觉靠挣工分分麦子自己吃大亏。在他们看来,农业社对于那些贫下农来说是有利的,对于他们则是不公平的。
“弯弯绕”这个富裕中农,“他对农业社,对统购统销政策,一向都是势不两立,做梦都是自由自在地发家,都是自由自在地捣鼓粮食得利;如果看着风向有利,有便宜可占,他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主儿。”受到马之悦的鼓动,与马大炮等人闹土地分红,没有闹起来就喊着断粮,故意给女儿做一些糠团子女儿不吃就追着满街打骂以示穷。可是当他的妹夫往他脑子里灌输“变天论”思想时,他又说,“要我说,这天下,还是由共产党来掌管才好……”,“你说情分吗?唉,这真难说。想想打鬼子,打顽军,保护老百姓的事儿;想想不用怕挨坏人打,挨坏人骂,挨土匪‘绑票儿、强盗杀脑袋;……只要共产党不搞合作化,不搞统购统销,我还是拥护共产党,不拥护别的什么党……”为什么呢?“我咬过旧社会的苦瓜尾巴,我受那害受够了,再回去,我真有点怕了……”可见,这个中间人物跟马之悦之流是根本不同的。“我别的指望没有,就图把土地给我,把麦子给我,让我自己随着便过日子,想怎么就怎么,全有了,别的,我可管它干什么呀?”“弯弯绕”把鸡放到麦子地里,想不到自己给自己引火烧身。当他跟焦淑红理论的时候,他争取的只是自己过日子的自由。对于焦淑红说他勾结奸商倒卖粮食搞投机,他据理力争“赖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粮食是我种出来的,不是打杠子抢来的,甭说卖了,我就是扔到河里,抛到坑里,谁管的着?”焦淑红却说是政府的明文规定“让你过社会主义的日子,不让你过资本主义的日子!”“什么自由?在社会主义这个圈内兴自由,出这个圈就不行!”终于胳膊拧不过大腿,“弯弯绕”还是因擅自把鸡子放到地里而受到一场政治批判并被迫检讨。从这里不难看出强势政治话语对民间真实声音的压制和扭曲及作家对此的矛盾态度。
另一个“中间人物”代表是“马大炮”,他没有“弯弯绕”那么多的心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个见好事就上,见便宜就拣的主儿。他说话口无遮拦,“我不管他是黑人红人,今年不让老爷多分点麦子吃,我就牵牲口单干了。”所以,每次闹事他在马之悦、马凤兰的挑唆、怂恿下总是冲锋前阵,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炮”,也成了被马之悦利用的一颗棋子。而马大炮的“单干理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看,单干也有好处!各家有地,各家有牲口,咱们来一个你家跟我家比赛,我家跟你家比赛,比着劲儿把地种得好好的,打了粮食,该交公粮交公粮,该支援国家支援国家,家也发了,国也建了,这不两全其美吗?”他的“单干理论”在当时肯定是行不通受到坚决批判的。但以现在的观念看,与后来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何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他的思想和目光在当时以政治的标准来考察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如果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又有一种超前的、预言的性质。那么这群“思想落后的人物”的发家致富梦想之路注定是“不能走那条路!”那是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条黑道儿!焦庆媳妇也是“一心想发家,起早摸黑地苦干,小日子就上升了”,遇到政治是非问题时她说“管他哪一伙,谁给我办好事儿,我就向着谁!”焦二菊让她和“弯弯绕”他们划清界限答应分麦子后自己送给她麦子,她就高兴得眉开眼笑。韩百安更是一个典型的只为自己打算,不问外界政治时事的富裕中农形象。他“最老实、最胆小、最自私、又最能钻牛角尖”。他将马之悦当作恩人,是因为日本鬼子要烧东山坞时马之悦保住了他的性命和家产,还因为宣传总路线时马之悦给他送过信,他提早将粮食藏了起来。而当村子里传言萧长春等人要翻粮食时,作家对韩百安细腻的心理、行动刻画真实地传达出这个曾经饱受苦难的老农民对自家粮食的深情:“这小米是韩百安的心尖子,命根子,他要永远保存着,他就是从此用不着了,也要保存着的……有两布袋小米子在屋里藏者,他活着就踏实,过着就有兴头,连走路迈步都有劲儿。”这群落后的中间分子形象之所以丰富复杂来源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作家对农民心理的准确把握,也是作家真实的民间生活经验的文学表达,因而更具有民间精神的朴素性和真实性。土地是他们的命根,他们发家致富的美好梦想也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生活理念和精神世界就是守着一片土地,辛勤劳作,圆发家致富的“创业梦”,这也是乡土中国的千年梦。“政策也好”“路线也罢”,农民们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他们常年与土地打交道,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形成了他们只看眼前实际利益的目光狭隘、保守的特征。所以以先进的政治思想标准来衡量,他们自然就成了跟不上时代潮流发展的落伍分子。
四、结语
从文本中作家设置的三种人物类型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政治年代,乡村民间世界不再是单纯自在的自然田园时空,自在的乡村民间世界成了政治权力的战场,成为不同政治势力和政治力量较量的舞台和角力场,这某种程度上导致朴素的某种民间精神的失落。与此相应,文本将特定时代的乡村民间世界中的乡村人物分为不同谱系分别属于正、反、中三种类型。在塑造正面人物时有了后来的“文革文学”里的“三突出”的创作倾向;在塑造反面人物时则有丑化、漫画化的趋势;在塑造属于中间派别的落后人物时因创作者的乡村民间生活经验而使其显出鲜活真实、丰富复杂的生命力。“这一切使《艳阳天》成为一个既真实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的奇怪的混合体。”[3]《艳阳天》堪称是一部乡村世界的政治“传奇”,一个特殊时代的政治“寓言”,这是将十七年文学典型的政治文化特征发展到顶峰的标本,预示着十七年文学的终结和“文革文学”的到来。
注释: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2]王蒙:《小说家言·王蒙谈小说》,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5页。
[3]金进:《从痛别乡土到拥抱农村》,殷都学刊,2006年,第1期,第80页。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