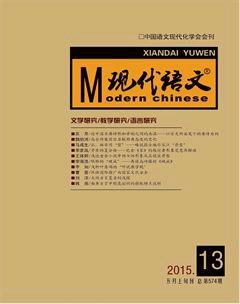本土经验与非中国性
程振兰
摘 要:从穆旦与艾略特诗歌相似的结构方式和相近的经验意象中,依然可以看到穆旦在现代主义诗歌写作中基于中国经验而呈现出的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种差异,艾略特着力批评城市文明对人的生命力的销蚀,穆旦却更加倾心于呈现城市生活对于人的物质性生存的褫夺。本文试图从穆旦对艾略特的借鉴与转化,来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在其生成过程中所融入的独特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穆旦 艾略特 非中国性 结构方式 经验意象
近来年,研究者对于穆旦“非中国性”的论断做出许多反思与辨析,试图重新勾连穆旦与本土传统的关系。但是,从穆旦诗歌的呈现方式到经验意象,无处不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印迹,尤其是艾略特、叶芝、奥登。叶公超在1937年赵萝蕤《荒原》译本序言中,谈到艾略特的诗和诗学“已造成一种新传统的基础”,以奥登为代表的青年诗人都可以说是脱胎于“艾略特传统”[1]。穆旦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接触到英美现代派新诗,周钰良在穆旦逝世十周年后回忆到:“在西南联大受到英国燕卜荪先生的教导,接触到现代派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青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文论。……我也记得我们从燕卜荪先生处借到威尔逊的《爱克斯尔的城堡》(Edmund Wilson)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The Sacred Wood),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大开眼界,时常一起谈论。他对艾略特著名文章《传统和个人才能》有兴趣,很推崇里面表现的思想。当时他的诗创作已表现出现代派的影响。” [2]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相似的结构方式、相近的经验意象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穆旦基于他的中国经验而呈现出来的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某种差异。概括言之,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着力批评城市文明销蚀人的生命力的地方,穆旦却更加倾心于呈现城市生活对于人的物质性生存的褫夺。尤其是在对艾略特的借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艾略特笔下爱欲销蚀、生命衰颓的资本主义场景与穆旦文本中物质褫夺、阶级对立的城市生活场景的差异。因此,本文试图从穆旦对艾略特的借鉴与转化,来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在其生成过程中所融入的独特的中国经验。
一、结构方式的借鉴
艾略特的诗歌形式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诗剧的方法,将戏剧性的场景融入到诗歌中,这种戏剧性的场景是由人物的对话、内心独白以及跳跃式的生活情景组成的。在艾略特的诗歌中,一个清晰的特定的人物已经很难呈现在我们面前,“诗人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这个媒介,只是一种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个性,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料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3],艾略特在评价叶芝的时候说过:“抒情诗人——而叶芝就是抒情诗人,甚至在他创作诗剧时——能为每个人说话,甚至能为那些与他自己迥然相异的人说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需有能力在某一时刻使自己成为每一个人或其他人。”[4]艾略特赞赏叶芝的诗剧,他通过诗剧的形式来表现出其诗歌的“非个人化”的特征。《一位女士的肖像》通过变换的三幕生活场景表现了女士的生活悲剧,而变换的场景恰恰显示出了现代生活的焦虑和不安定感:
而我必须借助于每一种变形
来表现自己……跳呵,跳呵,
象一只舞蹈的熊,
象鹦鹉般呼喊,象猴子般啼叫。
让我们出去散步,陶醉于香烟中——
这里人已不再是人,而如动物一般生活着。穆旦的《从空虚到充实》(1939年)中诗人设置了几个生活的场景:Henry王和家庭吵架后,带着潮水上浪花的激动,疲倦地,走进咖啡店里;张公馆的少奶奶;德明太太和老张的儿子的谈话,这样的生活场景的跳跃式呈现,也恰好代表了一种现代生活的不安定。
穆旦的诗歌中也有着类似的诗剧形式的呈现,他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1945年)完全是由森林、人的对话以及最后的祭歌组成的;《神魔之争》(1941年)由东风、神、魔、林妖之间的长短不一对话构成的。但是,在诗剧形式的借鉴中其实非常关键的是经验的并置。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年)标题名为抒情诗,却是由一系列的对话、内心独白以及跳跃式的场景组成的鲜活的生活图景,而这种生活情景却又是与战争、生活琐碎联系起来的,这样就和抒情形成一种很大的差异,有着一种反讽的味道;类似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年)虽为情歌,却通过多重的视角和内心独白勾勒了一个性能力萎缩的中年男人的病态生活,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讽刺意味;《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在自由诗的叙事中,插入了两节炼丹术士的诗句,这里炼丹术士和现代人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工整的诗歌结构和自由体的诗歌结构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视角上的对比。像这样的还有一首诗《五月》(1940年),在自由体诗歌中插入了五节类似七言绝句的诗歌,古典的诗情中夹杂着现代性的产物: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这或许就正符合艾略特所说的“诗人在任何程度上的卓越或有趣,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感情,不在于那些被他生活中某些特殊事件所唤起的感情”[5]。这里也是通过经验的并置而达到一种多重视角的差异呈现。
结构的借鉴还表现在文本内部的时间结构,在艾略特与穆旦诗歌中都有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当然这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也是一种经验并置的方式。艾略特的诗歌给人一种历史感,通过对历史的追忆来跟现在生活进行对比,《一位女士的肖像》:
让我们出去散步,在香烟中陶醉,
欣赏着纪念碑,
谈论最近的社会花絮,
等公用钟一响,拨准我们的表。
然后再坐半小时,喝黑啤酒闲聊。
这里纪念碑就是过去的象征,象征着过去的某种庄严庄重的生活,跟现在的无聊的谈着社会花絮,在喝黑啤酒闲聊中来消磨着生活形成对比,这更能够说明现在生活的无聊,一种荒诞的生活状态。类似的在穆旦的诗歌《童年》(1939年)中也可发现:
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云雾里,
(那时候云雾盘旋在地上,)
矫健而自由,嬉戏地泳进了
从地心里不断涌出来的
火热的熔岩,蕴藏着多少野力,
多少跳动着的雏形的山川,
这就是美丽的化石。而今那野兽
绝迹了,火山口经时日折磨
也冷涸了,空留下暗黄的一页,
等待十年前的友人和我讲说。
这里化石就是代表着那野兽过去自由的生活,通过追忆过去野兽游行在云雾里,蕴藏着野力,进而来说明现在的绝迹带来的一种野力的丧失,生活只留下暗黄的一页,这是没有野力的病态的生活。
除此以外,穆旦对于艾略特的借鉴,在结构上还表现为题词的引用。尽管这类作品在穆旦的诗歌中是不多的,但仍然是可以看到某些关联的所在。穆旦的《蛇的诱惑》(1940年)中对《圣经》故事的引用恰恰跟艾略特诗歌中题词的引用在形式上不谋而合,《蛇的诱惑》中对《创世纪》的引用:
创世纪以后,人住在伊甸园里,而撒旦变成了一条蛇来对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么?
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就被放逐到地上来。可是在我们生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了呢?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
这样的引用与下面诗歌中的内容是紧紧联系的,也是一种指涉,第一次的放逐到地上——“那时候我就会离开了亚当后代的宿命地,\贫穷,卑贱,粗野,无穷的劳役和痛苦……”但是,当“我”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的时候——“我总看见二次被放逐的人们众,\另外一条鞭子在我们的身上扬起:\那是诉说不出的疲倦,灵魂的\哭泣——德明太太这么快的……”那么另一条鞭子是现代都市文明强加在人们的身上,这就引起了一种思考——“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这样题词和内容之间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可以相互指涉,这跟艾略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题词的引用所起的作用不谋而合。《神曲·地狱》篇的引用也即是引导人们去思考普鲁弗洛克的生存状况,“普鲁弗洛克像被贬入地狱的吉多从火焰里说话一样;他所以对诗中的‘你(读者)讲话,是因为他认为读者也是被贬入地狱的,也属于和他一样的世界,也患着同样的病”[6]。
二、经验意象的学习
我们还可以看到,穆旦对艾略特的学习,不仅仅是在结构方式层面,在经验意象层面也颇受艾略特启发。艾略特有一类表现生命走向垂暮之感的诗歌如《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年):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
这里通过黄昏、病人、麻醉、手术台这些意象可以看出生活处于黄昏状态,人是一种在手术台上的病态,人的生活和生命都将走到尽头的感觉。而在穆旦诗歌中也有着类似的诗句,比如《玫瑰之歌》《不幸的人们》:
无尽的涡流飘荡你,你让我躺在你的胸怀,
当黄昏融进了夜雾,吞蚀的黑影悄悄地爬来。
(《玫瑰之歌》)(1940年)
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破碎的心里
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
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
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
(《不幸的人们》)(1940年)
穆旦在给人的信中也写到黄昏,说生命好像是进入黄昏,这是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预感。当这种黄昏发展下去,在艾略特那里就发展为岁月的暮色降临,人在失去野性之后生命进入黄昏,就会变为老人,如《枯叟》(1920年):
这就是我,干旱岁月中一个老人,
由一个男孩给我读书听,等候甘霖。
这里的老人是生活的象征,是生命的象征,既是一个人的生命的焦虑,也是一群人的生活状态,既无青春也无老年,表现出生存的艰难,类似的穆旦的诗歌《漫漫长夜》(1940)的开头:
我是一个老人,我默默地守着
这弥漫一切的,混乱的黑夜。
……
我是一个老人,失却了气力了,
只躺在床上,静静等候。
这里的老人是经历了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而逐渐变得没有野性没有气力,仅仅是在静静等候的老人,这个老人是“既无青春,也无老年”,也没有性别,就像艾略特的诗歌《荒原》(1922年):
我,提瑞西士,悸动在雌雄两种生命之间,
一个有着干瘪的女性乳房的老头
这个老人已经是没有了性别,没有了原始生活的野性和气力,生命已经临近黄昏,在黄昏中有着一种历史感的存在。艾略特诗歌中的没有雌雄的老人,拥有女性干瘪乳房的老头,一个老头拥有了女性的乳房,尽管是干瘪的,也就意味着这个老人力比多的丧失。从这里可以看出,艾略特始终有对爱欲的暗示,现代人似乎完全退化成爱欲的动物,当然也有爱欲动物必然的命运——性能力的衰退。而穆旦的黄昏意象很少指向爱欲衰颓的主题,而是指向一种意志的削弱。
穆旦还注意到了资产阶级现代文明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这类诗歌恰恰就是受艾略特影响的现代性的诗歌,如《还原作用》(1940年):
泥污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
……
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
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
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穆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首诗是“表现在旧社会中,青年人如陷入泥坑中的猪(而又自认为天鹅)”[7],泥污里的猪也就象征着当时陷入了生活的泥污里的人们,只能在梦中才有翅膀,翅膀是让猪能够走出泥污的唯一的希望,所以一直渴望着飞扬。这种潜意识的想象跟醒来时的现实进行对照,对于现实,只能够是悲痛的呼喊,要想摆脱现实,只有将自己异化,而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八小时工作,就像一个网一样将人捆绑,人被异化成了没有肉体和精神的空壳,这主要是社会的作用,指向的还是物质,人被捆绑着工作是为了摆脱泥污的生活状况,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一种生活条件。
艾略特的诗歌中通过潜意识的想象来描述出现实的生活状态《河马》(1920年):
我看见河马张开翅膀
从沼气的草原上飞升,
而天使的合唱班围着他
高声歌唱上帝的赞颂。
……
他将被洗得如雪之白,
殉道的圣处女都会吻他
艾略特写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的丑恶和脏污。河马是一种丑陋的性能力较为旺盛的动物,诗人写出了这种动物的生活环境是已经发酵为沼气的草原,其实也就是一片没有活力和生气的荒原。在这里河马是有翅膀的,有着天使的合唱班围着,还以圣处女的吻。河马已经与荒野和融为一体,代表着现代社会失去活力的一种生活状态。穆旦和艾略特的这两首诗歌在形式上和主题上是非常相似的,同样是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生活状态,穆旦指向的是物质的生活现实,而艾略特往往是带有一种性能力的指涉来对现代社会生活状态进行描述。
在经验意象的学习中,穆旦还像艾略特一样有意识地勾画现代城市生活场景,《蛇的诱惑》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借鉴非常明显:
从大码头到中山北路现在
亮在我心上!一条街,一条街,
闹声翻滚着,狂欢的季节。
这时候我陪德明太太坐在汽车里
开往百货公司;
在穆旦这首诗歌的开头有着典型的城市的意象:大码头,中山北路,汽车,百货公司,这些都是现代化的产物,艾略特的诗歌《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也有着典型的城市意象: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
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
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
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
这里的街、休憩的场所、歇业旅店、饭馆,都是典型化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场景。这样看来穆旦诗歌中的艾略特传统确实是不容忽视的,这也许是众多研究者将目光集聚在穆旦的“非中国化”的一个原因。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结构方式上和意象上穆旦从艾略特那里得到了很大启发,可是在内在经验层面他们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在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评层面,艾略特更侧重于爱欲主题,而穆旦则更关心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物质压抑。
可以看到,在上述所论及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与《蛇的诱惑》,虽然在结构上引文和文本内容之间都具有指涉关系,但《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首诗主要涉及的是爱欲主题,艾略特笔下的爱情具有私密性,是跟性有关的私密的东西,更多的是自我内心的独白:
把一块秃顶暴露给人人去注意——
(她们会说:“他的头发变得多么稀!”)
我的晨礼服,我的硬领在腭下笔挺,
我的领带雅致而多彩,但为一个简朴的别针所确定——
(她们会说:“可是他的胳膊腿那么细!”)
这个中年男人的秃顶已经预示着性能力的萎缩,他的爱情完全发生在对女性猜测的内心独白之中,有着性的意识,而《蛇的诱惑》呈现的却是在物质性的生存场景中生存意义的丧失:
我想要有一幅地图
指点我,在德明太太的汽车里。
经过无数“是的是的”无数的
痛楚的微笑,微笑里的阴谋,
一个廿世纪的哥伦布,走向他
探寻的墓地
一幅生活场景画呈现在眼前,在物质性的生存场景中的人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无奈,想要地图的指点,像哥伦布一样去探险发现新大陆,但是最后在这种生存场景中探寻到的却是墓地,这就显示出一种生活生存的无意义。
类似的,穆旦虽然在结构上借鉴了艾略特的文本内部时间结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一位女士的肖像》的过去所昭示的是一种具有重大事件的庄严历史,而现在转化了琐碎与无聊,以至于爱欲的渴望与游移主宰了阿尔弗雷德那样的现代人;穆旦《童年》中的过去所昭示的却是一种自然野性的生存,而现在虽然同样转化成了琐碎与无聊,但是穆旦并没有对爱欲进行一种嘲讽似的的书写,相反而是将爱欲、原始生命力构建为一种理想形态以形成对现在的质疑与批判。穆旦借鉴艾略特经验和意象的手法来勾勒出现代城市景观,但是穆旦《蛇的诱惑》中在这种由现代化产物组成的城市生活场景中,依然是给人一种物质生活的存在,诗歌中写到空间位置的移动终点是百货公司,这更能说明人物存在于物质性生活场景之中,这与艾略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爱欲暗示是有着差异的。下等歇夜旅店,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这些都带有色情的暗示,艾略特用一种灰暗的带有厌恶的心情,通过爱欲的暗示来写城市生活的庸碌与肮脏,而穆旦没有太多的感情,写出了物质性场景中人的庸常生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穆旦的诗歌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经验意象的借鉴上都有着艾略特的影子,也正在于这一点,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中说:“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8]而这种“非中国”的,却恰恰和战争年代结合在一起,在40年代战时的中国,诗人们用一种呼喊式的形式甚至是民歌改造的形式来表达这个时代,但是这样的诗歌不可能会长期的流传下去。穆旦作为中国的一员,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他是深深关切这个中国的,作为接触到现代派的西南联大的一员,他在现代化的中国现实中又融入了深深的思考,将这种非中国和中国结合起来。正如艾略特所说的“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去运用普通的感情,去把它们综合加工成为诗歌,并且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9]穆旦恰恰将时代的经验和个人性的经验用一种新的形式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非个人性”的特点。
注释:
[1]陈子善编,叶公超著:《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2]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3][5][9]李赋宁译注,[英]托·斯·艾略特著:《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第10页。
[4]王家新编选:《朝圣者的灵魂 抒情诗·诗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页。
[6]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7]穆旦:《穆旦诗文集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
[8]穆旦:《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