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不等式
本刊编辑部 费婷 郝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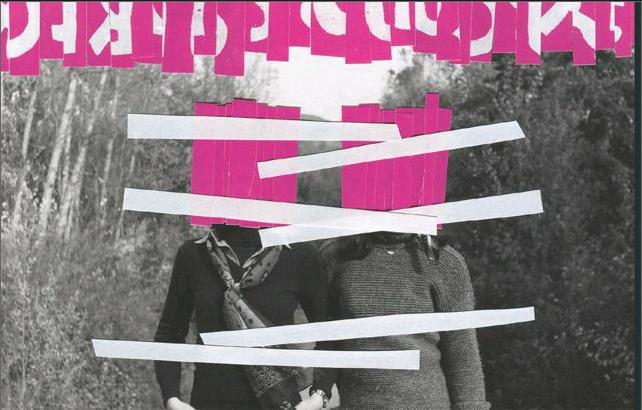
A 我们都在某个等式或不等式的序列中,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
就像一只香烟,在尚未被点燃的时候,它无法独自完善出一个“凶手”的生动角色。而在由它作为诱因并演算出的“角色不等式”上,打火机或火柴的角色是 “帮凶”,身体的角色则是“享受者”和“被戕害者”的不定复合体。
提到“角色”我最先想到的是一座舞台。
从出生之后的三年到死亡前的15分钟,在假想的聚光灯下或镜头前,“扮演”与“角色”是相伴而生的双生花:
B 在妖娆根茎的哺育下,花朵上生长出的必然是一颗颗虚荣的果子。
不论其外表如何朴实,我们却依然在用心装扮成别人喜欢或不喜欢的样子,用图像、用文字和每个隐藏在头脑中的真实欲望等等,并在同类规则的重彩下浓妆前行。
在不等式的辩证法里,每个有机物和无机物都可以成为独立的角色,或者成为某个角色中的一部分—辩证法也是诡辩术冠冕堂皇的新装,所以一切都可以自然地切入到扮演甲方或观看乙方的角色设定中——它们在互换的陀螺上不断地旋转,在向心力和脱缰惯性的龃龉间互为因果。
城市是单个角色的集中营。
相比乡村而言它显得庞大,相比旷野来说它显得明亮。在每个拟人化的赋予之下,城市将每个幻想着离群索居的动物汇聚进自己摩肩接踵的面孔之中,又用狐疑的目光在我们之间设定好适当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看,不等式也是悬在隐私与公共间的荡漾游丝。
作为角色的城市,既热闹又孤独,既恐慌又安全。而关于它的不等式或许正在于我们对于角色本身的巨大幻觉:不竭的自来水、“保护”大地的水泥铠甲和覆盖了整片天空的无形电网等。
C 城市的包容和单调自有其邪恶的一面,但我们却能够从中轻易地获取到段段痉挛般的快感。
就像The Fall在《This Nation's Saving Grace》专辑中唱的那首歌《wonderful and frightened(奇妙和恐惧)》。
最后,关于角色和不等式,我想在米兰·昆德拉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里就曾有过完美的表述。
他的文字不仅只是对传统角色概念的简单悖离,而更多地是在通常被忽略的影子中,插入了一个开门见山的不等式。当我们的目光被迫从主角的凝视中移开时,剩下的或许只有一种对于自我既无奈又尴尬的深入反观吧—昆德拉的原文摘录如下,作为结尾:
第一场
[雅克和他的主人上;他们走了几步,雅克的目光落在观众身上;雅克站住了……]
雅克:(偷偷地)先生……(对他的主人用手指着观众)为什么他们都看着我们?
主人:(他颤抖了一下,整整衣服,好像害怕因为衣冠不整而引人注意)装做没有人一样。
雅克:(对观众)你们不能看别处吗?那好,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从哪里来?(他朝身后伸出胳膊)从那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带着一种哲理性的轻蔑)难道人们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对观众)你们知道吗,你们向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