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观念作为观念……
梁舒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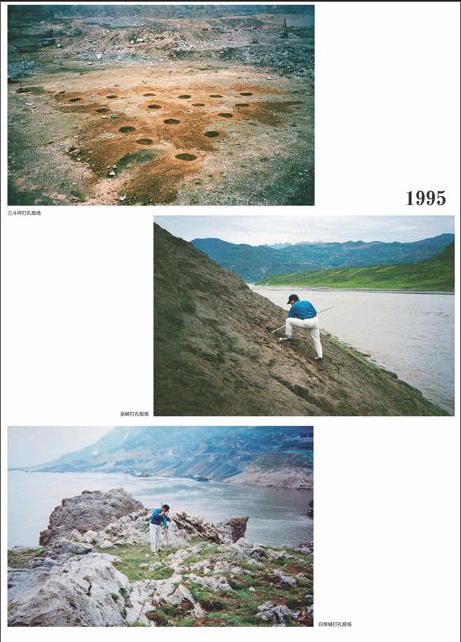
在面对云谲波诡、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而又神秘兮兮的(或自诩的)“当代艺术”时,资深外行和资深内行们好奇与反思的也许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艺术”?或者说这种艺术和其他艺术区别何在?其实,旨在回答这一个问题的著述已然汗牛充栋,但越是这样,反而越是助长了当代艺术的曲高和寡。其实,在诸特征中,有一点最为明显又最易被忽略:与“传统艺术”相比,“当代艺术”更容易被语言精确地描述(无法描述只能说明君还没有找到此作的那个“点”)。例如,对于一件传统的古典肖像画,你尽可以用“雍容华贵、婀娜多姿、庄重典雅”等词汇描述,可与此对应的图像却有多种可能;当代艺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大冬天,有个人匍匐着不断向地上哈气。”君必能想出如此的一幅场景。因为“当代艺术”大都要表达某个想法,或者想用“艺术”的方式说点什么。为了实现这些作品传达想法的初衷,是否还需舍文本之近,求物性之远呢?《东方艺术·大家》的专题栏目“纸上展览”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此栏目实现了理想的“策展”原理,即按照某个主题(例如“时间”“城市”“身体”等当代热门话题)收录、组织展览,并围绕这个既有主题对这些作品进行说明和初步的相关性阐释。因此,“纸上展览”展出的不是艺术家,不是作品,而是阐释本身,因此才堪称一个个有主题的“展览”。这也许是纯粹策划理念唯一可能存在的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图片可以避免作品运输、安装等物质条件的限制,更不必考虑艺术家的代理关系、展览契约、空间租赁等问题。稍等,当代艺术需要展览空间吗?一个艺术的行为和作品产生了,到底是产生在了彼时彼地,还是产生在了媒体的世界中?
如果非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个栏目的确也有一个问题:将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作品,用设定在前的“观念”统摄起来,遮蔽了其原初的意义。作品与它的情境之间的关系被作品与栏目主题之间的关系所置换,这样,作品们就自然而然成了概念们的服务生。但细思之,此举也无可非议,因为阐释本身也是一种关系,它会留下这个时代我们接受艺术的斑斑足迹。当然,这一切之所以可能,还是建立在一个前提的设定上—“当代艺术”一定是当代观念的象征,同时我也想起了那句老话:“作为观念的艺术本身也是一个观念,循环不已(Art as an idea as an 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