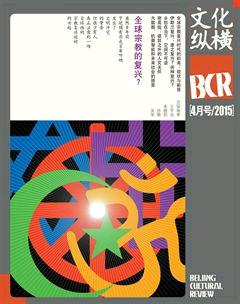“我们受够了!”
蒋亦凡


[文章导读]本文的启示意义,不只是它为我们描绘了德国小农对工业化农业的游行抵抗,而是它也为我们展示了欧洲“后现代政治”的丰富运动细节。它不同于传统的议会政治,也不同于由《查理周刊》事件揭示的欧洲多元文化政治的困境。它体现了当代欧洲政治的特殊活力,而如果仅仅依照旧式的政体学说或政治想象,都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欧洲政治的内在动力及其发展趋势。
“我们受够了!”:德国的农业生态政治
1月17日中午,柏林波茨坦广场,一场色彩斑斓、声势浩大的游行在寒风中开拔,即便是五天前德累斯顿那场在《查理周刊》事件后骤然升级的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Pegida游行及反游行的阵仗,在这场游行面前都相形见绌。整整90辆高挂标语口号的拖拉机浩浩荡荡向北边不远处的总理府挺进,人们打扮成鸡、猪、牛、羊,甚至是树的样子,仿佛在过狂欢节,一群养蜂人穿着白色的防护服和面罩,如同一支军队,更多人高举着内容纷繁的标牌行进,队伍最前端的两条横幅分别写着:“阻止工业化养殖、转基因和TTIP”、“我们受够了!”
先后在德累斯顿和柏林见证了两场游行的作家英果·舒勒策(Ingo Schulze)在报上评论道:相比Pegida口号的空洞和自相矛盾,柏林的这场游行提出的才是真问题。
“我们受够了!”(德语“Wir haben es satt!”)正是这场游行的名字,它是欧洲迄今最大的反对工业化农业,要求可持续农业的游行。从2011年开始,每年一月在柏林的农业博览会“国际绿色周”(International Green Week)期间,它都如期开拔,人数从第一年的两万人,增长到去年的三万人,今年来了五万人,每一年都是柏林,很可能也是全德国最大规模的政治游行。除此之外,同名游行还在过去几年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去年10月2日至5日,它还在柏林考埃茨堡(Kreuzberg)举办了同名大会,来自全德各地乃至讲德语的邻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人们聚在一座教堂和一个前卫食品市场里,深入讨论已经通过游行抛上台面的话题。笔者有幸参与了会议,并在此期间走访德国南北多地,试图理解:关于农业,这些走上街头的德国人究竟受够了什么?
参与这个游行的团体多达两百多个,诉求十分多样——小农权益、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反转基因、有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反贸易自由化、第三世界减贫和发展,甚至包括基督教会的“捍卫造物”。五年来,这个年度游行成功地把这些诉求多样,有时甚至相互抵触的社会运动团结在一起,共同抗议工业化农业的蔓延,伸张小农权益,要求更好的农业和更好的食物。
“阻止工业化养殖、转基因和TTIP,支持农业转型”是今年运动的主题口号,这无疑是这些运动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和当前最紧迫的议题。工业化养殖把动物当作无生命的工业品一样大规模生产。这首先意味着大量的废物排放,造成养殖场所在地水体、土壤和空气的污染。它也无助于提供健康的食物。密集养殖容易引发疫病扩散,因此大量抗生素被使用,并最终进入肉制品消费者的食物链。它还虐待动物,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饲养尽可能多的动物,大型养殖场广泛采用不符合动物生活习性的手段,不仅把动物终身拘禁在狭小的牢笼里,为了防止它们在逼仄的空间里相互伤害,会剪掉鸡的喙、猪的尾巴,根除牛犊的犄角。这其中的动物福利灾难因为其情感冲击力,成为近年来不少德国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也自然激起了公众的厌恶和愤怒。这不仅事关伦理,也事关吃肉时的内心感受,这促使很多原本不了解、不关心农业的城市消费者走上了街头。
转基因产业对欧盟的土地仍然虎视眈眈。欧盟对转基因的抵制运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转基因的环境释放、标注和可追溯性的立法在1990年代就已就绪,这让“反转”阵营可以有效地监督转基因在欧洲的传播。在舆论普遍抗拒转基因的局面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授权过程总是旷日持久,可以长达十几年,即便完成授权,成员国政府也不断动用保护性条款搁置种植,甚至还成功通过诉讼吊销过一项已经颁发的授权。如此种种,使得迄今只有一种玉米和一种土豆曾经获准在欧盟的土地上进行商业种植,而目前仍被允许的则只剩下玉米。除了商业种植,欧盟还允许进口50个可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转基因作物和微生物品种,但由于严格的标注要求和消费者一面倒的拒斥态度,转基因食品在欧洲几乎没有市场,这些进口基本都用于饲料。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据说让一些转基因巨头打算退出欧盟。
说到这里必须插一句: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理由虽然同样包括对这种技术的安全性的怀疑,但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是欧洲人意识到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将使种子被控制在日益少数的种业巨头手中,传统的育种方式和作物品种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被边缘化甚至扼杀,继而,农民的经济自主性和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将受到威胁。这是后面还会涉及的话题。
磋商中的欧盟与美国之间的TTIP(以及与加拿大之间的CETA)却有可能扭转转基因的困局。如果被通过,其中关于食品和环境的标准和监管要求将在两者之间取其低。转基因产品将有机会被装入TTIP的“特洛伊木马”叩开欧洲之门。一起漂洋过海而来的,还会有含有生长激素的牛肉、氯水漂洗过的鸡肉——那些因为消费者的抵制而长期被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拒之门外的“美国特产”。正在磋商的一些条款,还会赋予外国投资者在贸易仲裁法庭挑战成员国政策的权利,而这些私立的仲裁法庭独立于欧盟和成员国的法律框架,且常常偏袒投资者。这样,成员国通过民主机制确立的转基因和食品监管制度将有可能被釜底抽薪,这让很多欧洲公民无法淡定。
口号中的“农业转型”一词,是个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Agrarwende”,这显然是在效仿“Energiewende”,德国政府雄心勃勃的以分散式可再生能源来逐步替代核能和化石能源的“能源转型”,它的目标是在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到全国总能源供应量的80%。如今在德国农村,随处可见可再生能源设施——高耸的风电机、农舍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圆头圆脑的沼气发电装置,以及与之配套的大片大片的“能源玉米”。
与“能源转型”相似,“农业转型”追求的是农业模式的根本转变,使之从被资本主导的工业化农业,走向以小农为主体的可持续农业。发出这种强烈呼声的大背景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小农在高歌猛进的工业化农业面前节节败退。
小农经济与跑偏的补贴
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德国大小农业的区域化分布。二战之后,两德分裂,东德出现了很多大型国有农场,在两德统一之后,这些农场往往被整体私有化,因此今天的原东德地区仍然有很多超大型农场。而在原西德地区,农场平均面积仅为40公顷左右,它的北部为平原,传统的继承制度为长子继承,因此土地集中,大农场居多,而南部多为山地丘陵,加上传统上多实行平均继承制,因此土地分散,小农集中。但是这种格局并不稳定,小农一直在衰退,农场正越来越大。
何为小农,何为大农?这并没有量化界线。通常而言,小农规模从几公顷(1公顷=15亩)到几十公顷不等,更重要的特征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大农的土地规模则远高于以上数量级,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以家庭为单位,而是农业企业,更关键的是:他们把农业套上工业的逻辑,而忽视农业的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
2008年,粮农组织等五个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58国政府联合发布了历时三年完成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简称“IAASTD”),这是迄今对当今世界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最完整的大盘点。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前盛行的大规模集约化农业并不比小农农业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意义上更加优越,如果小农拥有了充足的资金和生产资料,那么他们的单位土地和单位能耗产量将大于前者。这份划时代的报告开始影响小农的“国际地位”。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联合国“国际家庭农业年”,旨在突显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小农在捍卫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均衡营养,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这是对小农价值的迟来的承认。
可是,光是在2003年到2010年,德国就减少了四分之一的农场,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科隆附近的阿尔滕基兴(Altenkirchen)的一位有机农民说:“政策是产业界的傀儡,补贴不是为了让产品更好,而是鼓励你把农场变得更大,这很危险。农民无法做多样化种植,而是少量品种大规模生产。”从柏林,到科隆,再到南部的弗莱堡,我们见到的小农都在抱怨农业补贴制度对他们不公平。“我们受够了!”运动的核心机构之一、旨在支持有机种子和有机农业技术开发的“未来农业基金会”( Zukunftsstiftung Landwirtschaft)负责人Benny Hearlin在去年10月接受笔者采访时断言道:“在现有的补贴制度下面,小农将持续被挤出农业,农场将进一步整合。”
他所说的补贴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2013年底完成改革的2014年至2020年度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另一个是长期以来对能源作物的“双重补贴”。
农业是整个欧盟最集中安排的领域之一,其核心的制度就是“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CAP”)。CAP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7年奠定欧盟法律基础的《罗马条约》,该条约定下了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初目标:提高生产力、确保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稳定市场、保障供应、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食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保障收购价格制度被引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政策的负面效应充分显示出来:欧洲农产品严重过剩,化学合成的农药和肥料的大量使用,动物养殖的高度集约化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肉制品中的药物残留,养殖场中的动物福利状况也开始得到关注。糖和牛奶的配额制度随之建立,1992年的“麦克萨利改革”(MacSharry Reform)改变了补贴模式,从原先根据产量补贴农民,转为参照过往补贴水平和农民当前耕种土地面积来发放补贴——土地面积越大,补贴越高。这种新模式虽然抑制了生产过剩,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2011年10月,上一轮共同农业政策即将于2013年底到期,欧盟委员会农业专员(相当于欧盟的农业部长)达契安·乔罗什(Dacian Ciolos)拿出了他的2014~2020年阶段的CAP的改革提案。虽然他声称这份提案将让CAP变得“更加公平”,但它首先就没有改变直接补贴与土地面积挂钩的计算方法,这让小农群体乃至整个可持续农业阵营都倍感失望。因为,土地面积并不与农场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正比,精耕细作的小农场的单位面积投入往往大过大型农场,而生态表现通常也优于后者。他们要求:补贴额度应该与农场的就业人数和生态表现挂钩,同时排除那些不从农业赚取其主要收入的农场主,以及财大气粗的企业。农业补贴给错误对象是CAP常被诟病的一点。据《明镜周刊》2013年5月的一篇报道,1.9%的经营主体领取了德国30%的农业补贴,其中一些甚至都不是干农业的,比如汉莎航空和莱茵金属这样的工业巨头。因此,他们希望新的CAP能够切实甄别谁是真正的农民,并对补贴额度予以封顶,以免大家伙们拿走太多的钱。可是,直到2013年底博弈结束、政策定稿,也仍未能改变补贴额度与土地面积挂钩的做法,而提案中关于单个经营实体补贴最多不超过30万欧元的“封顶”条款也最终被放弃,成为各成员国的“自选动作”。
CAP的主体内容是高达欧盟总预算40%的农业补贴,用这笔钱来实现政策目标。这笔钱分为两部分,被称作两根“支柱”。第一支柱称为“直接补贴”,旨在增加欧盟农民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第二支柱是农村发展基金,旨在改善乡村环境,促进社会发展。这笔钱对地处偏远,采用粗放耕作、善待环境而不追求产能的农民来说尤其重要。可是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第二支柱的预算比2006年缩减了20%,只占CAP总预算的25%。不止如此,新的规定还允许成员国视自身情况,把第二支柱中最多25%的资金拿到第一支柱中去使用,换句话说,就是把原本用来促进乡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钱用来扩大生产。这让小农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同样的经营成本下他们得到的补贴要比大家伙们低,更重要的是,这让他们在与后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另一个问题是对能源作物的“双重补贴”,虽然即将终结,但多年的实施已经造成了多种后果。这得从前面提到的“能源转型”说起。
1998年上台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为了推动德国能源走向绿色,同时激励生产过剩的农民休耕,开始鼓励农民用多余的谷物发电挣钱。2000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规定:在二十年内,电网必须以高于市场价的保障价格优先购买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来自于消费者电费单上的一笔附加费。能源作物在获得卖电补贴(术语叫“上网电价补贴”)的同时,依然能够获得农业补贴,这就享有着“双重补贴”。默克尔政府在2010年提出,并在2011年立法通过的“能源转型”政策进一步鼓励了这种小规模、分散化、大众参与的能源供应模式。2011年3月的日本福岛事件加速了德国退出核能的进程,默克尔政府在5月宣布永久性关闭全国17座反应堆中的9座,并将在2022年底关闭其余,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
在双重补贴的刺激下,德国的沼气发电发展迅猛,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据《明镜周刊》2012年8月的一篇报道:2011年,因为太多耕地改种能源玉米,德国在25年内头一次无法生产足够的谷物供自己消费。一个典型的沼气发电设施需要大约两百公顷(合三千五百亩)的玉米,这让以玉米为主的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开始盛行。这不仅改变了乡村的景观,也造成生态问题:广大范围内只种一种作物,既不间作也无轮作,不仅难以控制病虫害,也更消耗土地肥力,因此更加依赖农药和化肥。单一作物开花时间集中,广袤区域内又缺少其他开花植物,也令蜜蜂在其他季节无花可食,造成这种对农作物至关重要的自然授粉者的大量减少。不仅如此,双重补贴激励着能源农民扩大产能,同时赋予了他们在食物农民面前的竞争优势,他们不断购买或租赁更多的土地来扩大规模,而这些土地,常常来自被市场淘汰出局的食物农民。升值的预期也引发了土地投机潮,导致地价飞涨。这种土地集中和囤积的现象,被称作“土地掠夺”(landgrabbing)。我们在柏林东郊一个叫“Bienenwerder”的新型集体农场采访的一群归农青年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四年,当地的土地价格上涨了三倍,让小农和返乡年轻人很难获得土地,因而他们在务农的同时,组织了“青年农民联合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反对土地掠夺。
除了以上问题,上网电价补贴带来的高居欧洲之冠的电费也引起了消费者的普遍不满,沼气发电的效率也受到质疑,因此德国政府决定将从2015年1月开始大幅削减沼气发电补贴。
苛刻的市场与全球化冲动
德国小农不仅受到补贴制度的歧视,他们还承受着来自市场的挤压。
Jochen Fritz是“我们受够了!”游行的协调机构“我的农业”(Meine Landwirtschaft)的总协调人。说起小农面对的市场条件,他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德国最富有的三个人不是来自汽车或机械行业,而是来自折扣超市集团,这个体系之强大让沃尔玛在德国都没有立足之地。根据2014年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披露:德国四家折扣超市集团控制着全国食品总采购额和总零售额的85%,因此在考虑对它们采取行动。这种在德文里被径直称作“discounter”的折扣超市其实是一种小型连锁超市,它们网点众多,品类少于普通超市,供应链简单。它们一方面在供应商面前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在彼此之间开展激烈竞争,因此把德国食品价格降到欧洲最低之列,而德国人的食品开支占收入的比例仅为12%,已然全欧洲最低。
食品零售业的高度集中和低价盛行,挤压着小农的利润空间。Fritz认为,另一个后果是破坏了社会的饮食文化,人们不重视食物的价值,不愿意为高质量的食物多付钱,同时也鼓励着食物浪费。因此 “我们受够了!”游行的九大诉求中还有一条“给农民公平的价格和市场规则!”
在一个利润空间有限的市场上,让小农更难做生意的,是德国的食品卫生监管制度和零售渠道对农产品的“美观标准”。即便是我们采访的对德国现有的农业和食物体系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人,都认为由于严格的监管,德国食品从卫生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因为,这种监管是为工业化农业设计的,却让小农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而另一方面,供应链中对农产品的美容要求,让农民的很多产品无法卖掉——弯的黄瓜、太大或太小的土豆和南瓜可能都无法进入流通渠道,最终被浪费掉,成本则由农民自己承担。
因此一些最先锋的农民开始与消费者建立团结伙伴关系,以“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模式与消费者团体抱团,为产品找到稳定的客户群。一部关于弗莱堡一群反全球化社运青年组织的CSA农场“Garten Co-op”的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做“弯黄瓜的策略”。据位于该市的区域经济研究机构Die Agronauten的统计:德国目前已经有了68个CSA农场,报告执笔人Peter Voltz告诉我们,当下在德国还出现了一波农夫市集复兴的浪潮。但是由于严格的卫生监管,小农在开展这些直接销售活动时,也还是会遇到多重障碍。我们在波恩以东的Hennef见到有机奶农Bearnd Schmitz因为没有条件根据卫生法规对牛奶进行巴氏消毒,只能将鲜奶卖给加工商,同时只向120户CSA会员提供并非农场主业的产品——蔬菜。
在小农阵营的对面,站着强有力的工业化农业阵营。德国农民协会(DBV)是德国一个独大的农林行业协会,自称是地区性农民协会之上的伞状组织,代表着德国90%的农民。在本次CAP改革拉锯战中,它是反对乔罗什提案中“更绿、更公平”内容的强大游说团的中坚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在保护这“90%的农民”的利益。国际组织“德国观察”(German Watch)世界食品、土地使用和贸易研究团队负责人Tobias Reichert说:“虽然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但DBV的种种举措却不断透露出这样一种立场:只有三分之一最有竞争力的德国农民应该活下来,并做大做强,其余的农民都应该退出农业,另寻出路。”他说,DBV及其所代表的农业产业界的思维方式表述出来就是:我们在环保和动物福利方面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地方做得好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别要求我们太多。德国向全世界出口汽车、机械、化学品,这让我们骄傲,现在该农产品了,这样农民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为世界的其他部分工作!”
这也正应和了2013年卸任的上一届德国农业部长Ilse Aigner的观点,她在一份题为“2010年德国农业与食品对外贸易”的小册子的前言中,盛赞农业部门出口的持续增长,同时表示:由于国内市场处于萧条,德国农业必须以出口促增长。但是,在国际市场逐浪也意味着承受它的剧烈动荡。2007年,德国生奶价格跟随国际乳制品价格暴涨,一年后又随之急剧下挫,并在2009年夏天跌入历史谷底。德国奶农并不孤单,统计数据显示这一时期欧洲十五国的生奶价格坐上了同一辆过山车。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关注国际贸易问题的Tobias Reichert说,这是欧洲奶农第一次感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屋漏偏逢连夜雨,同一时期,饲料、燃料和食品价格在以同样夸张的态势上涨,双向的挤压,令中小奶农不堪重负,并最终走向集体政治抗争。号称代表三万四千(但一直在减少)中小规模奶农的“德国奶农联合会”(BDM)认为市场上过多的生奶供应与价格下跌有关,因此,欧盟在2008年11月作出的逐步取消牛奶生产配额的决定更是刺激着他们的神经。2008年到2009年,BDM不仅在柏林举行了多场群情激愤的示威请愿活动(一群女性农民甚至进行了绝食抗议),还在全德各地发动了数轮抵制行动,奶农们不仅将自己农场的鲜奶倒入下水道,还封堵乳制品厂,防止别处的牛奶被送上生产线。而DBV却支持取消配额制度,好让有竞争力的农民尽情生产,把握全球乳制品需求上升的机遇。这造成了BDM和DBV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大批奶农退出DBV。
BDM在2011年就加入了首届“我们受够了!”游行。Benny Haerlin说:“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奶农未必同意环保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看法,但是他们也认同:我们不应该生产超过德国所需的乳制品。”就这样,小农生计、环境保护、动物福利,乃至保护发展中国家农民生计免受欧洲受补贴的农产品冲击等多重诉求,找到了“区域性农业”(regional farming)这样一个交集。用Jochen Fritz的话说:“如果反对工业化农业的运动不能建立在区域性农业的基础上,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因为农民仍然会受到来自国际市场和欧洲以外的工业化农产品的冲击。
必须保护种子
被边缘化的不止是小农,还有环保。乔罗什的提案中有一个被挫败的抱负——让欧盟的农业变得更绿。
农业补贴占据欧盟总预算的四成之多,每年高达六百亿欧元,欧盟农民差不多一半的收入来自于补贴。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盟的农业就业人口却仅占欧盟劳动力总数的5%,而农业对欧盟GDP的贡献不到2%。向如此少数的农民和一个对欧盟经济贡献如此小的产业提供如此高额补贴,需要一个可以向欧盟的纳税人交代的理由。
正如达契安·乔罗什说:“农业补贴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农民应该为他们所得到的农业补贴回馈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就是:环境和景观的保护,以及以农业的可持续性为前提的粮食安全。
在乔罗什提案中,直接补贴中30%的额度只有在农民满足了一定的“绿化”(greening)要求之后才能得到,“绿化”手段包括三种:其一,保持永久草场,避免它们被开垦为农田;其二,要求农民进行至少三种作物的轮作;其三,每个农场保留至少7%的土地作为“生态聚焦区”,不施化肥不用农药,不种绿肥之外的作物,仅供保持生态平衡。
但是,这一揽子绿化要求在博弈过程中被不断稀释,最后生效的法律充满了漏洞与豁免:欧盟一半的耕地被豁免为生态平衡留出任何面积,四分之一甚至不需要轮作;欧盟四分之一的耕地和94%的农民不需要做三种作物多样化种植,意味着给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留出了空间。最后,“生态聚焦区域”中被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这意味着担负授粉重任,而数量却在整个欧洲不断减少的蜜蜂仍然会被农药杀死,区域内的土壤和水源仍然会被化肥污染。
共同农业政策的不绿已是板上钉钉的现实,但还有一件事情正和TTIP一样,还处在博弈的进行时,这就是新欧洲种子法的立法。由于它事关农民对种子这种生产资料的自主权、农业的生物多样性,乃至粮食安全,因此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无怪乎“保持种子多样性的自由”跻身今年“我们受够了!”游行九大诉求之一。
由于欧盟具有一个共同市场,所以对种子和其他繁殖材料(比如根茎、苗木)的生产和经销进行统一监管。直至今日,这些监管是由一系列散布于不同法律中的12条法令来规范的,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欧盟允许成员国基于国情,以合理的理由,弹性对待本国小型育种者。但是从2008年起,欧盟委员会开始着手将这些法令整合到一部单一的法律中去,而且不再允许成员国根据国情来灵活阐释法条。
2013年5月,欧盟委员会拿出了这部法律的提案(名叫“为了更安全食物的更聪明的规则”——Smarter Rules for Safer Food)。Tobias Reichert说:这份立法提案的动机,来自于草拟者因为欧洲过去几年曾经出现的几次大型食品丑闻而产生的偏执心理,同时也是为了文件中所直言不讳的——提升欧盟农业的全球竞争力,增加出口,换句话说,就是促进欧洲农业的工业化。
这份提案要求:欧盟范围内所有种子和繁殖材料的传播——无论是销售还是赠送——都必须得到行政许可,传播者必须注册为“操作者”(operators),被传播的种子和繁殖材料必须注册,而注册必须满足三种条件——独特、一致、稳定。
这构成了对农民和他们的种子的双重限制。对农民来说,如果他把自己生产的种子赠送或卖给别人却没有注册自己,就涉嫌违法,可能被罚。而对种子的三种要求中,光是“一致性”一条,就足以排除无数的农民自留种和稀有种,因为这些品种来自于自然授粉而非人工授粉,自然授粉的花粉来源复杂,因此所创造出的种子具有极大的遗传多样性。而商业则采用受控的人工授粉,因此具有高度的遗传一致性。
可以说,这份提案对种子的要求,是为商业种子量身定制的,而让农民种子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并且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古以来生产和交换种子的方式。缺少自然授粉和广泛的民间育种,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将大打折扣。大自然所馈赠的生物多样性,是农业抗风险能力的保证,只有以巨大的多样性为基础,人类才能不断发现或筛选出最具有适应能力的品种加以繁殖,让地球不至于出现电影《星际穿越》开头地球上的农作物一种接着一种灭绝的景象。当人类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层意义就更加重大。此外,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食物的口味、外观的丰富选择,即便不是事关生存,也足够值得珍视。
规范种子市场最符合跨国种子公司的利益,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个产业本身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多样性的产业,它的集中程度已经远超汽车业。据欧洲议会党团“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发布于2014年1月的一份报告,十家最大的种子公司控制着全球75%的种子市场。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整个欧洲,前五大公司控制着一半的种子市场份额。在欧盟,前五大公司控制着95%的蔬菜种子市场,一些主要的非蔬菜作物的集中度也非常高——玉米,五家公司控制75%的市场;甜菜,四家公司控制86%的市场。如果种子市场被标准化管理,那么种子业的集中势必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将受到威胁,为了获得种子,他们将不得不依赖于几大寡头,进而丧失议价权和选择权。这种对农业领域权力集中的警惕,也是欧洲“反转”运动的一个重要动机。
2014年3月11日,欧盟议会在一读之后否决了这份提案,让反对它的人们松了口气,但这个议题仍然没有过去。2014年11月上任的新一届欧洲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初拿出新的提案。拥有一万会员的奥地利育种者组织“诺亚方舟”(Arche Noah)指出:新提案很可能会是对原提案的修改,而不是听取公众呼声之后的重写,因此公民社会必须保持警惕。
希望之岛
“过去的四年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完完全全的胜利。第一年我预期会来五千人,结果却来了两万”, Jochen Fritz在去年10月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敢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丰富了社会对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话语”。 10月初的大会之后,他觉得德国终于有了一个“可持续农业运动”。
Tobias Reichert说这场运动成功地让德国政府开始讨论动物福利和动物养殖中的其他问题,并迫使产业界做出改变。比如不久前新的农业部长Christian Schmidt要求动物养殖业主动停止剪掉鸡喙和猪尾的行为,否则将立法禁止。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对动物福利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切。此外,它还让一贯支持可持续农业的绿党进入了原先没有活动的地区,这个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环保运动的政党在去年11月的年会上,决定将与代表工业化农业利益的游说团正面交锋。
在Benny Haerlin看来,目前的成果在于:运动内部大体上建立起了诸多关于“可持续”的共识。除了前面提到的“区域性农业”,大家还同意农业不能让土地承载太大的压力,应该对环境有积极的影响,应该尊重动物,拒绝转基因并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还有,消费者应该和生产者联合起来以寻求改变。大环境也在变化,统计显示,德国人的肉类消费出现下降,这意味着动物养殖的环境负荷将会减轻。消费者正变得更加亲睐来自本区域的农产品,使得商家开始宣传自己的产品是“区域性”的。此外,欧洲反对转基因的运动仍然强盛而且团结。他把这些称作“希望之岛”。作为欧洲可持续农业阵营在欧盟层面的倡导平台“农业与乡村协定”(ARC2020)的一员,他在想一个问题:如何让“我们受够了!”提出的这些政治议题进入其他欧盟成员国公众的意识中,这样,到了2020年,欧洲才会更有机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共同农业政策。
2014年10月在德国的采访由常天乐与本文作者共同完成,此次采访因两人参加德国亚洲基金会(Stiftung Asienhaus)的“2014中德学习之旅”而成为可能,该项目得到米索尔基金会(MISEREOR)资助。
贴士:2015年“我们受够了!”游行的“九要九不要”:
我们要:
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
无抗生素滥用的动物福利!
推广区域性饲料生产!
全世界的食物权利!
所有人享有健康且买得起的食物!
给农民公平的价格和市场规则!
种子多样性的自由!
对蜜蜂和环境友好的农业!
全世界所有人都能获得土地!
停止:
自由贸易协定TTIP和CETA!
动物工厂!
转基因!
饥饿!
食品丑闻!
农场倒闭!
植物与动物专利!
单一作物种植!
国家和投资者的土地掠夺!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