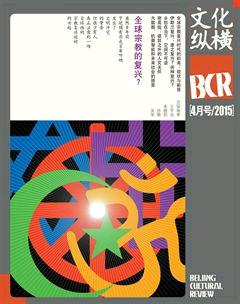俄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
程东金
2015年2月底,俄罗斯自由主义反对派重要领导人涅姆佐夫在莫斯科街头遇刺。涅姆佐夫曾在叶利钦时期担任第一副总理,在普京时代,他又投身反普京的活动,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象征。涅姆佐夫的遇刺,使得本已处境暗淡的自由派丧失了仅有的组织天才。这也是自去年乌克兰危机导致俄国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以来,自由主义反对派遭遇的又一个重大打击。
普希金曾说过,在俄罗斯,唯一的自由派在政府里。历史上,俄国社会结构并不存在一个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成分,如自主的商人阶层。说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似乎并不为过,很大程度上,它是特定时期国家的铁腕政策的产物,就像在斯托雷平时期那样。十月革命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自由主义宪政实验,但它同时面对着来自左翼的革命和右翼的反革命,无力在帝俄的废墟上建立秩序。
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是俄罗斯自由派的黄金时代,那也是涅姆佐夫们的最好时间。但他们显然把事情搞砸了,大多数俄国人对这一时期的集体记忆,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无耻的寡头掠夺和民族羞辱。俄罗斯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分析了自由派的病理:自由主义精英在政治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但他们在新政权,也就是叶利钦总统的小圈子里,在大众传媒中,拥有强大的力量。自由主义少数派自封为国家的代言人,企图把一个狭隘小集团的意识形态提升为全民族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把它强加给社会。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历史性缺陷的简单想法,构成了这一自由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于是,就需要彻底改造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文化习俗,以完成这场宏伟的改革。自由派坚持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向西方文明母体的回归,而历史上俄罗斯脱离这一文明母体,只是由于错误的选择(接受东正教)和各种悲剧性事件(蒙古入侵)的巧合。毫不奇怪,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集体意志体现的国家,成为自由主义议程的首要攻击对象。自由派全盘消解国家在俄国和苏联历史上所起的关键作用,梦想建立一个最小国家,而这一最小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作为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调节者和规范者的全能市场的附庸而已。这种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极严重的后果。
总的图景是,自由派竭尽全力去破坏历史形成的俄罗斯国家,却又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总统这一国家的人格化身之上。自由派虽然思想上贫乏,但却不乏良好的政治嗅觉。在激进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反弹,自由主义的革命潜力日趋耗尽时,他们转而求助于具有本国精神特色的家长制权威主义,集结在叶利钦周围,主张铁腕。
在叶利钦执政的后半期,也就是从1996年总统大选结束之后起,自由派开始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国家彻底丧失行动能力,变成金融政治帮派的玩物,要么击败他们,收回被他们僭据的功能。这次朝着增强政府职能目标迈进的正是自由派。1997年春天,丘拜斯和涅姆佐夫开始了带有国家统制色彩的第二次自由主义革命(第一次是在1992年,由盖达尔负责推进)。在扩大国家职能这一问题上,他们与金融政治集团发生严重冲突。到此时,自由派不得不向产生它们的畸形体制宣战,而后者的力量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一时期,涅姆佐夫将自己所面临的敌人称之为“寡头”,这一称呼很快流行开来。
1998年的8月危机终结了这一不对等的拉锯。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金融政治集团的力量,也导致自由派一并出局。叶利钦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先后出任总理的是普里马科夫和普京(斯捷帕森的任命是个插曲和烟幕弹),前者通常被认为是左派,而此时的普京则尚未表现出有何种意识形态归属。
自由派的悲剧是,他们浪费了历史性的机会,与叶利钦时期的畸形体制一同被人民所抛弃。在新的普京时代,他们无所适从,条件反射式地抨击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集权。实际上,他们所叹惋的叶利钦时代的民主,只是个幻象。在寡头所控制的大众媒体中,国家权威瓦解和丧失被描述成民主。寡头所界定的民主,不过是他们能方便地接近权力中心,最大化其利益。自由派可悲地与一小撮寡头连带在一起。当普京制服寡头,消除这一潜在的权力中心之后,自由派政党也随即失去了金融赞助人,暴露出悬浮在社会之上的脆弱性。
当然,自由派也并非全无希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一个可称之为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出现了。在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分权、司法独立等一整套制度和价值下,这一阶层的利益能得到最好的保护。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自由主义事业终于在俄国生根了。但类似控制一个政府的好事,再也不可能重复了。普京体制也吸收了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如前财政部长库德林、现任副总理祖科夫等,但他们主要是作为财经技术官僚发挥作用,并无法对总的政策进程施加影响。
2011年和2012年是俄国政治的危机年份,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上演了惊险的职位轮转。这期间,俄国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反对派运动一时高涨,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戏仿马克思的一个说法,一切历史都是精英斗争的历史:统治精英如果团结一致,就不可能被底层所颠覆,而当精英陷入分裂时,反对派就有了一线机会。正如一些人所说,抗议运动得以发生,仅仅因为它从体制内部得到了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支持。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职位轮换在俄罗斯政治史上并无先例。这一“并行统治”不可避免地在最高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紧张,伴随着总统权力从梅德韦杰夫回归普京,精英内部产生了分裂。那些更倾向于梅德韦杰夫所隐约代表的现代化和自由化色彩的,以及认为自己在梅德韦杰夫治下能有更好未来的精英,试图阻止普京回归。
这本质上是个精英更替问题。在成熟的选举民主政体下,选举是一个有效的选拔和轮替机制,选举结果决定着去留和升迁。而在选举不占多大分量的时候,精英更替问题就棘手得多。这就是俄国的情形。对此,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设立闲职,目的只在于防止出局的老人们加入街头的反对派。而在梅德韦杰夫时期,这一精妙的平衡被打破了。
这或许是反对派和体制内的一部分精英联手颠覆普京体制的一个好机会。但声势浩大的反对派抗议或许能挫败通常类型的腐败的独裁政体,却不适用于普京体系。原因是,普京享有民众支持,是一个克里斯玛型的领袖,高踞于日益官僚化的政府和政党体系之上。
如何认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体?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双元国家:同时存在着一套基于规范和制度的宪政体系,以及一个独裁性质的专断国家。米格拉尼扬则认为,普京政权最好被描述为一个选举式的民主政体,外加一个作为舵手的克里斯玛型领袖。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这一政体的动力机制:在人民和领袖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领袖拥有巨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并在民众支持下,控制整个官僚体系。实践中,这一体系容易蜕变为官僚威权。而三种内在的冲突有助于保持体系的发展和自我调适:政治家与官僚,官僚领域和政治领域(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以及领袖与政治体系之间。在缺乏这些张力的情况下,体系即陷入僵化和停滞。
在当代俄国,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冲突已经消除,官僚取代了政治家。克里姆林宫基本控制着立法机构,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的冲突也不复存在。幸运的是,在领袖和反对派之间,仍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角度,一个良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有利于俄国政治的健康发展,避免其走向僵化。人们注意到,普京从其谋求第三任期开始,日益强调某种基于俄罗斯历史和文明共同体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也开始逐渐显露出与美国主导的后冷战秩序分离乃至对抗的迹象——乌克兰危机强化了这一转向。有理由相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轮转过程中的精英分裂和重组,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变化,更趋保守和强硬的精英群体现在集结在普京周围,赋予其力量,也向其施加压力。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中,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平衡而非主导性力量,永远有其价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