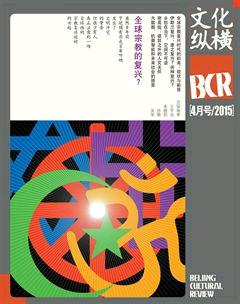现代通讯技术与抗争政治
木怀琴
据统计,2013年底互联网移动设备的数量超过了全世界人口总数,其中最为迅猛的移动流量增长发生在中东和非洲地区。这一趋势显示出过去十年中至为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技术迅速创建了一个高密度的全球通讯网络,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联系起来。第二,这一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愈见普遍。依靠强大的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信息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进行分享与接收。发展经济学和政治行为学在此方面已经颇有建树,而国际政治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发掘到信息技术对抗争政治的理论意义。脸书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究竟是不是关键的催化剂?社交媒体是否真是一种“解放技术”?以往研究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笼统的,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撑。有鉴于此,《和平研究》(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杂志于2015年3月推出特刊,选编研究论文对通讯技术与抗争政治之关系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
现代通讯技术以数字化为基本特征,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主要代表,以电子化、计算机可读性信息为表现形式。其中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数字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其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硬件之先进,使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进行信息交流;第二,信息传播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传统传播技术往往只关注某一类信息,而现代信息传播的内容不再拘泥于特定类别,丰富的信息能够大大增强信息交流的社会效果;第三,用于播散信息的网络类型也发生了变化。以往的信息网络存在一个中心节点,由此节点将信息向受众传送。作为现代信息传播基础的互联网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结构,基于对等网络形成了远比传统媒体网络复杂得多的信息结构。在所谓“网络2.0”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是一个自媒体,通过社交网络为不特定的、无限多的人提供资讯。
基于这些特征,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通过四种机制与政治冲突发生关系。(1)集体行动机制。现代通讯技术促进了群众动员,为抗争力量提供了更好的串联手段。例如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使用脸书组织了埃及的广场抗议活动。(2)审查机制。传统信息技术通过中心节点发布信息,容易遭到政府审查。只要相关部门控制了大的信息节点,便可以将信息塑造成它们喜欢的样子。而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信息往往通过海外服务器传递,造成以往的审查技术失灵。(3)情报收集机制。数字化网络的信息流也会为情报收集提供新的可能。研究表明,西方情报机构的控制能力已经成熟到可以反向定位到信息的发布者及其所传播的信息。由于用户数量和流量在数字上极为庞大,使得这种情报收集成本高昂,而这对政府来说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4)受众效果机制。数字化传播能够更加丰富地描述实时发生的事件。因而政治冲突的各方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在冲突现场以外的其他地方得到回应,例如暴力事件的影音资料可以迅速激发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
对于抗争政治研究而言,关键的挑战在于上述四种机制往往相互交织。信息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对冲突与暴力的影响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和被传播的信息类型。这种双向效果也给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造成了困难。理论模型需要认识到技术可以同时为冲突双方所用,也会产生彼此对立的效果。同理,经验分析在获取这些作用结果时也存在困难,也难以在一个准实验的模型中推导出某种可靠的因果关系。现代信息技术与抗争政治是一个新问题,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因而在理论上存在不周延的地方,研究方法和论证设计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出于问题的重要性,恰好可以大展身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