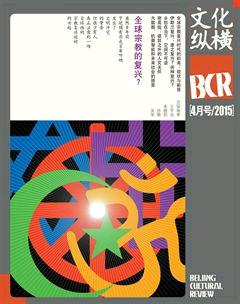乡愁在当下,空间不可逆
朱晓阳



[文章导读]在昆明的拆迁大计中,宏仁村只是无数历经“台风过境”的普通村庄之一,而当野火烧尽,看似卑微如野草的基层力量却能趁着喘息的契机迅速自我修复并重生。在拆迁与造城运动试图重建城市环境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表面上破败的传统民居环境其实并不萧条,对于文化传承来说,失去宏仁老村一般的“废墟”或许也意味着整个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将要面临萎缩。新旧交替之间,我们应该审视不可逆的生存空间更迭给城市文化根基造成的影响。
宏仁村基层自治的复兴
2010年7月,昆明滇池东岸的宏仁村因抵制违法拆迁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而成了昆明市有名的“钉子村”。宏仁村包括老村和新村两部分,在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高潮时期(2010~2011),新村和老村都曾被列入拆迁范围。其中老村有数百年历史,是一座有滇池地区典型聚落特征、古村落格局和一批传统建筑的居民区,宏仁举全村之力,保全了以“新农村建设”之名统一建盖的新村(共502幢新房子),但老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经过几轮拆迁的 扫荡,相当部分的建筑被拆毁。
在延续两年的大拆迁时期,宏仁村的正式组织(社区和小组)从村中撤出,村两级组织的干部都签了拆迁协议,将自家房子交给拆迁办拆除,搬到村外去住,他们被留守本村的人称为“流亡政府”。这期间村干部每天开车来驻村的拆迁办上班,也就是说一个村社的正式组织及其成员都成了拆迁方的雇员。拆迁办(指挥部)本身也是一个奇特组织:它由各级政府(区和街道办)的职能部门抽调一些人,加上社会招聘人员组成,由开发商提供资金支持其运转。它是一个临时机构,被拆迁户到法院起诉拆迁办,会被以“拆迁办不是主体”为理由拒绝。但拆迁办的权力又很大,完全取代了村落层面的正式组织。从拆迁项目推进的策略着眼建立拆迁办、撤出正式组织,甚至破坏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例如水电、公共厕所)等是为了加快拆迁的进程。与此同时,拆迁方甚至还可能联手灰黑势力出没于这种“无人区”,使之尽快变成不可居之地。宏仁村在一段时间内就是这样的地方。
自前年初昆明的城中村改造运动陷入停滞,特别是村小组换届选举以来,混乱数年的宏仁村走上了缓慢修复和秩序重建的路途。在2014年初宏仁村还是秩序不彰,但从下半年开始,即使从地方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角度看,这里的生活秩序和社会治安都值得表扬了,街道派出所的一名警官称赞到:宏仁的刑事发案率直线下降。区和街道办领导也对前年上任的村小组组长李绍荣及其班子的克勤克俭和治理成效表示赞许。但在几年前,这些领导却是与抵抗拆迁的李绍荣团队相互对立的。新年前几天,村小组的“村民代表会”听取了李绍荣的述职报告,他决定继续过去一年多以来的工作方向。如果不是碍于宏仁村过去几年已成为拆迁者眼中的一颗“钉子”,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将这里当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反四风”和“法治建设”的先进单位来上报。但这里的人们并不关心虚头八脑的荣誉,他们只希望政府给他们一些自治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将日子过好,不要再有人隔三差五打着“xx发展”的大旗来搅扰他们原有的生活秩序。
宏仁前些年的混乱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发展”项目引起的,影响最甚者莫过于2010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为了将宏仁村拆平,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和拆迁雇佣军一起,几乎将这个基层社区变成了“不可居之地”。在这个“无人区”,灰黑势力也乘机坐大,最终成了一股威胁地方和平的力量。但是基层社会自我修复的能力仍然强大,一旦地方政府停止干预,假以时日,秩序便自然恢复,公正和正气重新当道。原因很简单,这里有几万人过日子,自然会遵循过日子打交道的规矩,也就不会顺遂拆迁者制造“无人区”的愿望,任其溃烂。
一个空间上的社区仍然存在是很重要的:只要社区存在,其内必有乡贤或乡绅说话和定规的机会。先是依靠乡贤的领导来反拆迁,后来又在基层换届选举时,将他们选进“村小组”和“村民代表会”,宏仁村依靠这些乡贤和协商民主的治理结构,重新走上了今天的治理道路。
几年前宏仁村的正式组织成员撤出村庄后,留守的村民自发形成每星期三傍晚在“桥头上”(村内的公共场所)举行聚会的习惯。村民们在聚会上听乡贤莫正才老人等讲解中央政策、讨论村内事务。2013年村小组换届选举以后,“桥头会”不再举行,村民集会变成由村小组长召集的“户长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自2013年6月上任以来,这届村小组长召开过十几次“户长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更是每逢有重要事项必定召开。一年多来,村小组长的建议一部分被“户长大会”或“村民代表会”通过,一部分被要求调整,还有一些则没有通过。无论议事结果如何,“重要事项要经过这两级治理结构通过”已经成为一条规矩。在两级治理结构之外,宏仁村几年前组织抵制违法拆迁的乡贤们仍然给村小组长提供治理意见,有些则直接参与行政管理工作。这些人在村内都德高望重,由这些人以正式或非正式身份形成的社区治理系统是今日宏仁村的政治和社会核心。
将乡绅/乡贤指导与“村小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等基层正式组织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村落协商民主治理”是今天宏仁村独特的政治机制。其形成也是2013年基层换届选举的结果。宏仁村的现状虽有其历程的特殊性,但这种基层治理机制具有可复制性。
必须承认,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身份转变很关键。前些年基层政府与开发商关系紧密,甚至到了共用办公场所的地步。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互相绑架,形同“政府-公司”。去年以来,政府收手、开发商跑路,拆迁部队不再骚扰地方,公安派出所还能主动配合村小组改善治安环境,给村落社区提供了朝向健康方向的制度基础。
由宏仁村案例可见,当下解决基层治理的路径是给予基层社会充分的自治和自决的空间。有学者哀叹当下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缺失是不再有传统士绅及其对乡土社区的教化。宏仁案例说明所谓传统的复兴或消失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要有一定的地势依凭,只要能假以时日,只要这些“人物”肉身不死,士绅就能够涌现。有了这种地势、时势和人势,再辅以法治和为政旨在保一方平安的行政,“地方乡绅/乡贤-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就能形成。endprint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宏仁村也出现过与当前相似的治理和复兴。那时候周边的村庄都被税费和提留等重负所困,到处都有农民上访,唯有宏仁村比较安静。宏仁村那时候刚从此前十几年的衰败和混乱中走出来。当时的村长声称:“我家村子不是先进典型,我家村子也没有人上访。”我将那时的宏仁村称为“处于台风之眼中”。果不其然,从2003年以后,“台风眼”的平静不再,狂风重来。新一轮风暴是征地拆迁的城市化和城中村改造,最后在2008~2011年演化为所谓“城改大业”。这是大拆大建的巅峰,也是政府作为的极致。一系列“政府-地产”资本的联袂侵入将滇池沿岸社会的伤害达到空前程度。去年10月发生在晋宁致使9人死亡的征地事件也是这场“城改大业”种下的恶果和延续。当今天的宏仁村艰难复兴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历史,必须提醒地方政府切勿重蹈覆辙。我们不愿再看到今天的宏仁经历另一次台风过境。
新村与老村:落脚城市或在废墟上生长
宏仁新村现在有两万左右外来人口租住,加上本村的数千人,这里已经是一个小城镇。这是什么概念?宏仁村低廉的房租为国家解决了两万余外来打工/经商者进入城市的问题,而且他们还能基本安然地生活在这里。今天中国所谓有前途的城市就是那些能够吸引人口流入的地方,因而宏仁村一类的地方对昆明城市的贡献就更明显了。在旁观搞所谓“蚁族”、流动人口、创业人才等等安居工程时,我们不妨想一想谁能够一次性解决两万人的居住问题,如此大的一个居民区,仅有二十来人(五六个村小组干部加上12个综合管理联防队员)在管理。仅就此而言,政府也该给宏仁村发一个奖。
相对于新村来说,地方领导已经习惯将宏仁老村视为“烂尾工程”。他们一见到宏仁的小组长就会问:你们的老村还要放多久?每当这种话题开启,对话就会在讨价还价的维度展开。政府官员坚持老村应被拆除,村小组长坚持在保留部分历史传统区域的前提下,对老村进行更新。其他条件还包括对搬迁居民的安置——盖回迁房;根据目前市场价格重新谈判拆迁补偿标准等等。双方都知道在这些条件下无法取得共识。
外来人对宏仁老村的第一印象是废墟。它的一半房屋或者被全部拆毁,或者主体虽在但门窗已被卸除。村内道路高低不平,路边有拆除房屋后的建筑垃圾,倒塌的房子内有生活垃圾。整个村庄如同地震后的废墟。
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和立场,宏仁老村会呈现出另一种“情景”和另一种生活的丰裕。我最近与居住老村的几个人谈话时,问他们:“你们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感受是什么?”他们都回答:“好在”或“舒服的很”。这种访谈本属多余,直接观察更有意义。老村中的居民都在房前屋后的土质废墟上种菜,有些更将废弃的房子稍加围堵,改成养鸡场。村子南面一块荒废多年的土地则被一些村民分割成各家的菜地。他们用的肥料大部分来自村内的传统厕所里的人粪尿。因为较少使用农药和化肥,他们种的菜在农贸市场很抢手。这些人每年种菜的净收入一般都在3万元左右,自家基本上不买蔬菜。由于老村安静,老年人生活不用爬楼,一些先前搬进新村与子女居住的老人又搬回老村来住。
两年前,村中大寺的侧屋和山门由村民捐钱得以修复。寺院被重新恢复成村民请客的客堂。去年9月以来,一个由花灯票友和退休职业演员组成的戏班子租用大寺的一间房子作为常年演出场地。这个戏班子是从官渡古镇移过来的,据说原来的那边成本已提高,难以找到负担得起的剧场,戏班子每天下午两点至四点演出,门票每张3元(附带茶水),演出的都是追本的传统大戏。10月份他们正在上演《烟花女告状》,这出戏从头至尾要演十六七天,水准相当高。其风格杂糅了花灯、滇剧、京剧和相声小品,既基于经典脚本,又调侃当下的社会现象。观众对演出有直接呼应,每天有五六十人,一部分是本村老人,另一部分则来自官渡、呈贡甚至昆明其他地方。剧团剧目以及非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对传承花灯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如果没有宏仁老村这样的“废墟”,这个剧团几乎不能生存。有时候因为天气冷,观众来的太少,村里的老观众便凑钱补偿剧团,反讽的是,当现今的官渡古镇被打造成愈发高大上的“文化古镇”的时候,真正能传承花灯文化的剧团却不得不从那里逃到这个废墟上来生长。这与中国很多地方的文化古城修复一样,最后的结果是光鲜的舞台上仅剩一些刘老根大舞台式的小品和折子戏。
“追本大戏”犹如大学里的读书会和“席明纳”(seminar讨论课),前者是演员的童子功,而后者则是学生学术成长的基础。读书会或“席明纳”是一种“低成本”的学术活动,但没有读书会和席明纳的大学和学术是空中楼阁。现在大学里到处充斥着“论坛”和“读书汇报会”,但很少有人了解大学的精髓就是这种“低成本”的读书会,就像在折子戏荟萃的现代舞台,很少人理解追本大戏是传统戏的根本一样。在这样的剧团和演出能扎根宏仁的时候,地方上有识见者,特别是地方政府领导应当对他们小心呵护,应当重新审视宏仁老村这种“废墟”的价值。
广而言之,当代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成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废墟”养育的。例如北京的圆明园、东村、草场地、宋庄和黑桥之于视觉艺术;树村、五道口和安河桥之于流行音乐;北大和清华附近的城中村之于学人。这些所谓“脏乱差” 的地方正是文化和艺术中最具创造力的北漂们曾经或现在落脚的地方。在世界范围内,艺术成长于废墟也是普遍现象。例如纽约的苏荷艺术区曾经是一片废弃的厂房,巴黎的拉丁区是19世纪巴黎城市大改造中幸未拆除的老旧城。今天要谈论当代西方艺术不能不提苏荷区,就像谈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艺术必须提到培育了波西米亚精神和生活方式的拉丁区。
实际上宏仁老村的保留与政府的城中村改造“收尾”之间并不矛盾。上面提到,村小组长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缺少共识,是指在过去几年沿袭的大拆大建思路上,双方无法取得共识。而若换一条思路则会有达成共识的可能。例如,宏仁村在过去一年已经提出将该村1950年代初以前的村界范围内作为修复保留部分,其余部分土地由政府和开发商拆除作为回迁安置房和商业开发使用。这一建议虽然离几年前政府的完全拆除的目标有距离,但是它能够使该村的历史文物(如两所挂牌不可移动文物寺庙和几十所传统民居)和传统村落格局,以及最重要的传统生活方式,得以保留。与此同时,部分已经签了拆迁协议的村民的回迁安置房也能够得到解决。此外,政府和开发企业也能够平衡资金投入。endprint
被围困空间的抵抗
如果将宏仁老村当下的价值置于其周边的滇池东岸变迁背景前,会显得更突出。这里仅举一例。
宏仁村的邻村五腊村有两座古寺,分别为“圣恩寺”和“宝龙寺”。在五腊村的民居被拆平以后的四年多里,两座寺庙一直立在废墟中未被拆除,庙里分别有一些老人坚守。几年来我们曾经数次访问这两座庙,守庙的老人们谈及拆迁时称:拆迁方必须在本村地界内盖一所新寺。地方政府和拆迁方确实答应了老太太们的条件,两年前(2009年9月)开始在该村南部地界内盖一座寺庙。去年下半年这座寺庙落成,名为“宝圣寺”。我去年7月份在新建寺院中见有一块寺碑上刻着:“两所寺院,由于年久失修,面临倒塌,急将(待)拆除。”我们都见过那两所被称为“面临倒塌”的寺院。它们都是始建于明朝晚期的寺院,最近一次被修复不过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不存在“年久失修,面临倒塌”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这两所寺院处在新螺蛳湾商贸城圈占的核心地盘之内。其中圣恩寺被新螺蛳湾开发的安置房和商业住宅楼盘的24幢高楼项目所围,宝龙寺的后墙角被一条新修的道路切过。这条路是几年前螺蛳湾开发商修建的一条通往其物流仓库区的通道。两所寺院原来都是在村落的中央,而村落都在2010年的城中村改造中被拆平。宝龙寺所处的照西自然村在拆迁时候甚至还是一个有大量耕地的乡村。
几年来两所寺院虽然势单力孤,但一直被老人们驻守和看护。实际上即使在当下,两所寺院也无拆除的必要。被商业住宅楼所围的圣恩寺与新建楼盘可以相互映衬。从“经济价值”着眼,与一所古寺为邻能使新楼盘的价值得到提升。宝龙寺后墙边的那条通道本来不是一条规划道路,虽然其野蛮切过,宝龙寺也不是非要被拆不可。从两所寺院的文化价值来说,它们更不应该被拆。它们不只是五腊村村民的财富,更是滇池东岸甚至整个昆明市的财富。以五腊村两所旧庙的历史和规模计,它们应当属于区(县)一级不可移动文物。我们曾多次问过庙中老人是否知道此方面情况。他们回应说: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宏仁老村两所寺庙的“不可移动文物”铭牌是在拆迁办被撵出村子后,被村民在拆迁办放弃的办公室(村客堂)内发现的。在此之前宏仁村人都不知道村内两所寺庙是挂牌文物。
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社会性财富,在这里最终变成了街道办与村民关于“值钱的地”和一文不值的“破房子”之间取舍权衡的谈判。就土地而言,这两块地所在地区每亩土地招标价格在数百万元,这些土地被征收、转让,已经落入开发商囊中。如果再容许两所寺庙保留,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完全无法想象这两块肉如何被割舍。不仅值钱的土地不能舍,后来新建的寺庙也能带来钱。新庙的投资为九百余万元,这样的建设项目一般都有寻租的空间,仅因此地方政府和村组织领导都会积极推动拆除旧庙盖新寺。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与驻守两所寺庙的老人们谈过多次,最后似乎达成了共识,即在五腊村地界内重修一座新寺院,然后拆除两所老庙。现在的新庙在昆明南部绕城路南边,按昆明市的最新规划,绕城路以南将保留为农业区,今后不会再有规划的城市建设。去年新寺庙建成后,似乎两所老庙的驻守者再无强硬理由拒绝拆庙了。当时庙里的老人称:他们要求拆迁方对其修缮寺庙所花费的钱财给予补偿。
五腊的两所寺庙在去年底被拆平。新建的寺庙富丽堂皇、流光溢彩,五百罗汉塑得像敦煌的盛唐经变图一样气势磅礴,令观者震撼。如今寺庙门上挂着“居家养老活动中心”的牌子,到那里开过会的宏仁村人都称“盖得好”。将来人们只会知道原来的老寺庙因为“年久失修,面临倒塌”。“过去”就是这样被刻入新的空间,一段历史就这样被记录。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说过“空间是当下的”(present)。列氏的意思是虽然一个社会空间内留有历史意味、时间痕迹,但那个让人侧身其中的具体空间是“现在的”,是整体当下的。换句话说,一个地方可以被当作乡愁和怀旧之地,但这是一个“现在的”空间。列氏是一个深谙政治行动的人,他的这句话可以当作有政治洞见的警句。如果再发挥一下,可以说:空间不可逆。这意味着,一个空间一旦被改变,未来无论出现何种政治“复辟”,人们都只能在“敌人”生产出的当下空间中栖身,都只能在那个当下的空间中想象,只能以那个当下的空间为感受、认知甚至认同的基础。例如很多人发现一个现象:已经“上楼”的农民在小区房中重新扎根。农民在小区延续了社区传统和网络,找到了使神灵得到安置的新位置,其自身也在探索中与新环境相互适应,比如昔日的农民大妈开始热衷于广场舞,“上楼”农民形成了对小区的认同。
再例如一般都认为今天的巴黎是奥斯曼大改造留下的空间。19世纪中叶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经奥斯曼之手,巴黎从一个欧洲古城变成“现代之都”。在奥斯曼进行巴黎大改造的时候,雨果等作家都纷纷起而反对。但反对声没有能够阻止奥斯曼的拆迁,在十几年间数万幢房子被拆倒,许多道路被拓宽成“林荫道”。后来仍有许多人批评奥斯曼毁了古城巴黎,但奥斯曼的巴黎已经是不能逆回的巴黎城市空间。人们是在这个空间中现身、感受、获得认同。在这里人们安居下来,感受奥斯曼创造的这个当下空间,仰慕19世纪以来的巴黎,不再知道奥斯曼之前的地方。
这些例子表明人的地方认同是在当下的空间发生的,因而试图用当地人个体感受的方式来批评“农民上楼”就会显得矫情。从这样的路径去观察,研究者或批评者往往困惑于当地人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和认同。更不要希望古城复建能带回历史和乡愁。因此拆毁平庸的山西大同,建唐宋“古城”是荒谬的:观念上的复旧可能出现,空间上的“复辟”不可能。虽然某一地方/空间的表征可能会能容纳“过去”,但被冠以“唐城”、“宋城”或“古滇国”的地方的“空间是当下的”。
今天要想感受非奥斯曼的巴黎古城,只有在他的拆迁不及之处,例如马黑区、拉丁区或一些背街僻巷。这些地方在19世纪末巴黎大改造之时,相比于林荫大道两边的奥斯曼式六层标准建筑,是一些“脏乱差”和“废墟”的所在之地,但幸而他们得以存留,才有今天的巴黎风情。与此相似,寻找老北京生活也要去那些非旅游热点的平庸老城区,例如东四和西四一带的胡同里。所谓老昆明的生活情景则在不伦不类的钱局街这种地方,在宏仁老村这样的废墟之地。
“空间不可逆”,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应当以此为行动的警示。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彻底的批评和行动应当是阻止社会空间发生根本变迁。让这些现存的社会空间继续延续。政治的选择不应当是让一个“废墟”被以“改造”、“重建”或“复旧”的名义放弃或取代。这也表明我们的乡愁是从这些不伦不类的平庸城市,甚至当下的废墟之地发生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