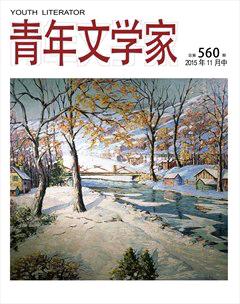张艺谋电影内在关照的转型
摘 要:文艺作品是社会意识的直接反映,电影是社会思想的审美投射,艺术审美趋向的改变往往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变迁以及创作者观念的转换,电影创作的转型也必然与导演所处语境、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密不可分。张艺谋电影创作在90年代早期与晚期先后发生了“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两重转型,两次转型在具体内涵方面也存在着艺术关照的变化,进具体来说即从对现实的重视到轻视,历史的在场到缺席,以及对“人”的关注到淡化。三重关照揭示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及历史文化与张艺谋电影创作间存在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转型;现实主义;形式主义
作者简介:宫瑱(1984-),男,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助教,文学硕士,单位: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媒介文化批评与网络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2-0-02
艺术表现的不同体现的则是电影内在关照的差异。反过来,也可以说电影的内涵与作者的观念是决定影片艺术外在表现特征的因素。
一、对现实考察的由重视到轻视
对比《红高粱》类似传奇故事的世界,张艺谋经过现实叙事转型后的作品,尤其是《秋菊打官司》和《活着》展示的现实世界异常真实、深刻,并且对现实的理解也抛开大是大非、非是即非的简单二元化,呈现出对复杂、多义与丰富的现实世界生活状态的认同。在《红高粱》里,人物显得单调和脸谱化,每个角色只被赋予一重单纯性格,没有层次更没有发展,而且善恶的对立分外明显,《菊豆》在一定程度上亦没有抛开这一点。但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人物开始因欲望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生活的层面开始向深处掘进。而《秋菊打官司》中,出现了一个“人人都是好人”却处处存在矛盾的世界,无论是村长坚持的“不认错”、秋菊坚持的“要说法”或影片最后的执法行为,从一定角度都说得通都没有错,但作用到最后,却产生了令人迷惑的荒诞感。现实的多面与立体跃然屏幕。至于《活着》,这部作品对现实的捕捉细致入微而又没有一丝拔高与夸张,其“对生活和人的解释是成熟的,对生活的复杂性表现得真实而协调”。作者对现实中人面对苦难的无助与忍受、对未来“越过越好”的简单期望和“活下去”的最根本信念的把握,已经非常准确而透彻。《活着》反映的个体在历史洪流中时浮时没的挣扎与社会的复杂、命运的无常,无疑达到了张艺谋对现实关照的顶峰。
很难想象在拍出了《秋菊打官司》这样的电影之后,张艺谋会将他的农村题材演变到《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立意苍白、对生活的反映平面化的浅薄上去,现实生活的复杂深刻经过其“形式主义转型”对形式的过分侧重,仿佛一下蒸发了,只剩下“重构了一种纯真的近乎透明的电影寓言形式[1]”。而其中聪明、漂亮、感情细腻得接近城市女中学生的农村人形象无疑是对煽情的重视背后,对现实的漠视。而之后的两部武侠大片中,现实已经被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打斗、调情及超现实的逻辑嘲弄得毫无地位。在“形式主义转型”后的张艺谋电影中,《秋菊打官司》与《活着》曾着力刻画的现实的复杂、多义与残酷神奇地彻底消失了,导演完全放弃了对现实的观察、思考与表现。
二、历史的由在场到缺席
与对现实的关照相对应,在作品的历史观念上,经过现实主义转型洗礼的张艺谋90年代前期的作品亦表现得愈加深刻。一些评论指出,张艺谋的作品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在于“模糊时空观”,即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所以历史感较弱。其实,在张艺谋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的大多数作品里,历史始终处于在场的状态,不过它更多的是以“民族精神、传统思维、文化制度”这类高度抽象与概括的形式潜伏在作品的内核中。《红高粱》里的我爷爷们是活跃在僵化的古典主流话语外充满昂扬生命力的民族精神代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大院是压抑的千年家长制的具象投射,《秋菊打官司》中的矛盾对立与中国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不无关系,而《活着》更是将批判与表现的方向直接指向了历史。中国漫长厚重的历史偕同经其造就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与国民性成为张艺谋此时期最重要的语境与表现对象。中国古典传统与规则有如父亲般,是张艺谋艺术创作上的母体及无法回避的生长情境。但面对这个“传统父亲”,作者的态度却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红高粱》中炽烈的情感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父亲”无保留的赞颂,但这单纯的“崇父”很快便化为90年以后伴随着影调的压抑而显露的对其劣根性与束缚、扭曲人性的本质的揭示(《菊豆》)、震惊(《大红灯笼高高挂》)与迷惘(《秋菊打官司》),在这一时期,对家长的反抗(《菊豆》)、民告官(《秋菊打官司》)与对夫权的屈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勾勒出了作者对历史传统的既“从父”又意欲“弑父”的复杂心态,这当然源于其在“现实主义”倾向的引导下对民族历史的认识一步步掘进的深入。
不过其2000年前后拍摄的电影,却仿佛被抽空了所有的前后文,换句话,那些编造出的故事已经完全割裂了与历史的联系,导演“做出越出历史边界的举动。而在他过去的所有作品中,他都依赖历史意识,在历史中来完成一种反思性的叙事[2]”。虽然《英雄》等片借用了历史的外衣,但它们“刻意地使他的秦始皇与历史脱节[3]”,只是借用历史作为点缀,来拼凑一些类似神话甚至童话的玄虚故事,没有任何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历史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第一次真正缺席。这是一部‘空的电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始终纠缠于与传统的关系的张艺谋抛弃了他的这个创作母体与成长情境,最贴近中国历史的《英雄》里,竟然奇异地生长出一个类似今日美国主导下的反恐的霸权的“天下”,传统的正义观和弱者抗争的天然合理性这些中国几千年历史叙述中的正道被排除在了这个“中国的历史故事”之外了。可以说对“形式”的迷恋使他的大片里已不再有民族精神、传统思维或文化制度这些中国古典传统内核了。
三、从对“人”的关注到“人”的淡化
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是重要的,但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创造与承载的根源,文艺作品最终的关照落脚点应当在“人”,这也是张艺谋在9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转型”中最关键的一点:由对民族精神的寻找转化为“将这种寻求置放在个人的基本生存本能上[4]”,关注个体命运,并最终将二者结合起来。如果说《红高粱》是一则关于民族精神的寓言,角色的设置为了体现民族气质而具有泛国人的特点,脸谱化而缺少独立个体的立体感与细腻的触感,那么到了《秋菊打官司》,作者自身也意识到“必须在创作中不断磨练自己刻画人物的功夫[5]”,人物已经成为了电影叙事的绝对主体,秋菊这个人物不再是只供调度的表现元素,她的鲜活充分说明作者对人洞察与关怀的力度。而到了《活著》这部作品,既可以说它是小人物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无声呐喊,也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民族半个世纪坎坷的历程。对民族历史、精神的思考和对个体命运的感悟在作者精准的把握下充分融合在一起。或者换一种说法,承接上文的叙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族精神及中国五千年历史和现实这一创作母体,张艺谋由“崇父”转为“从父”与“弑父”相纠缠的矛盾,但最终,其在揉合个体与民族双重现实命运关怀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父亲”超然的理解。对历史的平和与对人性与命运的洞达使这部作品显示出独特的悲悯气质,也使之成为张艺谋最具“人道精神”与思想厚度的作品。
而与轻易地弃绝现实和历史相辅相成的,是在“形式主义转型”后的张艺谋电影里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亦没有了民族,电影的终极已经不成其为对“人”的关照了。如果在《一个都不能少》里,张慧科接受采访被问及感觉,还能说出“饿”,这样的诚恳使该片还能拿到金狮(威尼斯与戛纳的囹圄当然更关键),那么《英雄》里,始皇帝说“他看出那‘剑字的真谛是‘和平”时,就已经说的不是人话了,而到了《十面埋伏》,小妹怎么也死不掉的时候,“人”就已经不是“人”了。这样违背现实的话语情节安排不仅反逻辑而且“反历史、反人道[6]”。
参考文献:
[1]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二元性发展》,载《电影理论:迈向21世纪》,蒲震元等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2]陈晓明:《张艺谋的还童术》,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术)》2005年1月号,第2页。
[3]张颐武:《帝国英雄》,载《书城》2003年2月号,第62页。
[4]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5]张艺谋:《张艺谋:创作与人生》,载《90年代的“第五代”》,杨远婴等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6]郝建:《英雄遮住了人的脸》,载《书城》2003年1月号,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