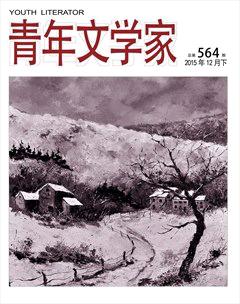评钱穆的“郭象《庄子注》中之自然义”
严金东
本文为2013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钱穆中国文学观研究》(项目号:2013PYZW04)的阶段性成果;重庆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钱穆中国文学观研究》(项目号:13XWB028)的最终成果;2014年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央专项配套资金”项目(WXY201F035)的最终成果。
摘 要:钱穆认为,先秦道家思想中,自然主义并不占重要地位。道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真正要等到郭象注解《庄子》一书时才算成立。钱穆此说,有他的特定视角,并不是很恰当,但它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自然之道的意义。事实上,老庄思想中的“自然”仅仅是对“道”而言,仅仅是“道”的一种内在的逻辑规定,万事万物则不能说“自然”。老庄在一个能“生天生地”、“生万物”的道的视角下对世界的解悟境界,要比万物“自生”、“自然”、“自然而然”郭象之论重要得多、高明得多。老庄之道,指向一种丰厚的文化意味。
关键词:钱穆;郭象“自然义”;老庄之道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3
钱穆《庄老通辨》一书由各篇相对独立的论文集合而成,其中一篇论文名之曰 “郭象<庄子注>中之自然义”。该文关于郭注及道家的“自然义”,有着较为新颖的发现,但更重要的是,该文能激发我们再一次思考老庄之“道”。
一、钱穆析郭象“自然义”
钱穆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出,“道家尚自然,此义尽人知之”,但“自然二字,在先秦道家观念中,尚未成熟确立,因亦不占重要之地位可知。”[1]
钱穆通过他自己独特的考证,认为《庄子》中的内篇先于《老子》一书,《庄子》中的外杂篇则后于《老子》,此意见基本无关于此处对“自然义”的探讨,故本文对此意见亦存而不论。我们在这里感到新颖的是,作者认为“自然”并不是老庄思想中的重要成分,这一点的确并无太多人提及。文章接下去,作者依次论述了《淮南子》、《论衡》中的“自然义”,又论述了王弼注《老子》中及相关一些人的“自然义”,最后,文章详细阐发了郭象注《庄子》中的“自然义”并认为,“后世遂谓庄老盛言自然,实由王弼之故也。”[2]但“惟郭象注庄,其诠说自然,乃颇与王弼何晏夏侯玄向秀张湛诸家异。大抵诸家均谓自然生万物,而郭象独主万物以自然生。”此处我们当然要问:“自然生万物”,“万物以自然生”,两者到底有何不同呢?钱穆认为,“(诸家)仅就当前之生生化化者言之,并未由此上窥天地万物创始之最先原因,……故苟涉及宇宙原始,天地创造,则仍须回到庄老道生万物,有出于无之旧说。……必俟郭象之说,始为创成一宇宙乃自然创始之一完整系统[3]。为论证郭象的这个“创成”,作者举郭象注如下: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4]
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与时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齐物论》“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注)[5]
所谓万物的“自生”,“自然”等,郭象也名之曰“独化”、“独生”:
死者,独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独化而生耳。死与生各自成体,独化而足。(《知北游》“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体”注)[6]
独生而无所资借。(《知北游》“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注)[7]
从天地万物“独生”、“独化”的角度看,则“生天生地”之“道”其实是不存在的。“故在庄书有明白赞道之辞,而郭象之注又明白非之者。……而郭象曰: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8]
于是作者得出结论:“故虽谓中国道家思想中之自然主义,实成立于郭象之手,亦无不可也。虽谓道家之言自然,惟郭象所指,为最精卓,最透辟,为能登峰造及,而达于止境,亦无不可也”。[9]对此结论,笔者以为,钱穆所说,有他的特定视角,但并不是很恰当,特别是,其字里行间还洋溢着对郭象“自然义”的称赏,并且,这种称赏之高,似乎给人一种印象——郭象通过对“自然义”的阐发,其对道的理解、体悟可能已超越老庄。若此印象真能坐实,则笔者不敢苟同。换句话说,笔者以为老庄在一个能“生天生地”、能“生万物”的道的视角下对世界的解悟境界,要比万物“自生”、“自然”、“自然而然”的说法重要得多、高明得多。
二、老子的“自然义”
由钱穆之论,我们须重新认真检讨一下老庄的“自然义”究竟是如何不同于郭象的“自然”义的(本文对老子庄子的“自然义”不做区分,以下主要以老子的“自然义”为例)。试看老子原文: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10]
细玩之,可知“玄德”、“自然”等关键词皆是对道的某种说明。但以“自然”论道,人所皆知;以“玄德”论道,似乎不多见。笔者在这里的个人看法是:第一,“自然”仅对道言,而不对万物言;第二,“玄德”是对“自然之道”的进一步说明。请以老子原文先论证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11]
这里说得很清楚,人、地、天都需要“效法”(道),如此当然不能说他们“自然而然”——“自己如此”。但“道法自然”的“效法”则跟人、天、地的“效法”不一样,因作为“自己如此”的“自然”显然不是一个实体,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则“道法自然”的“道”就不是效法外在的某物了,“道”则显示出独立自足性。其实,从全部《老子》的主旨来看,唯“道”才可谓之“自然”是一种清楚明白的逻辑必然性——老子既然认为“道”“为天地母”,则万物就不能为“自然”,“道”本身才是“自然”。
试再举几处《老子》原文的中“自然”之论: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
希言自然。(23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章)[12]
表面上,这里强调了人及万物的“自然”,但这几处的上下文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老子此时正在以帝王师的身份,谆谆告诫君主如何以“无为”之道治理天下,如何才是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13]
从社会、历史、政治的实际运作着眼,我们不能不说,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绝对的“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在所有这些广义的“自然”背后,都有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对老子这里的意思而言,这个外部条件是指君王需要一种高明的合乎道的统治方式以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化、正、富、朴”,这个高明的合乎道的统治方式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看得见的君王的行为,无不为也是看得见的天下大治,天下大治到百姓自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如此”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的这个理想,正相通于尧时古歌《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如这个传说歌谣所唱的那样,尧的高明统治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以至于百姓似乎感觉不到统治的存在,认为一切都是自力自为,自然而然——对君王而言,这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统治境界。
“无为而无不为”,是政治技巧,更是政治的至高境界。老子的这个政治观从何而来?当然来源于道的启示。我们现在也不妨从道的这个“无为而无不为”政治启示再次逆推回去,重新去体会一下老子眼中的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姑且说整个天地万物的范围就好像是放大了的一个政治领域,在这个放大了的政治领域中,道为万物之出,为万物之本,为万物之首,为万物之君。一方面,天地万物自始至终也不能脱离道的“统治”(《中庸》有论:“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此则根本上,天地万物绝非“自然”;另一方面,道的“统治”是如此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如此的“无为而治”,以至于天地万物均能“自然而然”地成就每一个自己,天地万物的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然”的个体。故我们再次强调,说万物“自然“最多只能是一种现象上的仿佛,而严格地根本上地说,则是唯道”自然”。
三、老庄之道指向的文化意味
郭象的“自然义”其实就是对“道”的否定,用现代的学术语言说,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郭象之说,实吻合于20世纪以来由西方蔓延开来的反形而上学的思想大潮,钱穆推崇郭象的“自然义”,似乎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股现代潮流。但在21世纪的今天,已并无理由再简单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了,人们需要重新认识传统的形而上学。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牵涉的是某种宏大的思想潮流如何转变及为何转变的大问题,绝非一篇小文可以回答的了的。但在这里,有一个看似简单然而深刻的理由可以强调一下:人文学科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语言不能证实、但也不能证否形而上的东西(上帝、理念、天道等等),如当代学者张志扬先生就明确提出“语言的两不性”。[14]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促成重新认识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理由,因为,一旦真正承认理性或者语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形而上本体这个事实,就本文论题来说,关于生天生地生万物的道是否真正存在的问题就不是想当然的可以判定的了,在这种实事求是的认知前提下,郭象的“自然义”可能也就并不像钱穆推崇的那样“精卓”、“透辟”了。
老庄认为存在着一个“生天生地”的道,郭象则认为道不存在,万物“独生”“独化”。纯粹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评判,这两种说法的真理程度其实是相等的,谁也不比谁高明。但从思想史事实看,郭象之论只是对“道”的一家之解说,其重要性、高明性当然不能同老庄比。笔者这样说,还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某种常识的、习惯的立场上立论,例如说老庄是轴心期原创的思想大家,而郭象只是后世高明的专家学者等,所以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这当然是如此,但此外,我们更可以直接地就实质内容而言,老庄之道更高明更重要,因为它指向的是一种丰厚的文化意味,而郭象之论相较而下只能是一个文人学者的精致立说。道存在还是不存在?不妨悬置此问题,不做判断,但“道生万物”和“万物独化”、“万物自然”哪一个更具文化意味是能够区别出来的。所谓老庄之道指向一种丰厚的文化意味,限于篇幅,本文并不能就此展开阐述。这里我们纲要性地指出两点内涵。其一,老庄之道是一种形而上言说,它本源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超越性追求,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它也满足了后世众多高明之士的超越性追求。其二,老庄之道和先秦时期更古老的天道观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它也通向了儒家的形而上之道(儒家的形而上之道同样来源于先秦时期更古老的天道观)。由此更进一步说,道家之道和儒家之道相通为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持久的心灵鸣响。
关于第一点中的“超越”或者“超越性”(transcendent),这是一个源于西方思想的哲学概念,与不同的西方思想大师相联系,该术语的含义可以做出差别很大的解释,这里无能也无需专门一一去辨析。在其最基本最通泛的含义上,即在其刻画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上,“超越性”意味着人的本质上的可能性,意味着人总是一个能超越自身的人——超越自我身体、自我经验、自我的现成等等,从而人能够走向他人、走向应该、……走向超验、走向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承认人具有一种超越的本性的话,则人类思想事业中的形而上学永远不可能被简单否定。具体到本文论旨,我们要说的是,人们可以说郭象的“独化”、“自然”之论非常精妙,但老庄的“道”论则具有真正持久的思想魅力。一代代学者反复阅读思考《老子》《庄子》,不仅仅因为它们有一个外在的“经典”的名号,更因为它们内在地呼应着这些学者们超越的精神需求。关于第二点中的儒家之道和道家之共通于更古老的天道观,这也是学界公认的,毕竟孔孟老庄的时代,已是中华文明有了相当程度发展以后的时代。《尚书》、《诗经》文字俱在,其中“上帝”、“天命”、“天道”等等形而上用语一再出现,这些用语无疑反映了更早时期的天道观,反映了更为原始久远的中国古人的心灵诉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形而上学当然渊源于此,扩大地说,诸子百家的形而上追求都可以一统于此。《庄子》中的《天下篇》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个认识,历来学者同样以各自不同的时代语言申说着这个基本看法。如现代历史大家吕思勉先生就说:“要之古代哲学之根本大义,仍贯通乎诸子之中。有时其言似相反者,则以其所论之事不同。”[15]
我们强调老庄之道指向一种丰厚的文化意味,为什么单单挑出它的“超越性”追求以及与“天道”传统的关系?概括答之,由此想强调的就是老庄之道不是一种过时的虚幻的假想:在一般的意义上,它体现了人之为人的一种本真追求;在特殊的意义上,它又体现了古老中华的精神超越。更具体地说,老庄之道不仅仅是历代专家学者的所思所想,在终极的追想中,它可以指向帝王祭天祀地的仪式,指向诗人“天命靡常”的感叹,指向农人风调雨顺的祈求,指向小民百姓呼天喊地的悲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老庄之道指向丰厚的文化传统、丰厚的文化意味。也许,反过来说更确切,老庄之道原本就来自于丰厚的文化传统、丰厚的文化意味。
注释:
[1]钱穆:《庄老通辨》),361—362页,三联书店2002年。以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2]《庄老通辨》363页。
[3]《庄老通辨》368—369页。
[4]《庄老通辨》369-370页。
[5]《庄老通辨》370页。
[6]《庄老通辨》370页。
[7]《庄老通辨》371页。
[8]《庄老通辨》375页。
[9] 《庄老通辨》368—369页。
[10]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261页,中华书局1984年。以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11]《老子注译及评介》163页。
[12]《老子注译及评介》130页,157页,309页。
[13]《老子注译及评介》284页。
[14]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5]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7页,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