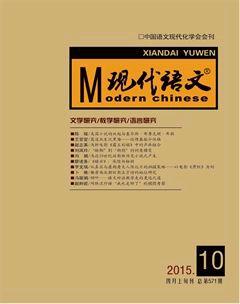《克莱伯恩公园》中的“我者”与“他者”
摘 要:《克莱伯恩公园》是布鲁斯·诺里斯描写种族冲突的最新的政治喜剧,剧中反映了当下美国的种族问题。笔者将从分析种族之间的“我者”与“他者”出发,从白人“我者”里黑人“他者”地位和黑人“我者”中白人“他者”地位来探究人与人之间自私冷漠与虚伪,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为何跨种族对话难以实施。
关键词:布鲁斯·诺里斯 《克莱伯恩公园》 “我者” “他者” 种族对话
引言
种族问题一直都是美国文学上的热门话题,虽然《解放黑奴宣言》发布已经150多年,但是种族之间和跨文化交际间的冲突却屡见不鲜。关于种族的文学也一直都有出现。2011年普利策最佳戏剧奖最终颁给了布鲁斯·诺里斯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戏剧——《克莱伯恩公园》。普利策颁奖委员会将《克莱伯恩公园》形容为“极具力量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以风趣敏锐的方式讲述了美国人在种族与阶级意识中的挣扎。”此剧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前还在2010年获得了奥利维尔奖的“最佳新戏剧”。在普利策奖之后,该剧作还获得了托尼奖。
布鲁斯·诺里斯是美国的演员及剧作家,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的戏剧系,之后在胜利花园剧院、好人剧院等演过戏,写过的剧本有《退休的演员》(1992)、《异教徒》(2002)、《紫色的心》(2002)等。“这个戏的演出是2010年2月在纽约外百老汇剧作家视野剧院开始的,随后,它东渡大西洋,到了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又去威恩汉姆剧院、旧金山的美国音乐戏剧学院等陆续上演,受到广泛好评”[1](P117)。许多人认为这部剧作是关于人性缺点、种族问题,以及揭露中产阶级的虚伪和质疑美国的自由平等。笔者将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剧情背后利益冲突的根源。
一、白人“我者”中的黑人“他者”
“他者”这一术语自古就有,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性出发来看待他人的,总是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对象。他进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主奴关系”,即每个人都力图维持自己的主体性,都互相把别人对象化为“身体”而占有。他在《禁闭》一剧中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阐述的人与人的关系用文学语言概括为“他人就是地狱”[2](P55),即他者总是一个人在实现真实的自我过程中与之发生冲突并且必须克服的障碍。黑格尔认为主人和奴隶的冲突来源于两个意识的对抗,每个意识都谋求首先被对方承认,冲突的结果就是强者成为主人,弱者则成为奴隶。对于强者来说,弱者就是“他者”。在白人的社会里,白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天生高贵,黑人则被视为劣等的、野蛮的、无知的人种。这在剧中也有体现。
第一幕中,即将要搬来的那些黑人邻居,虽然始终未曾露面,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在剧中出现,但是由于人种的问题,他们已经是他者的形象。对于他们即将的入住,中产阶层的住户认为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入住的黑人在没有任何交集的前提下理所应当地被认为是会给小区带来危害的住户。《克莱伯恩公园》作为《日光下的葡萄干》的戏仿,人物设置以及情节上是以《日光下的葡萄干》为蓝本的。卡尔,也就是《日光下的葡萄干》中那个劝说扬格一家不要搬进新居的那个劝说者,在这部剧中也来劝说拉斯一家不要把房子卖给黑人,他也声称见过那一家。他把他们一家描写成“令人讨厌的一家人”。并且黑人也被卡尔称为是“黑奴”。他拒绝称他们为黑人。《日光下的葡萄干》中主要是描写即将搬入克莱伯恩街道406号的黑人一家的生活,从那部剧中可以看出其实那里面的黑人一家并不是“另人讨厌”的一家,但是在以白人我为“自我”,黑人为“他者”的白人文化里,黑人的形象早已异化。他们是野蛮而可怕的人,他们天生低等,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成为邻居,社区里搬进了黑人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房价。
在第二幕中,协商是很难进行的,从最开始协议进行到第三页,到最后还是第三页,因为身为白人的史蒂夫和琳茜在协商的过程中每当谈到一点点重要的话题,接而又被打断,“他们的交谈始终无法进入主题,他们谈论摩洛哥的首都、布拉格的食物、斯蒂夫的滑雪技巧等等”[3](P43)。直至最后,莉娜无法忍受地说:“我知道不只我一个人重视现在的场合,我也不想表现成这样,但是我已经等了15分钟就为插句话。”[4](P143)在白人以自己为主体的社会中,白人无视黑人的需求。而作为他者的凯文、莉娜夫妇以及社区的其他黑人,如同隐形人,因而白人与黑人间的谈话始终难以进行。
在第一幕中,卡尔问黑人女佣会不会滑雪,既而说到“滑雪在黑人社区不受欢迎”,在他们看来,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是无法懂得滑雪的娱乐。第二幕中史蒂夫给大家说的关于黑人与白人同进监狱的下流笑话,在笑话中,黑人是下流、猥琐、庞大的。黑人作为他者,其形象在以白人为主的主流文化中被“丑化”。在白人的心目当中,黑人是没有知觉的“他者”,是丑陋事物的代名词
二、黑人“我者”中的白人“他者”
根据后殖民的理论,“我者”和“他者”这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的,在白人的圈子里,黑人是“他者”。然而在黑人的圈子里,白人也成了“他者”。经过了整整50年的时间,克莱伯恩公园也如当年卡尔所预言的那样,白人居民逐渐搬出社区,2009年的社区已大部分为黑人住户。一对白人夫妻即将搬入当年的406号,然而,他们的搬入也很不顺。他们想要把当年的那幢老房子拆了,在那基础上建一个现代化的住宅,这自然引起了社区里黑人的不满。在剧里,莉娜作为代表反对此事。此情此景,与第一幕的画面有几分相似。“他们在与黑人邻居商谈房屋重建事宜时,双方都体现出与50年前一样的仇恨情绪”[5](P117)。他们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毫不退让,谈话也得不到进展。
简单两幕剧的设置,似曾相识的情节向读者展示了当角色互换时,黑人住户面对白人入住的态度。在剧中莉娜等人,对于即将搬来的白人住户,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例如不许他们把原先破旧的住宅拆掉,原因是因为那老住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着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性建筑,所以他们不能拆,而且新建的房子也不能过高等等。这一系列要求就是要刁难这对白人夫妻,目的就是把他们拒在克莱伯恩之外。之后他们还试图告诉白人夫妇这个房子里面死过人。其实莉娜和其他一些黑人居民一样,也是个种族主义者,她想要做的也和当年的卡尔一样,不让另一个种族的人搬进来。在黑人的社区里,白人变成了“他者”,受到了刁难。正如其中史蒂夫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争吵。另一个团体、一个部落努力地侵略一块土地——现在你们有了这块土地了是不是?现在你们不想这个土地被抢走了,不想这土地像其他东西被美国人抢走那样,对不对?”[4](P186)由于人种的原因,白人想要入住黑人社区遭到了排挤。
虽然种族问题在剧中显而易见,在第二幕的后面,剧中人物也不再掩饰“种族”这一话题而纷纷开起了关于种族的玩笑,但是这种看似好笑的玩笑不但没有惹人发笑,反而再三地把种族问题展示给大家。在场的每个人都被冒犯了,其中黑人莉娜的笑话是白色的女人喜欢卫生棉条。这个笑话里,白人尤其是白女人也被比喻成粗俗而满是欲望的生物,丑陋而肮脏。所以到了最后面,白人琳茜愤怒地说:“你们说的那些使我很受伤,我想要的只是和你们成为邻居然后让我的孩子和你们的一起长大,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的道德都变得让人质疑了。你说的话真的很伤人。”[5](P200)在50年后的克莱伯恩街道,白人变成了“他者”,在想要住进来的过程中需要忍受着黑人对他们的刁难与排斥。
三、结论
“种族”这一话题虽然陈旧,但是经过布鲁斯·诺里斯以幽默而又讽刺的方式被提及,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理性的思考。《克莱伯恩公园》再现了现代美国种族问题的现状,以看似搞笑的情节呈现出种族问题的不容乐观。他运用多个维度,引发读者思考人性的阴暗面,这部剧也表达了剧作家对不同人种间平等友爱这一理想的深深质疑。人心的狭隘与排除异己,使种族问题比想像中更难解决,不同种族的人想要和谐、融洽地相处只是乌托邦。人们只有摆脱自己的狭隘心理,克服自身弱点,用友爱之心对待他人,真正视其他种族人为兄弟姐妹,才能解决种族问题。人们需要做的并不仅仅只是颁布法令,更需要是跨越自身的人性。
注释:
[1]濮波:《百老汇观戏记——看托尼奖剧作<克莱伯恩公园 >》,海外飞鸿,2012年,第6期。
[2]陈宣良等译,[法]萨特:《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3]周莉莉:《隐身的隔离:“克莱伯恩公园”中的伦理困境 》,戏剧文学,2011年,第11期。
[4]Norris,Bruce:《Clybourne Park》,New York:Faber and faber,2011年版。
[5]许诗焱:《在对话中揭示真相——解读2011年度普利策获奖剧作<克莱伯恩公园>中的“对话性”》,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2期。
(王歆 湖南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4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