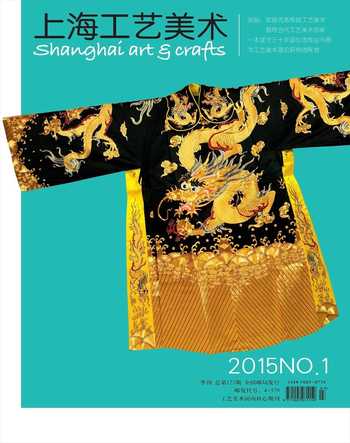青铜文化的延续
徐蓉蓉

The bronze cultur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It prospered in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y but declined after Qin dynasty. In Qing dynasty Jiaqing years, there appeared a new bronze rubbing method - fullscale rubbing. It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improve with photography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perspective. However,due to its complex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other technologies including photography, it had gradually lost its advantages and pragmatic values. Less people continued to do this job and it was on the edge of being lost forever. So now it has become a hot spot how to inherit this method.
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曾经辉煌一时,秦汉以后则日趋衰落。清代嘉道年间,出现了一种对青铜器器物形象的传拓——全形拓,后又结合照相的技术和运用西方透视原理,全形拓技术不断完善。由于全形拓技法的繁复以及摄影等科技的进步,导致全形拓实用价值降低,掌握和从事全形拓的人员减少以致濒临失传。全形拓技法的传承问题,已成为目前文博界的关注重点。
全形拓,又称拓全形、拓器形、立体拓、器形拓、图像拓。它以墨拓为主,结合了绘画的修饰技巧,剪纸拼贴,后又从照相或西方素描的角度来观察青铜器物,运用透视的原理,以浓淡的墨色变化将青铜器物的立体形象完整地传拓在纸上。在各类传拓技法中,全形拓的难度最大,因此历来擅长此拓法者不多。
一、“以灯取形”全形拓的产生
清朝嘉道年间,照相术发明之前,浙江嘉兴人马起凤开创了器形拓,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云:“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傅岩为马起凤字),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论》“彝器全形拓始于嘉庆年间马起凤所拓得汉洗……”焦山寺主持达受(字六舟)和尚独创以灯取形受到藏家欢迎,量好焦山鼎的尺寸,画出鼎轮廓,用毛笔将白芨水刷在器上,六吉棉连纸做传拓的纸,用绸包包好棉花作扑子,用扑子传拓上墨。据《前尘梦影录》记载,六舟和尚得到了马起凤全形拓技法的传授。又根据他自己所撰《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必拓其全形”。金石家阮元对六舟和尚极欣赏,以“金石僧”来称呼他,并邀他用其独创的拓法传拓自己收藏的青铜器,以便给友人欣赏。达受曾经为阮元做过一副《百岁图》,“先以六尺匹巨幅,外廓草书一大寿字,再取金石百种捶拓,或一角,或上或下,皆不见全体著纸。须时干时湿,易至五六次,始得藏事。”六舟和尚拓的焦山鼎器形拓本卷轴上也有阮元的题跋:“焦山周鼎余三见之矣,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刻本而印成鼎形,又以此折纸小之以拓其有铭处乎。再审之,并铭亦是木刻。所拓篆迹浑成器于无别,真佳刻也。”六舟和尚创造的这种“以灯取形”的方法,依灯照所得器物的投影,根据投影勾划器物的形状。这对于以往的传拓是一种全新的思路。
二、照相术与全形拓技法的衍变
晚清时期,外交和贸易活动频繁,照相技术开始传入中国。被称为“南潘北陈(江苏的潘祖荫和山东的陈介祺)”的金石学家陈介祺开始发现照相术可以运用在传拓青铜彝器上,这也是他对传拓技艺的一个奉献,是他发现了“形拓”。“形拓”拓出的器物拓片,器物的外形、大小与纹饰效果佳,神韵更典雅古朴。形拓也即图像拓。由此,他慢慢摸索精心实践,提出了“刻图用洋照(照片)”的构想。同治十一年(1872)夏,陈介祺致吴云的书札可见,他对照相与传拓的结合颇为推崇,并亲自试验过,发现利用照相术可以更好地刻画器物的图案。“刻图有洋照法可用。古器不易照,可以白纸糊之,用墨拓花纹照之,用其尺寸(胜以意为之),仍用拓花纹,作图自佳。洋照近大远小,过分明亦有弊,形似而神不大雅,究不能全用其法,器之曲折处,以横纸度之乃审,其不可见而仍不能不见者,仍不拘洋式照。”
陈介祺既痴迷于照相也发现了照相的缺点,比起传统的拓片,照相只能一段时期保存照片的效果。在光绪元年曾致书王懿荣:“洋照虽不必好其奇,然照古器形,缩三代古文字锓木,以补其不能久存之憾,而用其能不失真之长,亦佳。”在附笺上又事无巨细地讲述照相的好处。
另外,陈介祺也注意到虽然照片上的实物无比逼真,有利于传拓。但照片比起拓片少了古器的神韵。光绪元年致王懿荣书札:“洋照乃取物产之精而明其用,亦可谓泄造化之秘矣。然只是取其形而不能取其神,以形有定而静,神无定而动,动则或造成二物而不工而反拙矣。形工而神拙,则具物而已。点睛飞去,颊上三毫,西法岂能得乎。”从上面的叙述可知,陈介祺对图形拓亲自实践,又将积累的经验和好友分享。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和技法上的局限,图形拓还颇为不成熟。
三、民国以后全形拓的发展传承
民国以后,西洋画的透视和素描技法才逐渐被人们熟知,某些传拓名家开始利用墨色来表现物体的明暗变化,拓出的铜器全形拓片立体感比以往的拓片更强,全形拓技法也逐渐成熟。因此,全形拓的真正鼎盛期是在民国以后。周希丁、马子云是这时期主要的传拓名家。
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收藏的全形拓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周希丁手拓精品。例如在拓片下角钤印“纣丁手拓”、“希丁手拓”、“甲子孟东纣丁拓于闽县赢江”、“金谿周康元手拓金石文字”等。故宫武英殿、宝蕴楼所藏铜器也为周希丁亲手传拓,后由容庚先生编辑整理出版。另外还有《澄秋馆吉金图》所著录的全形拓片,一些拓片被郭沫若收录《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于传拓,他专门研究过西方的透视,并将此融入到传拓片作品中。在此之前,传拓仍然依照陈介祺的图形拓方法,使用照片刻图,再使用放大镜放大来进行传拓片。周希丁不同于陈介祺的是传拓多采用分纸拓“以纸裱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周希丁使用整张纸进行传拓,需要随器形分段来上纸,每次移动不可过多,更要衔接好器物的线条和花纹,传拓时为了不失真变形,必须始终在所绘的线内。从陈介祺所撰写的《簠斋傅古别录》开始到周希丁,全形拓有了质的飞跃。
马子云的作品既兼顾传统又将西洋透视原理和摄影融入其中,其代表作为虢季子白盘器全形拓(藏故宫博物院)。此铜器出土于清道光年间,在马氏之前未拓过全形只粗略拓过铭文,在其著作中叙述了这件铜器的拓法:“先照一相片,然后再按原器形的尺度放大成一简单图稿,再用铅笔描绘在拓纸上,然后按各个部位需要拓之。器的形状与凸凹处,都按照片上的色调层次拓的。惟有花纹不用整纸拓,为的是使花纹特别清晰显著。照片的色调,是凸处淡,凹处黑,愈凸愈淡,愈凹愈黑,所以亦不能完全依据其色,宜灵活运用。又如器上的花。”传拓者既要有透视学的知识,还要学习绘画器物图形的技能,在传拓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15岁就在周希丁的古光阁做学徒的傅大卣也是全形拓高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全形拓片,其中有很多为周希丁和傅大卣的作品。马子云先生的弟子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的纪宏章先生也有关于青铜器全形拓的传拓技法论著《传拓技法》。甘肃博物馆的周佩珠女士也是马子云先生全形拓技法的一个重要传人,出版过书籍《传拓技艺概说》。2003年,保利艺术馆邀请周女士传拓一件圆鼎全形——王作左守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拓本组也曾邀请周女士来教授全形拓技法,为了更好地保存这门技艺。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全形拓收藏最多的官方机构,馆藏全形拓片700多件。
今天,生于金石世家的我国文物修复专家,铜器修复“古铜张派”传人贾文忠承继了全形拓这门技艺,其师承傅大卣先生,并将青铜器修复技法运用到全形拓技法中。
结语
全形拓因传承不易,同时需要具备高超的传拓技巧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心制作,导致掌握和从事全形拓的传统手艺人员减少以致濒临失传。因此,全形拓成了珍贵而稀罕的艺术品。从另一个方面看,青铜器全形拓延续了对青铜器的研究。在清末民国,对传统金石学潜心研究的文人学者都偏好收藏青铜器全形拓本。以往对青铜器的研究多偏重铭文资料文献的考释,也因此忽略了铜青器器形的重要性、艺术性、美学价值等,正是青铜器全形拓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参考文献:
〔1〕参纪宏章《传拓技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03,页59。
〔2〕徐康《前尘梦影录》,载《美术丛书》黄宾虹、邓实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册,页118.
〔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页131.
〔4〕释达受《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载于《北京图书馆藏珍藏本年谱丛刊》第14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5〕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M].济南,齐鲁书社,1991.
〔6〕桑椹《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发展的分期研究》,刊于《东方博物》第十二辑,页37.
〔7〕参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傅斯年图书馆藏铜器全形拓[J].古今论衡,1999,(第3期).页161.
〔8〕陈介祺《传古别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
〔9〕郑珊珊,纪宏章,郭玉海,周佩珠,冀亚平,贾双喜,张辛,郑岩.纸墨留香 传继手的荣耀——传拓技法·全形拓[J].紫禁城,2006,(第5期).页50.
〔10〕参贾双喜《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 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