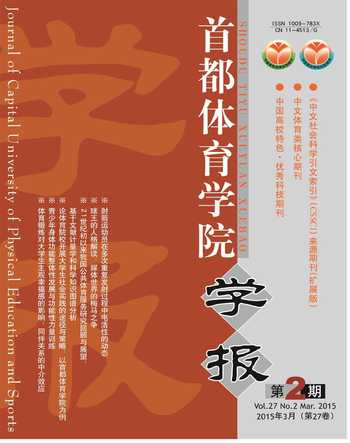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
陈章源 於鹏



摘 要:在测试人口学变量调节效应的同时,探讨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验证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修订版)和青少年运动友谊质量量表对33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但其体育锻炼现状却不容乐观;性别在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中差异显著(男生均显著高于女生);体育锻炼、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间两两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回归效应显著,并分别解释变异的3.1%和4.4%;同伴关系在体育锻炼基础上对主观幸福感回归效应显著,在体育锻炼解释主观幸福感时具备部分中介效应,其效应占总效应值的13.91%。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影响,以及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性别的调节效应。
关键词: 大学生;体育锻炼;主观幸福感;同伴关系;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G 804.8 文章编号:1009783X(2015)02016507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The study seek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on 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and verif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er relationship.Through using the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PARS3),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Revised Edition),and the Sport Friendship Quality Scale of Chinese Youth (SFQSC) ,this paper makes investigation on 330 college students (age=20.72±1.840;Male=160,female=170).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good peer relationships and SWB,while the status of their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is,however,not optimistic.Gender differences i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peer relationships and SWB are significant (mal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 students).Ther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peer relationships and SWB.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gression effect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is significant on peer relationship and SWB,and then explains 3.1% and 4.4% of the variance in them.Moreover,the regression effect of peer relationship is significant on SWB on the basis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The peer relationship has a mediating effect partly i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explaining SWB,and the value of mediating effect explains the 13.91% of variations in total.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onfirms the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and peer relationship on SWB,and the peer relationship's mediating effect as well as the gender's moderating effect.
Keywords:college students;physical exercise;subjective wellbeing (SWB);peer relationship;mediating effect;moderating effect
收稿日期:20140731
基金项目:“十二五”规划教育科研项目(WJ125YB080)。
作者简介:陈章源(1979—),男,江苏无锡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发展和体育教学与训练;於鹏(1978—),男,江苏南通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
作者单位:1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江苏 南京 211800
1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Nanji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Nanjing 210023,China;2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Nanjing Tech University,Nanjing 211800,China.1 问题的提出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是自身设定的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3个部分[12]。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提升主观幸福感是促进个体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锻炼心理学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与大学生的锻炼支持、身体自尊、自我效能密切相关[36],受人口统计学、家庭因素[79]等变量调节。还有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因素包括人格特质等,而外部因素包括社会人际等[10]。社会人际作为大学生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体育锻炼中主要体现在锻炼实践的同伴关系上。同伴关系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热议的焦点话题,它具有相互认同、共享快乐、分担恐惧等功能[11]。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能使个体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12],减少孤立感[13],激发生活热情[14],提升主观幸福感[15]。体育锻炼是个体社会化行为的一部分,考察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理应考虑到社会因素(同伴关系)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中的作用机制,这样既可为大学生提供获得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又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高校体育急待攻关的重要课题提供有效方案。
国内外研究者在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两两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成果:1)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被学者所认同。Jacobson[16]利用渐进放松的运动锻炼方式干预个体焦虑,借以考察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还有研究证实,体育锻炼与健康成年人的总体幸福感密切相关[17],适宜的体育锻炼能使个体获得较多的运动愉快感[18],改善大学生紧张、焦虑和愤怒等不良情绪,使精力感和愉快程度显著提高[19]。2)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具有促进作用。研究表明,体育锻炼是大学生促进人际交往的一种有效方式,同伴关系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认同和自尊[20],Bigelow认为,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同伴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发展同伴关系是个体参与锻炼的基本动机之一,同伴关系与锻炼频率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指出,锻炼中的社会关系比客观环境更具社会支持作用[21],体育锻炼实施较好的个体,会获得更多运动伙伴及同伴的支持和帮助,更易形成运动支持网络和团队协作关系[22]。3)多项研究表明,同伴关系是体育锻炼和输出变量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同伴关系在锻炼行为和锻炼氛围[20]、锻炼投入[23]、锻炼效果[24]中起中介作用,是体育锻炼行为与心理健康、愉悦快乐、生活满意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25]。具有好交际、合群、活跃等外向性格的人,更乐于在他人陪同下从事社会行为,这种在体育锻炼中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创造积极的锻炼氛围,有利于提升个体幸福感,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26]。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27]认为,尊重需要和社交需要是建立在低层次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基础上更为细致的高层次需要。满足高层次需要不仅会使人充满自信,还会使人获得更多理解与支持,减少孤独感。Deci基本心理需要理论[28]认为,若关系需要得到满足,将会为个体带来积极的发展结果,其幸福感也会上升[29]。Dweck成就目标取向理论[30]认为,实现目标会使个体产生主观幸福感,目标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也是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在体育锻炼领域,大学生会因不同的目标取向而形成不同层次的、可迁移的锻炼需要,当满足低层次需要或实现目标,个体会产生积极的锻炼自信,形成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获得主观幸福感,进而出现高层次需要;当高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个体会在锻炼自信的基础上产生锻炼胜任力和群体归属感,形成更高的满意度和更积极的情感,提升主观幸福感,从而出现最高层次的锻炼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Haken协同理论[31]认为,协同效应是由复杂个体相互作用而生的集体效应,个体当外来作用或聚集态达临界时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质变成协同效应,使系统无序变有序,并从混沌中产生稳定结构。大学生作为在实施锻炼的个体,会在同伴的协同作用下产生集体效应,这种形成于体育锻炼中的集体效应,会使无序的锻炼行为趋于有序,形成理想的锻炼氛围,还会使个体获得更高层次的情感体验和群体归属,达到提升幸福感的效果。根据上述理论,可以认为: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基于锻炼需要的满足或目标取向的实现;体育锻炼中的同伴关系,属于高层次体育需要的范畴;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因同伴关系协同效应的变化而变化,即体育锻炼在良好同伴关系的影响下,可使个体在原有获益的基础上提升幸福感,同伴关系可能是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中介变量。
已有研究对梳理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该类研究存在些许不足:1)缺乏人口统计学变量控制。已有研究较多笼统探讨2个核心变量间的关系,较少对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加以控制,致使结论概括化。2)缺乏社会因素控制。已有研究多关注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忽视了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会因外界变量的介入而复杂化,即体育锻炼可以通过调节某种外界变量达到间接改善主观幸福感的目的。类似研究在其他群体的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中得到了验证[32],然而,以大学生为群体,在测试人口学变量(性别)调节效应和验证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基础上,考察同伴关系中介效应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研究构念关系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如图1所示):1)性别是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一个调节变量(H1);2)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H2),体育锻炼与同伴关系显著正相关(H3),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H4);3)同伴关系是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中介变量(H5)。高校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在已有相关理论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体育锻炼、同伴关系、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性,并试图从结构层面揭示影响机制,旨为鼓励大学生科学健身、提高大学生生活质量、促进个体和谐发展、丰富和深化主观幸福感研究有所裨益,亦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
图 1 研究观念构架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整体抽样的方式,在江苏省4所高校随机选取400名大学生为被试。共回收377份量表,回收率94.25%,依据填答不完整、规则性填答或明显填答有问题的剔除原则,共剔除47份无效量表,保留有效量表330份,有效率82.50%。其中:男生160人,女生170人,年龄(20.72±1.840)岁;理科158人,文科172人;大一107人,大二118人,大三63人,大四42人。
2.2 测量工具
2.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
参照梁德清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33],共3个题项,主要从强度、时间、频率3个方面评定运动量,依据公式“运动量=强度×时间×频率”评价运动量大小(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0分),各维度各分5个等级,强度与频率从1~5等级分别记1~5分,时间从1~5等级分别计0~4分。运动量评定标准以≤19分为小运动量、20~42分为中等运动量、≥43分为大运动量,梁德清检验了量表,取得较高信度。本次测量各题项偏度绝对值在0.115~0.259范围内,峰度绝对值在0.360~1.243范围内,标准差最小值1.055。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04,分半信度0.800,各题项与量表相关在0.506~0.570(P<0.01)。验证PARS3量表符合测量学要求,支持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测量的构想。
2.2.2 同伴友谊量表(SFQSC)
Sullivan[34]认为,同伴接纳能够满足个体归属感的需要、增强其合作能力,在儿童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成熟期的个体需建立友谊以满足亲密感的需要,因此友谊比同伴接纳的意义更大。研究参照朱瑜的中国青少年运动友谊质量量表[23],结合研究目的将题项中涉及训练、比赛的主题词汇修正为“体育锻炼”等。共25个题项,各指标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以“从来不会”“偶尔会”“有时”“经常”“一向如此”分别计为1~5分,总分在25~125分范围内。本次测量各题项偏度绝对值在0.478~1.468范围内,峰度绝对值在0.224~1.975范围内,标准差最小值0.824。验证性因子分析6维度模型χ2=795.037,df=260,χ2/df=3.058,SRMR=0.0431,GFI=0.915,CFI=0.952。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6,分半信度为0.956,分量表α志同道合=0.920,α冲突缓和=0.748,α包容理解=0.793,α伴随愉悦=0.808,α自尊互助=0.782,α运动支持=0.782,各题项与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433~0.867(P<0.01)。验证SFQSC量表符合测量学要求,所得数据支持对同伴关系的测量构想。
2.2.3 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以Pavot的生活满意度量表[35]为蓝本,经Mantak Yuen博士修订并译成中文版(该量表已被跨文化研究证实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637])。单维度量表是用来评价被试对生活满意度的陈述,共5个题项,采用Likert 5级计分,每项指标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满分为25分。分数总计后,以5~9分为非常不满意,10~14分为少许不满意,15分为中立,16~20分为少许满意,21~25分为非常满意[38]。本次测量各题项偏度绝对值在0.062~0.519范围内,峰度绝对值在0.154~1.014范围内,标准差最小值1.034。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7,分半信度为0.805,各题项与量表相关在0.765~0.855(P<0.01)。验证SWLS量表符合测量学要求,所得数据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构想。
2.2.4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修订版)
以Watson.David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39]为蓝本,参照邱林[40]等人修订成中文版量表(国内研究证实了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4142])。量表是用来评价被试过去一个星期所感受到的情绪状况。考虑到主观幸福感是评估个体长期的、相对稳定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研究将量表的指导语修订成“请用1~9分来评价你在大学期间能够较多地感受到下列情绪的情况。”量表共2个维度,每个维度各9个题项,共18个题项,采用Likert 9级计分,各维度分值大小反映被试各维度的情感程度。本次测量各题项偏度绝对值在0.210~0.996范围内,峰度绝对值在0.093~1.181范围内,标准差最小值1.788。验证性因子分析2维度模型χ2=353.902,df=125,χ2/df=2.831,SRMR=0.0418,RMSEA=0.075,GFI=0.894,CFI=0.963,NFI=0.944,IFI=0.963。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积极情感分量表Cronbachs α=0.957,分半信度为0.936,各题项与量表相关在0.809~0.902(P<0.01);消极情感分量表Cronbachs α=0.954,分半信度为0.938,各题项与量表的相关系数在0.762~0.927(P<0.01)。验证该量表符合测量学要求,所得数据支持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测量构想。
2.3 施测过程
于2014年6月1—15日,采用集体施测和单独填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施测前提醒并解释指导语,保证被试者自愿参加,填答时间为5 min,填写完毕当场回收。在施测中获得被试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如性别、年龄、年级等。
2.4 数据采集与分析
将所得数据导入SPSS 19.0和AMOS 22.0。对相关数据进行奇偶排序、中心化等处理,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多元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处理,实现研究所需,并且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加以验证。
3 结果
3.1 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特征
3.1.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遵循梁德清对运动量的评定公式:运动量=强度×时间×频率,以运动量描述体育锻炼(满分100分);以同伴关系各题之和描述同伴关系(满分125分);沿用严标宾的测量方式,以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和评定主观幸福感(满分187分)。据调查,有47.27%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在30 min以上,26.36%能保证每周3次及以上的锻炼次数,30.30%每次锻炼强度保持在中等及以上水平。均值及标准差显示,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以小运动量为主(男=38.59±24.392,女=11.09±13.152),具有较为理想的同伴关系(男=104.83±13.582,女=101.91±17.565)和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男=112.35±24.154,女=101.46±22.153)。
3.1.2 方差分析
为验证假设H1,将性别设为自变量,以体育锻炼、同伴关系、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MANOVA分析。在辨别分析中,Wilksλ表示组内平方和与总平方和之比,介于0~1之间,Wilksλ=1表示所有观测组均值相等,Wilksλ值越大表示各个组均值基本相等,而值越小组间差异越大,辨别分析更有意义。本研究性别的Wilksλ=0.651(F(1,328)=58.346,P=0.000,R2=0.3494),说明性别的差异显著,并且可以解释变异的34.94%。性别组间方差分析显示,见表2。体育锻炼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1,328)=165.027,P=0.000),可以解释变异的33.47%;同伴关系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1,328)=4.828,P=0.047),并解释变异的8.55%;主观幸福感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1,328)=18.232,P=0.000),并解释变异的5.26%。多重比较显示:男生的体育锻炼(M=38.59)、同伴关系(M=104.83)、主观幸福感(M=112.35)均显著高于女生(M体育锻炼=11.09,M同伴关系=101.91,M主观幸福感=101.46)。
表 1 均值、标准差统计表
表 2 性别的主效应检验
3.2 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3.2.1 相关性分析
对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进行Pearson双变量双侧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r=0.201)显著正相关,体育锻炼与同伴关系(r=0.189)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r=0.200)显著正相关。由此,验证假设H2、H3和H4不被拒绝。
表 3 Pearson双变量双侧相关系数表
。
3.2.2 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H5,结合温忠麟等[4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的解读,采用公式:Y=cX+e1,M=aX+e2及Y=c′X+bM+e3,利用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3个变量,采用强行进入法进行了一系列含3个回归方程的回归分析,具体解释如下:1)考察体育锻炼(X)对同伴关系(M)的预测效应;2)考察体育锻炼(X)对主观幸福感(Y)的预测效应;3)考察体育锻炼(X)与同伴关系(M)对主观幸福感(Y)的预测力大小。为确定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必须证明如下条件:在第1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体育锻炼必须影响中介变量同伴关系;在第2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体育锻炼必须影响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在第3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体育锻炼和中介变量同伴关系必须影响因变量主观幸福感。若上述3个条件得以满足,表明同伴关系是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1个中介变量。
表 4 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的回归分析(方程1)
注:SE=标准误;R2=0.031;***表示F值达到0.001显著水平,** F值达到0.01显著水平,* F值达到0.05显著水平,下同。
表 5 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方程2)
方程1中,见表4,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的预测效应显著(F(1,328)=11.506,P=0.000,解释了同伴关系变异的3.1%);方程2中,见表5,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显著,并解释了变异的4.4%(F(1,328)=16.126,T=4.016,P=0.000);方程3中,见表6,自变量包含体育锻炼和同伴关系,二者共同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变异的6.8%(F(2,327)=12.944,T=8.825,P=0.001)。回归方程显示,体育锻炼和同伴关系皆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均达显著水平,从方程2中发现,体育锻炼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的4.4%,当同伴关系介入(方程3)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变异增加到6.8%,而此时(方程3)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由方程2的0.216降至0.186。由此验证,同伴关系是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1个中介变量,即研究假设H5被拒绝。其中,a=0.184,Sa=0.131;b=0.166,Sb=0.082;c=0.216,Sc=0.203;c′=0.186,S′c=0.202。对照Sobel检验公式输入对应项的值,其检验公式为Z=abS2ab2+S2ba2 经计算,Z=1.16,查MacKinnon临界值表:1.16>0.90(P
图 2 中介效应模型
3.3 结构关系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3.3.1 模型拟合及影响效应验证
利用AMOS 22.0分析软件,运用SEM项目组合技术(Item Parceling)[44]构建结构关系模型,如图3所示。1)拟合指标显示所构关系模型极好的适配性和简洁性;结构模型路径系数验证了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3者间显著的正向影响(P<0.001)。2) Bootstrap抽样法运算(自抽样5 000次,置信区间95%水平上)在迭代到第28次收敛得知: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效应显著(P<0.001),这进一步验证了同伴关系在体育锻炼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注:x2/df越接近1越好,5以内可以接受;SRMR越接近0越好,0.05以内表示较好。GFI、AGFI、NFI、TLI及CFI这些指标越接近1,拟合性越好,一般来说,若这些指标>0.90,表示数据支持构念假设。
图 3 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结构关系(项目组合)
3.3.2 调节效应验证
根据林嵩对调节变量检验的解释[45],设定性别(男=1、女=2)为群组分类,构建2种类型模型(无限制和限制)。经测算(表7),分组模型x2/df均小于3,拟合指标表明2组模型均具较好适配性;限制模型和无限制模型拟合指标存在显著变化,初步判断性别的调节效应显著;分组回归分析比较,假设默认模型的卡方值自由度比改变值x2a/dfa=21.750/3=7.25,其临界比率P=0.000<0.05,卡方值改变达显著水平。说明性别在体育锻炼解释主观幸福感时的调节效应显著。
表 7 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4 讨论
4.1 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特征
本研究是建立在梁德清的体育活动情况、朱瑜的运动友谊质量、Pavot的生活满意度及邱林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自评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影响。调查显示,大学生具有较好的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但其体育锻炼现状却不容乐观。方差分析表明,性别在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显著,分别解释变异的33.47%、8.55%和5.26%。研究利用AMOS 22.0技术,通过分组回归分析,验证了性别在体育锻炼解释主观幸福感时的调节效应显著。研究认为,当考虑体育锻炼来预测主观幸福感时,男生和女生在锻炼行为和个体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在控制了这些条件的前提下,对于被试而言,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可能表现出性别上的不同特征。该结果与前人[4647]研究结论一致。多重比较显示,男生的体育锻炼情况、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均好于女生。相对于女生,正值青春活跃期的男大学生更喜欢参加体育锻炼,其自身的性格更活泼、亲和,情绪更积极、乐观,男生体育锻炼的氛围相对较好,在锻炼中建立的同伴关系更为巩固与融洽,对个体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亦相对较高。因此,人口学变量的性别因素能够作为体育锻炼解释主观幸福感中的一个调节变量,即研究假设H1不被拒绝。
4.2 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相关性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H2、H3和H4不被拒绝。1)体育锻炼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r=0.22)和同伴关系(r=0.18)。可见,体育锻炼可以使个体获得身心的满足和愉悦,提高自身对生活质量满意水平的主观评价,促进愉快、乐观的积极情绪,提升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体育锻炼还可以维持和改善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友谊质量,使个体行为获得更多的支持与接纳,提升个体自尊。2)同伴关系表现出与体育锻炼相似的作用,即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r=0.20)。可见,锻炼中具有良好同伴关系的个体,会从外界获取更多的运动支持、自尊互助及共享快乐,能够较好评估自身的生活质量,促进个体的积极情感,使个体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以上结果验证了以往的相关研究结论[2426]。
回归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H5不被拒绝。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β=0.18)和主观幸福感(β=0.22)均作出了显著正向预测效应,并分别解释了变异的3.1%和4.4%;当同伴关系介入时,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明显下降,其回归系数由0.216降至0.186;Sobel检验法验证了同伴关系是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中介变量;此外,研究还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在验证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基础上,证实了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可见,体育锻炼既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还可以通过同伴关系这一中介变量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数据反映出:体育锻炼能够提升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评估水平、缓解消极情绪、促进个体积极的情感,使大学生保持轻松愉悦的情绪和活泼开朗的性格;当与同伴共同参加锻炼时,大学生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和积极的情感会因同伴的介入得到进一步改善。研究认为,改善大学生体育锻炼的现状可以提升主观幸福感,而且,体育锻炼中同伴的支持与协同作用,能够使个体在获得已有积极心理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换言之,当考虑到体育锻炼影响主观幸福感时,在控制大学生体育锻炼特征的前提下,对于被试而言,体育锻炼中不同程度的同伴关系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考察了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积极心理特质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同伴关系在体育锻炼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所得结果既有利于解释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关联,又映射出同伴关系在体育锻炼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诚然,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因人格特征、家庭及生活应对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存在而更为复杂化。未来研究应着眼更多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探讨,为全面揭示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提供实践基础。
5 结论
1)大学生具有较好的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但其体育锻炼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性别在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中的差异显著,其中,男生的体育锻炼现状、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均显著高于女生。
2)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两两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效应显著,并分别解释了变异的3.1%和4.4%;同伴关系在体育锻炼的基础上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效应显著,在体育锻炼解释主观幸福感时具备部分中介效应,其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13.91%。
3)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综合影响,以及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性别的调节效应。
参考文献:
[1] Suh E,Diener E,Oishi S,et al.The Shifting Ba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Cultures:Emotions Versus Norm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2):482.
[2] 严标宾,郑雪,邱林.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应用心理学,2003,9(4):2228.
[3] 谢敏芳,李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与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28(8):103106.
[4] 张羽,邢占军.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7,30(6):14361438.
[5] 毕重增,张萍,朱晓菲.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心理科学,2012,35(3):683686.
[6] 孟慧,梁巧飞,时艳阳.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科学,2010,33(1):9699.
[7] Furnham A,Cheng H.Perceived Parental Behaviour,Selfesteem and Happiness[J].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2000,35(10):463470.
[8] Huebner E S,Gilman R,Laughlin J E.A multimethod Investig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Childrens Wellbeing Reports: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9,46(1):122.
[9] 刘芳,李维青,买跃霞.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4):470473.
[10]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心理科学进展,1996,14(1):4651.
[11] Hartup W W.Peer Relations: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and Interaction in Sameand MixedAge Situations[J].Young Children,1977,32(3):413.
[12] 万晶晶,周宗奎.国外儿童同伴关系研究进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18(3):9195.
[13] Sullivan H S.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ology[M].New York:Norton,1953:164188.
[14] 赵红梅,苏彦捷.心理理论与同伴接纳[J].应用心理学,2003,9(2):5155.
[15] Ladd G W.Peer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Competence during Early and Middle Childhood[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9,50(1):333359.
[16] Jacobson E.Progressive Relaxation[M].Oxford,England:Univ Chicago Press,1938:133158.
[17] Snyder E E,Spreitzer E A.Involvement in Spor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1974(5):2839.
[18] 季浏,李林,汪晓赞.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8,14(1):3843.
[19] McInman A D,Berger B G.SelfConcept and Mood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Aerobic Dance[J].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3,45(3):134140.
[20] 董宝林,张欢,朱乐青,等.女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机制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6):9198.
[21] 杨鄂平,丁爱玲,唐晓东,等.大学生健身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J].体育学刊,2007,14(8):8387.
[22] 朱健民,黄超君.关于大学生运动不应群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体育,2003(5):6364.
[23] 朱瑜,郭立亚,陈颇,等.同伴关系与青少年运动动机、行为投入的模型构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5(3):218223.
[24] 张欢,董宝林.女大学生体育锻炼动机的因子分析:以上海为例[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3,21(6):1719.
[25] 杨剑,王韶君,季浏,等.中学生运动友谊质量、体育锻炼行为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构建[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3,32(4):913.
[26] Konu A I,Lintonen T P,Rimpela M K.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choolchildren's General Subjective Wellbeing[J].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2002,17(2):155165.
[27] 刘烨.马斯洛的人本哲学:第一版[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14.
[28] Deci E L,Ryan R M.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Psychological Inquiry,2000,11(4):227268.
[29] 王芳,陈福国.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6):575576.
[30] 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心理学动态,2000,8(4):2328.
[31] 哈青.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6471.
[32] 陈爱国,殷恒婵,颜军.体育锻炼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体育科技,2010,46(1):135139.
[33] 梁德清.高校学生应激水平及其与体育锻炼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8(1):56.
[34] La Fontana K M,Cillessen A H N.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the Priority of Perceived Statu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Social Development,2010,19(1):130147.
[35] Pavot W,Diener E.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Psychological Assessment,1993,5(2):164172.
[36] 徐维东,吴明证,邱扶东.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5,28(3):562565.
[37] 严标宾,郑雪.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2(3):6064.
[38] Mantak Y.Exploring Hong Kong Chinese Guidance Teachers' Positive Beliefs:A Focus Group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2002,24(3):169182.
[39] Watson D,Clark L A,Tellegen A.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the PANAS Scal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8,54(6):1063.
[40] 邱林,郑雪,王雁飞.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J].应用心理学,2008,14(3):249254.
[41] 邢占军,王宪昭,焦丽萍,等.几种常用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试用报告[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10(5):325326.
[42]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5456.
[43]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44] 吴艳,温忠麟.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12):18591867.
[45] 林嵩.结果方程模型原理及AMOS应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8112.
[46] 章建成,张绍礼,罗炯,等.中国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报告[J].体育科学,2012,32(11):318.
[47] 王钱芊,许启晓,王维维.运动员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因素的相关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20(3):2022.DOI:10.14036/j.cnki.cn114513.2015.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