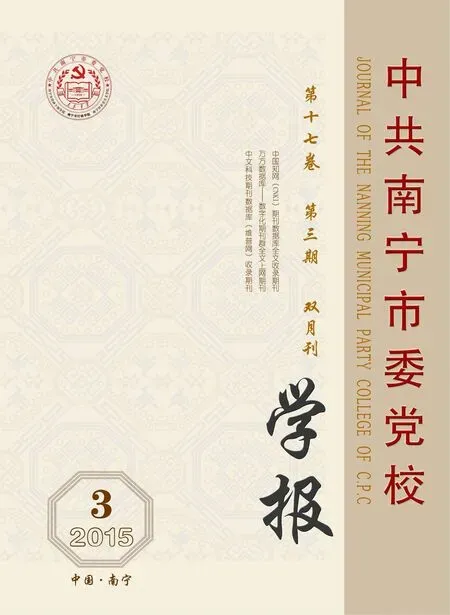明朝武官法律思想及制度建设初探
龚廷春
[摘要]明朝作为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典型代表,其法律思想和法制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明朝的武官法律经过长期的发展,也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明朝武官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丰富了军事法律的历史研究内容,其内在演变规律为当前军队法制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明朝武官法律思想武官法律制度武官权力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245(2015)03-0043-05
明朝是一个法制建设十分发达的朝代,其规范之详密、特点之鲜明、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均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武官法律作为军事法律的重要方面,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为后人留下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一、开明的用人思想和选拔制度保证了武官人才质量
从朱元璋用人“至公无私”始,明朝统治阶级的用人思想便彰显出开明的取向。后世各朝皇帝在制定和执行武官的选拔法律制度时都继承了这一思想。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世袭制的弊端越来越为人所察,统治者便适时调整了武官入仕的方式,把武举这一具备进步意义的制度的地位提到首位。
(一)对世袭加以限制,遏制武官队伍素质下降
武职世袭古已有之,也曾在特殊的时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如世袭制在战争对峙阶段能很好地完成军事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的使命;也可以较好地使将领与士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武官世袭的弊端也逐渐为有识之士所察觉,其中不乏统治集团中的政治家。明天顺八年,福建监察御史魏翰上书言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世袭之弊:“今天下武职子弟生长庇荫之下,崇尚骄奢之习。一旦承袭,侈然自满,纵欲无忌。”另外明代武官袭替的标准在总体上呈放宽趋势,这也导致了从明太祖洪武末年(公元1398年)至明宪宗成化七年(公元1470年),在军队总数并未扩大的情况下,武官人数由2.8万猛增至8.1万。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形成了军队的大量冗员,不但增加了政府开支,而且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为了克服武官世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明朝政府对世袭制度也相应做了调整。在实行武举以后,所有应袭子弟也要和庶民子弟一样考试策论弓马,中选后方能授官加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世袭制,更是选才制度有所进步的一种反映,也是对世袭特权的一种限制。所以孙承泽说:“及嘉靖间,此途(武举)渐重,于是世胃彼为虚器,而功臣之泽斩矣。”
但是不论武官的世袭制度在之前曾如何对军队战斗力产生过促进作用,之后又进行过如何的改革,这都无法掩盖其作为封建专制统治下贵族特权的实质。明朝政府对世袭制加以限制,为武举的实行拓展了空间,使高素质的武官人才能够大量进入军队,对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提高武举地位,增强武官人才选拔力度
在明中期以后,明政府为了在不断扩大的战场上取得胜利,将武举作为武官的主要来源,增强了武官人才的选拔力度。随着一套完备的武举制度逐渐形成,一批卓有才干的将领也得以通过武举进入了军队。尤其是在嘉靖以后,几乎在各个主要战场上都有武举出身的人卓立战功。例如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献就是武举出身;曾当过戚继光参将的朱先,“大小数十战,皆先登,杀倭甚众,以功授都司”,他也是武举出身,像这样武举出身的抗倭将领在战场上可说是俯拾皆是,许多人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辽东和抵御蒙古诸部的战场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武举出身的将领。例如安固,正德三年武会试第一,赴陕西三边立功,后“以材武致大将”。这些武官人才为军队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使军队在训练水平、作战能力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提高。这充分说明武举制得到统治者的肯定和大力运用,也是符合社会和军队发展规律的。
从明朝整个的政治体制上讲,武举的进步意义在于其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文举和武举一直是国家人才的重要来源,发展至明代,武举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礼仪日益隆重,并最终取得了和文举大体同等的地位。应该说,武举的制度化和完备化是在明朝完成的,且直接影响到清朝。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武举制度,只是稍加变通。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被废除为止。
由此可见,明朝武举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对于武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军队战斗力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武举法律制度并不能解决当时社会所有的弊端,明代统治者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才“锐意重武”,幻想以此来挽救颓势尽显的明王朝,结果只能是走向衰亡。
二、严格的规范思想和惩罚措施塑造了纪律严明的武官队伍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与“刑”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其中,“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不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军队,管理者都要讲求“礼刑结合”,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治理效果。明朝军队对于武官的礼治规范思想和军法从重原则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古代法制“礼刑结合”思想的体现。“礼”“刑”二者相辅相成,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武官加以最为严格的规制。
(一)“礼”强调等级关系,增强武官上下凝聚力
明朝统治者从儒家行王道仁政的思想出发,以“礼”作为定国兴邦、约束军队之策。其“克城以武,堪乱以仁”的军事法律思想虽有出于战时需要而收买人心之嫌,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降低战争危害、保护生产力发展和平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建国初期战事频仍的时期,明军“由是人心日附”。
由于“礼”是以封建传统的家族伦理思想为核心内容,凶此以“礼”作为规范部队的行为准则,不仅非常容易为官兵所接受,而且约束力也很强。戚继光在他的《纪效新书》中用一段十分通俗的话来告诫官兵:“你今既来当兵,队长就是你的里长,哨长就是你的老人,哨官把总就是你的父母官……你冉思量世间有无里长老人管的百姓无有,就知在军中有无队哨长管的兵无有;世间有无父母生的人无有,就知在军中有无哨官把总管的兵无有。”这样,家族内部的伦常关系被引入军队的日常管理当中,上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下级的“父母官”,对上级的约束和命令,下级便绝不能有任何反抗。诚然,这种军礼所确立的上下级关系和等级名分虽有利于强化将帅的权威,但也容易造成上下的隔阂,使军中缺少亲和力。军事家们为弥补这种弊端,提出“军中之正,以连情义为首务”,即一方面强调遵守上下级的名分,另一方面加强上级与下属的关系,用同命运共患难的感情将官兵联系在一起。如此情礼并用,使军队内部上下左右形成一种相互珍贵的纽带,从而明确了上下级各自的责任和权利义务状况,也符合“礼”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要求。由此使得军礼与军法结合在一起,达到“在下事上,则尊而亲之;在上使下,则顺而悦之。三军之众,可使赴汤蹈火矣”的效果。
(二)“刑”强调军法从重,保证武官军纪严明
白从春秋时期军事家尉缭子倡导“军法从重”以来,“军法从重”就成为古代军事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明代统治者也继承了这一原则。如明初期,大将胡大海在进攻绍兴时,其子触犯禁酒令,有部下劝朱元璋宽赦以安抚胡大海,但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遂处死胡大海之子。又如洪武四年,部将廖永忠率军进驻四川,下令禁止官兵侵掠百姓,有士卒拿了百姓七个茄子,立即被斩首。如此严格地执法在战争频繁的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保证军事法律的贯彻,才能使部队协调一致。
明初军法从重的原则,保证了武官在作战指挥中的军纪严明、令行禁止。明军在建国初期的战争中,朱元璋在军中厉行“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的纪律,明军进入集庆时秋毫无犯,拔镇江“民不知有兵”,征婪州“市不易肆”,克杭州“城中帖然”。戚继光在其所著《草庐经略》中也对戚家军规定有“遏乱安民”的禁暴条令。“师到之处,无暴神诋,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蟠墙屋,无焚树木,无掘丘坟,无取六畜、禾泰、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慰归无伤;虽遇壮者,不可无礼。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秋毫无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将禁戒之严,故其下奉命不敢违也。”
从明朝建国时期明军力克诸强一统天下,到明朝中后期戚家军威名远播,无一不是依靠了一支纪律严明、明赏严罚的武装力量。历史一再向我们证明,严明的军纪是妥善处理军民关系的前提,也是使部队拥有强大战斗力的保证。明朝的军法虽带有专制王权的特征,但其军法从重、军纪严明的军法原则对于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言,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缺乏评判和监督机制的军功制度导致了武官的冒领功次和消极应战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一直信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点,诚然,在作战中对立下战功的军人进行奖赏,能够起到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这种方法运用不当,也会造成很大的弊端,甚至会抵消军队的战斗力。
明代的军功标准有二:一为“以战斗表现论功制”,一为“首功制”。在战场实践中,明代所实行的这两种军功标准都表现出缺乏有效的评判和监督的弊端①。
“以战斗表现论功”标准在明成祖时建立功赏勘合制度,凡遇战斗,“令内官将象牙牌临阵看视,有勇敢当先、奋力向前杀贼能建立头功、奇功者,即与牙收牌收执,径赴大营奏知,给与勘合,以凭升赏”,稽查之法可谓甚严。永乐之后,稽查制度虽在,但在实际上却已弊端凸显,借此标准冒滥功级者日众。“故事,镇守官奏带,例止五名。后领兵官所奏带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斩谶之例,别立名日,曰运送神枪,曰费执旗牌,曰冲锋破敌,曰三次当先,曰军前效劳。冒滥之弊,至斯极已。”凶为“以战斗表现论功”并无严格的判定标准,在事后也无法核实,所以只须巧立名目,冒领功次要比“首功制”方便容易得多。由于“以战斗表现论功”标准始终存在着冒滥功次这个最大弊端,以致于战场上常发生斩首不过几级,而升赏却有数十百员的情况。于是明廷对以此标准论功渐渐持谨慎态度,而后转向以“首功制”为准。
“首功制”虽然使得军功奖赏的标准更加明确,但其背后的弊端更大。“首功制”最大的弊端有两点:一是杀良冒功,一是临阵割级②。杀良冒功的情况在有明一代可说是层出不穷,如“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曹钦反。将士妄杀,至割乞儿首报功。市人不敢出户。林聪署院事,亟令获贼者必生致。滥杀为止。”正德十年(公元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上书说将士以首功进秩,“此赢秦弊政,行之边方犹可,未有内地而论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议所致”,由此可看出明代杀良冒功的祸害之烈。关于临阵割级之害,更是屡次被实践证明。明人郭光复说倭寇与明军对阵“合战先以数倭蹈阵,胜则群拥以进,不胜必侯我兵争取首级而乘之,故常胜。”戚继光也对部下强调,“每每致贼以数人为饵,诱你上前都去争功,他却大众一拥杀来一个首级又不得,不知被他杀了多少,乘众少却将营盘冲破,全军没了。”本是用来激励将士奋战的军功赏格反被敌人利用来屡败明军,本意为提高明军战斗力的“首功制”反而束缚了明军的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由此可见,明朝统治集团在设计军功制度之时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但由于制度本身在导向上的偏差,以及对战场杀敌表现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评判和监督标准,导致武官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可钻,而且对军队战斗力形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四、文官压制和特务特权破坏了武官法律的秩序 从以文制武的思想,到无所不察的监督,冉到法外设立的厂卫特务,我们不难看出,大明王朝的武官们始终处在一种受特权压制和限制的态势下。所有的特权和压制归结到一起即可以概括为对武官权力的过度限制,造成了对武官法律秩序的破坏。
(一)文官的压制削弱了武官尽忠职守的意志
明朝作为汉人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若要巩固其统治,就必然要借鉴前朝的经验。对“以文制武”思想的继承就是明显的例子。明朝的统治者深明制约武官权力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上一系列的制度在实践中贯彻了“以文制武”的思想。
明朝武官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受到的约束和限制也会凶平时和战时而有所不同。在平时,虽然兵部是最具实权的军事机关,但不管是五军都督府还是兵部,其兵权行使总要受到其他文官部门的牵制,如军粮供给归户部、武器装备归工部、马政归太仆寺,凡重大事项还要兵部会同有关部门奏请皇帝定夺。另外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中央军事领域的最高领导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取士而为官的文人,虽然他们担任的是武职,但不能否认他们同文官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说武官受文官的牵制,并不为过。而在战时,朝廷为加强对军队将领的控制,派出了专门的文臣来督军。如派都御史巡抚而兼军务的称捉督;有总兵的地方设赞理或参赞;管辖地域广或战略重要方向则设总督。这些措施,含有以文官领军之意,用以防止将帅专兵。明中期以后,战事较多,此时朝廷即在原在的基础上增派了多种临时军事领导,如“总督潜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总督药、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管粮饷”及“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兼巡抚河南”等。这些官职均为朝廷凶事制宜、临时选派的文官大员,但无形中给地方原有的军事领导机构上又增加了一层,并逐渐形成了地方军队的文官领导武官的模式。
除文臣督军外,言官的弹劾对武官的影响也绝不容忽视。明初,太祖皇帝是禁止风闻监察的,但他的这一思想的约束力对明朝后世愈加淡化,导致风闻监察层出不穷。风闻是一种特殊的监察,科道官能否直言无忌不挟私妄奏,不怕获罪报复,敢于指责朝政之弊,痛斥君主之失、大臣擅权为奸,一则在于言官本身白具的一股刚直之气与一颗忧国为民之心,再则在于有否保护与惩戒措施。
尽管明朝统治者不断力图完善风闻弹劾制度,力图避免弹劾的泛滥问题,然在实际运作中,却往往事与愿违,其负面作用日益突出,尤其在明中后期随着政治大气侯的变化,整个社会呈现结构性腐败。在这种环境下,武官往往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明哲保身,为求政治上的稳定而放弃在专职上施展拳脚的努力;第二,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本就处在重文轻武的朝廷中的武官,其地位和处境只能日渐尴尬。对此,翰林大学士商格曾指出“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捉拿取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捡家财。”从而形成内外文武重臣“皆不安于位”,而百司庶府之官“举皆不安于职”的局面。
(二)特务的特权阻碍武官作用的发挥
明朝的武官不仅在朝要受言官的监督,在外统军时还要受到另一“监督”,即特务的监视。在唐宋便已有的“监军”之职,在明代使用得最为普遍。“无论战时平时,军营边塞,都有宦官特务在里面捉督监察,从朱橡起到朱由检止,一直没有停止过”如此,失去皇帝信任的武将们便只能低声下气地去奉迎、拉拢这些特务监军,冉加上特务们背后有皇帝撑腰,于是武官们也就在实质将军队操练、指挥的大权拱手让给了皇帝的心腹们。这些在皇宫内养尊处优的宦官,全无带兵取胜之法,由他们指挥的军队,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基本上没有可能,英宗年间太监王振造成的土木堡之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占役买闲”现象是特务监军对军队造成的另一大破坏。至正德年间,占役买闲已发展到可怕的程度,武宗即位之初,京营“十二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削弱者二万五千而已”,到了正德末年,给事中王良佐奉敖选军,“按籍三十八万有奇,而存者不及十四万,中选者仅二万余”。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部尚书王邦瑞曾揭示出京营的腐败情形。“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战守俱称无军……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而当时昏庸的皇帝根本不听从这样的意见。史载:“……然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从武库索甲仗,主库奄人勒常例,不时发。久之不能军。”这也正是“占役买闲”对军队战斗力造成负面影响的真实写照。
这“占役买闲”的种种腐败情形到崇祯时已病人膏育,纵想整治,也会遭到宦官们千方百计的阻止。终至无法收拾的局面,丁易先生说:“明朝统治者这样信任宦官特务,派他们统率京营大军和自己的亲军,在统治者看来,这该是可以高枕无忧了,但结果呢,明朝的灭亡就在这上面。”对此,《明史》评论道:“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祷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明朝灭亡当然并非在宦官特务,而是一整套臼趋腐朽的系统运行的必然结果。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明朝皇帝对宦臣的极度信任和对武官的极度不信任使得特务监军手握监军和统军大权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因素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上面两则引文才如此痛切地将明朝的覆灭和宦官特务直接联系在一起。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出于保护专制皇权的需要,一直以各种手段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并限制武官权力的发挥,但由于过度的限制和缺乏有效运行的监督机制,从而超出了统治者最初的构想,造成了对武官法律秩序的严重破坏,同时也对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和提高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