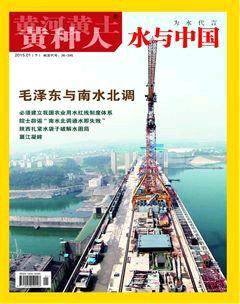毛泽东与南水北调
靳怀堾
一
1952年深秋,金风习习中,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出现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畔。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湛蓝的天穹下,滔滔大河更显得雄浑壮观。
这是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3月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进入北平(1949年10月1日后改称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后第一次离京巡察到达的地方。
古语说:“黄河宁,天下平。”动辄决口泛滥,被称为“中国之忧患”的黄河,让毛泽东牵肠挂肚,寝食难安。
“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在河南兰封(今属兰考)黄河大堤的东坝头,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的地方,毛泽东发出了震古烁今的一问,他老人家急切地想找到解决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对策。
看完东坝头,在专列上,毛泽东向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主任王化云详细询问了黄河治理情况。个子不高、精明干练的王化云在谈到黄河治理与开发的打算时,带着憧憬的神态说:“将来黄河水不够用,需要从长江流域引入黄河。我们黄委的一支勘测队正在查勘黄河源和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想把通天河的水引到黄河里来,以解决华北、西北地区水源不足的问题。”
毛泽东闻听此言,眼睛霍然一亮:“好!这个主意好,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
顺着王化云的想法,毛泽东接着问起通天河的水量及黄河上游的情况,王化云一一作答。
听着王化云的介绍,毛泽东那装满宇宙风云的大脑,开始急速盘旋起与防洪相反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神州大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何以丰补歉?
于是,毛泽东带着期许的神情对王化云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也是可以的。”
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却点燃了共和国跨流域调水的星星之火,从此,国人开始投入极大的热情和智慧编织起一个宏大的“水之梦”——南水北调!
其实,南水北调这一伟大构想的首倡者并非毛泽东,而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
当年,孙中山为创建一个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精心勾画了一张宏伟的蓝图—— 《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在《实业计划》这部洋洋10万余言、充满远见卓识的皇皇篇章中,孙中山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百年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其中就包括“引洪济旱”、“引江济河”的计划。
但是,对当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中国而言,“引江济河”,只能是一个望梅止渴的空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驰骋于川、黔、滇3省之间的广大地区。是年8月的一天,扛着一肩硝烟和征尘的毛泽东,脚步踏上了四川阿坝地区一个叫麦尔玛的村庄。站在村头的一座小山丘上,山脚下有两道潺潺流水,一条往南淌,一条往北流,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问起了这两条河的情况。一位熟悉当地地理的人告诉他,南面的流入长江,北面的流入黄河。毛泽东闻听此言,突发奇想:“从山中打个洞,长江水就流到黄河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只是随便一说,并未多想——充其量不过是诗人即兴的浪漫遐思而已。
后来,当他转战到陕北之后,面对极度干旱缺水的黄土高原,他的脑海里是否会不时冒出那个江河分水岭的小山丘?
毛泽东生在水乡,长在南国。以42岁为界,之前,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南方;之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方——先是陕北(主要是延安),后是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再后来就是北京。相对于江河泱泱、雨水丰沛的南国,无论是延安黄土高坡的水贵如油(土地因缺水而贫瘠),还是华北地区经常出现的苦旱焦渴,强烈的反差,在毛泽东的心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
毛泽东深知,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离开水利的支撑和保障将寸步难行。而南方水多,常常泛滥成灾;北方水少,常常旱渴成患。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国土整治,南水北调,以有余补不足,才会打破中国北方干旱缺水的瓶颈。
这个“瓶颈”必须打破!
于是,黄河边毛泽东对王化云发出的一番“借水”宏论,便不再是麦尔玛小山丘的浪漫遐思,而是一个重构中国南北互济巨型水网的宏伟构想了。
转过年(1953年)的2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南方。16日,车到郑州,毛泽东再次接见王化云,一见面就问他:“通天河引水问题怎么样了?”
王化云说:“根据我们查勘的情况,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需要打100公里山洞,还要同时在通天河上建筑一座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
毛泽东问:“需要多大工程量?得多少年完成?”
王化云答:“约需10万人,加上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引100亿立方米太少了,能从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就好了。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几天以后,毛泽东高大魁梧的身躯又出现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上。
1953年2月19—22日,毛泽东乘“长江”舰视察长江中下游。在踏浪而行的“长江”舰上,毛泽东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掌门人林一山纵论长江治理开发。此前两天,他们谈论的重点是长江防洪及长江治理规划等问题。22日,他们讨论的话题转到了南水北调上。
毛泽东是有备而来,林一山也做足了功课。不过,林一山心里仍有些忐忑,他是“考生”,不知道“考官”提出的问题他能否对答如流。自从1949年12月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后改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部长由民主人士刘斐担任)、兼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以来,他一头扎进治江实践,靠着过人的天赋与执着,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基本摸清了长江的脾气秉性。后来,从考官满意的表情可以读出,林一山是个好学生,他的考试成绩不错——在“长江”舰上3天多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惊叹于林一山对长江情况的了如指掌,亲切地称他为“长江王”。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这件事情你想过没有?”毛泽东见到林一山,便微笑着挑明了话题。之前两天,他们围绕治江大计的长谈,林一山的睿智和博闻强记让毛泽东对他颇有好感,很愿意与之探讨更多的水利大事。
“想过,当我想到全国农村水利化问题时,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不敢想,也没有交代给我这个任务。”林一山实话实说。
毛泽东在桌上展开林一山带来的《中国地图》,开始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指点江山”。
毛泽东手上的铅笔首先指向了四川北部的白龙江:“白龙江水大,能不能调到长江以北?”
林一山答:“不行。”
“为什么?”毛泽东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林一山。
“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势低,不可能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注:这里指华北)。而将白龙江的水引向西北更有意义,引水工程也有兴建的可能性。越是河流的上游,地势越高,居高临下,则利用地势自流引水的可能性越大,但水量较小,因此引水价值不大;反之,河流越是下游,水量越大,地势又越往下越低,引水工程的可能性越小。”林一山侃侃而谈。
毛泽东觉得言之有理,又把铅笔指向了嘉陵江的源头之一西汉水:“这里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道理同白龙江一样?”
毛泽东手中的铅笔又指向了江汉:“汉江行不行?”
“汉江有可能。”
“道理何在?”
“汉江与黄河、渭河只隔着秦岭平行东流,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规模反而越小。”
毛泽东面露喜色,他用铅笔从汉江上游至下游画了一道又一道横杠,每画一道,都要问一句:“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性,但要研究哪个方案最好。”
当毛泽东的铅笔指向丹江口一带时,林一山说:“这里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线路。”
毛泽东目光如炬:“为什么最好?”
“汉江从丹江口再往下即转为向南复向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乏兴建高坝的条件,所以不具备向北方引水的有利条件。”
林一山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最好,并非信口道来,因为近年来,他和长江委的同事在研究汉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时,曾提出过在丹江口修建水库,只是还没有考虑利用这个工程进行南水北调。毛泽东的这一指,让林一山顿时开悟:丹江口工程有可能成为南水北调的一个方案。
“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查勘,一有资料就立刻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毛泽东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
“长江”舰顺流而下。
大江奔涌,滔滔东去……
不知不觉间,“长江”舰到南京了,毛泽东在与林一山告别时说:“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到长江许多知识,学习了水利。”又叮嘱道:“三峡工程暂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对很多事情确实有“叶未落而知天下秋”的前瞻性,当别人对前面的路怎么走还在踌躇徘徊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山巅登高极目,畅想未来了。
林一山对毛泽东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
2005年12月的一天,林一山的北京住所,《环球视野》杂志记者王香平专门就毛泽东与南水北调的话题采访了他。94岁的林一山虽然双目失明,但思维依然敏捷,回忆起与毛泽东在“长江”舰上纵论南水北调的情景时,他心潮澎湃,动情地说:“主席在‘长江舰上勾画的这幅宏伟蓝图,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使我豁然开朗。主席的眼光、胸怀和气魄确实与众不同,他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长江治理与开发中最为关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大课题。从主席的总体设想来看,虽然对三峡工程仅仅是摸底,暂时不干,只抓紧南水北调工作,但他并非厚此薄彼。我理解他的意思,是相对于三峡工程而言,他所设想的南水北调这项工作尚未起步,他所了解的情况远未达到三峡工程的程度,因此指示我立即回去做调查,有了情况马上给他写信,使他对南水北调也能与三峡工程一样心中有数。以后的事实证明,由于我们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南水北调工作,同时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各项研究,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才决定兴建丹江口工程,从而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基础。”
二
林一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回到长江委机关后,立即组织人马开展了“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
由谁来带队开展这次意义非凡的查勘工作呢?林一山想到了王明庶。王明庶是科班(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出身,精明能干,做事认真,时任长江委第二勘测队队长,手下有十六七个人。就在毛泽东与林一山在“长江”舰上纵论南水北调的时候,王明庶刚刚带着他的队伍完成了丹江口水库坝址及库区的首次查勘的外业工作,正在忙着整理查勘报告。
新任务下达了。王明庶和他的队员们闻风而动,立即着手“备战”,他们找来了汉江河道地形图,找来汉江流域1∶10万军用地形图,找来有关汉江的水文资料、前人查勘报告,还找来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古籍。林一山也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解放战争时期1∶200万的彩色地形图慷慨地借给了他们。
一番“纸上谈兵”(即借助地图和资料,经过研究分析,初步确定一个“理论方案”,以增强实地查勘的针对性)后,王明庶带领他的人马出发了;一番跋山涉水后,勘测成果出来了:位于陕西旬阳县境的汉江支流旬河口以下1~2公里的河段最好,用队员们的话说是“天赐宝地”——此段河道顺直,两岸山势狭窄、山坡陡(地形狭窄可以减少工程量和造价),地质条件好,就地取材就可以建起一座巍峨的堆石大坝(坝高250米)。至于引水线路,他们测定,从秦岭的南坡,沿子午线(经线)方向开凿一条穿越秦岭的隧洞(约80公里),便可将水引至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当时初步估算,年引水量200亿立方米,平均流量600立方米每秒,开隧洞的石方约4000万立方米。
初步的查勘成果出来后,最兴奋的人当属林一山。
勘测结果一出来,林一山便把王明庶请到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林一山一边听汇报一边看地图,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还不时插话,向王明庶等人讲述毛泽东南水北调的战略构想。
是啊,林一山怎能不高兴呢,在“长江”舰上,当毛泽东问到从哪里引水北上合适时,凭着这些年来对长江和汉江的了解,他脱口而出,说汉江“可能性最大”。此次第二勘测队查勘的结果,初步验证了他大胆设想的可行性。
“现在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了。”听完汇报,林一山笑吟吟地对王明庶说,其实更是对他自己说。
几天以后,林一山专门在汉口长春街长江委机关小食堂宴请了全体勘测队员。宴会开始时,林一山致辞,这位被人誉为“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长江统领”,博闻强记,满腹经纶,尤其是嘴巴特别厉害,人送雅号“林铁嘴”。林主任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讲到兴奋处,更是眉飞色舞,顾盼生辉。他讲到了在“长江”舰上与毛泽东纵论南水北调的情况,讲到了毛泽东与他的“约定”,又讲到了“引汉济黄”的伟大意义……最后,他满怀豪情地说:“200亿立方米的引水量,接近于半条黄河,效益巨大,这是一个壮举,也是长江委的一项重大任务。”
林一山的讲话热情洋溢,充满鼓动性,一下点燃了全体勘测队员的情绪,大家的心里像抹了蜜一般,盛满了甜甜的成就感。酒还没有喝,气氛早已热烈起来。“干杯,干杯!……”林一山招呼着,与勘测队员们一一碰杯。
从林一山在长春街小食堂宴请第二勘测队员那天起,南水北调的秘密就在“长家大院”彻底公开了。
“林主任在‘长江舰上见到了毛主席,主席让他开展南水北调的前期查勘工作。”
“应该是‘引汉济黄。”
“听说王明庶他们已在汉江旬阳口一带找到了引水的口门和线路。”
“要开凿80多公里的隧洞,难度可不小。”
“可不是,投资太大不说,技术上能行吗?那可是硬邦邦的山体啊!”
“能否还有更好的引水地点呢?”
……
一时间,南水北调成了“长家大院”的热门话题。
这件事更触动了长江委规划处主任工程师王咸成的敏感神经。
王咸成是浙江武义人,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先后供职于国民政府中央水利实验处、汉江工程局;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进入新组建的湖北省水利局任工程师;后又调到长江委中游局、汉江工程处任副科长、科长,对汉江水系比较熟悉。1950年2月,王咸成参加汉江查勘组,跟随林一山等查勘了汉江中上游,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这天,王咸成在查阅地形图时,发现在河南方城县东北部江淮分水岭——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间有一处自然形成的隘口——方城垭口(又称“方城缺口”、“风口”),是一段沉陷的山地,形成了东北窄、西南宽的喇叭状地堑(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20公里,两侧地面高程达200米以上,而地堑最低处仅为145米)。
“这个隘口能不能利用呢?”王咸成心中一动,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天晚上,王咸成在读《宋史·河渠志》时,从发黄的书中读到了一则“秘密”:北宋年间,为了打通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与汉江之间的漕路(襄汉漕渠),朝廷曾派数万人马先后两次开进方城垭口,企图凿开一条渠道,让白河(源于伏牛山玉皇顶东麓,经南阳至湖北省襄阳县龚家嘴与唐河汇合后称唐白河,西南流至襄阳注入汉江)与石塘河(甘江河)、沙河牵手,“合蔡河入京师”。但由于受到方城垭口段硬岩和沙砾层的强力阻击,“白河终不可开”,留下千古遗憾。
先贤们关于“南水北调”的大胆探索虽然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却给王咸成以莫大的启示。蓦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如同闪电划破夜空一般,在他的心中跳跃而出:在丹江口河段筑坝引水,通过明渠引水至方城垭口,再经许昌、平顶山,至郑州附近把水引入黄河,岂不是一条捷径?!
王咸成的思想火花一出,立即引起了林一山的兴趣:在旬阳口一带筑坝,好是好,可是要打很长的隧洞,投入多多,困难重重,如果丹江口那儿行,真是太好了……他禁不住大喜过望,心向往之。
于是,林一山再次调兵遣将,派王明庶带人到现场查勘求证。
很快,好消息像春风一般,从丹江口一带吹入了“长家大院”。
11月的一天,满怀兴奋的林一山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了引汉济黄查勘情况。信中说:为贯彻“长江”舰上毛主席关于南水北调工作的指示,长江委组织了引汉济黄线路查勘。在丹江口河段,先后查勘了3条可能的线路,经比较认为,由丹江口水库自流引水,绕经唐白河平原,翻越汉淮分水岭方城垭口,然后向东北,经舞阳、许昌等地,在郑州附近入黄河,这条线路最为理想。
后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方案,就是以丹江口水库为水源,引水过方城垭口,向东北流至黄淮平原,在郑州荥阳附近通过隧洞穿过黄河流向京津冀的。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就是汉江水量有限,难以满足北方大规模用水的需要。
如之奈何?林一山的眉头又蹙了起来,锐利的目光不时在地图上扫描着,那颗睿智的头颅中思考的翅膀不停地在肯定与否定间翻腾着。
好在“长家大院”藏龙卧虎。正当林一山苦思对策的时候,有人星夜叩门,向他献策: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在距今并不遥远的地质年代,曾是汉江的河源,后因嘉陵江上游巴山南侧河源水流的不断侵蚀和切割,袭夺了汉江上游,变成了嘉陵江的一源。能否通过做些工程,把嘉陵江上游的水引回到汉江来,以增加汉江的水量?
林一山听罢,顿有茅塞顿开之感,脱口而出道:“果真如此,那太好了!”
为了验证嘉陵江调水的可行性,林一山亲自出马,率领一哨人马跋山涉水于汉江和嘉陵江源头一带。在汉江源头,林一山看到,这里的河床开阔,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与一般分水岭地区的河源大不相同(绝大多数的江河源头,初始处都是由点点滴滴汇成流苏般的小溪,涓涓而流)。再到西汉水一带查看,证实了汉江之源西汉水被嘉陵江袭夺是千真万确的。这样一来,把嘉陵江上源之水引到汉江,应当是可能的。
回到武汉后,林一山就马上组织力量完成了“引嘉济汉”方案。方案一出来,林一山觉得可行,便挑灯夜战写信给毛泽东。信中简明介绍了“引嘉济汉”的方案,并解释了以往认为白龙江不能向华北引水的原因:当时不知道嘉陵江上游河段曾经是汉江的江源,因而认定从嘉陵江上游引水不能直接穿越秦岭。实际上可以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形条件,沿秦岭以南的等高线,绕道通过汉江向华北引水。
为了找到更多的引水线路供中央决策参考,林一山又组织开展了自三峡向丹江口引水、从长江下游沿大运河调水及巢湖引水等多个方案研究……
三
林一山快速反应,源源不断地把前方查勘论证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呢,尽管有操不完的国家大事,但南水北调一直是他心头上盘旋的大事之一,特别是有了林一山这位“侦察兵”不断送来的“情报”,多谋善断的他信心更足了。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其中的一项议程就是专门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的意见》,里面明确提出了“引江济黄”方案。毛泽东在讲话中纵论南水北调,他挥舞着手臂,踌躇满志地指点江山:“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从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领袖的万丈豪情,赢得了一片热烈掌声,掌声的热浪涌向会场的每个角落,撞击着回荡着盘旋着。
后来,林一山回忆说:“看了毛主席的这段讲话,证明毛主席看了我写给他的信。”林一山接着说:“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我听说毛主席追问陈伯达,为什么把林一山写给他的信丢了一封?我当时只知道这件事,却不知道主席没有看到的是哪一封信。”
1958年,丹江口工程上马,1973年建成。其水工建筑物除了通常的大坝、水电站、泄洪闸、船闸之外,还有向华北引水的引水闸和渠首工程。
不过,从调水意义而言,丹江口水库也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在近期不考虑南水北调的指导思想下,丹江口水库的建设着眼的是防洪和发电,在设计坝顶高程175米不变的情况下,先按坝顶高程162米施工,正常蓄水位157米。因而,向华北引水的引水闸和渠首工程也只是个象征性的摆设。
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强调:“除了各地区进行的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指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加速制订。”
“南水北调”,这四个意味深长、重若千钧的大字第一次赫然出现在中央的红头文件上。
1959年4月2—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设想。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一天步行走30里,骑马走30里,骑骑走走,一直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上海崇明岛……这样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
讲话中,毛泽东还向与会者推荐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他充满感情地说:“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差不多把中国走遍了。《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政治家的毛泽东,为什么“想学徐霞客”呢?
有人说他有“江海情结”。难道他真的醉心于游山玩水吗?不是的,他是想对黄河、长江进行一次全面考察和调查研究,以便弄清这两条大河的地形、地质、水文、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直接目的是为决策上马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做准备。间接的目的就是对中国的国情、水情进行一次综合大考察,从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战略构想和规划。
1960年5月,毛泽东到河南视察,在郑州听取河南省关于工农业生产的汇报。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汇报河南的自然资源情况时说:“河南缺石油。”毛泽东插话道:“你们还缺水,要南水北调。”可见,毛泽东对南水北调是时时记挂在心上的。
1964年夏天,毛泽东在为“走黄河”做着各项准备工作。这天,北戴河浴场一号住所,刚刚从北戴河大海中搏风击浪归来的毛泽东忽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黄河的事情可以如愿了,再不搞就来不及了。这次去黄河,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一大批专家……”
看来,这次毛泽东真的要走黄河了。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因为天有不测风云。
1964年8月2日,在北部湾海域,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战争迅速升级,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北部湾事件”的爆发,让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考察黄河的计划,他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北面,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南面,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为了有备无患,开始运筹和推进战略大后方基地——“三线”建设;1966年5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毛泽东走黄河、长江的夙愿亦在“革命”的滚滚硝烟之中被淹没了。
再后来,毛泽东老了,虽然雄心犹在,但许多事情已力不从心了。南水北调,还有其他许多事情只好留给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