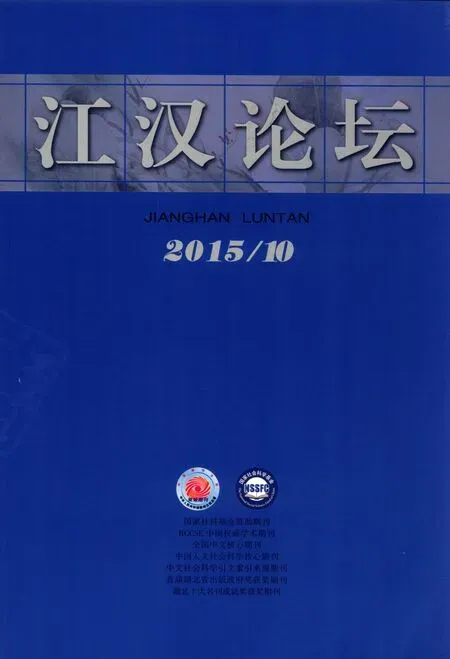论20世纪50—80年代小说对“孝”的消解*
周水涛
忠孝观念与文学书写
论20世纪50—80年代小说对“孝”的消解*
周水涛
百善孝为先,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几十年内,主流意识视域中的小说对“孝”进行了消解。消解的主要方式有三种:由反对封建主义而拒斥“敬老”“孝亲”;将“老”与“亲”设定为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对象;将伦理性的“敬老”“孝亲”转化为政治敬仰。
当代小说;主流意识;孝道;后喻权威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国封建伦理观念的核心。近年来,弘扬中华孝文化、提倡现代孝德,已被提升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实施文化战略的高度,随之,具有“孝亲”倾向、倡导孝行的小说不断问世。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一时段内,鲜有关联“孝”的小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多种原因,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是关键性因素。
一、由反对封建主义而拒斥“敬老”“孝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敬老”与“孝亲”的具体行为,是孝行的核心内容,但十七年小说对“老”或老父辈的“敬”具有选择性。此时的作品中有多种冠以“老”的人物类型,如老模范、老贫农、老支书、老革命、老坚决、老封建、老顽固等。在特定的时代,“老”既是一种辈分标记,又是一种政治属性。老模范等带“老”字的人物是“正面人物”,对于这些正面人物而言,“老”即人物优良品格保持的持久性与永恒性,是一种红色政治印记。老封建、老顽固等带“老”字的人物在一般情况下是“反面人物”,对于这些人物而言,“老”往往关联着反动、腐朽、没落等阶级属性。因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道伦理规范在十七年小说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至少老封建、老顽固等带“老”字的人物被排除在“敬老”或“孝亲”之外,因为这些人物是“封建残余”,是阻挡时代车轮前进的障碍物,是被批判或否定的对象,而对这些人物的批判与否定实际上构成了对“孝”的排斥。在张克杰的《婆媳之间》中,腊狗娘是一个“好使个鬼心眼儿”的媒婆,此人在旧社会凭她那两片巧嘴“混得个肠肥腰包圆”,在新社会好吃懒做,偷奸耍滑,与思想落后的媳妇狼狈为奸,处处与年轻干部雪雪作对,尽干一些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坏事。在骆宾基的《父女俩》中,坐地贩子刘四与81岁的老光棍刘子兴都不是地道的种田人,他们都憎恨新生事物,反对“走社会主义的路”。进入60年代之后,在那些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作品中,部分老人成了遭人唾弃的坏人。例如,在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马之悦、马小辫等老字辈就是典型的“阶级敌人”,这些人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投机分子”,是必须无情斗争的“地富反坏分子”。
毋庸讳言,十七年阶段的诸多价值理念在“文革”时代得以顺承、扩张。在文革小说中,部分老人是罪大恶极的坏人。这些人一般都有晦暗的人生经历,旧社会的为非作歹与新社会的反动投机构成了他们晦暗的人生轨迹。例如,在浩然的《金光大道》中,范克明与冯少怀就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与人民为敌,作品通过他们与以高大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较量,展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因此,这些“反动”的老人也被排除在“敬老”或“孝亲”之外。
很明显,无论是十七年小说中的腊狗娘、刘四、马之悦、马小辫,还是文革小说中的范克明、冯少怀,都是“封建主义”的化身,因此,他们的政治属性将他们与温情的家庭伦理截然分开: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中,他们是“反动元”或“负面元”,作品的整体叙事指向不是家庭伦理,而是政治审判。此时,“老”成为他们的政治污点与耻辱印记。“敬老”与“孝亲”是一种“相对行为”——“敬”或“孝”的具体行为由子辈或子女发出,而与家庭伦理的分隔,使他们失去了被“敬”或“孝”的可能,而他们反动的政治属性又使他们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因此,老封建、老顽固等带“老”字的人物与“孝”无缘,也因此,十七年小说与文革小说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敬老”与“孝亲”,间接颠覆了“孝”。
进入新时期后,反对封建主义的重心发生偏移——对“文革”的定性决定了“反封建”的重心,因而小说创作与“孝”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流意识视域中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仍然存在,但叙事对象、叙事重心、叙事指向发生了迁移。最显著的变化是:二元中的“反动元”或“负面元”不再是老字辈,而是在“文革”阶段叱咤风云的弄潮儿,因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客观上规定了谁来充当“反动元”或“负面元”,因此在“反封建”层面,主流意识形态视域中的“老”与“亲”获得解脱,也因此,新时期初期小说对“孝”的拒斥不再像先前那样强烈。例如,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赵镢头的遗嘱》等作品中,被批判的对象是郑百如、李保等“四人帮”的爪牙,而不是许茂等父辈。时至80年代后期,文学的“多元化”趋势渐趋明显,主流意识对文学的规范日趋弱化,因而主流意识视域中反封建主题日趋边缘化,部分小说对“孝”的拒斥也逐渐弱化,不过对“孝”的书写暂未得到广泛认同。
二、对“新”的推崇使“老”与“亲”成为被审视的对象
“敬老”与“孝亲”是典型的“孝行”。《尔雅》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将“孝”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礼记·内则》提出了“敬老”的基本标准:“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礼记·大学》甚至认为“敬老”是“治国”具体举措之一,曰:“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很明显,在传统孝文化中,“老”与“亲”被先验地定为尊敬的对象。然而,在特定时代背景中,主流意识对孝文化层面的“老”与“亲”持审视态度,从而在客观上颠覆了对“老”与“亲”的“孝”。在此,我们以“文革”结束为界限,分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建国后的文化氛围、政治理想、经济建设需要等因素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运作的统制。特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新人新事”“新风尚”“新气象”“新面貌”的重视——事实上“新”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哲学范畴,同时也决定了主流意识对“老”或“旧”的排斥与遗弃。从1950年到“文革”结束,在主流意识的规范下,小说创作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表现新精神,反映新生活,刻画新人物,“表现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①。这在宏观上或方法论层面决定了当时小说对伦理学范畴内的“老”与“亲”的态度。作为“新”的对立面,“老”与“亲”成为被审视的对象。首先,部分“老”与“亲”成为应该继续社会化的对象②。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中,部分“老”与“亲”成为落后于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能力缺陷的人,这些人往往不能理解新精神,没有能力接受新生事物。在孟广运的《父亲》中,身为技师的父亲勤劳肯干,爱厂如家,但文化程度低,在关键的时候“下错了料”,使一批牙轮不能淬火,面对众人无声的指责,父亲哭了,但“我”与青年工人最后用“渗碳法”挽救了这批产品。在克勤的《比赛继续着》中,刚进门的新媳妇带领的青年队与以公公为首的老头队展开生产竞赛,思想进步的年轻人敢想敢干,将一系列新技术用于棉花种植,而老头队墨守成规,最后青年队的棉花产量远远高于老头队,“保守”的公公不得不俯首认输。在王家大的《竞赛》中,在“翻地竞赛”中失败的年老人深有感触地对年轻人说:“咱们这死脑筋不够用啦,以后得向你们学呀。”“新老对比”或“两辈比照”是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演绎了一个主流意识认可的政治社会学命题:老辈生产者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继续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与规范,参与新的生活,即“老”与“亲”必须“继续社会化”。事实上,在主流意识的引导下,十七年小说与文革小说将描写接受了新思想、紧跟时代潮流的年轻人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从十七年阶段的劳动模范、技改闯将、生产能手到“文革小说”中心红眼亮的阶级斗争尖兵、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青年人一直是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例如,《萌芽短篇小说选1964》收录的14篇小说全部描写在不同战线斗争生活的年轻人,文革小说的主人公几乎全是年轻人,还有比年轻人更年轻的“红小兵”。其次,部分“老”与“亲”成为应该再社会化的对象。在新时代的新环境中,部分“老”与“亲”是思想落后保守的人,甚至是对新时代、新形势、新思想强烈抵触的人。在《三里湾》、《创业史》等长篇小说中,亭面糊、梁三老汉等人物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典型的“落后人物”。在1949年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新”“老”对立是短篇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许多“老”与“亲”在道路选择、人生理想、生活方式等方面与“新”发生冲突。例如,在骆宾基《父女俩》中,父亲邢老汉热衷于“投机倒把”的贩买贩卖,并粗暴干涉寡居女儿的恋爱与再婚,父女关系紧张;张克杰《婆媳之间》中的李二婶认为思想先进的新媳妇不守妇道,由于受坏人挑唆,她反对儿媳当干部,婆媳矛盾尖锐。在上述作品中,“老”与“亲”就是自私、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而进步的子辈或年轻人则是新时代新精神的化身,“老”或“亲”与子辈之间的代际冲突具有浓郁的政治隐喻性。这些作品客观上演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农民群体是一个需要“教育”的阶层。教育农民,即对农民进行世界观的改造或对农民进行再社会化。再社会化,是“指改变原已习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确立新的生活目标的过程”③。关于农民的再社会化思路,十七年小说与文革小说有两种演绎方式:一是对旧思想旧文化的主要承载者老农民进行批评教育,于是乡村的“老”与“亲”成为批判的靶的,就有了梁三老汉、邢老汉、李二婶等人物形象;二是树立楷模,用新思想新精神引导农民,因此,《耕云记》、《李双双》、《农场新苗》等颂扬新时代的新精神新人物的作品层出不穷。
“老”与“亲”成为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对象,客观上对“敬老”和“孝亲”进行了颠覆。这种颠覆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老”与“亲”向子辈或年轻人学习,动摇了“上尊下卑”的孝道伦理秩序。“老”与“亲”对新时代新环境的适应性不及子辈或年轻人,从而需要继续社会化,而继续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向子辈或年轻人“学习”,而这种后喻行为导致“老”与“亲”的“至尊”地位的动摇。众所周知,子辈或年轻人“敬老”或“孝亲”的原因之一是“老”与“亲”享有由前喻文化④所产生的前喻权威:长辈有着子辈所没有的生活生产知识与人生经验,长辈在向子辈传授知识与经验的过程中获得“教导权威”,二者知识与经验的差距自然形成长者的“堕距权威”。前喻权威是“孝”生成的关键因素,然而,特定的叙事语境赋予子辈或年轻人“后喻权威”,因而“老”与“亲”的“至尊”地位开始动摇,基于前喻权威的“孝”随之也被撼动。其次,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的“保守”“落后”使“老”与“亲”蒙羞。在“老”与“亲”成为再社会化的对象之际,子辈或年轻人对他们的尊崇与膜拜也随之消失了,至于那些被“强制性再社会化”的人,甚至成为子辈或年轻人嘲讽、蔑视的对象,因此,子辈对再社会化的父辈“行孝”被消解。
进入新时期之后,主流意识形态对“新”的推崇仍然将“老”与“亲”置于被审视的位置。但是,时过境迁,“元话语”的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发生了变化,因而主流意识视域中的新时期小说观照“老”与“亲”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主流意识视域中的部分小说展示了“老”与“亲”的政治价值观的“过时”,进而展示了他们在新的政治氛围中的精神困惑及举措失当。《这不仅仅是留恋》(矫健)、《满票》(乔典运)、《村魂》(乔典运)、《祖先的坟》(赵本夫)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清算“四人帮”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尽管政体未变,但主流意识核心价值理念发生了变化,饱经“传统”价值意识教化的“老”与“亲”们仍然坚守先前的偏激价值立场,于是,困惑产生了。在《这不仅仅是留恋》中,老支书巩大明面对“包产到户”的新局面痛苦而惶惑。在《满票》中,大队长何老十坚决贯彻上级的一切指示,“三十多年来一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官清如水”,在公选村长之际他志在必得,但选举的结果是他仅得两票,尴尬的选举结果和众人的哄骗使他老泪纵横。《祖先的坟》中的福淳爷勤勤恳恳地当了二十几年支书,但最终未能带领村民们摆脱贫困,而在他退位后“村子里富了”,他为自己的失败而悲哀,在除夕之夜痛苦地离开人世。上述作品的叙事指向是:对时代过错作出解释,高度肯定新时代的政治路线,而这种叙事指向就是对主流话语的演绎。其次,主流意识视域中的部分小说展示了“老”与“亲”在经济变革中的精神困惑及举措失当。“改革开放”带来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老”与“亲”在全新的经济格局中惶惶不安,无所适从,力不从心,甚至抵制“改革开放”。矫健的《老霜的苦闷》描写了“被左倾思想毒害”的老霜对专业户老茂的仇视。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通过描写两代木匠的冲突,客观上揭示了老木匠黄志亮对按劳取酬、等价交换等基本经济运作规范的无知与隔膜。浩然的《土地》展示了父子两代人在“改革开放”背景中因道路选择所致的冲突,作品以儿子的成就证明了父辈的保守落后。周克芹的《秋之惑》的主题之一是观照改革者自身文化心理素质的缺陷,作品通过描写江路生承包果园的失败及其女儿的婚恋坎坷,展示乡村父辈的思想局限。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描写了小镇文化名人韩玄子对“专业户”王才的嫉妒与仇恨,在经济秩序变更的背景中展示了老辈“能人”的落伍。总之,上述作品揭示了经济之“新”对“老”与“亲”的冲击,揭示了“老”与“亲”在经济变更之际因不适、自身局限等因素所致的惶惑、困窘,乃至苦痛。事实上,为了说明“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证明党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的英明,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阐释主流话语,描写新局面新风尚新人物的作品,如《彩虹坪》、《赔你一只金凤凰》、《山月不知心里事》、《小月前本》、《桃花湾的娘儿们》等。此时,“新”仍然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概念。
很明显,同十七年阶段和“文革”阶段小说中的“老”与“亲”的境遇一样,新时期阶段的“老”与“亲”也不是值得孝敬或应该孝敬的对象。在主流意识的规范下,“老”与“亲”成为作品中演绎主流话语的道具:或展示“极左路线”的灾难性后果,或言说新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或证明英明决策的伟大成就,既定的“剧情”规定了他们的角色与地位,即他们必须是被审视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被孝敬的对象。
三、将伦理性的“敬老”“孝亲”转化为政治敬仰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几十年内,并非没有表达子辈对长辈尊崇的小说,因为生活中存在许多可亲可敬的老字辈,但主流意识规范视域中的小说将伦理性的“敬老”“孝亲”转化为政治性的精神敬仰与精神崇拜,这种转换事实上构成了对“孝”的颠覆,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将“老”与“亲”塑造成子辈的精神楷模。这种叙事行为主要出现在十七年小说与文革小说中。作为精神楷模的人物,主要是老模范、老贫农、“老革命”或老饲养员、老保管员、老工人。大公无私勤俭节约、爱社(厂)如家、政治立场坚定、阶级爱憎分明、关注下一代的进步与成长,是这些老字辈的共性。在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中,赵大叔全身心扑在合作社的牲口喂养上,以致在城里探亲时半夜起来“喂草料”。李准的《孟广泰老头》中的孟广泰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喂养集体的牲口,儿子天祥拿了集体的草料,他毫不留情地向书记检举。王云飞《风雪之夜》中的黄师傅劳动积极,关心集体,以厂为家,他是青年工人心目中的精神标杆。肖关鸿《小将》中的先进工人老郑言传身教,在他的影响下,徒弟小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克服困难完成了电机的“线圈计算”,取得“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生活斗争”中的“老少互动”和“以老带新”,是常见的描写内容,作品的描写表明:长辈的高尚情操对子辈施以潜移默化的革命精神濡染,长辈伟岸的人格成为子辈面前的精神丰碑。于是,生物性、宗法性的伦理辈分转变为革命思想传承的政治梯级,子辈对长辈的伦理尊崇转化为政治皈依,因此,宗法性、伦理性的“孝”被消解了。进入新时期之后,由于元话语的言说重心转移,将“老”与“亲”塑造成子辈精神楷模的叙事模式开始变化,但“老”与“亲”的“楷模化”还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例如,在《剪辑错了的故事》等新时期初期作品中,从老寿等人物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楷模化”的“老”与“亲”的影子。
二是将“老”与“亲”升华为子辈的精神导师。这种叙事行为也主要出现在十七年小说与文革小说中。这种叙事行为的基本表现是:“老”与“亲”以老党员、“老革命”、老支书的面貌出现,其中“书记”或“支书”出现的频率最高,年长的“书记”或“支书”关注子辈的身心健康,赋予子辈政治生命,引导子辈在正确的道路上奋进。在茹志鹃的《阿舒》中,老支书不仅像父亲一样呵护了阿舒的“快乐”,而且引导这个17岁的小姑娘在快乐中成长。在李准的《耕云记》中,气象预报姑娘萧淑英在关键的时候想起了党委书记的教导,作出了准确的天气预报,为生产大丰收奠定了基础。在《艳阳天》中,区委书记王国忠总是在萧长春面临困难的时候出现,在“这位英明长者”的指导下,萧长春最后粉碎了反动分子的变天阴谋。《迎春展翅》中的党支部书记老吴坚信“万物生长靠太阳,革命青年的成长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他为“根红苗正”的小方姑娘提供快速成长的政治环境,使其最后成为技术过硬的大型吊车操纵员。在上述作品中,长辈给予子辈父亲般的关爱,但这种关爱不是伦理层面的爱抚与眷顾,而是政治层面的引导与规范,因此,父爱的政治化使长辈对子辈的关爱,转化为对子辈的政治人格塑造以及对子辈道路选择的指导,也因此,伦理层面的尊崇转化为政治层面的敬仰,伦理性的孝敬转变为政治敬仰及对党的忠诚。于是,“孝”因这种转化而消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伦理转换与当时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建国后的文艺创作建构了一种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伦理隐喻模式:党在许多语境中是“人民”和“祖国”的代名词,在文艺作品中被慈父(母)化,与之相对,年青一代或“群众”被“子辈化”,党和年青一代构成了具有特定政治关联的代际关系;“党的好女儿向秀丽”、“人民的好儿子雷锋”、“党的好儿子焦裕禄”等报告文学中的称谓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名是这种特殊代际关系的反映。因此,伦理性的孝敬转变为政治敬仰及对党的忠诚,就是这种政治伦理隐喻模式的具体表现。
进入新时期之后,“老”与“亲”的“导师化”叙事模式随着元话语的言说重心的转移而逐步消失,但其余绪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规范作用。例如,在80年代中后期,《古船》、《绿化树》等作品流露出探寻精神之父的倾向,尽管隋抱朴、章永璘等人物所寻找的精神之父与先前小说中的精神之父完全不同。在元话语对孝的规范弱化之际,一个众语喧哗的时代到来,众语喧哗中的许多“语”从不同层面对“孝”进行了消解,因而在80年代中后期,“孝”仍然没有大踏步走进小说。
《孝经》载:“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父为至尊,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小说将伦理性的“敬老”“孝亲”转化为政治性的精神敬仰,存在着一种很明显的倾向:无论“老”与“亲”与子辈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作品的整体描写在客观上将“老”与“亲”设定为父亲——主要表现为“老”与“亲”以父亲的“姿态”对子辈施以关爱,子辈则对“老”与“亲”怀有尊上的敬畏之心。“老”与“亲”的父亲化,是伦理性的“敬老”“孝亲”转化为政治性精神敬仰的前提。当然,这种转换也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例如,老工人往往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代表,“导师化”的“老”与“亲”就是党的化身,而子辈对父亲化的老贫农、老工人、老党员、老支书的皈依以及老字辈对年轻一代的精神感召、人格吸引,是对关联阶级斗争、政党属性等一系列政治话语的注解与演绎。
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几十年内,上述三种方式消解了小说的孝文化内涵。当然,进入90年代之后,主流意识对“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烘托、“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推举等因素的作用下,具有孝亲倾向和颂扬孝道的叙事作品层出不穷,如《我的农民父亲母亲》、《跪乳》、《寻父记》、《父亲的黄昏》、《母亲的信仰》等一大批具有孝亲色彩的小说相继问世,《孝子》、《咱爸咱妈》、《家有爹娘》、《我们的父亲》等颂扬孝道的“家庭剧”先后热播,甚至《我是太阳》、《英雄无语》等“新革命历史小说”也流露出孝亲倾向。⑤正因为如此,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一时段内主流意识视域中的小说对“孝”的解构,就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与文化社会学意义。
注释:
①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②③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0页。
④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页。
⑤参见周水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后新时期”小说的“孝亲”倾向》,《小说评论》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保昌)
I206.7
A
1003-854X(2015)10-0074-05
周水涛,男,1956年生,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孝感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孝感,432100。
*本文系湖北省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新时期小说创作与孝文化之关联研究”(2014K01)和湖北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乡村书写对农民及乡村文化的价值认知研究”(13d1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