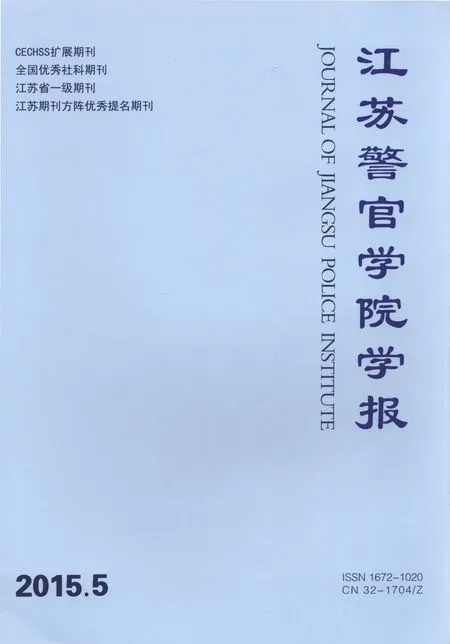风险刑法观之再审视
韩 雪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就在其所撰写的文章中区分了“危险”(hazards)和“风险”(risks)的概念。1983年,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美国政治学家阿隆·维达夫斯基合作完成了《风险与文化》一书,对有关风险的理论进行分析。尽管存在上述研究,有关风险问题的议题仍然未被主流的社会科学所采纳,对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保险和风险评估的领域。直至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著《风险社会》一书问世,“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才在社会学领域受到关注,并继而引发较为广泛的讨论。①[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及其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的。”②[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随后,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并对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伴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人类社会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1)既非毁坏也非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事实;(2)(依旧)与事实相反的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在数学化的道德中,它结合了事实声明及价值声明;(4)在人为的不确定性中所表述的控制和控制的匮乏;(5)在认知或重新认知的冲突中被意识到的知识或无知;(6)在同时重构为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全球地区性’风险;(7)知识,潜在的影响和有症状的后果间的差异;(8)失去了自然和文化间的二元性的一个人造的混合世界。”①[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第188-189页。
应予承认的是,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有局限性。美国学者弗兰克·费希尔曾尖锐地指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有许多含糊不清的漏洞。许多欧洲学者也曾以此为由将贝克视为一名广告员,批评他更多的兴趣在于建立一个哗众取宠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去捕捉环境实验中的证据。此外,费希尔总结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还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首先,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风险的论述有近乎夸张的倾向;其次,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从来没有真正质问过专家和知识的意义,尤其是没有质问过他们的不确定性社会文化基础,从未考虑过焦虑的市民们所担忧的风险;最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存在着风险民主的问题,这关系到他在政治上反思现代社会转型的有效性。②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述》,载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6-29页。
确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某些方面确实存有缺陷,但其价值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该理论所蕴含的反思精神不但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还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西方的英语世界国家,对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季卫东教授曾围绕风险社会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挑战一题展开过研究。他认为,随着产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网络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已经迅速进入“风险社会”。关于现代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正在受到来自风险社会的各种挑战。这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制度化的理论、管理系统的内部构成、公共选择的实践意义和影响以及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运作的反省机制。③季卫东:《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风险社会理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的关联性分析
受风险社会理论的启发,刑法学界有学者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风险刑法理论。风险刑法理论肇始于德国。1993年,德国刑法学者普里特维茨在其所著的《刑法与风险:风险社会中刑法和刑事政策的危机研究》一书中首次围绕“刑法与风险”一题展开讨论。此后,“风险刑法”的概念传播到世界范围,并频繁见诸于德国和日本学者的论著之中。④郝艳兵:《风险刑法: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对风险刑法理论持支持态度的论者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国家在风险控制中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作为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捍卫者,刑法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作出相应改变。针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未来性和重大破坏性等特点,刑法的治理模式应由事后惩治转变为事前预防,为此应提前刑法的介入时间、扩大刑法的干预范围。在刑事立法之中,风险刑法理念主要表现为危险犯的增加,预备行为、组织行为的独立犯罪化等等。有论者认为,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刑法表现出的增加危险犯的立法趋势就是顺应风险社会的到来作出的改变。①张晶:《风险刑法:以预防机能为视角的展开》,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5页。也有论者指出,受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刑法开始大量处罚抽象危险犯,增加法定犯的比重,并在刑事制裁中更多地强调“犯罪人”的危险性。我国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的环境资源保护犯罪、食品安全犯罪、交通犯罪等法定犯都是适例。②刘艳红:《“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
针对风险刑法理论提出的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尽管该理论建诸于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之上,但其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的联系仍然值得商榷。理由有两方面。
一方面,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风险”一词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处在不断扩张之中。早在贝克明确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之前,有关风险问题的探讨就已经存在。20世纪50年代,当人们认识到核能适用所潜藏的风险时,便开始围绕核能的安全使用、风险规避等问题展开过探讨。20世纪60年代,风险分析开始深入到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关风险问题的讨论扩展到生物技术领域,其后又逐步扩散到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之中。③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述》,载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3-5页。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贝克创立了风险社会的理论之后,“风险”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并未得以确定。不但不同的风险社会论者持有不同的风险观,就连贝克本人对风险内涵的描述也相当模糊。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他将“风险”一词界定为处理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在《风险社会再思考》一文中,他又从“真实的虚拟”、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对事实和评价的陈述、控制或缺乏控制、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等八个角度对风险社会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④[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郗卫东编译,载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贝克的上述界定仅仅揭示了风险社会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的特征。与其说这是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概念所做的概述,倒不如说是其对预期的风险社会所展开的一种猜测性的描述。鉴于风险社会理论本身对于“风险”的概念并无明确且统一的界定,就以之为根基构建起来的风险刑法理论而言,其中所言之“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之“风险”是否同一,也就值得进一步推敲。
另一方面,即便承认风险社会是真实存在的⑤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述》,载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0页。,风险刑法理论的“风险”也确实出自风险社会,也不能由此证明风险刑法理论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此,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齐白的一段描述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与当代风险社会密切相关的技术上、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变化催生了新形式的复杂犯罪,这些复杂犯罪的新形式特别在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经济犯罪领域构成重大风险。”“国家往往在法律修改中采取两个策略来对付这些新变化:首先,拓展刑法的适用范围,减少传统的正当程序与其他保护手段;其次,以其他法律手段补充刑法或者干脆取而代之,而这些法律手段被认为更适合在特定领域实现保障安全的目标。”⑥[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刑法确实是防范社会风险的一种手段,但其并不是风险防范的唯一手段,更不是风险防范的最佳手段。风险刑法的倡导者认为,刑法可以在恐怖犯罪、环境犯罪、基因技术犯罪和计算机网络犯罪等高科技领域犯罪中发挥重要的风险防范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恐怖犯罪而言,刑法的威慑是无效的。齐白在倡导以刑事责任的前置来惩治恐怖犯罪的同时,也曾不无遗憾地指出,“世俗的刑法也无法有效阻止出于宗教信仰的自杀性袭击者”。⑦[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第197页。对于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造成的环境犯罪和以基因技术犯罪、计算机网络犯罪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犯罪而言,刑法的适用不仅难以确定,甚至还将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的一般原理,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的农耕时代的风险和工业社会时期的风险,而属于一种新型的、“混合了现代政治、伦理、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而形成的、针对现代文明制度、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态风险而展开的风险”①黎宏:《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人民检察》2011年第3期。。这种风险具有其双面性。一方面,它可能对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极大地破坏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会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优先保护科学技术的进步,维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某些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讲有价值的行为,即便其可能给生命、身体等带来一定的危险,也应当予以容忍。这种“被容许的风险”(das erlaubte Risiko)理论是人们在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②于改之:《刑民分界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1页。正如“刑法不能直接将科学技术中具有风险的探索活动予以禁止”一般,其“也不能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实现以后,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③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以此观之,将刑法的触角延伸到科技领域,以确定的规定钳制难以预测的风险,不但损害了刑法的稳定性,而且还将违背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实乃有害无益之举。
边沁曾言,在惩罚必定无效和惩罚无益或者说代价过高的情形中,均不应施加惩罚。④[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8页。由此观之,风险刑法论者将刑法优先用于恐怖犯罪、环境犯罪、基因技术犯罪和计算机网络犯罪等或是属于刑法威慑无效,或是以刑法惩治无益的犯罪之中,其合理性确有其值得商榷之处。
除了上述两方面原因之外,笔者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构建并非完全出于对风险社会已经到来的确信,其中不乏消除或减轻人们不安感的考虑。不安感是人们对于其所生存的社会的一种主观感受,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出社会风险的大小,但又受制于个体感受和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社会风险的本来面貌。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决策研究院的研究者提出的一种被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理论就指出,被行业专家们评定为较小的风险事件往往能引起巨大的公共反应,并能给经济社会带来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媒体、网络的个体传播者以及专家对于风险评估的争论等都可能造成风险被放大。⑤师索:《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除此之外,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特定时期国家公权力机关对特定犯罪展开的集中打击等都可能造成人们的不安感急剧增加。而减轻人们不安感的方式则多种多样,诸如建立风险的防范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政府与媒体、民众的沟通等,都可能发挥比刑法制裁更有效的作用。不少论者之所以将刑法作为优先适用的风险防范手段无非是受“刑法万能”思想的影响,其并未对刑法作用的有限性持有端正的认识和态度。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构建而成的风险刑法理论实际上并不存在牢固的理论根基。风险刑法理论得以构建的时代背景更多地是基于该理论提出者自身的主观设想,或是其根据民众对个案的反应而作出的主观推测。在现阶段,就风险刑法理论是否确有其构建的必要性而言,需要展开进一步的社会学考察,并经过刑法学理论的严格考验。
三、风险刑法理论之辨伪
从刑法学上对风险刑法理论加以进一步的考察,笔者对该理论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更大的质疑,主要是因为风险刑法与现代刑法的基本价值和精神是相背离的。
与以“权威刑法”著称的国权主义刑法观相抗衡的“以人为本”的民权主义刑法观,是人类长期斗争的产物。在此种刑法观的影响之下,公正、谦抑、人道成为现代刑法的价值和精神所在。现代刑事法治正是在这三种价值和精神指导之下构建而成的,其“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其给予国家刑罚权,但又限制国家刑罚权的随意发动。”①刘艳红:《“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纵观风险刑法理论,无论其所主张的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还是其所强调的刑法打击范围的扩大,均是以国家刑罚权的扩张适用作为手段加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扩张并不以刑罚权适用的“迫不得已性”为必要,而往往假借“防范风险,维护安全”之名行扩张刑罚权适用之实。这就为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任意干涉私人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种情形之下,风险刑法的适用,“其本质在于用自由换安全,即社会成员牺牲部分权利与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安全的社会生活。”②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刑法理论在主张法益保护提前和法益保护范围扩张的同时,还带有明显的重刑化发展倾向。以德国政府颁布的《处理严重危害国家暴力犯罪之预备行为的立法草案》为例。有论者认为,恐怖袭击的潜在危险使得在刑法中规定预备犯的做法得以正当化。这是该草案第89a条和第89b 条将实施危害国家的暴力犯罪的预备行为予以独立犯罪化的正当化根据之所在。根据该草案第89a 条的规定,“预备实施严重危害国家之暴力犯罪的,判处6 个月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89b 条则规定,“出于接受有关实施第89a 条第2 款数码1 中严重危害国家暴力犯罪之指导的目的,与第129a 条或者第129 条意义上的团体取得或者保持联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③[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224页。从犯罪停止形态的一般原理来看,与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未遂、既遂行为相比,仅仅处于犯罪谋划阶段的犯罪预备行为,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明显较低,行为对社会的危害也显然较小。因此,对于预备行为配置的刑罚应比同一犯罪的未遂犯和既遂犯较轻。而根据风险刑法的一般原理,为了实现刑法的积极预防目的,上述相关预备犯的刑罚处罚实际上并不一定就必然轻于对同类犯罪的未遂犯和既遂犯配置的刑罚。即便对独立的预备犯的处罚确实略轻于对同一犯罪的未遂犯和既遂犯进行的处罚,“6 个月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这样明显偏重的基础刑期也势必会抬高为同类犯罪的未遂犯和既遂犯配置的刑罚,这就从整体上使得刑法典向着重刑主义的方向迈进。
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只要身处法治社会中,刑法的价值和精神就应予以坚守。风险刑法理论无视现代刑法的价值和精神,忽略风险预警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非法律防范手段和侵权法、行政法等“先行法”所应发挥的作用,而将刑法这一具有“迫不得已性”的“后置法”作为主要的风险防范手段,无非是为“刑法工具论”披上风险社会的外衣而已。如此看来,风险刑法理论并非真正源自风险社会,而只是“刑法工具论”的一种变形。与“刑法工具论”的观点无异,“‘风险刑法’理论的具体主张其实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就提出了,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风险刑法’作为一种口号的煽动性意义可能要大于其作为一种理论的借鉴意义。”④于志刚:《“风险刑法”不可行》,《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面对这样一种刑法理论,即便在其发源地德国,反对的声音也依然强劲。在支持该理论的论者中间也存在较为保守的流派。如以洛克辛、施特拉腾韦特等教授为代表的论者就在承认风险刑法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同时主张对刑法早期干预的形式采取有效的限制,以防止刑法过度地侵犯公民的自由。⑤张晶:《风险刑法:以预防机能为视角的展开》,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8页。
四、风险刑法观与我国刑法调整
正如风险刑法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确实面临着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曾出现过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也确如风险刑法理论所预设的立法路线那般,当前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刑事法均出现了扩大法益保护范围、前置刑事责任等立法趋势。这是风险刑法理论得以维系并被众多学者所认可和倡导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风险刑法理论与现代社会转型及各国的立法趋势之间就必然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主要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德日刑法,还是我国刑法,均成长于工业社会时期,带有鲜明的工业社会时期的特色,面对现代社会产生的新问题,其必然存在预见不能和处罚无力的缺陷。
此外,德日等国出现的法益保护前置和扩大的刑事立法趋势,并不能当然地得出我国的刑事立法亦应按此立法模式进行调整的结论。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仅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与之并不相同,还在立法模式上与之存在巨大的差别。一方面,从社会发展阶段上来看,在当前世界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我国和德日等国虽然共同迈入了现代社会,但发展阶段并不同步。德日等发达国家早已全面进入现代社会,而我国尚处于由工业社会时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在享受现代社会诸项便利的同时面临着现代社会的诸多风险。我国目前面临的风险包含两种不同的类型,一部分风险源于工业社会时期,而另一部分风险则属于现代社会的风险。“事实上,当前我国所谈的很多风险,仍然属于传统刑法的范畴,甚至许多风险后果的酿成与制度、规范的缺失、监督力量的薄弱有直接关系;当前发生的各种犯罪现象,也属于传统的犯罪现象,传统刑法的治理方式并没有明显不适应。”①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由此可见,德日等国的现代刑法转型也并不能完全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参照。另一方面,在制裁模式上,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相衔接的二元制裁体制别具特色。与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刑事制裁体制相比,我国刑法干预范围更窄,介入时间更晚,一些在德国和日本等国被认定为犯罪的危险行为在我国可能只被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并相应地划归到行政制裁领域中。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笔者虽不支持风险刑法的基本理论及其风险刑法观,但承认该理论蕴含着对我国传统刑法进行反思的合理内核,并认为德日等国的刑法转变模式对我国刑法调整具有借鉴价值。面对社会转型对刑法发展的要求和我国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我国刑法应当适时作出调整。一方面,面对现代社会以前未曾出现过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以危险犯的增加、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独立犯罪化为代表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和扩大化将成为影响我国刑法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顺应社会发展而调整法益保护范围的同时,应以我国现实国情和立法模式作为基础,始终坚守现代刑法的价值和精神,使得刑法的构建和调整既富有现代法治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