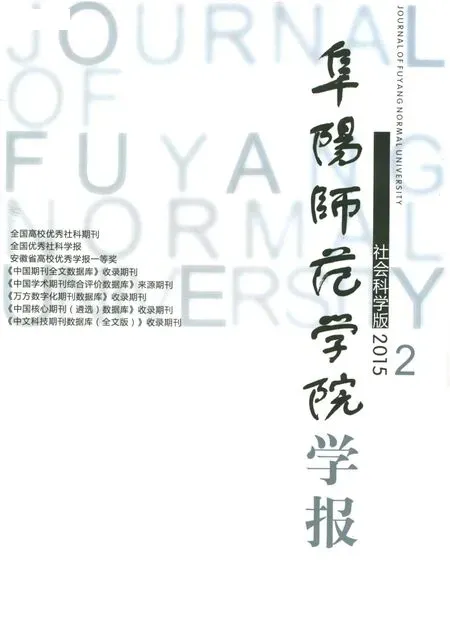“大”与“小”:小说的辩证
——当下阜阳小说一瞥
张晓东(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大”与“小”:小说的辩证
——当下阜阳小说一瞥
张晓东*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阜阳古称“汝阴”“颍州”,人杰地灵;到了现代的“阜阳”仍然人才辈出。就说小说创作,20世纪60、70年代阜阳有徐瑛,80、90年代有戴厚英,可谓领一时之风骚。然而,时移事往,旧貌已矣,新颜未至,戴厚英之后,阜阳小说在全国,几近寂寂无声。本文以“当下阜阳小说一瞥”来表达自己对当下阜阳小说的一点观察与思考,期待同道一起关注,期待阜阳小说的重新腾飞。
阜阳小说;大与小;罪与恶;关怀
一、对小说的认知、目前的印象、基本的判断
小说曾被视为引车卖浆者之言,不登大雅之堂;后来梁启超又把它抬升到几同“治国群要”之地位,直如“鸡犬升天”;而时至今日,小说被捧在天上,或踩在脚下,都属寻常,不由人不感慨世事难料。
读过许多小说家的小说论:萨特、塞米利安、福斯特、沈从文、萧红、老舍、张爱玲等等。最让我心仪的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1]《被背叛的遗嘱》[2]里的所言。其中一个意思说:对于真正的小说家而言,小说是他的信仰;写小说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我相信米兰的说法,所以好的小说家在我心中近乎圣人。
目前我所生活的这座小城还没有这样的小说家。目力所及,总体来说,我们这的小说家缺乏一种大的气度,当然,也就出不来大的气象。思想浅、胸襟小、趣味寡,合在一起,直言之,就是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作家的作品中最缺乏的是悲悯情怀的弥散。书里书外,就满足于小得意、小成功,执念于小名誉、小得失,以此,对写作的敬畏与热爱也就于无形中被瓦解。
即便不谈艺术,就谈一个人对存在的“悟”——对生活、生命的理解把握——也唯有抵达“悲悯”之情境,才能真使我们了悟人生。如果非得给“悲悯”一个直观的意象,我最愿意拿来比拟的是《西游记》中的如来,这意思是说,悲悯在人性中最具有“神性”色彩,所谓慈悲为怀是也;在神的眼中,一切都是可悲悯的。所以,神温柔、恬淡、宁静。而红尘中人则总是旺旺的、火火的、急眉赤眼的。
当然没有神。人通过造神把人做了区分。小说家身在红尘,可是,要做一个好小说家,就要好好涵养自己的神性。对于一个已有较长写作历史的作家,一个已经被放到某种谱系(不管这谱系是大是小)里的作家,这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当年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沈从文在谈及自己对写作的态度时常常提及的一个词是“谦卑”,他认为,写作是用文字在做“情绪的体操”,作者对待文字要像奴仆对待主子那样忠诚。从沈从文的“谦卑、忠诚”话语里可以读出一个关键词“虔诚”。而我们阜阳小说家身上恰恰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毛病,没有做到对写作的真虔诚。这其中的表现虽有种种差异,但这差异之中又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作为一个“作家”的不自信,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在我们阜阳这样的小城市,很多作家可能也认为自己很“小”,这个潜意识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混乱:有时觉得自己还行,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有时又会恍惚,自己不过是无名小卒。这恐怕是所谓“不够虔诚”实际“不能、无需(谁会关注我?)虔诚”的真相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阜阳作家要向契科夫学习,面对莫泊桑这样的巨大存在,契科夫说,莫泊桑是一条“大狗”,自己是一条“小狗”。大狗发出大狗的叫声,小狗也不妨发出小狗的叫声。在契科夫的话语后面,可以加上一句,不管是“大狗”还是“小狗”的叫声,得是“狗”的声音。文学就要有文学的声音。这个意识怎样,有一个问题最适合用来对之检验,这个问题是所有的作家都该、都要回答的,不能避免,即,我为何写作?毫不夸张地说,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作家本人对自我层次的清晰界定。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阜城作家在色彩不同的创作谈中还很少有人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有个别作家连面对这个问题的意识都没有。如果我们的小说家不把自己内心的混乱先整理清楚,个体或整体的重新崛起都将是一句空话。
二、当下阜阳小说的得与失
读了一些阜阳作家的作品,一个明确的认识是,我们阜城小说家们的文字,基本停留在说故事的层面上。别误会,这样说没有看低故事的意思。写小说,首先就要会“编故事”。可“编”并不是任意,而是要合情合理。如果你编的故事常常经不起常识常情的推敲,就无法使人相信,更不要说追踪故事后面悠长的韵味了。比如雪涅的中篇《面条》,(安徽小说对抗赛银奖作品)主人公张雨泉因过失杀人而逃亡,开始了始料不及的人生。在西藏,他遇到了来自四川的美眉阿兰,因为自己的一次英雄救美,赢得了阿兰这个风尘女子的感激,阿兰要以献身为报,阿兰说得很明白,她不愿意“欠别人的”。这样的理性和风尘女子的身份倒是相合。也许因为羞涩、惭愧、厚道……?当时张雨泉拒绝了后来想起多少有些后悔的这个献身。再后来,张雨泉因恐惧暴露(阿兰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他是个在逃的通缉犯。虽然他肯定阿兰不会举报,但终于还是不能肯定。这是这部小说最好的细节之一,写出了特定情境下人性的变异)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在误打误撞做“麦客”时,替一个年轻寡妇做事,因为年轻寡妇“熬了多年”,当天晚上就上了张雨泉的床,二人成了相好。张雨泉是个没经过多少世面的乡下小子,逃亡的煎熬时时在咬啮着他的心,终因不堪再忍受想投案自首。他通过一个电台类似知心谈话的节目,给美女主持打了求救电话,后来二人茶馆见面,在美女主持坦然、无私、热情的帮助下,事情真相不仅大白:张雨泉不是过失杀人,而是过失伤人;而且,张雨泉也最终获得了自我救赎。甚至故事到最后,张雨泉还娶了阿兰为妻,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团圆故事。
在故事的层面,《面条》有着不错的可读性,可是人物就太单薄了。特别是在其中起着关节作用的三个女子,其言其行于常理常情处是经不起再三玩味的。像阿兰那样一个自己都说见过了太多世面的风尘女子,最后乐于下嫁张雨泉这样的一个曾经的准杀人犯的乡下小子?那她的人间城市阅历岂不是白白经历了?一个电台的美女主持仅仅通过一通电话就相信一个自称为杀人犯的人,竟然一点顾忌自身危不危险的念头都没有就毫不犹疑地只身前往相约,还那样无私、热情?那个年轻寡妇再熬不住也让人很难理解那么快就对一个陌生男子知冷知热身心相报的吧?而这三个形象如果都经不起推敲,这小说还能剩下什么?作者是不是太善良了?还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不善良要写这么一些好人故事让这个世界善良起来?小说家不该是脱离真实闭上眼睛表达浪漫的人。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就是复杂的精神”。世界是这样地复杂,人心是那样的难测,难怪曹雪芹提醒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难怪胡兰成说张爱玲“是那样地善于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一个小说家的善,不是在小说里自顾自地表达善良的愿望,而是要睁大双眼,洞察真相,在呈现真实世界中陈述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不是冷漠,残酷的表象后其实含着悲悯。这世上有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地“冷、毒”,有谁像张爱玲那样地“荒凉”,有谁又像曹雪芹那样地有情而又无情?可是,谁又能否认他/她们的温柔、怜悯,那悠长的胡琴声后的一声叹息!
我倒要为苗秀侠《屋角的战争》喝一声彩,只获得安徽小说对抗赛的铜奖多少有些遗憾,而据说这还有点“恩赐”的意思,理由是这篇作品有违一般的“人伦道德”。天!竟然是这样一个理由。一个在“善与恶”方面表达的如此真诚、深邃而丰富的文本被贴上如此标签,我们开道德法庭的欲望真是太强悍了。
《屋角的战争》保持了苗秀侠一贯的乡土气息,不仅她那土头土脑的语言,甚至那些乡人的人名都是土得掉渣,可是,这还真不是作家的刻意营造,它们就是那个乡村世界的本来纹理。当初我读余华的《活着》,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福贵这些名字在我眼中有着无法言喻的神奇,在我狭隘的阅读史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受了一个个名字和一个个生命融合无间的感觉,他们须臾不可分离。这是余华的神奇,也是生命的神奇。我读《屋角的战争》再一次获得了此种感受。当然,这部作品对于苗秀侠真正具有飞跃意义的是在对人性的深度刻划。小说主要人物屋角是个“小人国”(侏儒),不得已娶了貌美如花眼里生了“棠棣花”(睁眼瞎)的毛凤,为了后代子孙不再经历自己因为“小人国”而来的种种耻辱,屋角忍辱向自己邻居粪箕“借种”生下了大手大脚的大树,屋角与粪箕之间的夺子战争从此开演。这战争双方都始料未及,这正是作品了不起的地方,作家没有强行插足其间,而是顺随着人物对自己人性的触摸、苏醒来延展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很多作家曾幸福地体验过的:不是作家按照自己的设计走,而是自己被故事领着朝前走。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是这样,余华写《活着》也是这样。托尔斯泰曾主观设计要把安娜写成一个“坏女人”,可是,在安娜故事的展开中,作家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他越来越不能抑制对安娜的同情,结果一个原被设计成道德审判的故事不得不改弦易辙走到它的反面。而余华写《活着》时,故事人物早就有了,可是迟迟不能动笔:他找不着叙述方式,直到有一天,一个类似于小时候奶奶讲故事的句子来到自己笔下,于是,一切都顺流而下。余华体会着写作给自己带来的无可言喻的畅意。他说,不是他在完成故事,而是故事在完成他。苗秀侠也没有为了世俗道德的舒适而牺牲自己对生命的发现,而是直面了人性深处的善与恶,虽然在刻划的厚度方面也还有力不能逮处,但作家对写作的尊重还是值得肯定的。另外可以提及的一点是小说的叙事,比作家过去的只是平铺直叙,《屋角的战争》有了长足的进步。二十年的故事,浓缩在过年前的几天去呈现,叙事的穿插来回作家处理得游刃有余,甚至还借鉴了魔幻的技法但合情合理并不显得生硬。不管怎么说,苗秀侠《屋角的战争》是我们这里近年小说最好的收获之一。如果苗秀侠再能在形而上的层面有所提升,则她可能会给我们更大的惊喜。她是一个有着较为丰富阅历的作家,如何从自己的生活中去提炼出有气象的艺术品,技巧的学习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小说的“小”,在形而上层面上有所悟才是根本,才是小说的“大”。
现在常有人反对小说的“寓言性”,因为过去我们虚伪太多,动不动象征、隐喻,以致今天过犹不及,寓言被许多人视为故作高深无病呻吟而弃之不顾。这是杯弓蛇影的浅薄。作家毕飞宇说得好:“寓言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小说当中‘大’和‘小’的关系上,一个平庸的作家总是无法使小说‘小’下去。‘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小’是一种能力,一种可能,一篇作品如果达不到一定程度的‘小’,小说是无法获得充实的内涵的,无法透亮的,无法使人联想起生活当中最基础的层面。而什么是小说的‘大’呢?也就是它的寓言功能,这反映出小说家在形而上方面所努力的程度。没有形而上,小说必然要缺少一种恢弘,一种浩瀚,一种气派,一种大。”[3]P142毕飞宇说的“小与大”也可换成“实与虚”,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寓言的成分,要么小说被写成无法空灵的实体,要么就会成为一种大而无当的东西。
较之于我们阜城目前的写作,我们小说家的弱项更多表现在“大”或“虚”上,用一些作家自己通俗的话说就是“层次上不去”。这个“层次”,不少作家把它仅仅理解成“思想”。却没意识到,没有思想只是“象”,没有思想能力才是“本”。而没有思想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思想的放弃,也就是没有思想的意识。许多人潜意识里把思想理解成书斋里的智力活动,好像是某些人的专利,以致在他们脑中思想仿佛还有了具体的形式:它藏在大部头砖头似的书里,那是围墙内学院派的阵地。这真是天大的误解。思想的权力属于所有人;小说家不是不要思想,他所要明白的是要用小说的方式去思想。
张殿权是一个年轻的“老”作家了,徐瑛先生曾称他为阜阳文坛的一匹黑马。而时至今日,说他是阜阳新生代作家的一面旗帜并不为过,虽然在更大的视野中他还有需要极大提升的空间。一个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储藏,张殿权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他的写作资源较多地都是取自自己的生活,甚至为了某种逼真性,他小说中常有一个非主要人物也名叫张殿权。2002年,就是被徐瑛先生称为黑马横空出世的那时期,他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中篇《青春街》,次年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中篇《青春散场》,在阜阳文坛可说是一炮而红。后来,作品虽不是绵绵不绝,但坚持到今天,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2009年合工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中学时代》,201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其小小说集《方向》,(差不多前后还有短篇集子《你的未来很成功》及《我的青春你的故事》,在我此篇杀青的时候,张殿全又出版了长篇《我们生长在这里》,期待他有新的突破。)除此之外,他的中短篇作品也时见于《清明》《安徽文学》《鸭绿江》等杂志,大大小小的奖项也获得不少,发表于2013《安徽文学》第7期的中篇《你就作吧》被安徽作协推荐参与鲁迅文学奖的角逐,可见实力不俗,如果说他是阜阳文坛近年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当无异议。
当然,论定一个作家的价值,质虽是根本,但量也不可小觑。从阜阳文坛的总体格局来看张殿权的小说,可说是成绩不小;就其自身而言,作品的水准则参差不齐。比如,去年出的《方向》,一言以蔽之,里面的东西根本不是文学的“方向”。其文学元素就像喜马拉雅山顶的空气那样稀薄。《方向》只是出自一个作家之手的文字产品,不代表这个作家文学的基本面,但其中折射的问题值得关注。
我读张殿权是错乱着来的,看到什么读什么。作家当然在成长,但也有他的一贯性。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青春散场》《到哪里去》《城里的月光》《中学时代》发表的时间头尾间隔将近十年,而最近的作品是《每一个新年都会过去》《方向》《你就作吧》。张殿权从一个青涩的写作者成长为一个写作技巧越来越丰富、文字驾驭能力越来越强大的作家,其中的勤奋与才气是显而易见的,而他的“一贯性”在其作品中也清晰可辨。所谓的一贯性就是一个作家风格的基本面,作家评论要找的就是它。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画家的工作为文学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作家和画家的工作是相似的,画家在为自己的对象作画时,他先需要做仔细的观察,为的是寻找对象“最像自己的那一瞬间”。
我对张殿权的基本印象如下:作品的取材微观,从材料到情绪常带有自己个人生活的印记,题材当然不是问题,但如果不能写得深,又无延展,就会给人重复之感,张殿全在深度的提炼方面还有不足。在“怎么写”上,张殿权的小说外松内紧,不重情节的戏剧性,靠人物的心理动力推动故事,这是他小说最好的地方。在构成情节的细节上,时给人平铺直叙之感,表面上戏剧性的张力不足,其实症结点还是作家的“知情意”综合力较弱所致,思想没有穿透力。所以总体看,张殿权小说平淡,不是很“抓人”;但人物心理描写细致,常能触人心弦,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到哪里去》是一部颇有想法的作品。篇名可能是有意对应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拟的。取材当然不是机械模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看得出是自己中学时代生活的一种记录,但还是让人不自觉地记起《麦田守望者》。如果作者说自己的《到哪里去》和《麦田守望者》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因为有了《麦田守望者》在前面,无论从规模还是到分量来看,《到哪里去》就成了一部无关紧要的作品。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作者也好一个作家也罢,你总是在文学史的链条中进行写作的。《到哪里去》的不足表现有二:叙述过于饶舌,这是进入不了叙述对象深处的不自觉表现;眼泪太多,心不能静,理性的沉思也就无从谈起。从字里行间我能体会到作者的用力,特别期待作品的“言外之意”,既在故事层面上有可读性,又希望故事具有延展性。但是,作者的叙事却缺乏与之对应的力量,在意图与能力之间出现了断裂。
《每一个新年都会过去》从“面相”上看,是很时髦的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但作品的芯子其实侧重的是对孤独的体验。仅从题材去判断此篇小说的价值只会流于浮面,就会无视作家的真正用心,无疑是不公平的。小说写年幼的陆小鱼盼着爸妈回来过年的故事,爸妈回来了,小鱼倒更多地体验了与爸妈之间的陌生疏离感,觉得怎么都不像一家人,爸妈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后面短短的几天相处慢慢地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但作品对小鱼心理的描写几乎到了密不透风的境地,使得作品内外总弥漫着一种孤独凄清的氛围。此篇作品一如既往地外松内紧,像记一本流水账,故事虽平淡无奇,但因为对人物心理的深度触摸,使得作品充满了一种有意味的张力。小鱼内心对人生的“天问”,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或许显得深奥,但由于作者细致入微的铺垫营造,并不让人觉得特别僵硬、不自然。应该说,张殿权的小说在对“意味”的追求上一直是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的,这个路子是对的。但是,和《到哪里去》一样,叙事过于松散和感情表现过于感伤的缺点仍然存在。
再有短篇《城里的月光》也大致如此,此篇大概算得上“几乎无事的悲剧”,简可意也好,郑树也罢,都是那样地温情脉脉,情意绵绵。张殿权太喜欢眼泪了,说来就来,凡事多了,就让人麻木了。人都诚挚、好到了完美的地步,对应于我们今天的世界,难免让人产生困惑。我要特别提醒,“眼泪”并不是表情的最佳元素,弄不好,还是肤浅的表现。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别声响》是老托尔斯泰最喜欢的,我觉得我们的作家要好好体会“别声响”的功夫。所有能被外相表达的往往都是肤浅的。所以,沈从文提出面对存在唯有“黯哑”才算诚实。在《荷马史诗》里也写到一个父亲如何面对了儿子的死:当儿子战死,身体被战马驮回营地时,父亲的反应宁静得让人窒息;等到儿子战死的仆从的身体也被驮回营地时,父亲对着仆从的尸身先是泪流满面继而嚎啕大哭。这才是深入到骨髓里的描写啊!儿子的死带给父亲的疼痛已超越了一切外形所能表达的范畴,父亲的泥雕木塑正是绝望痛苦到深渊般的表达啊——不能表达的表达。而仆从的死于人性处毕竟有所隔,父亲的泪和哭是痛苦得有形有限的表达。作家是需要有这样“深味”的功夫的。作为阜阳小说新军首领之一,所以对张殿全吹毛求疵,笔者心里包含更多的是殷殷期望。
三、艰难前行中的希望之光
就理性的分析而言,我觉得阜阳作家的写作始终少了真正直面真实的勇气和目力。特别是在直面“恶”上面,不仅浅尝辄止,更要命的是常以自以为善良的“善”去替代对“恶”的开掘,那就更不要说去探究“恶”后面的“罪”了。在文学上,把善写得回肠荡气,把恶解剖得入理三分,都是好。就此而言,我觉得高境的《一亩三分地》、朱东坡的《鱼人三章》、还有前面提到的《屋角的战争》才是较有深度的作品。
高境的《一亩三分地》完成了对自己的一次超越。
这篇小说,情节单纯,无枝无蔓,就围绕着“一亩三分地”的纠缠展开;人物集中,就那么三五个:夏中普的“倔”、宋西波的“横”、宋道成的“柔”、老木的“圆”、夏录的“浅”,在作者看似信手拈来其实苦心经营的细节描画中却也跃然纸上。
虽然从深度说作品还有不足,但作者善于捕捉细节凸显人物特征的能力还是让人惊叹。小说主角夏中普曾经是乡村民师,多少算得上乡村世界里的“文化人”,小说开篇,他做着家务唱着《空城计》出场,小说中后来又两次写到他哼着传统又乡土的戏文,很贴这个乡土小文人的身份;然而,毕竟骨子里还是中国万千乡民中的一员,小说中写及夏中普的言语时,就活龙活现地让他从戏文的世界里走了出来,来到了更具生活底蕴的红尘世界中。当村主任宋西波强势地要征收他的一亩三分地时,生命的原色出来了:“‘啥!就这事。’夏中普把壶搂在怀里,顿时脸红脖子粗了。他扭身往屋走去,走几步又站着,回头瞪着圆眼说:‘西波,别说我不给你面子。那一亩三分地是我家的,上次老木来,我已跟他说过我当墓地了。今我明告你说,往后谁不经过我允许,动那一锹土,我夏中普跟他没完。’”一向蛮横的宋西波没想到碰到了硬茬,当然不会示弱:“‘明告诉你,以后那一亩三分地就是木盾社的了,老子回去就把它用墙头圈起来,看你能咬我鸟。’夏中普闻言,把手中的壶一下子摔在地上,嘴唇颤抖着说:‘有种你来打我。要是眨巴眨巴眼,我是孬种养的。谁不打谁是狗日的。’”类似如此乡土的场景描绘在小说中还有多处,主要人物的性格在这些场景中就慢慢地“立”了起来。
写人永远是文学的核心,高境的《一亩三分地》里有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可是,高境的文学如果还要再上一个台阶,他还必须完成自己文学意识的转换:由对生活层面的关注转向关注生命。“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余华)一个好作家必须有能力用自己的精神去穿越他所面对的世俗世界。如果《一亩三分地》在思想层面上能有所建树,境界就会更上一个层次。而现在的《一亩三分地》所以能抓人最出彩的还只是它的语言,它有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那样的活色生香,高境的文字功力已很让人期待。
对于高境来说,要追求更“高境”,另外一个突破的方向即是破坏自己的“佳话意识”。这世上所有所谓的“佳话”,都难免人主观的幻想与期许,就难免有意无意对真实进行简化、粉饰、篡改。更有甚者,还要把文学意识形态化,于是文学就成了各式样的应声筒之一而已。再比如,文学难免常常写爱情,可是最为恶俗的佳话模式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或“好人有好报”之类,文学不是写宣传海报,而是要深味我们生命世界的苦难与欢喜。有人说,张爱玲“小而浅”,可是,写爱情,中国有几个比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十八春》更写出了生命的苍凉与温暖?她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空间地理学认为,某一群体的文化系统及思维方式与一定的地理区域有天然的关联。所以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成就了福克纳的诸多经典,“高密乡”也造就了莫言的许多名篇。就此意义而言,一切文学都具有地域文化底蕴,此言不谬。
与新时期以来众多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兴起不同,淮河流域文化与文学却一直隐而不彰,“养在深闺无人识”,在学界未能取得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声誉与影响,其一,与淮河文化研究者的边缘化有关,其二,与淮河流域文学没能取得更大的社会影响有关。尽管戴厚英及其作品早在新时期之初就曾引起轰动,但她的淮河文化基因却被遮蔽在新时期之初的“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思潮之内了。迟至今天,淮河流域文学也曾创造了许多亮点,但总是显得寂寞无声,落落寡欢。在此背景下,看到朱东波的《渔人三章》,甚为惊喜。朱东波的《渔人三章》单以浓厚的地域文化书写就已具备了自身特点,有“特点”在就是创作的一个收获,一个惊喜。
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一是题材意义上的,独特的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题材是成就文学的基本因素,《渔人三章》中的捕鱼、授徒、斗法无不是淮河流域独特的人事场景;二是人物意义上的,人物的塑造因带有地域文化的基因而使之在性格、脾气、秉性、情感等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主人公“三怪”也是我们生活中很容易见到的我们身边的人物,很亲切、鲜活、真实。捕鱼而不涸泽而渔,对人真诚可靠,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虚伪,不做作,不讨巧,不夸饰。哪怕到了派出所也毫不含糊为自己讨公道,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这不正是淮河两岸人民的共同脾气秉性吗?淮河文化因其多元杂交,道家文化源远流长等原因,形成了淮河两岸人民的朴实而粗野,耿直而愚钝这一多元混杂特性。可见,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对故事的雕刻是用心的,用情的,在艺术上的特点也是值得肯定的。三是语言意义上的,语言是地域文化的典型表征,一个地域的语言不仅渗透着该地域群体独特的心理特征、审美意识、历史传承和文化结构,而且蕴藏着该地域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这一地域文化区别于他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渔人三章》中语言,无论是描写性的、对话性的、抒情性的,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
地域文化之于地域文学是双刃剑,成就文学,也可以制约文学。过于俯就地域文化,会使地域文学的境界变小,意象单调,语言粗鄙,故事重复。从《渔人三章》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比如故事的提炼能力还有待提高;语言的雕琢还欠火候;文本的细节还要再揣摩。不过,作者力图从文化寻根中去建构淮河文学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正如文章标题所言,以上不过是个人(《渔人三章》引述了同事李长中的评论)对阜阳小说的惊鸿一瞥,难免挂一漏万,当然远不是对阜阳小说的完整判断,比如,我所尊敬的“老”作家崔波本文就没有提及,不管是多年前的《化蝶》,还是后来的《无极老子》,或者近期的《乱世刀锋情》,再加上多部影视剧作品,老崔的勤奋和多产有目共睹,实在可以自成一格。本文写作最基本的动机只是希望有更多同行来关注我们阜城的文学写作,期待它有更美好的未来,或许,因为此,批评似乎多了些,但其中真挚的期待想读者诸君能明察。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
[2]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3]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2.
Large and Small: Dialectic of Novel——A Brief Survey of Fuyang Current Novel
ZHANG Xiao-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Fuyang, a place with outstanding people, was known as Ruyin or Yingzhou in antiquities. New gifted people have sprung up in modern Fuyang. Novelists who led the tide include Xu Ying in 1960s and 1970s, and Dai Houying in 1980s and 1990s. However, things and world are changing. There were no new Fuyang novelists since Dai Houying in China. The paper is a brief survey of Fuyang current novel, which may draw popular attention to Fuyang novel and promotes its new prosperity.
Fuyang novel; large and small;sin and evil;solicitude
I209.9
A
1004-4310(2015)02-0065-05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2.015
2014-12-21
张晓东(1965-),男,江苏淮阴人,教授,硕导,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