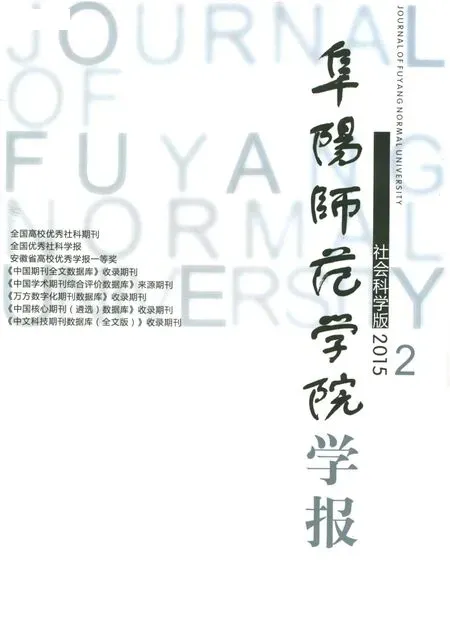论《管子》与《老子》“道”之异同及其后现代意义
程梅花,卢舒程(阜阳师范学院 a.学报编辑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论《管子》与《老子》“道”之异同及其后现代意义
程梅花a*,卢舒程b
(阜阳师范学院 a.学报编辑部;b.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道”是《老子》和《管子》共同的最高哲学范畴,两家“道”论有同有异。两家之“道”同为万物之所以然与所必然、万物之自然与所当然、人生和社会的“自然法”且均以“气”为物质载体;也存在宏观方法论与微观方法技巧、目标价值与工具价值之不同。通过两家“道”论的阐发和比较,不仅可以明晰两家之异同,而且可以彰显两家“道”论敬畏自然、彰显人性、以道御术、本体和谐等后现代意义。
道;《老子》;《管子》;后现代意义
“道”是先秦诸家共同的最高哲学范畴,但对这一范畴的涵义几乎都没有明确的界定,相对而言,《老子》对“道”的阐述比其他各家都更明确。《管子》的学派归属虽一直众说纷纭,但其中被公认为哲学著作的“四篇”,也被公认为道家著作。“四篇”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就是“道”,除了“四篇”之外,《管子》多篇论及“道”。“道”字在《管子》中共507见,除了少数是道路、说道及引导等含义外,绝大部分是哲学范畴,但涉及多重意义。系统检视并比较《管子》与《老子》中的“道”论,不仅可以明晰二者的异同,而且能够凸显两家“道”论的后现代意义。
一、《管子》与《老子》“道”论之同
《管子》与《老子》“道”论均有体、用两个层面,两家之所同主要在道体层面,即对“何谓道”或“道为何物”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两家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可归结为四点。首先,“道”是万物之所以然与所必然;其次,“道”是万物之自然与所当然;第三,“道”是人生和社会的“自然法”;第四,“道”之生成与规范均以“气”为物质载体。
(一)道——万物之所以然与所必然
《老子》之道,既无形迹可求,又无所不在、无物不由;既是“天地之始”(一章,魏源《老子本义》本,下同),又“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十八章)“始”“宗”“先”,有本原之义,但此本原不是某种或某几种原初的物质,也不是某种在天地、万物、神帝之外的意志,而是与天地、万物乃至神帝同在的,使天地、万物、神帝之所以成其为天地、万物、神帝的所以然之故。“有物”“有精”“有信”表明“道”的存在,“恍惚”“窈冥”说明“道”之无形无象,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从而不同于任何具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道”类似于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所谓的“是者”或“存在者”,是一切“是”之所以为“是”、一切“不是”之所以为“不是”,或一切“存在”之所以“存在”、一切“不存在”之所以“不存在”的原因或决定者。
“道”落实到具体事物中就成为此事物之“德”,《老子》之道德与儒家之道德不同,儒家之道德是人之先天本性中所共有之仁义礼智,《老子》之道是一切事物形而上的本原、根据、决定者,《老子》之德,也是事物固有之性,但不是一切事物的共性,而是不同事物的个性,也不只是伦理之性,而是一物之所以为一物的所以然之本质与所必然之规律。儒家道德本性源于天命,《老子》之德源于道,是道的分有,但德对道的分有并不使道有所减损。所以说“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一章),无论化成多少事物,道都依旧圆满。
《老子》之道是“无”,但不是与具体事物之“有”相对而言的“无”,不是没有,而是既非具体事物之“有”,又不与具体事物相对而无,是使一切有之所以为有的“无”。所以“道”是一切事物所必由之路,一切事物的存在与演变都由道规定,所以,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可以说一切事物都存在于道之中,一切都是道所化生,道是一切事物之本原、本根,具有原创价值,但道的创生不是一次性一劳永逸的,而是“生生不息”的过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管子》之“道”最高层次的意义也是万物之所以然与所必然,同样是既无任何规定性,又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同时所以然与所当然之道也是通过具体事物之德来体现的。如:《内业篇》曰: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身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心术上》曰:
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抵牾,无所抵牾,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
(二)道——万物之自然与所当然
《老子》与《管子》之“道”通过“德”对万物的生成与规范不是外在于事物或在事物之上的,而是万物之自然,所以“道”生成、规范万物的方式是“无为”。老子和《管子》“道”论的作者均认为,事物之自然即其所当然,最自然的就是最好最理想的,道家的价值取向是崇尚自然,所以“道”又是万物之自然与所当然。
所以然与所必然体现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事物属性、结构、功能及其变化过程之所以如此的必然性的体现;事物自然的样态与过程,虽然主要由必然性决定,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自然和必然并不能等同;当然或应然,是伦理范畴,体现了人对事物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当然与必然也不能等同。
《老子》和《管子》中都既有统而言之的“道”“天道”或“天之道”“天”等范畴,赋予这些范畴以所以然与所必然之义,又有分而言之的“正道”“善道”,相对而言之的“天道”“人道”“有道”“无道”等,赋予“道”自然与当然之义。说明所以然与所必然之“道”和自然与当然之“道”是不同层面和视域的。
所以然与所必然之“道”是最普遍的生成法则,无所不在,无论好坏、善恶、大小、高下……都有其生成演变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说,“道”没有正邪、善恶之分,是最高的哲学生成论与存在论范畴,不是伦理学范畴。
对于没有成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纯自然物而言,一切皆自然,在此视域内,自然也没有正邪、善恶等价值区分。但在人的视域和进入人类社会范畴的事物来说,“自然”是相对于“人为”“人文”而言,而人为、人文即是对自然的加工与改造,通过人为、人文的改造,使这个世界及其中的事物更加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加符合人类的价值取向。在此视域中,自然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儒家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争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善恶倾向。在《老子》和《管子》中,自然也被赋予了价值意义,即至真至信。老子和《管子》“四篇”作者均以自然之“道”为人文之真善的依据和标准。老子讲“人法道”“道法自然”,《管子》讲“静因”,都是要人顺应事物之自然,所以老子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管子》要求“无益无损”“舍己而以物为法”(《心术上》)。由此,自然获得了当然之义,自然之道即当然之则。
《老子》和《管子》“四篇”作者之所以认为自然即当然,乃是因为人为、人文都是以人为主体,从人的欲求和需要出发的,其中包含着主观尺度,一旦主观尺度偏离客观自然之道,就会背离所以然与所必然之道,从而导致恶或伪。所以,《老子》和《管子》“四篇”作者都强调“无欲”。有欲就会“有以为”,“有以为”就会患得患失,陷入君子争名、小人逐利的歧途与乱境;无欲才能为而无以为,“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感而后应”“缘理而动”(《心术上》)。只有消解了主观尺度,以自然为当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二章)。
(三)道——人生和社会的“自然法”
“当然”是对人而言的,自然物无所谓当然不当然,只有人的思想行为要遵循伦理规范,有价值取向。《老子》和《管子》均以“道”为人应该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在这个层面上,两家通常都在“道”前冠以“天”字,以“天道”与“人道”“治道”相对而言。相对于“人道”“治道”而言的“天道”之“天”,有两层涵义:一是天然、自然、本然,二是自然界、自然物。天然、自然、本然正是自然界万物之所以然与所必然之道的特征,所以,“天道”就是自然界天然、自然、本然之道。这个意义上的“天道”,就是人应该而且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类似于“自然法”。
《老子》和《管子》对人的关注,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个体人而言的养生修身,二是对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的治国平天下。前者即“人道”,后者属“治道”。两家均认为天道既是人道的根据和准则,也是治道的根据和准则。作为人道和治道根据与准则的“天道”的核心原则就是“虚静”“无为”。《老子》通篇有一种常见的句式:道……,圣人(侯王)……。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三十二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六章)圣人既是个体人养生修身典范的符号,又是统治者或管理者楷模的通称。而圣人言行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与道相合,道如何如何,圣人就如何如何。道“无为而无不为”,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抱一为天下式”(十九章)、“无欲”“无为”使万物“自化”“自正”(三十二章)、“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管子·形势篇》曰: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
一句话,顺应天道的行为就能成功持久,背离天道的行为就必定失败危亡,无论是个人的养生修身,还是君王的统治与管理,都是如此。
(四)“道”之生成与规范均以“气”为物质载体
《老子》和《管子》之“道”都无形质,是形而上的,但这种形而上的存在虽不依赖于形而下的形质,却是以形而下的形质为物质载体的,两家之“道”的物质载体都是“气”。《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万物存在和演变的方式,也是“道”最核心的内容。《管子·内业篇》几乎将“道”与“精气”等同,一面说:
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一面又说: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二者都是万物之源,又都是非感性的,没有具体的规定性。当然,道与气或精气并不是一回事。气,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气有阴阳,阴阳构成宇宙间最基本的矛盾统一体,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和演变都是这对矛盾运动的过程和结果,而阴阳之气的矛盾及其运动变化的过程及趋势,就是“道”。所以,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元素,道则是气构成世界万物及其所构成的万物一切运动变化的最基本的原理。这就是《老子》和《管子》共同的道气观。
二、《管子》与《老子》“道”论之异
《老子》与《管子》“道”论之所同,主要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形而上的视域,当“道”向下贯,进入具体方法的层面,在形而下的视域中,两家的差异就明显了。
《老子》总体上是一篇哲学论文,对“道”的运用仅限于宏观上人道与治道的原则性层面,具体的微观层面几乎没有论及。《管子》涉及领域较多,但总体上应该说是一部政论性的文集,绝大多数篇章都是以治国之道的探讨为题旨的,所以其“道”论更多的是关注实践中“道”的运用和实现的问题,尤其是具体的微观层面的方法技巧性的论述较多。
《管子》之“道”与《老子》之“道”的差异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点。
(一)宏观方法论与微观方法技巧
《老子》“道”论的主要内容是宏观上讲人当如何为人、帝王当如何治理国家,亦即“道”在人生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属于哲学方法论的范畴。至于君要如何为君、臣要如何为臣、如何操控经济、如何理财争利、如何运用法律、如何选拔人才、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等等论题,乃《老子》所少《管子》所多。《管子》中常见的是“君道”“臣道”“厉民之道”“爱民之道”“使民之道”“利之之道”“得人之道”“官上之道”“定民之道”“正民之道”“存身之道”“为之有道”等等。这些“道”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或技巧,不属于哲学范畴。
(二)目标价值与工具价值
《老子》之“道”无论是天道、人道还是治道,都是“道”自身的实现,即均是为而“无以为”,不是实现任何其他目的的工具,不是“有以为”而为(三十三章)。
《管子》之“道”大多是工具性的,是“有以为”的方法、技巧、智谋,通过“道”达到的目的、实现的效果,与相关事物的所当然之道往往并不相符,甚至是对事物本质的背离。所以,《管子》这个层面和视域中的“道”,更接近“术”的范畴。虽然对《老子》也有“君南面之术”的评价,但笔者认为,《老子》“道”论本身并没有下降到“术”的层面,“君南面之术”的意义应该说是滥觞于韩非对《老子》的解读,如果要归因于《老子》的话,也只能说《老子》文本的简约为这种解读与推导提供了空间。这种“术”的意义究竟是对《老子》的发展还是《老子》的流弊,还有待研究。
三、《管子》与《老子》“道”论的后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长期被批评为中国近现代化的阻力之一,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种种弊端日益暴露,尤其是全球性的环境、资源问题的彰显,迫使人们寻求消解这些弊端、引导人类进入后现代的思想资源时,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消解现代文明的弊病、引领人类进入后现代的意义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同。这种意义在《老子》与《管子》“道”论中也有很好的体现。以追求科技和工业飞速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现代文明中包含着如下四种现象:人欲的无限膨胀与对自然的放肆、以自然界的竞争法则遮蔽人文的道义准则、大技术论或唯技术论对科学合理性的漠视、主客两分对立导致种种不和谐。对这些现象的消解功能,体现着《老子》与《管子》“道”论的后现代意义。
(一)节制人欲、敬畏自然之道
对万物之所以然、所必然、所当然之道的肯定与推崇,意味着对人的自由意志与主观欲求的限制与规范,而且人生和社会是被包含在“万物”的范畴之内的,“道”不仅限制并规范着人对各种自然物的自由与欲求,也限制并规范着人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自由与欲求。《老子》和《管子》显然都充分认识到并高度认同“道”对人的这种限制与规范,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国都要“法道”“静因”,不可将人的自由意志与主观欲求凌驾于事物内在本质和固有规律之上。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基础就是对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和掠夺,与对自然放肆相伴而生的就是人欲的无限膨胀,所谓生产引导消费,就是不断开发新产品来激发人更多、更大、更新的欲望,而满足这些欲望的资源归根结底来自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枯竭,都与人们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有关。《老子》和《管子》对客观自然之道的这种敬畏,正是经过现代社会的肆无忌惮造成一系列弊病之后,后现代社会意识中必然应有之义,可用《大学》“知止”一语来表示,对自然的索取要知止,人欲的膨胀也要知止。相信万物皆有其所以然、所必然、自然与所当然之“道”,才能有敬畏之心,有敬畏之心才能知止。
(二)自然与人文之分合,彰显人性之道
随着科学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揭示,尤其是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提出之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被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运用于人对人的关系中。达尔文与进化论一同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在现代社会却几乎被集体选择性遗忘。达尔文在肯定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的同时,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竞争的同时对弱者的保护。意即:人类社会除了理性的竞争之外,还应有伦理的道义和人道的温情。现代社会却大量存在着崇尚竞争、认同竞争的无情,漠视道义、鄙视温情的现象。
《老子》向往在体道圣人的统治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二十三章),《管子》的社会制度设计中有救济体恤各种弱势群体的“九惠之教”。人文与自然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对必然与自然之道的背离,恰恰是必然与自然之道在社会与人的本质中的体现——人文之当然,亦即人文之所以然与所必然,是人文之自然本质的内在要求。《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五十四章)
西方现代文明是从人文的彰显开始的,人从神的绝对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与此同时,人却不知不觉中自然化、物化了,把人文变成了无情的征服、掠夺与竞争。重读《老子》和《管子》“道”论,可以唤醒人们对人文本义的记忆,消解弱肉强食的无情与疯狂,彰显上善的人性,构建弱者得到保护、不被欺凌或遗弃的社会,重拾伦理的道义法则与人道温情。
(三)“术”途知返,以道御术
《老子》有流为“君南面之术”的可能,《管子》更是充斥着大量的智谋权术之论。“道”下贯于人的思想行为,被人认知、运用的过程中,难免流而为“术”,如果是符合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方法、技巧,尚且离道不远,如果是背离事物本质与规律的奸诈权术,则会导致事物的危亡、“道”的遮蔽。这正是《老子》反对“智”的原因,也是《管子》鼓吹智谋奇巧的篇章历来受到诟病的缘故。通观《管子》,虽然其中的一些计谋很奸诈,但更多的篇章是以道御术的。当代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希望从《管子》中寻求所谓的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之术,研究《管子》的这种价值取向是不可取的,不仅难有所获,也不符合《管子》的根本意旨。
综观《老子》和《管子》,笔者认为,两家都不反对智谋权术本身,反对的是智谋权术对道的背离,方法、技巧的灵活运用并不错,错的是不能返归于道。所以,人们在发挥聪明才智的过程中,一定要知止、知返,即要在不背离道的框架内灵活运用各种方法技巧。
现代社会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崇拜技术,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运用于生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动力。但技术不设边界的运用,也造成了不少问题。技术、权术、智谋等本质上都是人对知识的运用,既然是运用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恰当与不恰当、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运用不当,必然会背离道。所以,《老子》与《管子》以道御术的观点,提醒人们在克服现代社会弊病的过程中,要注意知识、技术运用的恰当性、合理性问题,切忌滥用、妄用。
(四)“道”——和谐的本体依据
《老子》讲“道”“无为而无不为”、圣人“无为而治”,表明自然之道不仅是万物生成、演变的根据,而且是万物之间共生并存的和谐关系的根据。世界万物的和谐秩序乃“道”之自然,不是人主观随意的安排。《管子·形势》篇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天道自然和谐,人为则是不和谐的根源。“道”的创生价值不是粒子性的,而是像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一样,“道”既体现为万物各自不同的个性,是万物个体的创生者,又体现为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宇宙秩序的创生者。如前所述,“道”的创生方式是“无为”,所以,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乃是宇宙万物的天性自然,而人为的构建不是原创,而是完成,用《易传》的讲法即“人文化成”,是对万物之间,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本质联系合乎自然的体现与实现。
当然,根源于“道”的自然和谐,并不是没有冲突、取舍和伤害,生物链同时就是一个食物链,食肉动物要以别的动物为食、食草动物要以植物为食、人为了保全生命有时不得不放弃部分肢体或器官等等,这是自然的道理,是所必然与所当然之“道”。这些不会导致自然的不和谐。对于人来说,与自然的和谐,不等于不利用任何自然物,而是像《尚书》所说要“正德、利用、厚生”,对自然界的利用要以“正德”,也就是尊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自然之道为前提,以“厚生”,即“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的实现为目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亦如此,人的社会性决定着任何人都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帮助,换句话说任何人都要利用他人和社会,这也是自然的道理,但是,人对他人和社会的利用也要以尊重他人和社会的意愿、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以互利共赢为目的。无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还是人与社会,自然之道都是构建和谐关系的本体依据,背离自然之道是一切不和谐的根源。
这一点提示人们,现代文明中盛行的主客两分的世界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理念,都会导致对自然之道的背离,也都会导致不和谐。《老子》与《管子》“道”论表明一切事物都是道体呈现,也都由气构成,所以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有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有其与其他事物乃至整个世界的固有联系,人可以认知、也可以利用万物及其各种关系,但不可以无视、更不可以背离万物及其关系的内在本质和固有规律。换句话说,一切事物都有目标价值和主体性,任何人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任何物、任何人、任何组织变成单纯的工具或客体,如果执意如此,就必然遭到报复,就像人类把自然当作纯粹客体和工具,肆意掠夺、破坏之后正在受到的报复一样。这种报复也不是某种意志的体现或操控,而是“道”之所必然,是《老子》所谓“其事好还”之规律的自然呈现,所以圣人“以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不是不为而是不敢妄为。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oism in Guanzi and that in Laozi and Their Postmodern Significance
CHENG Mei-huaa,LU Shu-chengb
(a.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b.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of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Taoism, the highest philosophy scope, is both mentioned in Laozi and Guanzi. But the two versions of Taoism hav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meaning. They both believe that all things on earth exist with reasons and with inevitability, all things are natural, right and proper, life and society follow the law of nature which is carried by “Qi”, a kind of substance forming universe. They are mainly different in using the macro methodology or microscopic techniques and applying the target value or instrumental value. By elucidating and comparing the two versions of Taoism, we may grasp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gain their postmodern significance in respecting nature, commending humanity, and applying Taoism to mastering skills or tactics, etc.
Taoism; Laozi; Guanzi; postmodern significance
B226.1
A
1004-4310(2015)02-0023-06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2.006
2015-01-08
程梅花(1965- ),女,安徽潜山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