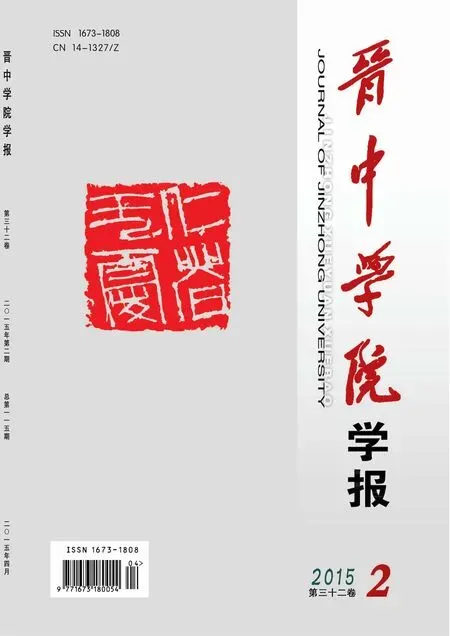调控与依附:社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闫翅鲲,张立波
(石家庄学院政法系,河北石家庄050035)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的经典话题,回顾各学科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二分范式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较为普遍认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无不置于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之下。社区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平台,更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基层政权组织,这种双重特性成就了社区国家与社会力量博弈场域的特定位置。自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单位——街居”制度逐渐瓦解,数以千万计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原来由单位承担的诸多社会职能亦从单位剥离出来回归社会,社区成为众望所归的接管者。因此,进入转型中的中国社区作为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域,其背后的故事更加纷繁复杂,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进入一种不稳定的博弈状态。在此状况下,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从管理到治理,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何在?”“在‘社区制’逐渐取代‘单位——街居制’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国家权力收放和社会力量成长的双赢共促,进而使社区善治成为可能?”为此,深入理解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力量博弈的场域——社区的结构性情境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状况及由此所带来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无疑就成为了我们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
一、社区转型:国家与社会力量博弈语境下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通过“单位——街居制”对城市社会资源实施全面配置,并通过计划对政治经济进行直接的全面干预,在这种国家几乎垄断所有资源的“总体性社会”[1]中,政府作为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通过强制手段对社区实施单方面的控制以保障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社会力量难以发育,社区权力结构单一,国家、社会高度重叠。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行,资源配置机制渐趋多元化,社会异质性不断增加,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2]城市社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单向度控制的单一权力结构被打破,社区场域内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和互动格局发生深刻转变,社区深层结构呈“碎片化”状态,表层结构体系已很难真正对其进行整合[3],国家与社会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构性情境正在发生根本改变。
(一)社区利益结构的转型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其著作《实践感》中界定了“场域”概念,这对我们理解把握社区转型后的结构变化颇具启发意义。布迪厄从场域的系统性和客观场域对行为的决定作用两个方面定义“场域”的概念,认为场域是各种位置中存在的关系或架构,行为主体在其特定位置上的行为受到各种位置关系的影响[4]。从场域理论视角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场域内,各行动主体在物质资源的获取和占有方面有着极强的同一性,国家借助统一制定的分配体制和户籍、单位制度向城市社区居民配置资源,居民们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力,因而在职业、收入、住房甚至教育方面都差异不大,社会力量依附于国家控制下的物质资源实现社区的高度整合。而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场域内的行动主体迅速发生分化,在职业、收入和教育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加大,行动主体的异质性改变了原有的阶层格局,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增强,对国家资源的依附程度降低,一体化的场域关系网络被打破。
(二)社区权力结构的转型
改革前计划经济的集权特征长期影响社区的权力结构,形成基层权力薄弱对上依附的状况,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空间极为有限[5]。经济体制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行使居民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身份被强化,利益下沉成为必然。同时随着大量公共事务从单位剥离出来回归社区办理,居民作为场域内行动主体参与社区决策的渠道拓宽,社会力量逐渐发育壮大,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这一切都对社区权力下沉提出新的要求,国家单向控制的基层社会管理格局难以为继,以基层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和以各种商业组织、自治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了其在社区场域内的位置,并因此而重新架构了社区权力结构。
(三)社区文化结构转型
传统社区的意涵是以亲密情感为纽带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转型前的中国城市社区亦是建立在地缘、业缘基础之上的熟人社区。在这里,世代为邻的人们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上构筑了“制度化领域”和“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的“非日常生活领域”[6],在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指导下大家共同守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制解体,户籍制度松动,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聚居的小区打破了原本的熟人社区格局,日常生活领域高度分化,温情的精神家园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的契约共同体。支离破碎的日常生活领域使传统社区场域中的“惯习”失去效力,国家力量亟待创新整合手段,拯救“碎片化”的社区,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
二、从刚性管控到柔性调控:博弈过程中国家权力运作机制的转变
如上所述,在社区转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社区场域内诸多行动者的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强,其在资源动员和资源获取方面的能力增加,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异质性凸显,社区场域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互动情境的改变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二者在新语境下的博弈。
在中国长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的现实情境下,虽然各种社会力量从未停止过对社区话语主导权的争取和对自身利益诉求的维护,但国家权力一直是型塑社区空间的主导力量,基层政府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权力运作方式实施对社区的有效控制。回顾转型以来社区内这两种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历程,可以根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变化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转型初期阶段的刚性管控
道格拉斯·诺思的路径依赖“锁定”(Lock-in)[7]概念或许为我们理解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权力的社区控制策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这一概念指传统制度框架的惯性可能制约新的制度路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权力对城市基层社会自上而下全方位控制的强大惯性即便在民主化进程有所推进,社会力量渐趋发育成长的转型初期依然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在这一阶段,国家权力仍然强势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刚从单位回归社区的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决策缺乏相关制度性规定,往往由政府安排,因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决策权仍在政府手中,原本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不过是基层政府在社区的延伸机构,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下,国家的基层社会管理理念已发生转变,开始主动通过政策调整进行自上而下的退让,这主要表现为1980年1月,全国人大重新颁布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通则》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四项有关居委会制度的法律文件[8]。
(二)20世纪90代至今的柔性调控
我国的社会转型始自经济体制的转轨,因而市场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社区这一互动场域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市场调控能力增强,体制外资源增多,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迫切需要突破国家一元主体控制下封闭的社区公共空间,国家不得不迅速调整控制方式和控制范围,做出适度退让。早在九十年代初,国家就提出要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实现社区自治[9],并着手通过巩固、加强社区居委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对社区自治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动。但在这一以自治为目的的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国家权力向城市基层的渗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10],国家权力在社区建设中依然占据实质的主导作用。在国家无法拥有过去那样强大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其权力运作方式开始从刚性转向柔性,从直接管控变为间接调控。
国家权力在城市基层社会运作机制的改变意味着国家权力需借助市场力量以更为隐秘化的方式向社区公共空间渗透。应该说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全面推行是国家权力在城市基层运作方式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量。住房商品化终结了单位制下的住房分配制度,国家不再是房屋产权的拥有者和分配者,市场作为社区场域中的新兴力量在转型期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崭露头角,国家逐步从社区撤出。为此,国家引入物业管理制度进行弥补,并通过相关制度规定强化物业管理与社区自治的结合,突出社区治理过程中两个主体——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的作用。但物业公司与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房地产管理部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关制度条例的规定又有着明显的市场培育化倾向,例如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中的规定就硬性要求业主必须选聘物业公司管理社区物业[11],而当时的物业公司多数是由街道或国企转制的开发商组建的。这使得国家力量从社区的淡出仅仅是形式上的,在实质上各政府部门一直是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社区治理行为的裁判,只不过从“台前”转入“幕后”,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间接调控。
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依附:博弈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回应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迅速改变了城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叠的状况,社会空间的相对独立性日益凸显,国家不得不改变其权力运作方式并有意识地调整控制范围,以新的策略渗透到社区公共空间。不容忽视的是,国家权力的收放和社会力量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的一体两面,正如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12]概念所指出的,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两方面中都各有若干不同因素,并且在不同方向上相互交织和彼此塑造。因此,我们在关注国家自上而下渗透策略变化的同时亦应探讨自下而上生长的社会力量对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对应国家权力行使方式变化的两个阶段我们将社会力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回应也分成两个阶段来探讨。
(一)转型初期阶段的被动接受
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决策程度一直被学者们用来判断社区自治的发育程度,同时也被认为是考量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博弈状况的重要指标。在社区转型初期,由于国家全能控制的惯性,社区组织生长的空间十分狭隘,原子化的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持漠然态度,对于社区参与的最基本权利——居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权都不够重视,居委会成员多数由国家权力的基层代表——街道办事处委派,并非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也因此而成了国家权力在社区的延伸机构,失去了其自治组织的本来特征。
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一阶段,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在数量和范围上还是有所发展。但由于原本的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在实际运作中的功能并非“居民头”,而是“政府脚”,对社区参与的公众动员是以贯彻国家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为意图的,往往令这种社区参与流于形式,呈现出象征性或仪式性特征。参与其中的社区居民是居委会有意识培育的“积极分子”,以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为主要力量,多数社区居民则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对于居委会代表政府所做的公共事务安排听之任之。显然,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来看,社会力量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仍被动地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管控之下。
(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主动依附
20世纪90年代住房商品化改革在令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从刚性转为柔性的同时亦令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发生较大变化。作为住房产权的拥有者居民们的权益意识增强,业主们为了维护房屋产权和社区公共环境的权益而日益提高组织化程度,最基本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在与国家权力互动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断加强。转型初期作为国家权力在社区延伸机构而存在的居委会在转型驱动下逐渐淡化其行政控制色彩,服务性特征日益突显出来。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基层控制策略日益隐蔽化和合法化,社区中居民进行公共事务参与的组织化平台也逐渐增多,专业组织平台、楼组平台、睦邻平台等组织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居民们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和决策的渠道,社区参与的目的和意义也逐渐从政治象征转向社区日常事务的管理,其实效性大大增强。
仔细分析社区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组织平台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威——服从”关系[13]。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中的国家代理人扮演服务性组织角色的意图是为了贯彻国家的“服务”理念,通过提高服务技能来获取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可、接受和支持,强化迈克尔·曼所指的国家基础性权力,建构社区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威——服从关系”,实现社区治理中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而这种“权威——服从”关系之所以能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在其成长过程中对国家权力的依附需求。社区参与的有效性在于其组织性,在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情境下,居民的自组织及其在社区参与中的组织行为的合法性认定主要源自国家而非社会。[14]正因国家权威拥有认定组织行为合法与否的强大功能,社区居民在不断增强的社区参与意愿推动下从漠视被动转向主动依附国家权力,以拓展自身的成长发育空间。
四、结语
学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无论是“国家中心”还是“社会中心”的视角似乎都无法对当前我国快速转型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社区场域内的博弈状况作出充分解释。在“第三条道路”视角下审视由转型所致的社区结构性情境的变化,关注由此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构,可以发现,虽然在我国社会转型速率不断加快,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的语境下,国家权力从社区撤出,社区居民逐步实现自治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在场也是必不可少的。博弈过程中双方的态度已然从刚性的管控和被动接受转向柔性的间接调控和主动依附,体现了一种非平等的合作关系。鉴于此,在社区场域内推动建构国家与社会力量相互渗透与包容的开放型互动机制应不失为我们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社区和谐的有效途径。
[1]李强.中国社会变迁 30 年(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40-50.
[4][法]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孙炳耀.对居民社区行动场域的理论解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8-24.
[6]王冬梅.从小区到社区——社区“精神共同体”的意义重塑[J].学术月刊,2013(7):31-36.
[7]曾芸.当“社区参与”遭遇行政路径依赖——以G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92-97.
[8]黄晓星.国家基层策略行为与社区过程——基于南苑业主自治的社区故事[J].社会,2013(4):147-175.
[9]刘娴静.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中国的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06(2):59-61.
[10]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J].社会,2007(6):102-126.
[11]张磊.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J].社会学研究,2005(6):1-39.
[12]MIGDALJ.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3]唐文玉.城市社区中的权威效能治理——基于T社区的个案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3(4):86-94.
[14]闫翅鲲,许爱青.融合与创新:“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路径探讨[J].晋中学院学报,2014(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