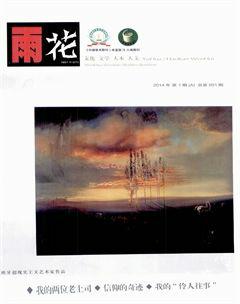体验自由
薛尔康
虽无自由之身,却有自由之心,意识既已感悟自由,肉体的禁锢还能算是禁锢吗?当精神摆脱客观现实的制约,营造出一份自在的心情,人便进入“监狱本无房,铁门亦无锁”的境界。
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说自由,颇有讽刺意味,恰如面孔饿得发青奢谈美味佳肴。转念一想,相比肠胃撑得难受的人来说,那个脸皮发青的家伙才真的懂得何为美昧。
号子分里外两间,里间是真正坐的,外间同样大小,顶上封着扁钢与钢管焊成的网,遛腿用,叫风场。
每当早晨传来空谷足音,“咔嗒”一声如同上帝咳嗽:风门开了。在六平米的里间足足憋了二十三小时的囚犯迫不及待到外间走动透气。风场是人性的表示,证实关在里间的不是两足哺乳类动物,一小时的放风大大降低精神性疾病发生的可能。
透过钢铁的网,仰望蓝色的天,内心总是悸动起来:在与自然的唯一联系中,远古的记忆在体内苏醒,发觉灵魂与天空存在着血缘的联系,我就是从那深邃的蔚蓝中诞生。凭着这样的感觉,我信了天人合一那句话,有理由拒绝人从猴子变来的学说。人类祖先该是遨游蓝天的会飞的动物吧?
没料到我的妄想竟然得到佐证。手头的一本佛教书籍告诉我,地球人类来自光音天第七重天,本来出于好奇,观光而已,结果贪吃地球上的食物,身体变重,再也飞不回去。可见地球上的美食领先宇宙。要想推定这种结论,目前可以找到的根据有二,一地球人个个是天生的馋嘴,二是人都爱仰望天空,带着几许惆怅。
几百万年来,所有的脊椎类爬行动物迫于生存的压力都在进化,唯独人直立,尚且颈椎骨特别灵活,做昂首向天的动作毫不费力。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从仰望天空开始,谁不想挣脱地球的引力,获得飞翔的愉悦呢?远古中国人的崇拜物一式是腾云驾雾的,就连太阳也被想象为鸟,称作金乌、赤乌、曙雀;古埃及的法老们不敢落伍,崇拜鹰神荷鲁斯,鹰至今刻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货币或者旗帜上。
人一出生便意味着与自由签订了生命之约。自由精神出于人类的本性,也是根本的追求,当是当今世界最无争议的事。
但是,人老是抬头望天也不是件好事,容易想入非非,像我现在凝望头顶上的天被割成36块大小相等的矩形,就犯糊涂:我与天空究竟谁被囚禁了?看来,鸟笼一定要用黑布蒙起来,开在牢房高处的小窗户虽然要跳起来才能望见外面,仍需用挡板挡住出于同理。
在号子里呆久了,我终于能平静地接受没有自由的日子,原来置身的那个世界淡出记忆。你是一只打开鸟笼也不想飞出去的鸟了吧?我没事找事问自己,直把自己问得心惊肉跳,惊悟自身处境的危险。
自由的意识竟能从人性中清除掉?
其实,在牢里不能说没自由,嘴巴就享有充分的自由,骂什么都可以,而且没人管,以至于我想谁想骂个痛快无妨坐一回牢。同仓难友哪天不骂就没法过夜,骂政府骂官员骂公安,骂得痛快恶毒、狗血喷头,贩毒犯盗窃犯抢劫犯都够判政治犯。他们是用言论的自由聊补人身的不自由吧?对于我而言无补于事,我的自由在哪里呢?
有一阵,牢里安排做工,插塑料花或做灯珠,尽是简单重复的活儿。干活是欢天喜地的事,因为风门就整天开着了。出于所方照顾,没让我干,其余五人到外面做活,我独占六平米不说,还能随时到风场溜达,活动空间一下子扩大到十二平米。这个便宜捡得大了去了,就因为那扩大了一倍的空间,我读书、思考竟然格外专注深入,写点儿笔记之类思路敏捷。早先写作,有一种不是我在写的感觉,我不过是某种力量借来捏笔的一支胳臂,夜以继日不觉得累。事后,常常觉得那些文字不是我写的,文章发表后读着会吃惊:这是我写的吗?
现在,脑血管的淤塞忽然被清除干净,这是扩大的那六平米做出的贡献,我重新变做那支捏笔的胳臂。自由实在用不着太多,甚至只需要是一种许诺或者象征,因为我整天窝在里间做我的事,懒得到风场去,有人往返进出的时候,还要叮嘱一声:“请关上风门。”
空间虽只扩大一倍,带来的却是十倍的自由,还有一百倍的感叹。空间如此可爱,空间原来等于自由,此种判断似乎触及到生存的本原,于是理解人为什么舍命追求空间。就拿人类历史来说,除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为争夺空间打打杀杀之外,也实在看不到别的故事。
两个月后,没工做了,长吁短叹在四壁间来回击撞。我的奢华生活戛然而止,内心已无法接受回归的正常,整日惶惶不安,靠来回踱步压制浮躁的情绪。自由原来是不能得而复失的,哪怕只给你那么一点点,这该是中外专制制度不愿意触碰自由,历代独夫民贼闻自由而丧胆的缘故吧?
我不时走过去捶风门出气,忘记这是一种违反监规的放肆行为。饭窗突然啪地打开,巴掌大的长方形中出现老管教的面孔,没等我说一声对不起,他就把饭窗啪地关上了。老管教一向对我颇为关照,但这一次的关照完全不同,是理解我的行为之后给予的格外开恩。他连一句警告的话也没说,让我感动了一整天。显然,锁住的风门是令我感到窒息的原因。平心而论,两个月来风门虽未上锁,也是关住的,与现在形式相似。形式的确具有欺骗性,但自由不能是欺骗,自由的涵义决定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以前,只是我不想出去罢了,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嗒”,除非白痴,谁要想象风门开着是不可能的。
时间又过去一年,说起来请别不信,我竟然喜欢上这个六平米空间了。几年来,马不停蹄,忙于商务,抱怨没有读书思考的自由,休息的自由,写作的自由,抱怨多了,命运便以荒诞的形式让我拥有这些自由。都说牢里时间如山,压得死人,眼下,我已将山挖空,还挖出坑来,对岁月生出白驹过隙的埋怨,冲破了“把牢底坐穿”的记录。
时间,正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逝,没做多少事呢,一晃眼一天没有了;一不留神,一周一个月又过去了。虽未坐禅,已进入“坐禅一日一弹指”的境界。
此种情状,促使我逼问自由的真义。
以前,我之所以坐牢坐得辛苦,是精神跟着肉体坐了牢,精神的牢是自设的,也就真的坐了牢。自由是生命活性和活力的体现吧,往更高的层面说,是生命力转化为创造力的重要环节吧,当我的生命重新焕发活力,进入创造的过程,不就处在自由的境界中了吗?endprint
坐牢并不是我的选择,但将牢房变为书房却可以是我的选择。这种选择对我来说很自然,就像桥牌迷沃伦·巴菲特说下面的话很自然:“如果一个监狱的房间里有三个会打桥牌的人的话,我不介意去坐牢。”
意想不到,监狱这种鬼地方竟是修身养性的好所在。如同蜗居深山的苦行僧,忍受环境的压迫,磨炼受难的心志,冥想修行,超然自得,获得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解脱。我觉得自己站着比从前更像一个男人。
风门,还有那扇每次关闭必会发出震悚心灵的金属撞击声的牢门,我已经不介意它们的存在。空间继续延伸,而且丰富,再联想那些打开笼子也不想飞出去的鸟,觉得可悲的不是鸟,倒是笼子。鸟不以为笼子是笼子了。
自由原来可以用意识来体验,环境压力在体验中分崩离析,并且获得生理快感和审美感受。当生命意识进人由被动进入主动自觉的追求,我感到意识世界的新鲜、美丽、辽阔、深邃,宇宙从来没有如此和谐过。
我对自由的感悟,可以从中国文化渊源中寻找到存在的理由。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自由来自自然之理,来自心与物、内与外、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自由既由人的内心世界来体验,如果没有心灵的自由,也便感悟不到生命世界的自由。这种哲学,与西方人认为自由来自神性的赋予完全不同,两者来路不同势必造成诠释的不同。
基督教世界认为人既是上帝创造,必享有天赋人权。这种观念源自《圣经》,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正值商代末期,其时华夏确认的是天赋王权的观念,老百姓的自由拿捏在一个人的手中,不当顺民便没有生路。《圣经》既由犹太人写出来,自然要表达在埃及当过四百五十年奴隶的民族的诉求,他们渴望人的解放、平等、博爱,对法老的统治发动孤注一掷的反抗。到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喊出的口号也是“不自由,毋宁死”。故而,西方世界的自由注重人身的不被奴役和束缚,至于对喜欢胡说八道的嘴巴和胡思乱想的大脑,没有专门予以强调,直至上世纪中叶发现疏漏,由此,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除了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外,宣称“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首先从西方将“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是严复,他老人家断言:“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其原因全在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此话锐利得在中华民族身上割出血来,指明自由是开创性和创造力的源泉,可见自由不止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世界上真理太多太多,能陪伴人类走到最后的少之又少,严复老人家对于民族强弱的发现是其中之一。
有人说,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是自由。哲学是哲学家脑子里摆弄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玄虚,哪里担得起这个纲呀,将哲学两字拿掉,写人人性两字才能颠扑不破!中国自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秦王朝起,历代兴文字狱和言罪,士大夫们只得放弃外在的生命世界的自由,转而寻求内心世界的自由,以避免肢体的不自由或者遭消灭。幸而在百家争鸣的年代里,老庄已经创建好一套完备的理论摆在了那儿,以供不时之需。中国的知识阶层大受其惠,以抽象为特点的中国文化便以更多的努力转入精神世界,于是,一种超越人身的自由观奇妙地出现。且不管这是中国人的幸与不幸,凭赖心性的熔炼、精神的升华而获得的自由,不须他人恩赐,即使类似寓言或者童话,却是实惠得很。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文人不仅未被折憋死,还竟然创造出那么灿烂的文化奇观。反之,中国历史和文明势必是另一码事了。
庄子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始祖,他对老子的道做出精微美好的延伸,首创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的自然主义的境界。他早年辞去蒙城小官,宁愿糁汤野菜,自囚陋屋著书,楚威王派使者携千金请他出山,庄子嘻嘻哈哈地“喻牛辞相”,要不然,世上便无《逍遥游》,后人也便无法体验那种摆脱物质世界、无极之外又是无极的精神自由。
比照中国的理论,西方对自由的诠释,及不及格是个问题。超逸脱俗,无为自化,西方人摸得着头脑吗?“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是上帝才有的自由吗?禅宗提出“平常心是道”,取自老庄又普及老庄,让中国式的自由观在世俗社会遍地的生根开花。
我是深得上述自由观的实惠的。譬如,头顶上日夜亮着的200瓦大灯泡不存在了,不再为之失眠,且具催眠之功效,我每天获得深度的一夜不醒的睡眠。又譬如,风门的“咔嗒”声不再是上帝的咳嗽,在风场呆不满半小时,我要紧告别上帝回来做自己的事了。再譬如说,读一本书读至入神,我从心里对自己说,可别在这两天放我出去,容我将书读完吧!
虽无自由之身,却有自由之心,意识既已感悟自由,肉体的禁锢还能算是禁锢吗?当精神摆脱客观现实的制约,营造出一份自在的心情,人便进入“监狱本无房,铁门亦无锁”的境界,以至将牢房认作再生之地,这是我不愿意恶咒这个该死的六平米的理由。
自由的实质不过是一种心理感受,所以,我要说精神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的落脚点,是更深刻的自由。看来,对前文“自由即空间”的诠释必须加以修正,这个空间应当包括精神空间的超越在内。人啊,如果你将自己的精神推进某一间囚室,也便只拥有爬虫走兽的快乐,离自由的真义远了去了。
精神的不可囚禁正如天空的不可囚禁,是人类不会退化为动物的保证。在最不自由的环境里,我活得充实,苦难仅限于肉体。有人说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有人说是人I生的堕落。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不堕落你们见到的将是一个傻子,精神病患者,眼睛斜着嘴巴歪着那种,这个人将会在你的脸上抓出十道血痕来。
尽管我头发变白,臼齿松动,脸色难看,有明显的营养不良症状,人反而变得睿智了,毕竟在没有自由的空间里找到了自由。
多谢老祖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