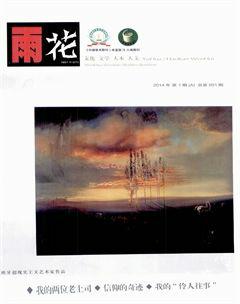亲爱的岛 亲爱的海
潘向黎
如果鼓浪屿是一位美人儿,那么白天她的笑容过于热烈和直白了,接近于美洲女郎的那种风味;只有到了晚上,她才变成了蒙娜丽莎,温婉、恬静而深沉,连笑容都那么神秘。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到厦门了。只记得:到厦门,一定会到鼓浪屿。
近年的鼓浪屿,和记忆中的相比,似乎越来越热闹,失去了过往那种海上仙山般的静谧优美,让我有微微的失望。但是,去年,我住在岛上的海上花园酒店,游客退潮后的夜晚和清晨,整个岛又向我露出了熟悉的静美朦胧。如果鼓浪屿是一位美人儿,那么白天她的笑容过于热烈和直白了,接近于美洲女郎的那种风味;只有到了晚上,她才变成了蒙娜丽莎,温婉、恬静而深沉,连笑容都那么神秘。夜晚的鼓浪屿,整个岛迅速地变成一幅浓烈的电影画面,或者一个深邃的幻觉,甚至就是一个梦境:散步的时候,有时候举起脚步会突然不敢踏下去,或者面对一枝挡道的三角梅犹豫着可不可以拨开,因为心里总觉得只要做一个动作就会醒来,会被无情地抛回城市的万丈红尘、十面埋伏、无穷辛苦、重重烦恼之中。
听到厦门、鼓浪屿这些词语,每一次都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愉快,好像和我有很深、很特殊的缘分似的。到了鼓浪屿,总有一种冲动,想要大喊一声:“是我,你还好吗?”
是了,我是福建人,而且是血统纯粹的闽南人(父母都是闽南人),但是我出生在泉州,并不是厦门;虽然,我从小就常来厦门,而且两三岁时就在鼓浪屿对面的亲戚家,凭窗对着海水咬字不清地说“海止(水)啊来呀,阿黎要澎澎(“澎澎”者,儿语“洗澡”之意)”,成了全家许多年取笑的“典故”;虽然长大后知道福建人的骄傲——林巧稚先生是鼓浪屿的女儿,成为中文系的学生后,更知道林语堂先生、弘一法师都曾经和鼓浪屿有过不浅的缘分;但毕竟,我的家乡是泉州,我不曾像我所仰慕的林语堂先生那样在这里渡过童年和青春岁月,更没有福份,和厦门的文化名片、诗人舒婷一样,神仙一般长久住在鼓浪屿上;甚至我的写作,也一直和厦门没有什么关系。实在很难解释为什么内心对厦门有这么真切而深深的感应。
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暗暗承认自己对鼓浪屿所怀着的,是一种类似单恋的、没有来由的感情。有时候,还暗暗嘲笑过自己的自作多情。但是,生命真是有她的逻辑,早晚会让人拜服于这种逻辑的神秘和天衣无缝。大概是十年前吧,父亲潘旭澜先生的一篇文章给了我提示。那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之约》。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和他的两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好友,曾华鹏先生、吴长辉先生,三位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在西湖边相约,等将来工作、结婚以后,要连同各自的妻子,六个人一起到鼓浪屿,找个好旅馆,好好住几天。这“承载着中国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真纯友谊的名义签字存在心底的合约”,毫无疑问,是年轻的他们的一个梦想。因为,能够在鼓浪屿舒舒服服地住上几天,又是成双作对,几乎已经是当时的他们能够想象出来的美好生活的极致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奢侈、对今天许多人来说几乎轻而易举的计划,几十年来,就是止于梦想,就是没能实现。为什么会这样,了解那段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人们都不会惊讶。
幸运的是,他们的友情从未改变,这也许要部分归功于闽地古风对他们的浸润。饱经忧患而一向语速迟缓、落笔谨慎的父亲,白纸黑字地这样评价他们的友情:“无论什么季节,无论风雨晦明,无论山呼海啸,即使音书断绝,即使朝不保夕,即使独处危崖,我们都知道,有那么两个好友,心底开着雷达,搜索着自己的动向,关注着自己的命运。”(此刻,泪水再次盈满我的眼眶。)终于,在那个约定的五十年后,他们在鼓浪屿住了一个星期,不过只是四个人,只有华鹏伯伯如约带了夫人赵春华阿姨,父亲和长辉伯伯都只是一个人前往,母亲和长辉伯母都没有参加,父亲的解释是:“都老了,早就没有什么闲情逸致了,而且各自家里有种种杂事缠住。”那次相聚非常欢乐,他们毫无计划,每天在岛上散漫地信步,一日三餐在岛上找喜欢的餐厅吃,还回宾馆午睡,晚上就在一个套房里喝茶、饮酒,“三家村夜话”聊得十分畅快。父亲感慨地写道:“我能活过七十岁,又能与也经过磨难的好友来这里寻梦,要说是幸运,自然可以。毕竟尚能行走的时候,踏遍全岛的街道和海边,找寻五十年前的旧梦。然而,它已苍老残破。”是啊,他们本该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大展才华的岁月,却在风暴的席卷、无情的摧折、备受压抑和歧视中渡过,而且青春永不再来,一切无法弥补。
是二O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今天,仔细重读《潘旭澜文选》中的这一篇,才发现当时他们住的就是海上花园,和我去年住的是同一个地方。父亲如鹤的身姿在二OO六年七月消失于长江人海处的苍茫——在此之前,华鹏伯伯和长辉伯伯各自从扬州和香港来看望了他。然后是长辉伯伯温暖人心的笑脸隐没于浅水湾的蓝天白云。最后,华鹏伯伯潇洒的身影也在二。一三年的一月悄然淡入江南的烟雨树木。天塌般的悲伤、海啸般的哀痛和孤儿般的茫然无措之中,我紧紧抓住一个想象来安慰自己:他们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得以欢聚,继续海阔天空地喝茶神聊……他们都是如此守信、重情的君子,一定是这样的,一定。
是的,鼓浪屿埋藏着父亲和父执们的青春旧梦、带来过他们一生中并不多的、因此弥足珍贵的悠闲和愉快。鼓浪屿上的那些古榕树、椰子树、罗汉松、棕榈树,那些凌霄花、三角梅、鸡蛋花、爆竹花,都见证过他们的流连忘返和彻夜长谈(我知道,他们饮的是铁观音,说的是闽南话);他们心里五味杂陈的感情和心绪,也肯定汇入过鼓浪屿海面上那不断涌动的波浪……鼓浪啊鼓浪,鼓起的是多少代人心中不灭的梦想和深沉的眷念,人们深爱的是这个小岛,又不仅仅是这个小岛,而是以“鼓浪屿”命名的一种生活:宁静、丰饶、舒适、优雅,以蓝天大海、琴棋书画为伴,在大自然和艺术的双重眷顾之中,远离贫穷和愚昧,远离稻粱谋、生存法则和尘世的纷纷扰扰……但这种生活,对多少代中国人来说,始终还是离梦想近,离现实远。
如果说,是父辈对鼓浪屿一生不移的情感,让我对鼓浪屿有特殊感觉,应该算“虽不中,亦不远矣”。endprint
但命运神秘的拼图中,还有一块小拼版,是不喜欢儿女情长的父亲没有披露的,幸亏母亲将它递给了我。去年,当我独自漫步在菽茬花园的栈桥上,身边的园景和眼前的海景包围着我,有两句话蓦然跃上心头:海阔天空。尘虑顿消。我忍不住拿出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对她描绘我所站的位置和眼前的风景。母亲听了,似乎也传染了我的好心情,笑着说:“那里我也去过的。当时我和你爸爸还在谈恋爱,就在你站的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合影。”是吗?我竟然不知道。于是我追问详情,母亲回忆道,当时父亲提议合影,而家教良好、性格单纯的母亲一听之下,内心颇为犹豫,总觉得一旦合影,好像两人关系就定了下来似的,事关重大,“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母亲说。“后来呢?”我问。呵呵,自然是终于同意合影了。我后来注意到了这张照片,就在菽蒋花园的小桥上,背后是园林和小洋楼,照片上的两个人都穿着朴素的衬衣,父亲站着,越发显得个子高高的,一身书卷气,母亲坐在桥栏上,梳着两条小辫子,年轻秀丽,她的目光没有看镜头,而是看向旁边,自然中带着些许闺秀的矜持。就在他们面前——在他们和镜头之间,有大朵大朵的花朵,不知道是不是扶桑花,但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仍然能感觉到彼时的春暖花开。“既遇良人,云胡不喜?”照片上的两个人就这样,初恋定终身,从此携手走过了四十余年的风雨人生。
如此说来,鼓浪屿可以算是我父母的定情之地。除了爱情,那时他们眼前的美景大概也对两颗年轻的心的彻底倾斜起了一定作用吧?上世纪的中国,做知识分子的妻子实在不容易,且不说生活清苦、身份低贱,单单是无法解决调动导致的长达十五年的两地分居,就误尽了两个人原本属于青春韶华的花朝月夕、相伴相随。所以父母的媒人、我的大姨妈曾经反复自问究竟当初有没有做错决定,我不忍心她这样反复“天问”而没有回答,于是在一本送给她的散文集的扉页上,我这样写道:“亲爱的大姨,你当初介绍我父母相识,无论别人怎么想,至少我是绝对赞成的,我永远感激你!”同样,无论父母携手相伴对他们来说是否算得上是此生之幸,但对我和妹妹来说,绝对是“赞成”他们当初不无浪漫的选择的,因此推动这个选择的鼓浪屿对我们也是有大恩的,是我要感谢的所在呢。
天风海涛,树影花香,红瓦雕窗,琴音诗韵,更兼花朝月夜,到处都是携手同行、低声笑语的双双对对。海上仙山哪有这么活泼泼的人间景气?哪似这般可以融入其间去看、贴在心里去爱?鼓浪屿,是亲爱的岛,亲爱的海。而对我来说,是这些,又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来自家族和血缘的神秘缘分,让这岛,这海,如此亲近而让我深爱。
连先知穆罕默德都说“既然大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里来,那么穆罕默德就到大山那里去吧”,早已成年的我如果再重复幼时“海水啊过来”的呼唤,就不再是天真而成了狂妄,大海不会为任何人“过来”,但我们可以一次一次地“过去”或者“归来”,向这个亲爱的岛,这片亲爱的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