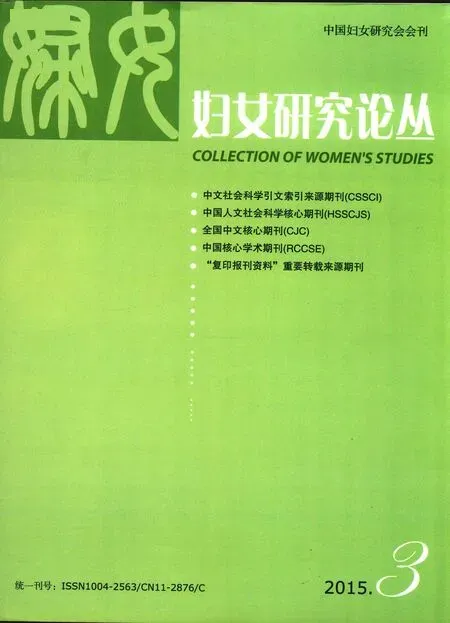社交公开、男女同校与师生恋: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情书事件
周宁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社交公开、男女同校与师生恋: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情书事件
周宁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性别立场;情书;男女同校;社交公开;师生恋
1924年5月,北京大学“校花”韩权华在《晨报副刊》控诉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诱惑女生,道德败坏,对男女共同教育产生恶劣影响。此事迅速在公众之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媒体持续关注。如何看待杨栋林向女生冒昧写情书的行为?又如何看待此事对男女同校产生的影响?众声喧哗的背后,其实展现了公众在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等问题上的不同理解和性别立场。在当时的校园环境下,社交公开与自由恋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礼教的思维方式与评价标准仍然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生活。
“五四”之后,有识之士鼓吹社交公开,男女同校现象日渐增多。从表面上看,青年学生获得了更多自由交往的空间,但实际的情况究竟如何?王印焕和陈湘涵认为学校秉承社会和家长的意志,极力避免异性学生间的接触;男女学生间过于敏感防线,也阻挡着他们的自由往来[1][2]。杨联芬指出,20世纪20年代,性道德似乎空前开放;但实际上,无论是社交中的青年男女,还是凝视他们的社会,都脱不了“旧”的眼光[3](P47)。在男女自由交往仍受禁锢的环境下,情书就成了男青年表达爱慕和追求异性的重要方式①20世纪20年代,写情书追求异性风靡一时,甚至出现了专门教人写情书的作品集,比如章衣萍的《情书一束》。目前,有关情书的研究多限于情书文本、版本和名人情书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由情书引发的公共事件。参见许建辉、徐俊:《章衣萍〈情书一束〉初版时间辩证》,《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1期;汤和柏:《章太炎的情书》,《书屋》2009年第4期;孙绍振:《徐志摩的情书和中国的男性沙文主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而对于女青年来说,男青年的情书并非仅仅是爱慕表达那样简单,有时会引发社会对自身道德清白的怀疑。因此,冒昧而至的情书并不一定受女性欢迎,有时竟使她们惶恐不安,甚至不惜诉诸媒体以证明自己的清白②夏晓虹就通过1906年杜成淑拒屈新彊函,探讨了新学界在男女交往中自觉的边界设置,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处境。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新教育与旧道德——以杜成淑拒屈彊函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在杨栋林情书事件中,北京大学校花韩权华的反应同样十分激烈,认为它不仅是对自己的冒犯,也是对男女同校的破坏,引发了京沪媒体持续关注。在精英知识分子代表孙伏园、周作人等人看来,杨栋林此举虽不免有诱惑之嫌,但韩权华将情书公之于众,也太过小题大做、惊慌失措了。而公众的义愤填膺,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同情惋惜形成鲜明对比。不同阶层围绕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尺度”等议题展开交锋,显示出巨大差异。本文希望通过对这样一起公共事件媒体言论的分析,增进对“五四”后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的认知,分析不同群体的性别立场。
一、情书风波
1924年5月7日,《晨报副刊》发表北京大学女生韩权华的署名文章,文中将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给她的一封情书全文转发。行文最后,韩权华不无愤慨地说:“不意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对本校女生——素不认识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为此等事匪但与权华个人有关,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4]韩权华的这篇文章立即把北京大学教授杨栋林推到了风口浪尖。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了“驱杨”运动,“有人张贴皇榜,发檄文,指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又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弃之之概”[5]。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长也致函讽杨辞职[6]。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杨栋林辞职通告。
杨栋林究竟在信中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众怒?客观上说,杨栋林在信中确有诱惑女生之嫌。韩权华,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身材高挑,容貌姣好③韩权华当时为公认的北大校花。许君远曾回忆道:“乙部(文预)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许君远:《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西安: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追求者如过江之鲫④韩权华说:“我在北大将近两年,唯一的目的在乎求学,所接不认识人的来信不知凡几。或已付丙,或并未拆。”韩权华:《一封怪信》,《晨报副刊》1924年5月7日。,杨栋林也是其中之一。不过,碍于师道尊严,杨栋林的爱情攻势比较含蓄。1924年1月12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为其兄代聘家庭教师。应聘者不乏其人⑤1924年1月17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称:“前星期我在日刊上登一代聘家庭教师启事,三日内接洽者已有五六十人,同学们如此热心帮忙,真使我感激不尽。此次所接洽者,我觉得都是良好教师,无奈只能选聘一位,实在有负诸君关切盛情。谨此申谢,并恕我不一一答复了。”杨栋林:《杨栋林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17日。,而杨特意私下将启事寄给韩权华,希望其能就聘,以此增进两人关系。此事后为韩权华同学获悉,不久北京大学就传出两人关系的谣言。杨、韩的暧昧关系让韩权华的追求者不免有些嫉妒,有好事之徒在北京大学厕所张贴启事[5],北京大学学生裴文中更是将此事写成报告文学投稿《东方日报》副刊⑥许君远回忆说:“《东方时报》有一张半新不旧的副刊,北大同学经常投稿。现在已成名的地质学家裴文中以“明华”的笔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在东方副刊上发表,男主角是北大教授杨栋林,女主角就是韩小姐,文章刊出后在校内颇引起一些骚动,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谈论那件事情。”许君远:《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西安: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面对外界传闻,杨栋林心中既忐忑不安,又不无正中下怀之意。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4月26日,杨栋林写信给韩权华,表面看似在澄清谣言,实则试探韩的真实态度。正如署名“起睡”的作者所说:“原信全篇都引外界如何如何的话,作成功自己婚姻的圈套。”[7]
情书事件引发社会热议。有学者认为,杨栋林的书信虽有不检点之处,但“究竟不曾犯了什么法律道德,不能就目为无人格,加以这种过重的惩罚”[5]。还有人从“五四”之后,社交公开、自由恋爱的时代背景出发,质疑公众反应代表了传统势力,并认为连韩权华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新女性也没有太大改变,说明新思潮影响甚微。
但是,在这起情书事件中,鲜有从女生视角的分析,比如在当时环境下情书事件是否本质上对女性构成了骚扰?相反,男性知识精英更关心1922年韩权华等一批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在当时的社会颇开风气之先。社会视她们为新女性,她们也往往以新女性自期。韩权华将书信公之于众,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否又说明相比晚清的女学生,这批“五四”的新女性并没有太大改变,仍然是新教育与旧道德复合品?它将对男女同校、北大自治、社交公开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二、男女同校与北大自治
如前所述,韩权华控诉杨栋林诱惑女生,道德败坏,对男女共同教育产生恶劣影响。其实,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五四”之前,一些保守分子就有类似的担忧。1918年,王卓民在《妇女杂志》发文,明确反对大学男女同校,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男女同校破坏礼法,大学变成青年自由恋爱的试验场。在他看来,青年德性未坚,中国早婚之俗又积重难返,“至大学修业大都已男婚女嫁,即未婚嫁亦多聘定”,“以已有配偶之人,忽焉而耳鬓厮磨,乐数晨夕”,能不见异思迁[8]?
然而这样的忠告,对于急于解决自身婚姻问题的青年学生来说,难免陈腐不堪。他们认为:“人生痛苦,婚姻不良为一大原因,而解除此弊在婚姻自由。欲婚姻自由非男女有公然交际不可,而男女交际以男女同校为最好入手办法。”[9]康白情更是直言不讳:青年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十分堕落,根本的原因“都是没有女朋友奋勉他们慰藉他们所收的恶结果”,“何妨把大学开了女禁,让他们有个挽救堕落的好机会呢?”[10]当时有类似观点的青年学生不在少数。很多学生将男女同校与婚姻革命联系到一起:“现在一般觉悟青年的讨论,已把‘机械式’、‘买卖式’、‘强奸式’的牛马婚姻的丑态暴露出来了。可是觉悟的青年,把他们的约解了,由男子方面提出把婚离了,试问和谁去恋爱?”[11]而男女同校,正好提供了由学堂知己发展为婚姻对象的机会⑦当时新旧女子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有没有到新式学校读书。男性青年学生大都对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女性表示渴慕,甚至不惜离婚或解除婚约,以恢复自由之身。,因此“实行婚姻革命,须先从男女同校做起”[11]。
“五四”之后,社交公开、男女同校渐由舆论鼓吹变成客观现实。1920年春,北京大学招收九名旁听女生。在北京大学的示范作用之下,南京高师等高校相继招收女生。这种风气逐步向下传导,一些中学也陆续实现男女同校。男女同校给青年学生提供了更多自由交往的空间,但是时人很快发现,这只是表面形式的改变,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更谈不上寻找学堂知己[1]。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女生现在为数已不少,但以格于习惯,在校与男同学向无交际,即在教室之内亦复不交一言。不惟男女之间如此,及女同学亦少接洽”[12]。甚至,有些男生抱怨:“照这样做去男生不但不能受伊们底陶冶,而且反被伊们束缚,因为男生从前是活泼泼的不受拘束的,现在偶然碰着伊们,反得低着头,垂着手了。”[13]
男女同校而又不相往来,既反映出青年学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也折射着保守势力施加的无形压力。早在北京大学招收旁听女生不久,教育部就给北京大学发来公函,指示北京大学“国立学校为社会观瞻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需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14]。省议会反对男女同校的提案也不时见诸报端[15][16][17][18][19][20]。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办学者,还是已经同校的男女学生,都不免顾虑重重。由此可以想象,韩权华将杨栋林诱惑女生的罪行公之于众,对北京大学和男女同校造成的冲击⑧尽管北京大学并不是最早男女同校的高校,但时人往往认为北京大学有男女同校开创之功,甚至一些保守势力也视北京大学为男女同学的始作俑者。如江苏省议员朱德恒在反对男女同校的提案中说:“男女合校,为全国极大污点,为人心生死关头,初作俑于北京大学。”见陈望道:《和时代思潮逆流的江苏省议员“禁止男女同校”提案》,《妇女评论》1922年12月13日。。
出于对北京大学的爱护,北京大学教授江绍原首先致函孙伏园,批评《晨报副刊》刊登《一封怪信》。在他看来,团体成员之间的私事“应该私下来解决;私人解决不了,再交团体里负责的人代为解决;如果仍解决不了,才可因为不得已求团体以外的社会公断”[6]。江绍原希望北大自治,此事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得到解决。然而,孙伏园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事件发生之后,北京大学对杨栋林群起而攻之,杨栋林被迫辞职,可见“用‘家法’来解决纠纷,结果也不会比社会的公断更为平允”[6]。孙伏园不满意北京大学对杨栋林的“家法”处置,但平心而论,其在《晨报副刊》刊登韩权华的《一封怪信》,何尝不是向北京大学施压,加重对杨栋林的处罚。
对于孙伏园倒打一耙,江绍原自然不能同意。他提醒孙伏园,此事公开报道对北京大学和男女同学造成的可能影响:“你们不该不知道现在还有许多女子胆小不敢入男女同学的大学。你们不该不知道假使顽固的人得势,女子们将没有大学可入。解决个人的问题,固然要紧;供给人新闻固然也要紧;但最要紧的是拥护大学男女同学制——拥护这个基础还未稳固全国还在那儿观望的男女同学制。”[21]
应当说,江绍原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当时男女同校的大学,闹出这样的风化事件,的确会授人以柄。江绍原担心事件对大学男女同校造成的影响。但是孙伏园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他坚持声称,“韩杨事件与男女同学没有丝毫关系”[21]。同在北京大学教书的周作人随后也加入了这场辩论。他虽同意江绍原处理类似个人私事的程序,但也认为将此事与北京大学关联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他说:“杨先生的罪案只在以教员而向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且发言稍有不检点之处,结果是‘不在北大教书’,这件事便完了,于学校本身有什么关系,难道北大应该因‘失察’而自请议处么?”[5]
周作人和孙伏园想撇清北京大学与杨栋林事件的关系,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正如事件的受害者韩权华控诉的那样,“此等事匪但与权华个人有关,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4]。杨栋林在北京大学给韩权华写情书,事件发生的场所不能忽视。在普通人眼中,北京大学对于此事的确难辞其咎。北京大学之所以同意杨栋林辞职,恐怕也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是较早的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高校。但也正因为这种标杆意义,官方与社会才对它分外关注。面对无形的外界压力,北京大学必须谨小慎微,因此言论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背离。一方面,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积极鼓吹社交公开和自由恋爱;一方面,他们又在真实的男女交往中十分敏感。由此,一方面虽然已经男女同校,另一方面校园中又存在着明显的两性隔离。面对现实的两性禁忌,校方往往从大局出发,态度就更加稳重。这种看似保守的背后,实际是对社会无奈的妥协。这些忧虑冲淡了舆论对这一事件中女性是否被骚扰这样一个权益问题的关注。
三、社交公开与“浮荡少年”
杨栋林向“素不相识”的女生写类似情书,这样的行为不仅可能对北京大学造成冲击和影响,而且不免有“浮荡少年”之嫌。
“浮荡少年”是“五四”后伴随社交公开出现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并不懂‘妇女解放’,‘自由恋爱’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意识中关于这几个名词的观念,大约都同顽固少年一样,以为就是野蛮时代的‘公妻’的意思。于是他们在路上看见女少年,就满口‘妇女解放’,‘自由恋爱’;接着就是些侮辱女子的蛮话,甚或马上加以侮辱女子的举动或状态”。“还有从各处探得女少年名姓,胡乱写情信,信中全作很有情交的话,往往引起女少年学校斥退,家庭禁锢的阴惨。”[22]很多年轻的女性,尤其是女学生,都抱怨受到了这种“浮荡少年”的骚扰[23][24][25][26][27]。
面对陌生男性的搭讪、情书,女生往往既紧张又愤怒。一个女生就向邵力子倾诉说:“我是男女同校里的一个学生,我平素也没有什么好出风头的事情,我不料男同学中竟有人拼命写了许多不能入目的信给我,你说讨厌不讨厌呢?我每次接了他的信,我都置之不理,万不料他却继续地写了许多信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呵!”[28]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位女生选择诉诸媒体。还有女生通过同乡会的力量进行制裁。署名“CW”的女生,就将情书寄到对方同乡会,“不过几天,接著他同乡会的来道歉的信,知道那个写信的著实受了处分,几乎撵出了他的同乡会”[29]。
平情而论,女生的这种反应可以理解。因为在当时保守分子的眼中,男女同校的女生大多有道德污点的嫌疑。署名C.Y.SU的作者谈到地方社会对于女生的观感:“在我们一个县城一个府城的地方里,以社会的人观之,在学校求学的女学生简直没有一个是好人。稍为解放的,其受人指摘愈甚。”[30]为了避免非议,女生往往谨小慎微,但还是不时接到陌生男子的书信⑨比如署名云青的女生就说:“我到吾校虽仅有一年与半载,而收到的五彩情书足有了二百余封,……满笺都是些‘一见销魂’、‘社交公开’与‘恋爱自由’的轻蔑人格的肉麻话。”《男女同学中的女学生(二)》,《妇女杂志》1925年11卷6号。。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往往有口难辩,内心倍受煎熬⑩署名CW的女生就谈到自己接到情书后的反应,她说:“当时我心理异常发恼,以为何以许多女同学,都不遇著这种事,而我独遇著呢?我自信并无足以引起这种‘横逆之来’的行为,何以竟有这种事实的发现呢?”CW:《一年来男女同学的经验》,梅生主编:《妇女年鉴》第一回(下册),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年,第257页。。因为在外界看来,这很可能是苍蝇不叮无缝之蛋⑪甚至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杨云矗抨击浮荡少年,但又认为浮荡少年“所对的‘人’,所处的‘地’,都和解放妇女毫不相干。”其潜台词,受到骚扰的妇女都不是正经人家。参见杨云矗:《“浮荡少年”不能和“妇女解放”并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10日。在韩杨事件中,知识分子费觉天也认为韩权华有诱惑之嫌。他说:“北大女生,就我所知,前后不下百余人,其中每不乏好学深思之士而较□于韩女士者,却为何别人皆无,独韩则有?”转引自奚明:《社评》,《妇女周报》1924年5月28日。。为了自保,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公众和盘托出,通过惩罚对方证明自己的清白。韩权华之所以将杨栋林的书信公之于众,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类似心态。正如杨栋林所说:“韩君文中云‘无谓之语不必声辩’,然昨日之文实系一种声辩,不过借我的信赖作骨子。”[31]
女生通过公众力量实行制裁,对“浮荡少年”的确有震慑之功,但有时也会造成“误伤”。很多青年男子给女生写情书,并非存心侮辱,只不过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爱慕之情。他们在写情书时,往往忐忑不安。比如周姓男子在给同班女生写信时非常惶恐,他说:“你对于这一个忠实愚蠢同学的表示,到底怎样?你能怜其情,谅解他吗?我写到这里,不觉心头乱跳而手颤抖起来,因为我想看了这封信后,不知将以何种态度对我,谅解我呢?或当我一个很坏的人呢?”[28]书信充满哀怜之情,似很难同“浮荡少年”相提并论。然而,接到情书的女生,仍然选择将书信公之报端。
对于女生可能的反应和后果,这些冒昧写去情书的男子大多早有预见。安庆一师学生邱功义写情书时,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我同你竟不相识,且又异性,忽冒昧修问,不能说先生不有所惊异特奇,甚至含羞愤辱,所以首先不得不要求你恳祈你对于我要宽恕点原谅点,施一点哀怜的心思,提一点恻隐的意思……至于你回信与不回信,乃是我第二层目的,不过我对于你一点儿的痴情痴意,你要体恤我,保全我的名誉和人格要紧,这就是我这封信的唯一宗旨。”[32]杨栋林在给韩权华写信时,其实也有这种担心,他在最后再次强调:“此信不要再给人看,并且不要告诉人,否则越发证实了,多惹麻烦。就我个人说,充其量,不过不在北大教书而已。至于你呢,不犯着因此而荒废学业。”[4]表面看似在为韩权华学业考虑,实则为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命运担忧。
如何看待男子给女生冒昧写情书以及女生激烈反应引发的后果?舆论似乎对此观点不一。邵力子忠告青年男子要为对方考虑问题。他说:“男女社交,自然是很正当很平常的事,但我写信给伊,而绝对不管伊将蒙受何种影响;就友谊而言,也不应出此呀!”[33]但这样的劝告并未取得丝毫的效果,以致两年之后邵力子不无愤慨地说:“此种行为在男青年见已成为一种流行病,而女青年的多数因之感受不安;这在我们——言论界——的天职上,决不容许我再缄默了。”“此种不问女同学或他校女学生的意见怎样,而投寄一种‘肉麻当有趣’的信,即是为变态的心理所驱使,其本心不必即为侮辱女性,或竟自认为纯洁的‘求爱’,而其行为终极与浮荡少年相似”[28]。
然而,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此表示理解,认为这是求爱的正常步骤。相反,他们对女生借助公众力量制裁的做法颇有微词⑫比如,署名荷荷的女生在《妇女杂志》上公布了六封写给她的书信,随后就引发了一些异议。有人批评说:“荷荷女士读了六个男同学所给她的信以后,不能尽同学的责任——忠告或劝诫——以为是受到了一种轻侮,就非常忿懑。我们从这一点上看,很足以证明女士,确是一个礼教的忠臣,把男女界限保守得十分坚固的。”夏启钧:《读前号》,《妇女杂志》1922年9卷9号。。在“韩杨事件”中,这种观点也不时浮出水面。费觉天就为杨栋林写情书打抱不平,他说:“假定杨氏所致韩女士之信,是意在恋爱,那这封信也并无不对之处,不但不是不对,并且很光明,很平常,而且丝毫不成问题之事。”[34]对于韩权华公布书信,更是引来一些批评之声。署名“起睡”的作者认为通信求婚,“这是两性间一椿习见的事”,即使是单恋求婚,“被求婚者只消严词拒绝或竟不理,不是无上上策吗?那里会成为社会问题”。在他看来,韩权华“这种态度和这种手段,罪恶浮于杨君的冒失求婚”[7]。《妇女周报》记者奚明也认为韩权华处置此事不免小题大做、张皇失措。他忠告一般青年的女子,“对于无因而至的信,除了置之不理外,不必再有进一步的举动”[35]。一向将男女之事看作“私而又私”的周作人,也痛陈:“我因了这件事得到两样教训,即是多数之不可信以及女性之可畏。”[5]
由上可见,在“韩杨事件”中,以《晨报副刊》《妇女杂志》和《妇女周报》为代表的一批精英知识分子,虽不尽赞同杨栋林冒昧写情书之举,但大都对其遭遇表示同情,这与一般公众的一片讨伐之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眼中,公众是“假道学”,是“少年人维持礼教”,“无一不是昏乱的思想”[5],这不仅说明了公众和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思想的差距,而且从另一个层面透露出这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看待类似问题上的“性别盲区”。
在“韩杨事件”中,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设身处地为韩权华考虑。他们无法体会韩权华面对流言蜚语的压力以及接到杨栋林情书后的内心惶恐。在他们看来,韩权华公布情书是小题大做,甚至直言女性可畏。他们坚持了思想的“正确性”,但却无法理解女性面对此类事件的真实处境。他们的批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事女性的另一种伤害。其实,公布书信,对于韩权华而言也只不过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杨栋林去职之后,韩权华也被迫转学。
与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不同,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一边倒地批评杨栋林。从表面上看,似乎与韩权华达成某种共识,但实际上他们同样缺乏对韩权华内心同情式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事前的流言和事后的讨伐,正是迫使韩权华选择公布情书、自证清白的重要动因。在这点上,由于性别立场的差异,他们对韩权华的伤害恐怕更深。
四、师生恋与单相思
在“韩杨事件”中,让杨栋林饱受苛责的还由于他以教师的身份向学生写情书。在中国传统社会,“天地君亲师”并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关系被包裹在伦理关系之中。尤其是男老师和女学生,受礼教观念的影响,更要求为人师表者有严格的道德操守。清代袁枚不随流俗,广招女弟子,就深受世人诟病。章学诚批评他:“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36]晚清以降,女学兴办,迫于世俗偏见,为减少办学阻力,大多以女子充当女学堂教师⑬如常州粹化女学延聘男教师,遭到官方严厉禁止,要求“速改聘女教习,以归一律而息浮言”。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56页。再如周南女校初创之时,为减少办学阻力,男教师采取“垂帘授课”的方式。参见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更是明确女学堂须用女教员⑭如《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长教习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素有学识、在学堂有经验者充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各种教习管理员)均以品端学优,于教育确有经验之妇人充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66、673页。。后由于师资匮乏,学部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规定:如一时无合格人选,“应由该堂精选年在五十以上、品学俱优之男教习,暂资教授”[37]。由此可见,时人在男教师和女学生关系上谨小慎微的心态。
“五四”之后,社会鼓吹社交公开和自由恋爱。相比以往,男教师和女学生有了更多自由交往的空间,但师生恋爱仍属社会禁忌,这不仅由于双方年龄的差距,更由于它挑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1923年高文蔚娶女学生为妻,就遭到了当地士绅和教育界人士的激烈反对。高文蔚,时任甘肃第三师范学校校长,与张崇贞订有婚约,后张病殁,张家将次女张淑贞许配与高。张淑贞为女师讲习所毕业生,与高文蔚曾有师生关系。因此,地方守旧人士发起“维持纲常名教会”,对高文蔚群起而攻。结婚当日,群众散发传单,誓将高文蔚驱逐出境[38]。还有人连打电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更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39]。高文蔚的老师甘肃学界名流杨汉公对此也愤愤不平,致函《时事新报》,激烈谴责高文蔚。他说:“师徒之谊,在父子兄弟之间,为维持人道尊重师道计,万不可有结婚之事。”[40]
不仅是相对闭塞的甘肃,即使是上海、北京,师生恋也饱受世人非议。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携女友勃拉克来华,上海媒体起初称勃拉克为“罗素夫人”,后获悉“实情”,“始知罗博士与勃女士仅有师弟之情,而无夫妇之关系”[41],特发出更正启事,并致函罗素表示歉意。然而罗素却表示:“前日之误会,余与勃辣克女士均以为无足重轻……盖余与勃辣克女士,除法律上之解释外,其关系与夫妇无异。”[41]这无异等于宣布他与学生勃拉克的事实婚姻。或许是敬其威名,或许因为罗素是外国人,国人并没有拿中国的道德标准在此问题上苛责罗素。然而,私下场合,时人还是对其与女学生结婚持有异议⑮张梓铭回忆说:“记得从前罗素先生带着他的学生勃拉克女士来华讲演,他们公然承认是夫妇,而且自以为经所谓正式结婚的手续为无关重要而不加以注意。当时我所听于我的先生、朋友、学生等的评论,都觉得此事似有不甚妥洽的地方。诚然,罗素先生既没有向他的前一个妇人表示婚约终止,即使他和勃拉克女士的恋爱是如何醇挚,而在他方面却不能不负破坏不成文的恋爱律的责任。然而大家攻击他反不在这一点,而在他不应该以先生的五十老翁和他的学生发生不合社会习惯的恋爱关系。师生如父子,是中国社会里不刊的定论,无怪罗素先生除讲学所得的赞美外,还要带着干犯名分的考语回去。然而罗素先生是外国人,以中国的道德观念去批评他,总觉不甚吻合,所以攻击他的,也就不十分激烈。”张梓铭:《成都的恋爱狱》,《妇女周报》1925年5月24日。。与罗素经历相似的还有鲁迅。鲁迅和许广平未婚同居,社会颇不以为然。成仿吾、冯乃超甚至批评鲁迅“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42](P88)
在师生恋问题上,时人高度敏感,师生之间任何的暧昧都可能成为公众批判的把柄⑯1924至1925年,舒新城在成都高师教书,因与女学生关系亲近,被人检举,遭到通缉,险些丧命。参见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第281-288页。,更不用说老师对学生单相思。在这种情况下,杨栋林冒昧向韩权华写情书,自然不免诱惑之嫌。而事后韩权华的激烈反应,更让杨栋林有口难辩。在韩权华的控诉中,杨栋林道德败坏,为达其目的,甚至不惜隐瞒婚史。杨栋林事先曾把《东方日报》所载《厕所内的婚姻问题》寄给韩权华,其中涂抹数处,后经韩权华比照,知系“他家已经有了妻,有了子”,“作正妻,作姨太太”,“妓女尚从良”等语[4]。韩权华认为这是有意隐瞒。杨栋林后来辩解说:“我涂抹了东方时报上的有些文字,也因为有甚么正妻,姨太,妓女许多言语不成话了,所以特代为涂抹,绝无何等意思。”[31]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公众信服。在公众看来,这无疑更加证实了杨栋林是士林败类,以致北京大学学生批评《晨报副刊》:“为免纠纷起见,许多人名都代以□,尚无不可;但为什么杨栋林的名字也以□代呢?难道如此无人格的人尚不欲令社会认识加以攻击么?”[6]
应当指出,在公众的批判声中,其实夹杂着对知识分子负面形象的想象和情绪宣泄。五四之后,一些大学教授因男女关系而饱受舆论指责。如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凭借经济势力横刀夺爱,山西大学教授潘连茹喜新厌旧毒杀发妻,北京大学教授谭仲逵丧妻三月就与小姨子结婚,东南大学教授贺康诱奸不成逼死女生刘廉彬[43],诸如此类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以致有人指出:“在男女同学的各专门以上学校里——无论私立或国立——常常发现的,并且为男女同学前途上障碍的,并不是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事情,却是教员和学生之间的事情。这种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止一次,不止一校了。”[44]杨栋林情书事件距北京大学教授谭仲逵丧妻新娶仅时隔一年⑰谭仲逵娶小姨子为妻,引发时人有关爱情定则的辩论。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青年均对谭仲逵的行为持有异议。以致晨报副刊编者在按语中说:“不过很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记者:《爱情定则的讨论》,《晨报副刊》1923年5月18日。,加之杨栋林追求的又是北京大学校花,自然北京大学学生愤愤不平。曾因类似问题而身处风口浪尖的谭仲逵为避免牵累,也急忙与杨栋林划清界限⑱杨栋林在给韩权华的信中,提到从谭仲逵处听得两人关系暧昧的一些谣言。信中,谭仲逵语气诙谐。谭认为与其本意相差很大,要求杨栋林立即进行澄清。他在致杨栋林的信中说:“我那天和你所说的话,虽自己亦不能一一详细纪出,但确信全本这个意思说出。不想今日看见晨报副刊《一封怪信》里所纪你和我的谈话,不但与我当时以很庄重的态度向你所讲的实情有些不合,并完全未把我的意思表出。想系因用笔匆促,致有混误。为此敬特声明,并请你即速更正,不胜盼祷。”杨栋林:《杨适夷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4年5月9日。。
在此次情书事件中,杨栋林在道德层面确实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抛开师生关系,杨栋林向素不相识的女生写情书,也有让人非议的地方。《妇女周报》记者奚明指出,杨栋林的错误不在于师生恋,而是由于单相思,不懂自由恋爱的步骤与方法。他说:“师生可以结婚,结婚应有自主,以及自由结婚常须经过书信往返互通情愫,这话原是不错的”,不过,“男女在结婚的历程上所经过的步骤,不是只有一个‘书信往返’:除此以外,还有相识、交谈、互相探访、投赠、旅行、宴会、跳舞,以致交换婚戒、握手、接吻等等……但这些步骤却有亲疏先后之别,并不是随便可以拣一种作为结婚的最初步骤的,否则不免为冒昧、失礼,……对于不认识的女子突然写一封信去和伊恋爱,这种举动即使不能说是对于女子的重大侮辱,但至少不能不说是冒昧或失礼。”[34]奚明打着自由恋爱的大旗,直接跨越师生之间的界限,侃侃而谈恋爱的方法与步骤,但这样的建议对于杨栋林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师道尊严,师生恋爱仍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这就注定了杨栋林只能单相思。
值此之故,当杨栋林写情书希望进一步增进感情的时候,就注定了他将被推上风口浪尖。北京大学学生称情书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5],虽夹杂着嫉妒之火,但的确反映了对杨栋林突破师生伦理道德关系的不满。与学生的义正辞严形成对比,《妇女周报》记者奚明忽略杨栋林的教师身份,大谈对待情书的态度以及自由恋爱的步骤,虽扮演观念守护与引导者角色,但却回避了相对守旧的社会现实⑲对于师生恋问题,上海比北京似乎相对开放。在高文蔚与女学生张淑贞结婚事件上,《时事新报》记者张东荪就致函杨汉公,批评其借外力进行干涉,称:“夫在学校内为师者不得与女性学生有恋爱,此固为天经地义。然出学校以外,若谓对于凡曾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结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论也。”杨汉公、张东荪:《通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4月15日。奚明、起睡等人似乎更进一步,从绝对自由的恋爱出发,直接跨越了校园恋爱的师生身份禁忌。。
五、余论
韩杨事件发生于1924年,此时距“五四”已有五年之久,社交公开、自由恋爱早已喊得震天响,多数的高校也已实现男女同校,为什么一件“可以不成为社会问题的事”会在公众之中引起轩然大波?在“起睡”等人看来,这是因为韩权华处置失当引起社会的无理取闹[7]。孙伏园、周作人等均不满公众的过激反应,认为“教育界充满了法利赛的空气”,“缺少健全的思想与独立的判断”[6]。但是,这里的公众不是一般的民众,大多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这或许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效力,或者说青年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差异。
此次事件,尽管孙伏园、周作人等与青年学生的立场上存在重大分歧,但他们却有着相似的性别盲区。韩权华在公布杨栋林情书的同时,一再表示:“我生平没有不可告人的信,更没有不可告父母的信”,“我在北大将近两年,唯一的目的在乎求学”[4]。这种自证清白的良苦用心,恐怕是这些男性知识分子难以体会的。在孙伏园等人看来,置之不理是处理类似事件的最好态度。他们忽略了女性面对舆论压力的内心惶恐。而青年学生的义愤填膺,同样缺乏对女性面对此类事件的同情式了解。他们对杨栋林的大肆讨伐,恰恰是韩权华必须先发制人、自证清白的最大动因。在对待情书以及自由恋爱的问题上,女性往往比男性要谨慎。她们害怕受到伤害,往往又通过伤害对手以寻求自保。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自由恋爱的难局。
在这场情书风波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杨栋林已经结婚的现实。周作人、孙伏园、奚明等人批评杨栋林冒昧写情书,仅仅是方法与程序上过于草率,似乎并没有否定杨栋林自由恋爱的权利。杨栋林的旧式妻子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缺位状态,由此也折射出周作人等人的性别立场,他们同样缺乏对中国旧式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真实处境的了解。
如前所述,“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主张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和自由恋爱,从某种层面而言,确有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打算。在他们看来,男女同校的校园无疑是寻求校园知己的最佳场所。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想大都打了水漂。礼教的禁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周遭人的生活。他们很难迈出社交公开的大门,大学校园仍是男女分隔的世界,更不用说自由的恋爱。在热情的驱使之下,他们不得不采取“旁门左道”,然而这样的行动不仅冒犯了旧派的礼防,也违背了新文化社交公开的原则,甚至被扣上“浮荡少年”的罪名。他们渴望恋爱,但又不知如何恋爱。他们害怕礼教的眼光,但又不自觉地用礼教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在特定情境下,哪些方式和言辞是不受女生欢迎的,甚至是使女生感到被冒犯和被威胁的。
[1]王印焕.试论民国时期学生自由恋爱的现实困境[J].史学月刊,2006,(11).
[2]陈湘涵.寻觅良伴:近代中国的征婚广告(1912-1949)[D].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9.
[3]杨联芬.五四社交公开运动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A].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十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韩权华.一封怪信[N].晨报副刊,1924-05-07.
[5]陶然,孙伏园.一封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信[N].晨报副刊,1924-05-16.
[6]江绍原,孙伏园.伏园兄我想你错了[N].晨报副刊,1924-05-12.
[7]起睡.两性间一椿习见的事[J].妇女杂志,1924,10(7).
[8]王卓民.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J].妇女杂志,1918,4(5).
[9]徐彦之.男女交际问题杂感[N].晨报,1919-05-04.
[10]康白情.大学宜首开女禁论(续)[N].晨报,1919-05-08.
[11]义璋.男女同校问题的我见[N].民国日报·觉悟,1920-06-01.
[12]野云.北京大学近况谈[N].申报,1921-02-03.
[13]求真.男女同校要怎样才有真价值[N].民国日报·觉悟,1921-10-28.
[14]教育部准大学收女旁听生[N].晨报,1920-04-16.
[15]陈望道.和时代思潮逆流的江苏省议员“禁止男女同校”提案[N].妇女评论,1922-12-13.
[16]顾静一.驳禁止男女同校之提议[N].申报,1922-12-22.
[17]召.各界教育界杂讯:鄂省议员反对中学男女同校[N].申报,1924-07-09.
[18]各界教育界杂讯:鲁省禁止男女同校[N].申报,1924-07-31.
[19]湖南限制男女同学之省令[N].申报,1924-03-11.
[20]薇君.禁止男女同学底上谕[N].民国日报·觉悟,1924-03-24.
[21]江绍原,孙伏园.经你一解释[N].晨报副刊,1924-05-15.
[22]佛突.妇女解放和浮荡少年[N].民国日报·觉悟,1920-08-17.
[23]水梅.又是“浮荡少年”[N].民国日报·觉悟,1921-01-09.
[24]浮荡少年底真相[N].民国日报·觉悟,1921-04-13.
[25]马延乾.通信[N].妇女评论,1921-12-21.
[26]归真.公园和少年[N].晨报副刊,1923-09-18.
[27]峙山.怎样处置河北党[N].天津妇女日报,1924-01-29.
[28]邵力子.社评(二)[N].妇女周报,1923-12-12.
[29]CW.一年来男女同学的经验[A].梅生.妇女年鉴(第一回下册)[M].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
[30]C·Y·SU.女子解放进行的保障[N].晨报,1920-05-08.
[31]杨栋林.杨适夷先生来信[N].晨报副刊,1924-05-09.
[32]道海,力子.浮荡少年与学校专制[N].民国日报·觉悟,1921-09-29.
[33]水梅.又是“浮荡少年”[N].民国日报·觉悟,1921-01-09.
[34]奚明.社评[N].妇女周报,1924-05-28.
[35]奚明.社评[N].妇女周报,1924-05-21.
[36]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7]吴民祥.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独特乐章:清末女子学堂教师之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
[38]高文蔚,张东荪.通讯[N].时事新报·学灯,1923-04-07.
[39]作人.离婚与结婚[N].晨报副刊,1923-04-25.
[40]杨汉公,张东荪.通讯[N].时事新报·学灯,1923-04-15.
[41]本馆与罗素博士之函件[N].申报,1920-10-16.
[42]周海婴.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43]周宁.同乡、媒体和新女性:刘廉彬自杀案再审视[J].妇女研究论丛,2011,(2).
[44]化芙.男女同学前途上的大障碍[N].民国日报·觉悟,1925-05-09.
责任编辑:绘山
Free Social Intercourse,Coeducation and Teacher-student Romances:In 1924,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Yang Dong-lin's Love Letters
ZHOU N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Bengbu 233030,Anhui Province,China)
gender standpoint;love letters;coeducation;free social intercourse;teacher and student romance
s:In May 1924,Peking University"campus Belle"Han Quan-hua went on Morning Supplement to accuse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Yang Dong-lin,of seducing female students,being morally corrupted,and having bad effects on Coeducation.This accusation rapidly ca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 in the public,and attracted the media's attention.Questions were raised regarding how to view Yang Dong-lin's love letters to a female student,and how to judge the impact of this event on Coeducation?Behind the Hubbub,what actually showed wa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gendered views of the'Free Social Intercourse',and'Free Love'.At the time of the campus environment,Free Social Intercourse and Free Love were only an existence"on paper."Traditional ways of thinking and standards of propriety still affect most people's lives.
D669.68
A
1004-2563(2015)03-0066-10
周宁(1978-),男,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妇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