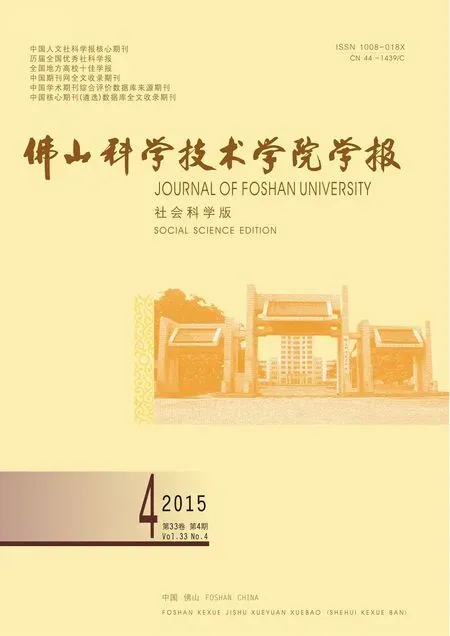清末革命党中越边境起义中的各方考量与博弈
吴智刚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思政部,广东佛山528000)
清末革命党中越边境起义中的各方考量与博弈
吴智刚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思政部,广东佛山528000)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1907年至1908年间,在粤桂滇三省接壤越南边境地区接连策动反清武装起义,中越边境一时风声鹤唳。孙中山原本计划以广东钦廉边境一带为起义发起之地,东西兼顾,并期望能够获得法越殖民当局的支持。但法国政府内部对孙及其南方活动态度并非一致,且各有盘算,清政府也困忧于法国干涉,在措置上多有斟酌,各方博弈,问题尤显复杂。
清末;革命党;中越边境
从光绪三十三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7—1908)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越南为根据地,联合两广游勇,接连在粤桂滇三省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其中的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现广西钦州原属广东)、河口起义,皆短期内集中策动于粤桂滇三省接壤越南的边境地区,“越边革党”一时震动清廷朝野,起义形势为此前之所无。
针对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潮,清政府内部、法国驻越南殖民地当局(法国印度支那殖民政府)、法国巴黎方面各有盘算,身为发动者的孙中山等人也自有考量,以至两年间问题错综复杂。学术界已有研究多从革命史角度出发,对法国政府以及清政府内部的态度举措尚乏深入探讨。对于事件中各方的真实考量以及互动关系的系统考察,将有助于了解事件背后的复杂历史面相。
一、革命党人对起义形势的考量
孙中山联合两广游勇发动起义的计划,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广西匪患正盛之时即已萌生。是年七月,孙在其《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谈到广西游勇会匪发动的“起义”“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指清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孙因此认为只要有足够供应,这些游勇会匪或许能够推翻清朝的统治。[1]255
光绪三十三年(1907),孙中山等人在越南河内甘必大街62号设立领导机关,积极准备指挥粤桂滇三省起义时,孙特别注意吸收西南游勇会党首领,广西三和会首领黄和顺亦是在此间加入同盟会。[2]399后又有梁兰泉(清廷多称其为梁秀春),为广西边防军游击,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失械获罪亡命越南,“纠率无赖,藉名起义”。[3]4555孙虽知梁“作恶多端,负义反噬”,仍表示“河内同志见其久在边防带兵,且多招游勇为咕哩,于军界及会党中颇有势力”,尽管“知其心术不端,而以为才尚可用”,仍招其入会。[1]340其他如黄明堂、关仁甫等人,亦是游勇会党中人,其中鱼龙混杂,孙等人亦早有所觉察,但仍希望利用其在两广云南边境一带影响力,在中越边境一带有所收获。
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策动的滇桂粤起义中心,即孙所称发起之地,正是既为中越接壤之地,又为桂粤两省孔道的钦廉沿边一带。孙指其策略是“在钦廉发起,以东西兼顾,沛然进取”,而后“全军进取南宁府城,以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1]346再“以长江、两湖、东三省之同志方预备响应,拟一齐并进”。[1]344即使此前诸役皆败,孙仍未放弃以钦廉为发起之地的决心。在起义尾声的云南河口之役前,孙还认为“广西、云南两省一起,则钦军无后顾之忧,可以长驱进取,而东路惠潮之义师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响应,如是则南七省之局定矣。”[1]365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滇桂粤大起义,首役却并非起于钦廉,而是广东腹地的潮惠一带。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潮州与惠州先后爆发起义,孙中山指“潮起于东,钦廉应于西,全省风动。尚有数路,次第俱发。当合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联为一气,则粤事机局宏远,大有可为”。[1]336则孙起初当是计划先平定广东,而后徐图向北与向西发展。但随后各处起义并未联为一气,孙的部署也未能实现。在此形势下,孙拟定的起义重心开始转移到钦廉一带。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最终促使孙调整策略,转而向西策动起义。
首先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钦州三那地方爆发人民抗捐斗争,清廷为镇压斗争,先后调集广东巡防营统领郭人漳驻兵钦州,标统赵声率新军驻兵廉州。据冯自由称,郭、赵二人与革命党颇有联络,黄兴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赴郭人漳处运动,[2]376据称郭、赵二人还经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4]157冯指“郭部将弁多克强故交,且信克强至深,即无统领命令,克强亦有指挥之能力也”,冯因此认为“两府(钦州与廉州)兵权渐入革命党掌握,机局之佳为从来所无”。[5]105据刘揆一所著《黄兴传记》称,郭确实答应“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彼必反戈相应”,[6]288有外间消息更指“乱党”在联络郭人漳的同时,还曾投书北海镇总兵李准,[7]若消息属实,则革命党确实在此间竭力争取钦廉驻边武员,冯称“机局之佳为从来所无”,恐也是此时诸革命党人恰逢“机局”,信心倍增的内心写照。
除了钦廉机局甚佳外,法越方面对革命军的态度也影响着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的计划。光绪三十三年(1907)防城起义失败前,孙中山曾致函新加坡侨领张永福等人,指“前月(当指是年五、六月间)广西边界有会党七八十人,谋潜行入边,经清朝官吏知觉,密告法国官吏,称为劫盗,法国官吏捕获之。讯供皆称实欲回广西举义,并非行劫。法国官吏以其犯国事,一概开释,不允交回清朝”,后河内同盟会“聚会员醵资,前后得二千金,代诸人缴齐身税并赡以盘费”,“法兰西人义会亦为之助”。[1]339孙在此没有说明此会党为何人,与革命党人是否有所关联,但极有可能即是孙先前派遣入桂边活动的关仁甫等人。
冯自由后来表示革命党人对桂边军事的经营,始于“丁未(1907)五、六月间”,“总理以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在桂边多年,情形熟悉,特使之分任镇南关、平宜、水口关等处之军事活动,三关均属桂边要隘,尤以镇南关为天险”,而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将领黄瑞兴有所联络,黄答应反正,准备里应外合于桂边大举。后为桂抚张鸣岐侦知而告失败,残部退入越南境内,为法扣押,后为当地华商担保开释。[5]119-120此次桂边大举有可能并未得到孙的同意,只是关乎个人行为,明显证据是同时分任镇南关军事活动的黄和顺,此时尚在廉州赵声军中,积极策划钦廉大举。显然孙等人此时仍着意于广、韶、惠、潮、钦、廉诸军联为一气的原定计划,对关的私自行为自不愿承认,对负责南洋筹款的华侨黄等人更是讳莫如深。
但此次事件之后,孙中山便意识到在中越边境起事或许能够到法国方面协助的可能。防城起义失败,孙在十月即命黄明党准备在广西镇南关起义,[2]416第二年又继续策动钦州上思之役以及云南河口之役,起义地点始终集中在中越沿边一带。孙对法越方面支持革命的憧憬更是不曾消退。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致书张永福,表示“自南关用师,外人颇知我军宗旨,大为信用,此皆足我同志一道者”,强调“法国报纸为我左袒尤力”。[1]353即便是在孙被法越当局驱逐出境后,孙还致函日本记者池亨吉,表示“法国则初表强硬,但如许以重酬,便渐可接受要求”,显然仍然对法越存有幻想。[1]359
持有此种认识的人当不止孙中山,胡汉民后来总结河口起义失败的原因时,称是有革命军败退队伍“窜入越南境,而以其枪弹暗资安南革命党者”,法人因此“大忌中国革命党,使警察四出逮余,将逐出境”。在此之前,“在安南之法国社会党人,先常力为余助,故其舆论甚佳,政府守善意的中立。吾党屡次密购军械,皆不禁”。但河口败退后,“事涉安南革命问题,社会党人不敢有言。而政府官场一切,尽反以前所为矣”。[8]28当是认为法方态度的转变,实因革命党人对起义败退队伍兼管不力,致使有枪弹流入越南革命党人之手,对失去法国的支持不无遗憾之感。
二、法国方面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态度与举措
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对法越方面寄予厚望,法国舆论界也确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赞赏有加。镇南关起义爆发后,有越南法文报纸《东京独立新闻》报道,在起义爆发之前,“风传革命党在谅山贮有巨款,该处居民曾目击驻同登法国军务官兼义勇团司令陶菲于二日率马队视察镇南关时,革命党对之行礼敬,当革命党首领等在同登休息及进飱之际,各人皆与法国武官交换名刺,极为亲善,故对法国绝无恶意”。[5]124另据上海《大公报》称,“此次云南革命军攻破河口,法人称其举动甚为文明,初一日河内法文报云中国革命党此回甚合万国公法,界限分明,既得信防河口将来进步不可限量”。[9]
但正如胡汉民后来所称,对中国革命党人表同情且表支持的,是法国舆论界以及在越的社会党人和部分武官,这并不代表法国巴黎方面也表支持。实则法国巴黎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孙等人对此显然还不曾有充分认识。学者曼荷兰德(J. Kin Munholland)就指出,“自从孙中山转而倾向于从法国政府方面获得协助后,孙的外文著述便开始夸大了法国协助他们的自我意愿”,而法国政府只是将其”置于法国亚洲策略的其中一部分”。[10]78
孙中山与法国方面的联系,并不始于镇南关起义前后,而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法国驻日公使哈马德(Jules Harmand)曾于是年致信给西贡法总督杜美,称此前孙中山要求会晤他,希望从法国方面得到财政、武器方面的援助,甚至希望法国派遣军事顾问。为此孙答应如果革命成功,将在中国南部给予法国某些特权。哈马德向孙表示此时尚不便改变法国对华政策的现状,但答应将其引见给杜美。哈马德同时也将此次会晤报告给了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但据曼荷兰德称,外交部对与孙中山以及其他的中国革命者的任何接触持谨慎的保留态度,部长戴卡(Théophile Delcasse)尤其对援助孙中山表示担忧,认为“通过提供哪怕是极小的援助,来介入与我们殖民地接触的中国省内的动乱是非常危险的”。而法殖民地部给杜美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认识,认为赞助孙是有害的。[10]79继杜美为法总督的保尔·博(Paul Beau)也认为允许革命党人穿越法国领土(指越南)输送武器弹药,会损害法国在中国西南各省的商业利益,表示“对中华帝国的遭受肢解或陷于混乱全然不感兴趣”。[11]55
但是法国方面对孙及其革命党人在中国南方的活动持谨慎的态度,并不代表法国放弃了与孙的接触或者说对孙等革命党人不感兴趣。随后孙中山到达西贡,虽然没有见到杜美,但杜美仍安排了他的一名助手会见了孙,保尔·博(Paul Beau)也曾派其私人秘书会晤孙。美国学者曼荷兰德指此种关系是“朦胧的”(“hazy”),“笼罩在法国亚洲政策与革命者密谋暗光之下”。[10]78但无论是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陆军部、殖民地部还是在西贡的法总督,以及各级武官,对于以孙中山等人在中越边境一带活动所持态度也不尽相同,所思所虑亦有差异。
美国学者巴洛(Jeffrey G. Barlow)指出,“(法国)所有各级官员对于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经常有分歧,最显著的分裂是在总督领导下的印度支那地方行政机关与外交部之间”,而且“军队各级也由于对扩张意见不同而发生分歧”。巴洛还特别指出,“一贯采用更富于扩张和冒险主义色彩的路线”。[11]44巴洛所言或许并非准确,但确实指出法国巴黎政府与驻越南殖民地当局方面在处理中越边境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巴黎方面显然不希望对孙中山问题的处理刺激清政府,但法却在为印度支那殖民地利益有所考虑。保尔·博在向法殖民地部的报告中也纠结的指出:“万一中国要求我们逮捕他(指孙中山),我们必须拒绝。我们冒着给予我们的对手机会,并会招致秘密社会不可调和的仇恨,这将会把他们如今用以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转而指向我们。”[11]55
对于法印方面的此种态度,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曾致电清廷,警告“粤匪以越南为根据地,法政府视为奇货,恐碍大局”,要清廷注意。[12]但相比法印总督方面的模棱两可,部分法国武官则对孙中山等人在南方的活动,尤其是边境起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法国亚洲情报局(the French intelligence machinery in Asia)成立的分支机构中国情报处(the 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Chine, 简称CSR)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系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该情报处主任为殖民地步兵部队布加卑上尉(Captain Boucabeille),布加卑企图将孙中山革命党人的谍报网纳入到其支配之下。在法陆军参谋部档案有关与中国革命党人会晤的报告中,布加卑提到了其对革命党人“创建南方割据国家”的兴趣,尽管此点据称在巴黎方面争议甚大。但孙中山当是接受了布加卑的要求,革命党人胡毅生曾表示,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曾带领一名法国武官赴桂黔川调查形势,并曾在桂林与这名武官同赴新军统带的郭人漳营中。[2]366另据巴洛称,此前经布加卑安排进入南方地区的联络官克劳代尔上尉(Claudel),也曾在一名支持革命党人的香港向导的陪同下,“走遍了接连越南东京的广东、广西边境地区”。[11]61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是年九月法国萨里安内阁下台,原本积极支持殖民地扩张主义,同时支持布加卑的陆军部长艾蒂安没有入阁,布加卑所称的“很可能法国政府会对你的努力感兴趣”的说法,已经不大可能实现。[11]61尽管其后仍有部分法国下级军官与中国革命党人保持密切关系,据称镇南关起义时还有“法国某炮兵大尉”随孙一同等上镇南关炮台。[7]25但这些法国下级军官的作用,已经远远不及前次布加卑及其后台法陆军部部长艾蒂安的影响,而殖民地政府也更倾向于与清廷修复关系,以维持中越边境治安。巴洛也认为,日俄战争期间,“法国的亚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十分明确,即(法国)殖民地部和外交部都不大同情孙中山,对他采取明显的不愿意帮办的态度,只希望对他的活动作某些谨慎的探索”,这些官员“宁愿让中国维持现状,而不愿看到中国内部发生革命的骚乱”[10]87
三、清政府对“革党”边境起事的思考与斟酌
清政府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越南的活动,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惠起义后便有所觉察,滇桂两省督抚尤其对将来可能在两省的边境起事表示担忧。先是广西巡防张鸣岐指“孙党由港兑越二十万金”,并称革弁梁秀春有“博部大元帅名目”,且“自言将往攻滇”,张同时还称,“有杨寿彭黄龙生等皆为会中巨擘,废弁散勇溃兵在越者,二千有零,迟早必发”,请外部速分电滇粤严防。[3]4557有报道指云贵总督锡良在收到外务部饬令后,曾派员至河内、海防密探,但锡指孙等人并未入滇,“惟既遣党分赴广东等处”。[13]
此时中越边氛已经愈发紧张,自防城之役后,九月二十九日军机处电寄两广督抚,对此前张人骏、张鸣岐电奏指“匪徒在越界秘密布置,想必备有军械,且难保无外匪暗中接济,自非寻常土匪可比”一事尤表关注,要二人“预为筹备,扼要屯防,并严饬沿边文武认真截堵,切勿稍涉疏虞”。[6]220此处无论是桂越督抚还是枢廷方面,虽无明言所谓外匪即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不曾指明其中关联,但“自非寻常土匪可比”一说,表明清廷对“肇乱”的利害关系已经有了深刻认识。
随后《叻报》有消息称“防城失守确有革命党从中调度”,[14]更闻“越南那岑那莫一带聚集会党数百人,希图窜越两广云贵各边省,阴谋大举”,[15]镇南关之役后,有报道指政府“知有革命党在内,由越南接济军火,因饬外部与驻京法使商议保护治安之策”。[16]更有论者称,在镇南关占据炮台的清廷所谓“土匪”,“系越境乱党”,[17]清廷也感“越匪有逆首主谋,外人又在暗中庇护,接济军需,进无所得,退亦可归,实为大局之患”。[18]张鸣岐曾向清廷表示:“桂省兵力均注意桂边,如寻常匪徒尚易除灭,近据各处探报,匪数日增,以河内为总巢,惟粤督电称越匪拟先犯桂林,旋窥滇蜀,志不在小,并闻革命党孙逆又在南集款数百万,从中接济,观越南增兵之速,前二说不为无因。”[19]
值得注意的是,自钦州防城之役,到随后的镇南关之役,再到第二年的钦州上思之役,尽管外间皆言之凿凿,指此匪徒与中国革命党人有联系,甚至有法人牵扯其中,但清廷始终不曾明言此种纠葛。即使是镇南关之役中有法国军官随孙中山等人登上镇南关,连法国外交部亦感惊恐之时,[11]76清廷也不曾遽然表态,并对法国援助“革党”有所谴责,此点不得不令外间颇感意外。
镇南关起义后,清廷一方面只是谕令广西巡抚张鸣岐,指“越境股匪虽经官军剿溃出边,而匪情狡黠,梗株未除,仍需严密布置,加意防范”,另指“谅山边境等处复有大股匪徒围攻要隘,实属异常悍顽,亟应严加防范”;[6]224-225另一方面则是经外部电饬出使法国大臣刘式训,向法国政府磋商剿办退入越南的“桂匪”办法,[20]有报道指此间外部曾请法国方面“准我军越界五里,俾得合围”,[21]后又有消息指外部令刘式训与法磋商,“援照对汛章程,协同缉拿”。[22]随后并获得法方承诺,允许“堵截桂边窜匪,并协力捕拿,扣留军械”。[23]
清廷之所以始终不提及越南“革党”与起义“土匪”的联系,很有可能与此前中法关于叛逃入越的梁秀春与李世桂的交涉有关。此次交涉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梁、李二人本是因失械罪,按中法新约有关交犯规定,理应交还,但梁、李却藉名起义,遂生中法有关国事犯问题交涉。清廷当是明白,如指明防城、镇南关诸役窜越之匪党与革命党有所关联,便难以要求法方交回,甚至难以适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中法会巡章程,牵扯甚繁。
如前所述,法国方面此时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仍持两可态度,对此清廷自然需要有所斟酌。直至第二年河口之役后,由于法国有意归咎云贵总督锡良,锡也只能将法“助匪”各情禀明清廷,并指此种情节“尤堪骇异,不敢不以附闻”。外务部才专门为此令刘式训“切商法外部,迅电越督,申明定章,严加防范”。[6]276但外部似乎仍有犹豫,对于锡所指匪首“皆孙汶(指孙中山)大头目”之以及法“纵匪知情”之说法,只要求“派员专查明法官纵容知情各证据,以便照诘”,随后便不见下文。[6]278《中外日报》此间就发现“滇边军事,据外间传述,革命党势焰甚炽,惟枢臣则异常秘密,一切情形概不宣布”[24],亦可见清廷之谨慎,其中当确有隐情。
四、结语
尽管此前由于革命党人、法国政府内部以及清政府对于形势考量各有不同,多方博弈,以至时局颇显诡谲。但自河口之役后,法国方面对于中国革命党人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开始积极与清政府合作,表示“中法友谊素敦,自当竭力相助”。[6]280在具体措置上,法越当局一方面答应清廷有关驱逐孙中山离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开始表示愿意与清廷方面商议中越边境“善后规条”。[25]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经此役失败后,元气大伤,也开始放弃利用会党在滇桂粤边境发动武装起义的方略,转而集中力量运动腹地新军,革命形势亦随之一变。
[1]中山大学历史系, 孙中山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陈锡祺. 孙中山年谱长编: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3]郭廷以. 中法越南交涉档: 第7册[M]. 台北: 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62.
[4]金冲及, 胡绳武. 辛亥革命史稿: 第2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5]冯自由. 革命逸史: 第5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 第3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7]佚名. 乱党投涵[N]. 叻报, 1980-10-30.
[8]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5.
[9]佚名. 法人对于乱党舆论[N]. 大公报, 1908-05-24.
[10]MUNHOLLAND J Kin.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France and Sun Yat-sen, 1900-1908[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2(1).
[11]JEFFREY G Barlow. 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 1900-1908[M]. Berket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1979.
[12]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8-01-02.
[13]佚名. 孙党密谋[N]. 叻报, 1907-07-26.
[14]佚名. 克复布置[N]. 叻报, 1907-10-17.
[15]佚名. 会党起事[N]. 叻报, 1907-12-03.
[16]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7-12-09.
[17]佚名. 论朝廷宜重两广[N]. 中外日报, 1907-12-10.
[18]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8-01-19.
[19]佚名. 电奏防匪[N]. 叻报, 1908-01-18.
[20]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7-12-12.
[21]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7-12-11.
[22]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7-12-14.
[23]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7-12-15.
[24]佚名. 专电[N]. 中外日报, 1908-05-21.
[25]佚名. 紧要新闻[N]. 中外日报, 1908-03-06.
(责任编辑:张惠fszhang99@163.com)
The Thoughts and Struggles between the Various Forces During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Uprising Launched by Revolut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Zhi-ga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Politics,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China)
Revolutionaries led by Sun Yat-sen launched an armed upris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region between 1907-1908,resulting in a time of paranoia Vietnam border.Sun Yat-sen began planning an uprising in Lim Chin region in Guangdong which was near the area around Vietnam to balance things in both directions,and expected to get support from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But the attitude from French government on the Sun’s interior was not the same,and Qing government also worried about the French intervention.There were many considerations between French government and Qing government,which made problem more complicated.
Late Qing Dynasty;revolutionaries;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region
K252
:A
:1008-018X(2015)04-0067-06
2015-03-24
2014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4CLS03);2014年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2014 WQNCX127)
吴智刚(1983-),男,广东丰顺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教师,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