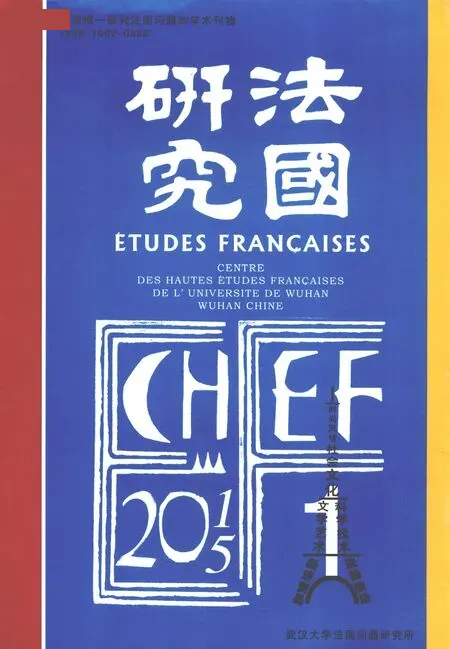解析莫迪亚诺作品中人物的“行走”模式
张 凌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通读莫迪亚诺的作品不难发现,其预设背景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而且以巴黎、日内瓦、伦敦等知名大城市居多,人物的主要活动在人类文明最为集中的城市中,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表现,作者细腻的笔触直接深入到人类精神、人类命运的核心点。而在诸多作品中,莫迪亚诺笔下人物“行走”得如此丰富,有《夜巡》里的逡巡为了逃离,有《来自遗忘的深处》里因背叛而出走,有《儿童更衣室》里在两种身份间的徘徊,有《午夜撞车》里过街时多迈出去的一步,甚至还有《夜草》里的主人公边行走边记录……行走有其目的地,也能毫无目的性,或者在找寻,或者在逃避,或者只是单纯证明自身处于社会之中,仅仅衬托出其存在感。笔者试图从莫迪亚诺的若干文本出发,剖析人物在城市里的“行走”,以达到分析其人物窘境,及其应对的目的。
简单剖析一下“行走”这个词,还原到原文著作中可以是marcher, aller, flâner, errer, fuir等等,它可以是慵懒地闲逛,亦或是漫无目的地踱步,亦或是优雅地拄着拐棍,亦或是匆匆地奔向下一个目的地。在如波德莱尔这样的城市诗人的作品里面,行走于城市里是诗人与城市间最好的互动模式,城市的律动来源于市民的行动,因此成为了诗人激情的最好来源,而错动的不和谐感时常令人感受到城市里面的异变。
人类在城市里面的活动有其目的性, 行走因此常与寻找相关,因个人的某种身份缺失而做出的寻找常常是莫迪亚诺式人物的最大活动目的,人物受制于一种主动或被动地与世隔绝或切断某种关系,他们会因此表现得怀旧或者恐慌。两种情感交织伴随着人物的活动,主动表现出销声匿迹的意向,但是自我消失于人群之外还是人群之内?如同作者,人物们既是城市景观的观察者,也是客观的行走者,他们同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错落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他们又成为了其他观察者的客体,主体与客体的交会转换,是人物身份、性格、命运反复被扭转,被压制的最好体现。下面从几部作品来看人物的行走模式。
《暗店街》-- 行走在社会的一隅
在该作品的封底,有一行文字介绍:这本书里,那些游荡的灵魂闯入了侦探小说的领域①Modiano,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 Ce livre pourrait être l’intrusion des âmes errantes dans le roman policier, Gallimard, 1978.。这里的游荡即一种方式的行走,而且伴随着逃避。这使我们想到,《暗店街》实际上同时写给莫迪亚诺的父亲和哥哥鲁迪。对于父亲的记忆,无不需要重构,是一种逃离的记忆,而对于哥哥的记忆,是一种侦探式的探究,是一种找寻的记忆。所以在《暗店街》作品中,主人公以找寻为出发点,进而转化为游荡者这个身份,游荡在文学作品中常被赋予找寻者的意义,找寻自身的意义。
《暗店街》里大量出现展现城市街道的场景。开篇即以街边的咖啡馆为视角的发端,主人公居伊·罗朗端坐其间,仅以背影示人,时间为某一个不确定的夜晚,身份不详。当然,这里为了点出作品的题目,涉及街道主题,点出人物即将无时不穿行于这陌生昏暗的街道。小说结束时,同样以主人公未尽找寻职责,小女孩哭着离开,作者以问句收篇,难道我们的生命轨迹就那么快就此消散么?用来行走的街道,在这里充当着人物心理的锻造场,除了忧郁伤怀,还有与未知性的最好勾连。人物行走在街道之上,从一个未知走向下一个未知,回望,却了无痕迹。行走的街道,与命运相连,与梦境相连,与梦魇相连。街道在行者看来,空幽、静谧、昏暗,是人物甚至作者心境的最好展现。空幽,表现出作者对父亲的缺失和兄弟的失去的感叹;静谧,表现与过往的决裂和失联;昏暗,表现出二战敌占时期的压抑和所谓失缺身份的恐惧。
《春季之犬》--光影的追随者
在这部略显简短的小说里,作者将人物的初次见面就安排在巴黎的城市中,略显传奇色彩的主人公杨森,以巴黎为背景创作他的影像作品。他自己的鞋子也成为了观察的对象,因为鞋子引领着他走入这片世界。以《1945年7月的巴黎》为名,战后的凋敝、人性的洗礼,都深深地刻画在杨森的相片底板上。他的行走,形式上走出了战争的物质废墟,却走向另一个心灵的废墟。作者再次将失去兄弟的情愫附加到主人公的文学语言里,消失,失去,死亡等极具幻灭色彩的词汇伴随其间。
作者坚信事物的兴起灭亡都注定在世间留有痕迹,即使这样的痕迹是令人不堪重负的压制。杨森以行走着的观察者身份,记录着时间留下的印记,他提醒着时光记录下历史。杨森为了记忆年轻的先行者、抵抗者孟瓦利尔,将其名字镌刻在矿工学校的墙面上,而当这一切不复存在的时候,关于他的记忆留存,也就被抹掉了。主人公的梦境行走,表现出行者如影般的幻境。主人公甚至将自己想象为杨森,不仅打破了自身的存在身份,而且成功融入对方的身份。犹如波德莱尔散文诗里面描述的人群那样,若有所思的孤独的行者能够自如地在自己或者他者之间转换。就如同那些游荡的灵魂,找寻着躯体,然后进入,成为对方。①Baudelaire, Le Spleen de Paris, Les Foules, Gallimard, 2006, p.27.
《朵拉·布吕德》--朝圣者的步履
莫迪亚诺以该犹太小姑娘的名字命名的作品,看似通篇在做所谓的寻找和探究朵拉·布吕德的踪迹,但是结尾处的文字暴露出,作者实际上对寻找没有结果,是满怀欣喜的。也正因此,主人公与她建立起来了某种必然的联系,是存在于跨时间在特定的空间内的勾联。她的存在,增加了主人公的存在感。作者为了建构起小姑娘存在证明的各个方面,甚至增添了许多想象的成份。
孤独的独行者成为了朝圣者,向着旁人无法理解的方向行进。当这段黑暗的历史,其中诸多细节被忽略或者自动被过滤掉时,主人公沿途捡拾起来,甚至珍藏。比如思维布林办公室的人近乎疯狂地在德朗西搜寻犹太人的细节,作者以近乎自虐的方式反复细致地回忆,反复地舔舐伤口,这是一种精神疗法还是自虐倾向?
《地平线》—迈步向曙光
这是莫迪亚诺至今的倒数第二部作品,也是为数不多题名里略带亮色的作品。小说中的行走不可谓不多,有巴黎街头的邂逅,有走向街对面迎接女主人公,有共同前往小诊所,有共同辗转到其它城市……人物反复地辗转就犹如作品的结构一般,反转曲折,往返反复。形式上的凌乱重复,给予读者强烈的压迫感,以至于主人公博斯曼大呼:我累了,我走得够多了,够久了,但是马上感叹感受到一种平静的感觉,似乎回到了过去的某时、某刻、某地②Modiano, L’Horizon, Gallimard, 2012, p. 171.。为什么能反而平静下来?作者没有正面给出答案,而是让博斯曼最终走向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特意留着的书店大门。开放的结尾,给作品增添很多亮色,经过长时间的辗转和找寻,主人公终于非常可能找到远在他乡的玛格丽特。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但给予读者的是更多的遐想和欣慰。
在行走即将实现它的价值,即将完成使命的时刻,作家借用约拿情结,提醒了读者,行走如同找寻,其意义不在行走到哪里,或是找寻到什么,行走在找寻意义的路上,其本身就极具意义。这个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推演,是作者在多年笔耕基础上得出的,是他停下手中笔时的顿悟。
结语
诚然,莫迪亚诺小说作品众多,容易挂一漏万。但论其人物在城市中的生存方式形式--行走,体现出一种所谓的人群联动机制,这是人类活动互相影响交织的结果,是人物性格命运交织的结果。而其中,丰富的变化或者是偶然性,给莫迪亚诺作品频添了一些神秘感,给所谓的人类命运笼罩上一层浓雾。没有了超现实主义者的乐趣,莫迪亚诺的人物只能痛苦地在城市中悬浮漂移着。正如波德莱尔称贡斯当丹·居伊这样完美的“行者”为“现代生活的画家”,他画着这幅城市图景:人们不在自己家里,但是感觉到处都是自己的“家”。这样的描述正好切合着作者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似乎总“无家可归”,在街上游荡,努力在城市里穿梭。但是作者的诸多人物们是真正为了行走而行走么?亦或是他们在找寻自己与其它人物生活、命运的交集,亦或是特意去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的大网,在某个网结上,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亦或是行走本身就是行走的意义所在。
我们将莫迪亚诺笔下的人物视为二十世纪的行吟诗人,二十世纪的城市诗人,他们行走在城市中心,又如同行走在城市边缘,能匿迹于周遭的行人中,也能特立独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呐喊者,磨砺成为一个智慧的思考者,但自始至终终究是位行者,徜徉在作者构建的诗性世界中,领略世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