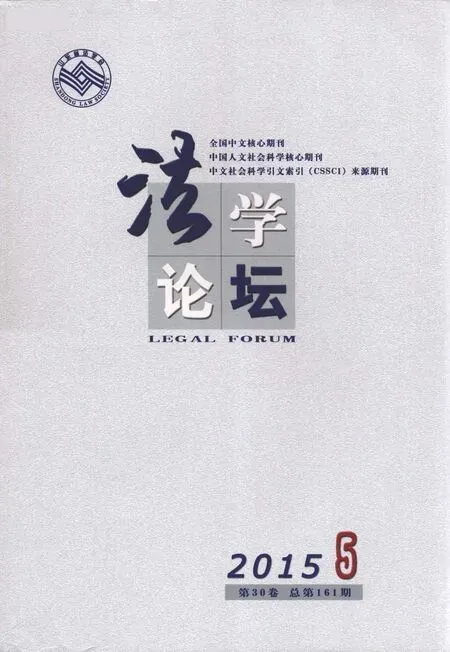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兼论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李 琳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兼论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
李 琳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是以人情往来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新型受贿犯罪类型。随着“感情投资”型受贿罪逐渐成为当前最为常见多发的受贿罪类型,阻碍其司法认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备受争议与批判。出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司法机关与理论界都在事实上采取了对该要件进行实质消解的策略,这是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行为。解决“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应当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这一方案比增设收受礼金罪更具合理性。
感情投资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礼金罪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普通受贿罪包括索取型受贿罪和收受型受贿罪。索取贿赂者只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便可成立受贿罪,而收受贿赂者不仅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还须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才能成立受贿罪。立法为收受型受贿罪增设“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本意在于将“感情投资”和亲友之间馈赠的现象排除于受贿罪之外,*参见熊选国、苗有水:《如何把握受贿罪构成要件之“为他人谋取利益”》,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6日。但随着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行、受贿手段的更新,立法之初被认为属于“单纯收受礼金”、危害性不大不足以入刑的“感情投资”行为却逐步发展为当下最为普遍的权钱交易方式。以往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感情投资”的行为不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而无法构成受贿罪,只能作为违纪行为处理的观念已经逐渐被学界和司法机关所抛弃,如何解决“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
一、受贿犯罪的新类型:“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
近年来,“感情投资”一词在媒体披露的受贿案件中频频出现,不少国家工作人员将其作为权钱交易的主要渠道,以接受馈赠之名聚敛钱财。贵阳市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受贿一案便是典型例证。樊中黔在担任公职的20年间共收受70多名房产开发商上千万元的贿赂,在这70多名开发商中,只有10名左右开发商是针对具体请托事项对樊中黔酬以重金。*参见:《“巨贪”樊中黔庭上最后陈述:“万物无罪,祸在人心”》,载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9/15/c_12572082.htm,2015年5月2日访问。类似案件还有重庆市永川区招投标办原主任戴兵受贿案。*戴兵在7年间受贿千万元,除了逢年过节时工程包工老板们要向他奉上3000元至1万元的“红包”,他的生日更是这些老板们不敢怠慢的日子,生日礼在1万元到几万元。参见:《生日成“进贡日”,办公室变受贿“宝地”——重庆市一招标办主任落马记》,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31/c_1111882931.htm,2015年5月2日访问。另外,与上述收受大额礼金不同,还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只接受小额的“感情投资”,自认为所收财物价值相对较小,不易引人注目。例如临沭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检测中心原主任赵大庆,9年间累计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91360元,在其24起受贿事实中,有22起收受的都是购物卡。*参见:《逢年过节收购物卡,山东一官员受贿9万获刑7年》,载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1/id/1207866.shtml,2015年5月2日访问。
从上述案件事实中,不难发现“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所具有的共性,即行贿人不再针对具体请托事项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或许以财物,而是以人情往来为名长期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礼金”。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行、受贿手段,其现实危害甚至已经超越了即时性权钱交易的常规受贿案件。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感情投资”绝非人情往来。“感情投资”是行为人出于拉近关系、培养感情的考量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财物的行为,由于赠财之时并无具体的请托事项,貌似只是一种单纯的“送礼”和“示好”行为。因此,受贿人往往辩称“感情投资”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并非行贿受贿。诚然,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亲友之间互赠礼物、联络情谊本是传统礼节和风俗的一部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也正因如此,“人情往来”便成为遮掩受贿事实最便宜的借口。行贿者采用各种方式为权钱交易蒙上人情往来的面纱,最常见的便是选择合适的时机送出财物,如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乔迁寿宴、子女升学等,以此为送礼寻找一个正当的借口;另有一种方式是行贿之人以自己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感情纽带为遮掩,他们或是利用既有的远亲、战友、同学、同乡等私人关系,或是以结拜兄弟、认干亲等方式与国家工作人员拉近关系,继而借助这些关系向官员赠送财物。这种打感情牌的方式更具迷惑性,“实践中,只要行贿人和受贿人具有某种远亲或者朋友关系,一般认定为赠予,而不认定为受贿罪。可奇怪的是,总是穷者向富者赠予、无权者向有权者赠予”。*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5页。事实上,双方是否具有亲友关系以及交往历史对于判断“感情投资”的构成并不起决定因素,只能作为一种分析判断的佐证。不管是名目各异的礼金,还是相交多年的亲友,都可能是行为人用以掩饰“感情投资”的“障眼法”,真正的人情往来与“感情投资”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亲友之间的正常馈赠是基于情感,以礼物寄托情谊,双方互有往来。“感情投资”则是“投资者”基于对特定利益的长远打算,对拥有特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长期且单向的“投资”行为,即使出现双方互有往来的情形,也必然存在双方所赠财物价值严重失衡的事实。这种单向“投资”的起始与双方之间利益关系的消长紧密相连,始于对方具有为自己谋利的身份,也会随着对方身份的消失或者贿赂目的的达成而终结。另外,“感情投资”所赠的财物一般都超出了正常馈赠的范围,如上述戴兵受贿案中数万元的生日礼金。2013年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在100名被调查者中,有近6成人参加领导婚宴时所赠礼金的数额超出一般同事间所赠的礼金数额,且高出的数额最高可达10倍,这些礼金与领导的官职和权力大小成正比。*参见戴先任:《份子钱也会涉嫌行贿》,载《法制日报》2013年10月8日。这种高出一般礼金数额的“份子钱”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承载美好祝福的意义,成为官员进行权力寻租或有心之人实施变相行贿的渠道。
2、“感情投资”的本质是行贿受贿。有观点认为,“感情投资”尽管不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但也不足以构成行贿受贿。“在‘感情投资’、‘事后受财’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没有与财物建立起直接的对价关系,使得此类行为虽然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但并未侵犯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在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情况下,其对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和职务行为公正性的危害性较一般受贿行为的危害性要小。”*郝艳兵:《“收受礼金罪”不是口号立法》,载《检察日报》2014年10月13日。依据上述观点,接受“感情投资”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是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因此影响到自己的职务行为,因此不属于受贿。但是,这种理解并没有触及“感情投资”的本质,只是流于表面的解读。虽然行为人在进行“感情投资”时没有提出具体的请托事项,但行为人双方都知晓这种“投资”所期冀的收益并非是培养感情,其真正所图的只是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所掌握的职权。樊中黔就曾以“喂塘子”来形容自己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他是“塘中鱼”,平时被人“喂”,别人有事需要他时就“上钩”帮忙。*参见:《“巨贪”樊中黔庭上最后陈述:“万物无罪,祸在人心”》,载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9/15/c_12572082.htm,2015年5月2日访问。由此可见,“感情投资”是一种刻意将“受财”与“谋利”隔离开来的权钱交易行为,双方在“受财”之时心照不宣,他日“谋利”之时依旧心照不宣。
再者,所谓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基于其职务获取薪资以外的不正当报酬。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基于其职务收受了薪资以外的“灰色收入”,就存在职务行为被置于贿赂的影响之下,进而损害“职务公正性”的危险。*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0页。因此,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感情投资”是为了收买其手中的职权却仍然接受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是国家机关公信力的重要保证,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感情投资”必然会导致国民难以信任其能够始终代表国家利益履行其职务行为。“由于侵害了社会一般人对于公务公正性的信赖,而最终损害到公务的顺利实施这种国家功能,这也正是处罚根据之所在。”*[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
3、“感情投资”的危害不亚于即时性权钱交易。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意欲以手中职权换取财富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接受临时抱佛脚式的权钱交易,转而青睐更加稳妥安全的“感情投资”。近年来,以联络感情为名向国家工作人员赠送礼金的现象呈现出送礼金额大、送礼人数多、送礼名目不断翻新等趋势。在2011年徐州市检察机关查办的行贿案件中,以人情往来为名,将行贿行为和基于亲情、友情的交往馈赠相混淆,以及利用节假日、婚丧特殊时机行贿等“曲线行贿”占到总案件数的79.74%,逐步成为行贿的主要方式。*参见赵阳:《“感情投资”放长线网罗掌控受贿人》,载《法制日报》2013年10月31日。“感情投资”已然成为当下受贿案件中最为常见的行贿手段。
“感情投资”的危害不仅表现在其普遍性上,相对于“一事一报”型受贿案件,“感情投资”型受贿普遍具有行、受贿双方勾结多年,长期不被察觉的现象。因为“感情投资”旨在“放长线钓大鱼”,行、受贿双方在长期“感情投资”经营的过程中结成紧密的团体,前述三个案例中,每一个受贿官员身边都环绕着一个长年固定向其“纳贡”的圈子。这种官商勾结互惠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不仅行贿人懂得“先前投资,日后享福”的道理,受贿人也利用职务便利“投资”于一些发展前景较好的富商,将其作为“潜力股”。*参见赵丽、古芳:《税务系统“感情投资型”权钱交易升温》,载《法治日报》2011年12月19日。双方都期待着能够结成一种彼此信赖且相互依存的权钱交易关系,为此他们一方面会竭力地通过行使职权或给付财物的方式来维护“感情投资”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会合力遮掩这种不法勾当。相较于分次出卖职权的即时性权钱交易,这种官商勾结模式其实是一种彻底将职权奉与金钱驱使的行为,其性质更加恶劣。另外,由于“感情投资”打着人情往来的名义,比之“花钱办事”的行贿更加令国家工作人员难以抵制。尤其是在“感情投资”蔚然成风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在逢年过节之时收受礼金几乎成为了公开的“潜规则”,因此,“感情投资”是腐蚀官员、滋生腐败的“糖衣炮弹”,是我国当前反腐工作所面临的巨大阻碍。
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对受贿罪“谋利”要件的冲击
由于“感情投资”逐步成为一种普遍的权钱交易渠道,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打击“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反腐需求。但由于我国《刑法》为收受型受贿罪设立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使得司法机关对“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认定困难重重。该要件也因此被诟病为掣肘反腐工作的立法缺陷,备受争议与批判。
当前司法实践中,是否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认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关键。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含了承诺、实施、实现三个阶段,行为人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已经构成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认定“承诺”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做出明示的承诺,只要其在明知送礼之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况下仍然收受了财物,就视为其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做出了默示的承诺。在“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的司法认定过程中,有部分案件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即案发之时“投资者”已经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也已经许诺或者实施了为其谋取利益的行为。针对该种情形,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受财”与“谋利”两个要件,司法机关认为应当对其以受贿罪论处,对于受贿数额,应当将历次收受的财物予以累计计算。*参见王玉珏:《受贿罪司法认定的轨迹与趋势》,载《法学》2013年第10期。这类案件中,虽然“受财”与“谋利”之间通常有较长的时间间隔,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实施“谋利”行为,先期接受“感情投资”就具有了权钱交易性质,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对其以受贿罪论处在理论上并无争议。
真正令司法机关感到棘手的是只有“受财”、尚未“谋利”的“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在这类案件中,接受了“感情投资”的国家工作人员既没有实施具体的谋利行为,也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投资者”从未提出过具体的请托事项,甚至连笼统的“关照”之语都没有。基于这样的事实,司法机关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默示承诺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很难将其行为认定为受贿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司法机关可能会根据行、受贿双方的客观身份推定受贿人明知他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继而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例如,丁某在担任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党委书记期间收受了正在承建该医院工程的某建筑公司经理张某给予的人民币50万元。一审和二审人民法院认定丁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有论者针对此案分析道:行贿之时张某虽然暂未说明具体请托事由,但丁某主观上应当预见该请托事项的内容为在张某公司承建的施工建设中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为其谋取一定经济利益。丁某应当预见到这种具体的请托事项却仍然接受张某的贿款,构成日后为张某谋利的默示承诺。*参见何晴:《“感情投资型”受贿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2期。但这种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进行宽泛解读的做法引发了学者的质疑,“往往是只要请托人与受财人之间具有职务上的相关性,例如属于行政上的相对人,再予以照顾等这样十分笼统的请求下,就视为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认定其收受行为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这样一种对具体请托事项的理解,无形之间消解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因而有所不妥。”*陈兴良:《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司法机关在遵循立法与惩治腐败二者之间进退维谷,进则要通过解释从实质上消解“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退则要放弃追诉大批“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在当前泛滥于社会的“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未曾谋利的情形不在少数。司法实践中有开发商对官员进行了十几年的“感情投资”后才提出请托事项,在这样长期的“感情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始终都没有提出具体的请托事项。如果司法机关对此类行为都视为不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而不予追究,便会纵容官员不断地基于其职位聚敛“灰色收入”。社会公众也会因此感到官员不廉洁的行为竟被法律所容许,因而无法信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亦无法信服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尤其是在近年高压反腐的态势之下,公众既对反腐工作充满关注和期待,又因触目惊心的腐败现实而对贪官深恶痛绝,当下的刑事政策取向只能是严密法网,扩大受贿罪的入罪范围。
除了如何解读“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这样的理论争议,“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难以被证明也是困扰司法机关的另一个难题。由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形态各异,“从谋利的受益人看,既包括行贿人自己,也包括应行贿人要求,为与行贿人有关的第三人谋利益;既包括为自然人谋利益,也包括为法人单位谋利益;从谋利的性质上讲,有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也有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所谋利益的内容看,既可以为他人谋取像住房‘工程承包’商品采购等物质性的利益,也可以为他人谋取招生‘招工’提职等非物质性的利益;从谋利的程度上讲,有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实现,有的部分实现,还有的正在为他人谋利尚未实现”,*孙国祥:《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3期。凡此种种,司法机关要收集证据加以证明需要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尤其是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纪要》,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成立标准由“客观实施了谋利行为”提前至“收受财物时承诺为他人谋利”之后,要司法机关对“承诺”拿出证据予以证明更是难上加难。行贿受贿多是在“一对一”的情形下秘密进行,在没有第三人或者录音设施的状况下,要证明行为人有“许诺”的行为只能依赖获取双方行为人的口供。“对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事后并没有实施或没有来得及实施的行为,如果只有行贿人的证词,而收受财物者不承认该许诺应如何认定呢?拿什么来证明有此许诺呢?”*朱建华:《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
具体到“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调查取证还将面临更多障碍。由于“感情投资”案件中“受财”与“谋利”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多则可达三五年,甚至数十年。司法机关要跨越如此漫长的时间差去搜集证据非常困难,“受财”与“谋利”之间的时间跨度越大,行为就越隐蔽,越与其他行为交叉,证据越难固定。*参见范传贵:《“收钱不办事”新型受贿案引发深层讨论》,载《法制日报》2012年5月8日。另外,“感情投资”的行为人双方往往已经结为紧密的利益团体,案发之时双方极有可能已经事先串通好以互相掩护,具有更强的反侦察能力,检察机关想要通过双方供述来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亦非易事。
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之提倡:简论收受礼金罪不应入刑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使得司法机关在认定“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时陷入步履维艰的泥沼之中。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不断冲击着“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同时也促动着立法为回应现实而做出完善。为了彻底解决“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思路被提出:一种是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另一种是在受贿罪之外增设一个收受礼金罪。尽管两种思路都能达到以刑罚规制“感情投资”的目的,但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做法更为可取。“取消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更是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已经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无益,应当尽早予以取消。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可追溯至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现行《刑法》依然为收受型受贿罪保留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者对该要件的解释肯定了该要件仅指代实行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利用职权行为为行贿人办事”。*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该要件的设立初衷即是为了限制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这种提升受贿罪入罪门槛的做法显然有些矫枉过正,不仅使“感情投资”行为游离于受贿罪之外,甚至导致多种显著侵害受贿罪法益的行为亦无法被认定为犯罪。例如,那些收受了他人财物确实意图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尚未着手实施的案件,司法机关只能选择要么以缺乏客观要件为由宣告无罪,要么认定为受贿罪的预备或未遂,两种方法显然都不妥当。*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页。对于另外一些刻意“收钱不办事”,期望以此逃避刑罚的行为人,也因为未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无法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面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立法机关始终未作出任何补救措施。司法机关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去解决实践中的各种燃眉之急。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纪要》,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成立标准由“客观实施了谋利行为”提前至“收钱时承诺为他人谋利”;这种“承诺”不仅包括“明示承诺”,也包括“默示承诺”。该司法解释解决了行为人收受财物后未实施具体谋利行为的受贿犯罪,但依然无法彻底解决受贿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最典型的便是“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由于行贿人没有提出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无法认定受贿人默示承诺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前述丁某受贿案中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受财之时对方连“关照”之语都不曾说的“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例时所运用的裁判理由更是直接根据行、受贿双方的身份地位推定“请托事项”的有无,行贿人即使连笼统的“请托事项”都没有提及,也不影响司法机关对受贿罪的认定。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如是理解与认定,“既是对刑法所规定的客观要素进行了保留,同时又‘虚置’了该要素,或者说大大弱化了该要素的功能,实质上使该要素成为可有可无的表述。”*周光权:《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页。
有观点认为,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后,“司法资源将会严重透支,实务部门难以根据这样的法律规定有效地查办受贿犯罪案件,从而造成法律规范与司法现实之间出现显著裂痕,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刘宪权、谢杰:《贿赂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57页。但随着受贿罪的常见形态转变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等更加隐蔽的受贿行为,司法机关为了追诉受贿犯罪已经不惜变相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该要件所发挥的作用不再是拦截少数危害性不大的权钱交易行为入刑,而是阻碍了大量受贿案件的司法认定,不仅没有节约司法资源,反倒给司法机关在法条理解与司法证明上带来各种难题。目前司法机关通过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宽泛解读而实质消解该要件的行为尽管无奈,但也确属越俎代庖,是一种突破法治底线的危险行为。
同样无奈和危险的是,理论界的学说发展也导致该要件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模糊。“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一经设立,其在构成要件中的性质便引发了理论争议,“这个犯罪构成要件究竟是主观要件(指受贿人的主观想法),还是客观要件(指受贿人为对方办事),在刑法理论上有争论,这反映出立法表述上的模糊性。”*储槐植:《完善贿赂罪立法——兼论“罪刑系列”的立法方法》,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这种争论持续至今,“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两相对峙,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性的结论。随着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体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成为学界共识,“客观要件说”已从早期的“行为说”进化为“许诺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其内容的最低要求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8页。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已经超出了该要件用语的文义“射程”,而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这一要件旨在说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如果脱离这种对价关系,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会使该要件丧失真实含义,从而导致受贿罪范围的不当扩大或不当缩小”。*张明楷:《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换言之,“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字面上的含义与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所收财物是否具有职务关联性并无直接关系,亦即这一要件原本就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相符合。至于与“客观要件说”对立的“主观要件说”,尽管一直坚持应当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行为人的主观要素,但也强调许诺或者答应是这一主观要素的客观显现。如果要证明这一主观要素的存在,就要首先证明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或者是“许诺”这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预备行为,继而推定行为人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目的。这种解释更加远离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本来含义,但落实到具体的司法认定上,又与“许诺说”殊途同归。
事实上,不论是“客观要件说”,抑或是“主观要件说”,“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支持者都在强调对该要件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字面,而要根据刑法教义学的理论对其进行塑造。*参见陈兴良:《新型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以刑事指导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为视角》,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所谓塑造,其实是学者在遵循当前立法的前提之下,只能采用突破立法原意的解释去试图改造该要件本身的不合理。因此,围绕着“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究竟是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的争论对于司法实践并无太大意义,长久以来在理论上一争长短却始终难以自洽的现实也更加印证了该要件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反腐败的司法实践,也给刑法理论带来无解的难题和无益的争论。“造成理论纷争的根源不在于人们对这一要件的理解,而在于这一规定本身。在受贿罪中取消这一要件本身,才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出路。”*朱建华:《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在该要件被取消之后,“感情投资”型受贿罪在司法认定中遇到的障碍将被清扫,也就无需为了解决该问题另设“收受礼金罪”这一独立罪名。先前“收受礼金罪”入刑的消息曾引发媒体热议,最终未被列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原因是“讨论时争议较大,很难区分正常的人情往来与非法收受礼金的区别”。*刘效仁:《收受礼金:人情的归人情,法纪的归法纪》,载《检察日报》2014年11月11日。笔者亦赞同“收受礼金罪”不应入刑的观点。该罪一经设立,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只在刑罚上比受贿罪轻微。*参见杨国栋:《设收受礼金罪须先定收礼标准》,载《法制日报》2014年10月21日。这将导致两种负面效用的发生:第一,如上文所言,无法区分收受礼金罪与正常馈赠的区别。在既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也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情况下,如何将那些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无关,确实基于人情的礼金往来排除在收受礼金罪之外?若以列举的方式将合法情形进行排除,将会导致立法更加繁琐和难以操作,且难保不会出现立法漏洞进而伤及无辜,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私人生活干涉过于严苛;第二,对于那些以赠送礼金为名,实则是进行“感情投资”,意图收买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这样的“礼金”就已经侵犯了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以“收受礼金罪”对其从轻处罚令人难以理解。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感情投资”型案件,司法机关能够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就认定为受贿罪,无法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就认定为刑罚更轻的收受礼金罪。“这究竟是处罚更严厉了,还是司法漏洞更多了?”*舒圣祥:《警惕“收受礼金罪”带来反腐新漏洞》,载《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9月29日。收受礼金罪给了实质上属于行贿受贿的“感情投资”型案件一个减刑的立法依据,将会异化为受贿罪的减刑版,成为一些受贿官员们逃避刑责的又一借口。
判断贿赂犯罪是否成立的标准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否具有职务关联性,基于其职务或职务行为而获得的非法收入便是贿赂,基于情感和礼尚往来而获得的财物便是馈赠。收受礼金罪中的礼金既非正常馈赠,又要与贿赂进行区分,为司法机关认定贿赂犯罪增加了毫无必要的额外负担,使受贿罪的入罪标准更加难以把握。正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所言,事无巨细的刑法规定未必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所谓“界限越多,则难以界定的情况愈多;难以界定的情况愈多,则争论的问题愈多;争论的问题愈多,则法的不安定性愈多”。*[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收受礼金罪模糊了成立受贿罪的界限,对“感情投资”等确属于行贿受贿的收礼行为失之于纵容,对一些并非权钱交易的收礼行为又失之于严苛。尽管国外不乏对于公务员收礼数额的严格规定的立法例,但其目的在于对受贿现象的事先预防,例如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规定政府人员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美元的礼物,新加坡《公务员纪律条例》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金额不得超过50新元,违反这些纪律性规定都不会直接导致刑罚的后果,而是要求公务员首先向相关监察部门申报上缴、或者出资买下。*参见:《收受礼金入刑能否堵住贪腐漏洞》,载http://news.sina.com.cn/c/zg/jpm/2014-09-28/1656281.html,2015年5月2日访问。体现对于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不能仅依靠《刑法》的规定,而是需要一整套的制度体系相互配合,《刑法》坚持从严惩处受贿犯罪的同时也必须要从实质上把握权钱交易的本质,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参见孙国祥:《实施“两高”<意见>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四、“取消论”对于“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司法认定的积极意义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与成立标准将更加清晰,司法机关只需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的财物是否与其职务相关即可。“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受“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阻碍而难以进行司法认定的典型,取消该要件将会对其司法认定产生更加显著的积极意义。
首先,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后,司法机关由于对该要件理解不同而导致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能够得到极大改善。如前所述,当前司法机关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感情投资”,但尚未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也未曾许诺要为他人谋取利益,“投资者”亦从未提出过具体请托事项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理仍然存有争议。尽管实践中存在根据双方客观身份与地位推定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对方有具体请托事项,继而认定其构成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默示承诺的案例,但这并非是普遍做法。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并不一致,宽松的视为正常的人情往来,严厉的视同受贿犯罪,更多的仅作违纪处理了事。同样的行为,不同的性质认定,不同的责任追究,既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也不利于犯罪预防。*参见王琳:《修订“受贿罪”的目标指向应更严厉》,载《天津政法报》2014年10月10日。如果取消了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感情投资”型受贿罪中的被告人将不能以“只是出于人情收受他人财物,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辩解的理由,“感情投资”将因其意在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而被认定为贿赂。
其次,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将会化解因该要件难以被证明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司法实务中认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的难点往往是证明行为人构成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承诺,而对“承诺”的证明通常只能依赖行为人的口供,难以达到《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目前的侦查实践中,受“十二小时现象”影响,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越来越困难,即使获取了口供,其稳定性也很差,出现翻供和前后供述矛盾已是常态,导致侦查质量和效率不高;*参见田玉龙、刘敬新:《贿赂案件侦查之“口供纠结”论——仅围绕目前查处贿赂案件的困惑来阐述》,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3期。随着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权利越来越大,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口供的获取更加举步维艰,*参见孙启亮:《论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由此导致“选择性司法”的发生。一些“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可能由于难以取证而无法受到《刑法》制裁,既不利于惩治受贿犯罪,又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最后,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后,“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变得有法可依,司法机关得以从惩治腐败与遵循立法的选择冲突中解脱出来。针对司法机关在认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超越法条原意的司法解读,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做的后果是司法机关代行了立法机关的职责,变相取消了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显然是违法的;并且强调这一问题虽然暂时被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以及反腐成效所掩盖,但可能对刑事法治造成长久的负面效果。在司法机关为了实现惩罚效果而选择任意突破《刑法》规定的状况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面临着紧迫威胁,这种不良效果不仅局限于受贿罪领域,还将蔓延至其他刑事司法活动中。因为对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违法解读和适用会起到一种恶劣的负面示范效果,会导致司法人员忽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随意突破刑事法治的底线。*参见左坚卫、王帅:《走得太远的司法与理论——对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解读的反思》,载《刑法论丛》2013年第4期。在我国当前刑事法治建设尚处于启航阶段,法治理念尚未广泛深入人心的现况之下,改善和杜绝司法机关此类行为方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概言之,导致“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难以被认定的根源在于立法机关怠于取消受贿罪中给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造成极大困扰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解铃还须系铃人,立法中存在的漏洞只能通过立法机关行使修法的职能方能解决。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与当前从严惩治腐败的刑事政策相左,严重阻碍了司法机关对于受贿犯罪的打击,致使“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等隐性受贿日渐盛行,显然已经成为完善反腐败立法进程中不可容忍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Emotional Investment Bribery——also on Abolishing the Element of “Seeking Benefit for Others”in the Crime of Taking Bribe
Author & unit:LI Lin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China)
Although in the name of human communication,emotional investment bribery is a new kind of taking bribes.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motional investment bribery,the element of “seeking benefit for others”, which blocked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emotional investment bribery, is facing controversy and criticism. Based on the need of Anti-corruption, the element of “seeking benefit for others” has been dispelled both in the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field. This choice is incorrect for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Abolishing the element of “seeking benefit for others”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emotional investment bribery. It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e plan of adding a new crime of accepting presents.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of emotional investmen type; seeking benefit for others; crime of accepting gifts
2015-07-06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成果。
李琳(1988-),女,河南新密人,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392
A
1009-8003(2015)05-0101-08
——由行为属性说转向职务属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