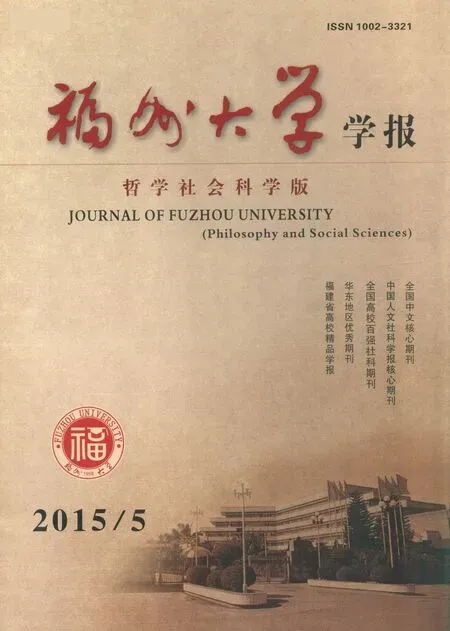论林燿德都市散文创作的“迷宫”特征
林美貌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作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台湾“都市文学”的领军人物,林燿德以其强烈的颠覆姿态和不懈的开创精神对都市文学进行了多元、开放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毕生笔耕不辍从未停止过对都市文学的探索与追求。当80年代的台湾散文依然弥漫着感性和抒情的乡园书写氛围时,林燿德作为“台湾社会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阶段的具有前瞻性时代高度的文学精灵”[1],揭橥都市散文的大旗,创作了《一座城市的身世》《迷宫零件》和《钢铁蝴蝶》三部都市散文集。林燿德自言最钟情的文类是散文,其散文数量虽不及诗歌等其他文类,但他在这一领域的用心程度至少不下于诗歌;加上散文最能表现作家人格主体性和书写广度与深度容易兼及的文体特征,他的都市散文也成了最能一窥其都市文学观和创作企图心的作品。郑明娳指出,都市散文异于以往散文者的地方是作者的观物角度有了大调整,部分台湾文学创作者认真思考文学的课题并非像以前一样重视时间发展顺序性,他们更注意空间性所寓含的意义。他们不仅是单一诉求而是多元考察、关注的不仅是进化还有异化的格局。[2]由郑明娳关于都市散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略概都市散文具有“立体化思考方式、巨视的世界观、辐射式主题”等特点,这些在林燿德都市散文中亦清晰可见。很多论者还从林耀德都市文学观与创作、题材的选取、知性的语言、隐藏叙述者等特色来检视其都市散文,或以“后现代”来看待其散文创作。那么,林耀德是如何运用散文之笔书写并建构他心目中的“都市”呢?在《城市·迷宫·沉默》中,他提到:“八〇年代前期我写作一连串《都市笔记》时,逐渐浮现两个主要意象系统,其一是地图,其二是迷宫;……我的《迷宫零件》(一九九三)是小说、诗或者散文,也即是另一座迷宫,关键处仅是由我导游罢了;只不过导游者隐身其中,成为‘零件’的一部分,那个消失的‘我’是逃避者又是追索者。”[3]指涉其欲以“迷宫”意象贯串其都市散文书写的意图。
“迷宫”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是希腊神话中对结构复杂的建筑物的称谓。关于文化符号概念上的“迷宫”的含义,法国学者雅克阿达利认为,迷宫作为人类思想最古老的一种图示,是世界各民族文明中都存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文化现象和思维模式,迷宫现象存在于人类各种文化类型中。[4]“迷宫”与文学本身有着天然的联系,自古希腊神话、史诗经中世纪文学到20世纪以来的文学,“迷宫”从古至今存在于文学中。现代以前的文学家认为,世界是井然有序的,文学的本质是营造艺术迷宫,通过穿越文学迷宫以追寻深度的生存意义。而现代以降,文学家们发现,世界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破碎的,“迷宫”成了作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多重、同质、混乱等一系列世界经验的表现。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迷宫”成为后现代作家们努力把握混乱,给予经验一种秩序的文学符号。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林燿德同20世纪诸多作家一样,对世界的体认有着浓厚的迷宫体验,他认为“随着人类智识和技术的不断拓展,生命对宇宙的困惑也因而不断蔓延,其间所呈现的各种迷宫意识足以构成一座无与伦比、无限延伸、隐而不显的、与现实颉頏的‘负空间’”[5]。这种迷宫体验的形成既是文化大背景滋养的结果,也与他对都市的体认、创作个性和理论思索分不开,这种体验同时影响了他的散文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
一、迷宫体验:都市和文学交织的双重迷宫
对都市的独有认识和敏锐感知是林燿德对世界迷宫体验的重要基础。林燿德说:“我将‘都市’视为一个主题而不是一个背景;换句话说,我在观念和创作双方面所呈现的‘都市’是一种精神产物而不是一个物理的地点”,“我的关切面是都会生活形态与人文世界的辩证性”。[6]痖弦认为:“在林燿德的观念里,人类进入后工业文明以后,城乡的定义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古时的城市以城墙为界,墙内为城,墙外为乡,一目了然”,“现在的城市概念不但延伸到‘城’外的卫星市镇,甚至在大众传播家的眼睛里,凡是现代科技、现代信息网络笼罩的地方,都是城市的范围,这么说来,所谓现代城市也应该包括乡村在内。”[7]显而易见,在林燿德这里,都市的边界越出了传统的行政地域的区隔,而易以“都市精神”的存在与否作为划分的标准。因此,都市作为一种“主题”,不单单是作为物质空间而存在,同时昭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景观,是为现代经验和现代感觉提供凝聚和发散的场地。他在《都市的儿童》中预言:“他们的故乡不再是一个‘地方’──一些固定的自然景观与原始建材的组合;而是一套“系统”,一套由无数预设概念、随机变数和人工规格造型所架构的庞大精神网络。”在他的散文里,都市是一个由严密的抽象概念、无形机制组成的一套独立运转精神系统,它不再是城/乡二元对立下的产物,而是一个可以同时承载一切,充斥著迷宫式布景的后现代都市。在这个迷宫里布满了各种生命零件、公寓零件、人类零件、地球零件等,而这些零件构成了其都市散文的“迷宫”意象系统。
林燿德的迷宫体验还与其创作个性和对文学的理论思索密不可分。林燿德是一位时刻处于思索与质疑之中的作家,对历史对文学充满怀疑精神。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层递的、互相顛覆的文学理念其实也是一座比一座严密的保险箱……”[8]。他勇于打破权威,突破成规,挑战大师,解构典律,一生都在践行他深具文学史“世代更替”意义的重写台湾文学史的努力,以建构自己世代的“正典”来对抗“保险箱制作商的阴谋”。他自称对都市文学的看法是“在自我实践以及对此一世代的观察中不断修正”[9],带有鲜明的颠覆意味与重构企图。林燿德说,迷宫“不仅是公共意象,也融入我个人的色彩”,“迷阵,自古以来就意味着死与复活双重的象征”。[10]在这里,迷宫暗示着林燿德对文学精神的寻觅,是他身陷文学生存迷阵以求复活的生命形态。他在《迷宫》一文中指出,马奎斯(马尔克斯)历史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中的迷宫“是现实与文本交织而成的神奇地域”,而文学,是为了引导读者从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里寻找这座看得见又看不见,既真且幻的迷宫中留下的足迹。他同时提到了另一座让他感受深刻的迷宫,即波赫士(博尔赫斯)笔下的《歧路花园》,所有人都误会崔朋“隐居起来是为了写小说”和“隐居起来是为了造迷宫”是两桩事,没人想到崔朋说的“写小说”和“造迷宫”就是同一回事,意指自己的文学创作即是“造迷宫”。
综上所述,在林燿德都市散文中,“迷宫”既是都市的象征,也是文学的象征。都市是一座迷宫,文学也是一座迷宫,他所倾心观照的都市文学是都市与文学双重建构的迷宫。后现代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向迷宫挑战》中说:“外在的世界是那么的紊乱,错综复杂,不可捉摸,不啻是一座迷宫。然而作家不可沉浸于客观地记叙外在世界,从而淹没在迷宫中;艺术家应该寻求出路,尽管需要突破一座又一座迷宫。应该向迷宫挑战。”[11]林燿德深陷都市与文学交织而成的迷宫中。他在《迷宫》开篇借马奎斯(马尔克斯)笔下拉丁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如何走出这迷宫”说出了这是他一生都在探寻的一个梦想,一个“从自我出发,向整个时代驰骋、放怀游牧的梦”。[12]
二、迷宫叙事:杂糅手法与晶体结构并置
林燿德自称一直以“异端”的身份在进行散文创作,他秉持“无范本、破章法、解文类,立新意”的创作原则,称其散文是对传统散文艺术定规的质疑以及对自己创作观的具体实践,并套用美国后现代学者伊哈布·哈山的话说:“它表明,一种文化力图理解自己,发现自己在历史上的独特性。”[13]林燿德以一种颠覆的方式拓展散文的边界,以一种解构的姿态来拓宽散文艺术的深度和广度,正是他对这种历史独特性的追求和努力。
(一)杂糅手法——解构中的建构
林燿德散文独特性之一就是他的散文将杂糅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散文的“杂糅”,包含了流派、文类、语言、语体、时间、空间等多个方面的越界与狂欢,从而使杂糅不再是一种局部的、临时的手法,而是一种全局性的策略,以一种与主题并置的方式呈现出来,用以建构都市及其本身错综复杂的迷宫。
流派的杂糅。林燿德认为,“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会互相影响,现代主义者影响了写实主义者,所以很多写实主义者也会受到许多现代主义技巧的影响……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批判,可是,它也是现代主义的继承者,这两者既有互相矛盾批判,也有互相吸收融合的地方”[14],所以文学创作不可以流派自限,而要揉融不同流派,辩证地吸收,才能够取其精华、用其精华,去实验它,让它本土化。以《靓容》为例,文章冷峻理性的风格、存在与异化的主题观照,明显受日本现代派作家安部公房的影响;对都市的“垃圾与罪恶”的描述又用了波德莱尔的笔触,使其笔下的都市有现代文明的一面又充满了“恶之花”的罪恶、颓废气息。其散文《钢铁蝴蝶》《我的兔子们》《房间》等则运用了魔幻写实的叙事技巧。在林燿德的散文里错综着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魔幻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叙事技巧,这种流派的杂糅本身也是一种解构。所以,有学者指出林燿德其实是掉进了“前现代或现代建构的巨大工程”里。[15]
文类的杂糅。林燿德认为“现代小说、现代诗、现代散文,他们可以互相融合、互相交济”,“应该用‘文本’(TEXT)的观念去取代‘文类’的观念。文学是创作,创作可以超越文类”。[16]他打破固有的文类界限,试图广泛化用小说、诗歌等艺术类型中的艺术因素,将诗歌、小说的零件组合到散文中。他的散文有诗的结构、小说的笔法、戏剧的张力。他的散文兼采众体,有对话体、寓言体、语录体等。如《未知次元的门》采用的是寓言体,用象征手法描述了一个独立空中通向未知的门,门是人类心灵世界自我隔绝、自我封闭的具体表征,同时预示着都市文明发展的困局。《城》采用语录体,运用边缘化、零散化、游牧化的言说思维,表现了都市生活的错综复杂,难以挣脱的种种现实。《绿屋酒吧》采用对话体,微具小说的情节感,又显示了诗歌语言的机智隽永。
语言的杂糅。林燿德散文的“杂糅”也体现在其充满感觉和想象的杂糅性散文语言。他同时是一位热情多才的学者,对历史、地理、文学、神话、哲学、艺术等均有涉猎,在他的散文中,不同时空、不各学科和不同风格的语言有机融合,往往在一篇散文中杂糅了凝缩跳跃的诗化语言、穿越时空的幻思语言和科学与文学有机融合的知性语言。如《铜梦》以“铜”为中心意象,追寻亘古蛮荒的人类文化发展史,古代与现代彼此渗透,穿越时空的幻思语言收放自如,体现了对人类文化的宏观审视。文中既有充满象征意义,敏锐而精确、细腻而跳跃的诗化语言,又有科学用语和专门术语,把许多概念和名词与文学进行有机的整合,如“龄式碳酸铜”,“他是人类自古已知的元素:原子序29,原子量63.546,在摄氏1083度时开始溶解,到达2595度时开始沸腾。”这样的杂糅性语言在《鱼梦》《希腊》《音乐》等篇数众多的散文中俯拾皆是。
林燿德高超的杂糅艺术得力于他新世代科技整合的知识结构和其对中外文学的长期浸淫,更得益于他极为自由开阔、不拘一格的创作心灵。他散文中的杂糅艺术象征了他眼中复杂的社会现实。其散文用杂糅的艺术手法,通过不同文化元素和形式的融合,在混杂相交的地带生成多力抗衡的文化空间,在解构中建构了散文文本深刻复杂的内涵。
(二)晶体结构——无序中的秩序
林燿德散文独特性还表现在他对结构的高度重视和自觉性的刻意经营,他说:“我作品中模糊的地方在于结构之间一个奇异的转换,不在语言本身。”[17]郑明娳也认为,林燿德散文的结构,实验性更高,部分作品呈现解构的处理。[18]他常常采取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结构,由若干短章拼接,以一种支离破碎的表面无序来表现后工业都市破碎的人生体验。如《城》字数不到三千由24小章节构成,片段式的章节结构趋于跳跃性,各章节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看似无序其实有着他形成的秩序即都市主题。这种散文结构具有多面性、立体性和散发性,呈现一种“晶体式结构”。[19]卡尔维诺用《看不见的城市》来解释这种晶体结构,他说:“(城市)这个形象像晶体那样有许多面,每段文章都能占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或主从关系。它又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20]这种晶体结构正契合了林燿德的都市“多棱镜”视角,除了一些短篇,像《希腊》《行踪的歧义》《紫色的警句》《房间》《靓容》《颜色》《鱼梦》等多数散文,均是片断缀辑的结构,一篇文章容纳若干互不相关或互相挂钩短章,没有了传统散文中的逻辑性、连续性、确定性,但都笼罩在同一主题观照下。这种晶体结构也可视为迷宫意象的一种转喻,“透过对书写对象的层层剥除,多层次的申述,旨在营造迷宫情状之余,亦暗藏一股走出迷宫的盼望。”[21]正如圣福德·斯克瑞伯纳·阿莫斯所言:“一个作家的语言会创造性的完成于各种有价值的结构中。”[22]林燿德试图以这种晶体结构去挖掘“都市”这个意象开放、多元,多种意义阐释的可能,展现其都市散文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和文本空间的开放性。
作为文体实验家,林燿德强调作家的创造力,一种“包含了丰富想象空间的创造力,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充满想象空间而使我们走出教条、走向世界的创造力”[23],以杂糅手法和晶体结构并置为主要特征的“迷宫叙事”正是这种创作力的最佳注脚。当然,作为一种文学尝试,林燿德都市散文颠覆读者长久以来对散文风格的软性期待,自然常常超越常人的接受能力。诚如郑明娳所言,林燿德散文是非“可口可乐”式的缺少作者的自我情感表露并以沉闷、肃穆、冷静为基调,因此不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在阅读林燿德散文过程中,读者常常会感到无法突破、无法抵达的苦恼。我想,这也正是其散文“迷宫”的特质,也是林燿德的睿智之处。
三、迷宫意象: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交错
林燿德用诗人的眼,借助种种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意象来突显都市的本质,是其散文的重要书写策略。他在“真实—想象”中书写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交错而成的各种都市意象,通过瓦解都市意象进行都市符征的深层探索,在散文意象再塑上常常是写实与象征交织,显示出其散文意象的特色。
我说到做到,第二天早晨我给周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林业局报到了,周书记在电话中笑哈哈地说,小孙啊,你这就对了嘛,好好干,你可是前程无量啊!我没有答他的话,而是尽快找到有关文件,又请人事部门的领导喝了一餐酒、洗了桑拿、找了小姐按摩,最后把颖春安排进了民政局。
(一)都市空间意象:现代都市的混乱与无序
最能代表都市空间的意象莫过于摩天大厦,“有两座连体婴儿似的大厦才刚完工,象征着文明的庞然大物,如两枚暗黑色的火箭矗立夜空,没有灯火,也没有人烟。埃及的人面狮身不正是如此地坐在沙漠上么?”[24]一方面,林燿德惊叹于都市文明和现代建筑的美好 ,另一方面,却同样看到文明背后的废墟景象——工地上“钢筋、废料和工人留下的泛黃汗衫四处散置,华丽大厦诞生前的情景,竟是如此接近废墟;其实人生的至欢与至悲,看来也是相仿的,高潮中饱欲的面容和哭泣的脸孔又有什么不同?”(《工地》)。如果说高楼大厦象征着人类的文明与理性,那么都市的地下世界则象征着人类的潜意识和黑暗思想。都市的下水道系统是沟鼠们的“地下都市”,可怕的是,它也可能是“人类所有黑暗的思想和性情”地底投影或隐匿之所。人类的黑暗思想和性情会“像数以百万计的丑恶鼠群继续潜伏在都市的底层”。而“思想和疯狂带来的瘟疫,又比生物带来的灾难要可怕多少倍,几场导源于狭隘形态和地域扩张理念的战祸,曾经成功地渡过鼠疫所无法穿越的山岳和海洋,摧毁无数善良的都市以及爱”(《九百万只老鼠》)。在繁华的都市里还有不明区域的“巷弄”,而且“不明区域是一种绝症、一种不死的恶魔,她已经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人间。人类投下无数财产和冒险家、宗教家的生命,好不容易在广邈的沙漠和冰原上涂去这条脚注,回头却发觉,不明区域竟然又出现在我们最熟悉的都市里头,并且超越地理、深及心理的层面”(《幻戏记》)。林燿德散文中摩天大厦与工地、“地下都市”、都市与巷弄等都市差异空间意象,交错着都市人所蕴含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空间,揭示了在都市中交织着文明与无明、希望与失望、理性与谬性交错的混乱与无序。
(二)都市器物意象:都市人的失落与孤寂
最能代表现代都市生活特征的是都市器物。《迷宫零件》卷二《公寓零件》以及《钢铁蝴蝶》卷七《自动贩卖机》集中观照了有代表性的都市器物意象,如果汁机、冷气机、洗衣机、电视机、点唱机、答录机、传真机、终端机、自动贩卖机等。现代资讯文明带来的崭新的资讯结构,在资讯网络控制下,人的生活逐渐被机器控制,人自身也成为偌大程序中的一个小零件。林燿德通过这些具体的都市生活器物意象,揭示了在信息社会里,随着各种智能机器的不断被创造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所代替,人们面对毫无感情的机器产生失落与孤寂感。《答录机》中写到:“每当我听到电话另一端的电话答录机播出主任留话,就仿佛看到了对方所拥有的那枚纸人空无一物的脸庞,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所拥有的那枚纸人,不禁为他空洞而寂寞的身世滴下眼泪来。”电子媒介可以将封闭的物理空间串联起来,实现超时空的人际交流;也可以关闭媒介渠道,使咫尺成为天涯,甚至可以无限设置屏障,使简单的人际交流困难重重。冰冷的机器映照了人心的麻木,《自动贩卖机》里都市中到处是步行匆匆、人情淡薄、不再思考的人群。“这个世界中的子民,若非相互拥有足以压沉一枚肺的误解,便是不相干到底”(《城》)。“孤寂,孤寂是都市人共通的命运,每个人都像是瀚海中形单影双的明驼,项上驼铃和着一个个身陷的脚印叮当响起……”(《靓容》)。林燿德从事物每个微小的细节出发来试图描述和表现都市,他对现代都市器物的思考,已经深入到主体性和人类生活世界的重建层面。
(三)寓言式意象——都市人的异化与迷惘
林燿德散文中除了表现都市空间和生活的符号式意象外,还通过寓言式意象表现对现代都市人命运的思索。如《钢铁蝴蝶》卷三《大师制造者》集中表现了对都市人行为和生存状态的关注。《搜集者》中都市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在不停地收集各种证件,都市人异化成了证件的搜集者这一符号。《宠物K》中的宠物K实际上指涉人类正像宠物K一样时时面临着既要被抉择又要自我抉择的困境。《W的化妆》揭示了在崇尚包装的都市,人也成了包装品。《幻戏记》以“我”为家中的白猫H找一只黑猫为伴结果失败的情节揭示了处于现代焦虑中的人类为摆脱困境进行着艰难的努力。现代都市改变了现代生命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颠覆现代人传统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在这种背景下,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就像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
在都市这座复杂的迷宫里,都市的物理空间与都市人的心理空间交错成为复杂的迷宫意象,真实与虚幻充斥着都市人的心灵观感,人们面对无法走出的迷惘不断提出问题,并且不断探索。最大的迷宫不是地图上的不明区域,而存在于人们最深的心里,人类迷失于自己所建造的迷宫中,无法自拔,这就是都市人的真实写照,也是林燿德散文“迷宫”意象系统的意义所在。
林燿德在多年散文创作的轨迹上,贯穿以“迷宫”意象来挖掘散文文本可能展开的复杂空间,并将都市思维推进生存层面和世界观层面,展现了散文多样化的图景,也将台湾都市散文推进到新的高度。林燿德以都市散文这座文字迷宫向现实的迷宫挑战,他认为“作家应该是一盏灯,他要照亮别人,照亮前面的路”[25]。走入迷宫,是为了走出迷宫,如果都市是一座迷宫,林燿德是以散文文本建构的这座迷宫给予都市一个出口;如果未来文学的走向是一座迷宫,林燿德则是以自己的对传统散文艺术定规的质疑和具体的创作实践给予这座迷宫一个出口,而这正是林燿德对当代散文的贡献。
注释:
[1]朱双一:《近20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2]郑明娳:《八〇年代台湾散文创作特色》,《时代之风——当代文学入门》,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第181-239页。
[3][5][6][10][13][23]林燿德:《〈城市·迷宫·沉默〉跋》,《钢铁蝴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3,293,292,293,294,294 页。
[4]雅克阿达利:《智慧之路(论迷宫)》,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7]林燿德这句话找不到出处,可能是来自痖弦和他的对话。痖弦在为林氏的散文集《一座城市的身世》写的序文《在城市里成长──林燿德散文作品印象》中透露,在应允为该书作序后,与林氏曾做过两次面对面的讨论,合起来是五、六个小时的长谈。参见该书第11、14页。
[8]林燿德:《迷宫零件》自序《如何对抗保险箱制作商的阴谋》,台北:联经出版社,1993年。
[9]林燿德:《都市:文学变迁的新坐标》,《重组的星空》,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
[11]吕同六:《现实中的童话 童话中的现实——〈卡尔维诺文集〉序》,吕同六、张洁主编:《卡尔维诺文集:意大利童话(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12]林燿德:《重组的星空——林燿德评论选》自序,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
[14][16][25]李 笙:《新观念新思考新方向——与林燿德文学对话》,《诗华日报》1994年8月21日。
[15]王浩威:《伟大的兽——林燿德文学理论的建构》,《联合文学》第12卷第5期,1996年,第61页。
[17]亚弦:《在城市里成长——林燿德散文作品印象》,《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年,第19-20页。
[18]郑明娳:《林燿德论》,《现代散文纵横论》,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19]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归纳了两种文学生命中的几何形式,即“晶体”和“火焰”。并将自己的作品归为“晶体派”作品。所谓“晶体派”文学作品,即是说文学作品像一个晶体一样,有着“精确的晶面和折射光线的能力”。
[20]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见吕同六、张洁主编:《卡尔维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58页。
[21]王文仁:《迷宫顽童——林燿德都市散文初探》,台湾第六届南区五校中国文学系研究生论文研讨会论文。
[22]圣福德·斯克瑞伯纳·阿莫斯:《结构主义、语言和文学》,《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58页。
[24]林燿德:《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