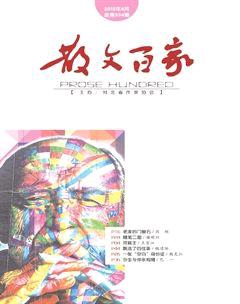买得青山种好茶
●罗光成
茶叶,一种名叫茶的叶子,一种让人宁静、给人温情的叶子。
有时也想,在那遥远得一派混沌漫漶的往古,这种名字叫茶、既不能果腹又无法蔽寒的叶子,是通过怎样的路数,进入人的视野,触动人的心灵,积淀为一个民族生生不变的味蕾基因?!一茶二饭,粗茶淡饭,茶饭不思,饭后茶余……除了这名字叫茶的叶子,世上还有哪一种叶子能够与“饭”——一个古老民族集体意识中至高无上的“天”,链接成一个个如此大俗大雅、难拆难分的语词,在人类的信息库里,流传千年,熠熠生辉?!
始祖神农,从五千年时光的幕后,踌躇而出。嘴唇翕动,传导给我们人类最初的秘密往事。
那时,人类还很幼小,还是大自然一个十分脆弱的孩子。洪水猛兽、山崩地陷,还有无尽的病痛瘟疫,都对人类露出狰狞的脸。始祖独自越岭翻山,遍尝百草,只为找到救人病痛的世间良药。一次,始祖被毒蝎咬伤。就在始祖昏迷奄奄的时候,一枚幽香的叶子,从树梢飘落始祖嘴边。始祖把这片叶子舔进嘴里咀嚼起来——这是始祖辨明药理的习惯动作。叶子嚼烂了,始祖的眼又睁开了。醒来的始祖,突然悟到自己“身处草木中”,就把这枚让自己起死回生的叶子叫做了“茶”……
一月的江南,是可以下雪的日子了。
只是不明白,一路无雪,平地的雪,怎么都跑到了仙寓山上。
怎么都跑到了这仙寓山上,裹拥着一垅垅、一排排、一簇簇、一层层名叫雾里清的茶树,把这冬天里的仙寓山,装扮成了一个穿着海魂衫青春勃发的春风少年?
是因为这座海拔千米的山谷深泉幽,卓荦世外;
是因为这座满植茶树的山流翠滴绿,遍地含硒?
垒瓦砾为灶,拾松枝为柴,化积雪为水,横原木为座。
一场最为原生的茶道,在遍植茶树的仙寓山顶,缓缓而庄严地演绎。
时间,也为此放慢了脚步,让我偷出一些闲暇,坐看风起云生。
松烟袅袅,氲向时间的深处,把散落的过往一一追问。
母亲挎着竹篮,我牵着母亲的衣袂,到茅山头的郑妈家去摘茶。郑妈家住在波浪一样圆缓起伏的山坡上,山坡上长着黑黑的松树,青青的藤蔓,还有五颜六色、数不尽、也叫不出名的野花。门前的一块空地上,亮绿的茶树、逐花的蜂蝶,把郑妈家的草房土院,幻映成梦中的童话。母亲与郑妈,隔着一棵茶树,面对面蹲下,手指在嫩绿欲滴的叶尖上翻飞。阳光斜斜,从一片高高盛开的云朵背后,裹拥春风,凭空倾泻,洒向母亲和郑妈,还有一棵一棵的茶树。母亲和郑妈,也不知为什么有趣的事咯咯咯咯笑个不停,笑得春风都在茶树边驻足侧耳、徘徊不前。我与郑妈家的小楠子,骑着竹竿,在土院里嬉闹追逐,打虎上山……太阳落到西边的山后休息了,月亮从东边的树林里钻出来了,星星移开白天害怕太阳刺射而蒙在脸上的双手,一个一个对着我们张开了晶亮的眼。我牵着母亲的衣袂,母亲挎着的竹篮一路飘散清幽的茶香。郑妈,小楠子,还有郑妈家喜欢翘绕着尾巴的小花狗,跟着我们相送。相送到很远很远,相送到母亲一遍遍劝他们早点往回,相送到望得见山下我们小镇的灯火,郑妈,小楠子,还有郑妈家喜欢翘绕着尾巴的小花狗,才在母亲又一遍“你们回吧”的劝说中,恋恋不舍地回转身,走向银盘一样斜斜悬在天庭的月亮……
七八个十六七岁的上海下放女知青,阿拉侬哇,像一群金色的凤凰,从天而降,栖落到我们大队的茶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领袖的话语,醒目在墙上,太阳一样鲜红、温暖。白天,姑娘们哼着撩人心魄的歌谣,在茶园无尽的碧波里,松土,除草,施肥,采撷;夜晚,老场长在场房门前挂一盏如昼的汽灯,姑娘们与邻队赶来的男女知青说起自创的快板,跳起自编的舞蹈,唱起“公社是朵向阳花,社员就是那藤上的瓜……”,让远近赶来的乡民,听得忘乎所以,看得如醉如痴。这时的茶园,就像不见边际的大海;这时的场院,就像一艘热闹在夜的大海上的航船,那如昼的汽灯,就高高挂在航船的桅杆上。节目演完了,乡民们像一群陶醉的仙人称赞着姑娘们的歌舞,咂摸着空气里的茶香,在夜空下墨绿的茶海里,踏浪而行,凌波而去……
雪水,在铁锅里沸滚;松枝,在灶洞里涅槃。拈一撮茶叶,放入青花瓷盏;舀一瓢煮沸的雪水,沿着盏边慢慢注入。一盏雪水雾里青茶,就这样氤氲在了眼前。叶子在盏中静静舒展、在水中悠然浮沉,就像在慢慢打开我们心中不能免俗的尘世纠结,就像在演绎我们人生无法避免的过往未来。尘世纠结打开了,过往未来破译了。淤塞的心胸,慢慢就被这样的茶,又一次洗涤得天空一样清明澄碧。流浪的心灵,慢慢就被这样的茶,又一次召唤回失落的家园。心重新放下了,心重新安顿了。重新放下、重新安顿的心,在这一刻,就又把我们重新变回到那个纯粹的、远离世俗功利的、在草木之间怡然无挂的大自然的孩子。
茶叶,一种名叫茶的叶子,一种让人宁静、给人温情的叶子。如果我拥有一亩青山,我一定要亲手把你遍植。不为别的,只为你对人类的恩情,只为做个与草木相依的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