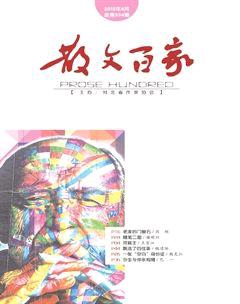今生与你永相随
●巴 一
1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恰恰是这句话,阐释了我的文学梦想和追求。
是啊,我的立项,我的梦想,我的追求,我的人生奋斗足迹,无不源于对文学的痴迷与热爱。散文,虽不是我文学梦想的唯一表达方式,但却是我倾诉性情和心声使用最多的载体。散文,成就了我的文学梦;散文,最真情、最直率地表达了我对事业、对爱情、对人生的感悟。在我的散文世界里,裸露着我对真善美的褒扬和向往,坦诚着我对假丑恶的唾弃和诅咒。乡村、城市,我热爱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往往在我的散文中才鲜活地从往事的记忆里栩栩如生地再现……
因此,我热爱散文,自然更热爱心中那个高手如林、名家璀璨的组织——中国散文学会。
我为自己至今还不是中国散文学会的会员而遗憾,我在为自己争取早一天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而勤奋写作着。
我常常安慰自己,虽不是中国散文学会的会员,但却得到了她很多次的帮助和恩惠。参加由他们组织的笔会,得到学会老师们的帮助,并且多次获得由学会颁发的散文奖等等。这一切无不标志着中国散文学会对我散文成就的鼓励和肯定。
2
我是1989年从安徽太和县文联辞职到重庆的。
在重庆打工的日子里,举目无亲的我四处碰壁,穷困到即便在看完电影后就睡在电影院台阶上的时候,我也没有绝望,没有后悔当初离乡背井的选择。文学青年的梦永远是七彩缤纷、瑰丽多姿的,文学青年的梦永远是越挫越勇、永不言败的。我把每一天的酸辣苦涩写成了散文,多则两三千字,少则三四百字,不为发表,只为愁绪排遣,只为自我劝慰,只为一塌糊涂的情感倾泻……
几年之后,我匆匆的行囊中,装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纸张组合而成的文稿。在手提箱里陪我走南闯北,陪我从重庆到安徽,又从老家拎回重庆。沉甸甸的文字,像沉甸甸的金条,我爱惜她们胜过金条的分量。甘苦寸心知呵!这种感觉兴许是这世界上只有热爱文学的人才有的啊!
火车上,我钻在硬座车厢座位下,睡躺着,回味着我文字里记录的一切,嘴角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微笑。有时,坐在火车餐厅的茶座上,取出我的手稿,重读文字时,热泪盈眶。尽管周围很多人误认为我读失恋情书而悲痛欲绝,我全然不在乎他们诧异的目光,独自徜徉在我自己构筑的散文世界里……
文字,驱走了我的独处和寂寞。入夜时分,有的人跳舞去了,有的人泡茶馆去了,有的人打麻将去了,我却坐在桌前,读我步行二十几华里到重庆解放碑书店买来的文学书籍。为了节省一元钱的公交车费,我常常在周日上午从两路口步行去解放碑新华书店里看书、买书。尽管囊中羞涩,尽管打工的日子艰辛难熬,每当静坐桌前时,心间涌来的却是幸福感。读书时,联想起对未来的憧憬,我的全身热血奔涌,自信自强的力量常常撞击着我的灵魂……
3
在一次商业活动的年会上,我偶然结识了重庆散文学会的常务副会长邢秀玲老师。我称呼她“邢会长”,她却连连摆手说:“我是副会长,傅德岷老师才是会长。”像是电影里走失的小战士终于找到党组织一样亲切,我把我这些年在重庆的酸辣苦甜、对文学的热爱与痴迷,一股脑儿地向邢大姐诉说着,宛如一个可怜兮兮的祥林嫂,宛如一个苦大仇深的苦孩子,无遮无掩地向她倾吐着。邢大姐修养极好,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诉说,平静地问道:“这些故事和感受是其他作者所没有的资源啊。你完全可以把它写出来,我们《西南经济报》副刊需要你这些文章。”
我惊喜地回答她:“我都已写出来了,能发表吗?”
邢大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安慰我说:我也是外乡人,我当然理解外乡人在重庆的不容易了。你先把稿子拿来我看看,再说能不能发表,好吗?”
像一个沙漠中的跋涉者望见了绿洲,我的心被希望与梦想撞击着。
自从认识邢大姐之后,我经常往她的报社跑。她编辑部里的几位老师,从相识到相知,我和他们都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于中绳高大的侠客形象,满腹经纶、气宇轩昂,是一位让人见一眼就难忘的美男子。刘显平女士被邢大姐称为小刘,典型的重庆美女。我的稿子被她勾画得圈圈点点,每一个错别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她都认真给予斧正。张慧,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秀外慧中,谦逊的微笑,给人以亲近随和的美感。帅哥钟斌是一位小老弟,在办公室里面很少说话,英俊儒雅,只管埋头干活,很少谈及与稿子无关的事情……
这些人的面孔,至今美好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感激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编发了我的稿子。
当一篇篇心血之作变成了铅字,要当一名作家的梦想在我心间潜滋暗长着。
邢秀玲大姐介绍我认识了重庆散文学会的傅德岷会长,认识了学会里的杨大矛、万龙生、孙善齐、许大立等老师们……我的散文作品陆续在杨大矛老师的《联合参考报》、万龙生老师的《重庆日报》副刊、许大立老师的《重庆晚报》副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
4
因为我的户口不在重庆,重庆散文学会破例吸纳我为会员,并且担任常务副会长。散文学会像一所学校,让我在这里学会了谦虚和上进;散文学会像一所医院,让我在这里没有了狂妄和躁动。学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比我的文学成就大,都比我资历深。他们对我这个外乡人并不排斥,而且特别友好和亲近。渐渐地,我在重庆文学界有了知名度。我深知,这都是散文学会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结识了这么多朋友,让我在重庆有了温暖的依靠。恰恰是这些朋友,在我的商业活动中又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是一家医药企业的推销员,我的职责是联系购买单位、推销药品。有几家医院,根本做不进去业务,老板找到我,再三吩咐,一定要攻下这几家大医院。为了不让老板失望,我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什么好的促销招数来。一天晚上,我把散文学会的几位老师邀请到一起吃火锅,问他们有没有熟人可以打通关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终于使我茅塞顿开。对啊,我是散文学会的会员,为什么不利用我自身的条件优势去和那些推销员竞争呢?
凭着重庆散文学会会员证,我走进了一家家医院,采访他们,以散文的形式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他们的感人事迹。当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后,喝彩声、祝贺声让医院院长们大喜望外。
常常是这个时候,我拿着报纸和杂志,去找他们推销药品。兴许是我的真诚和才华打动了他们,兴许是他们看在文学的份上,给了我一个合作的机会,不到一年时间,老板交代我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至今,让我愧疚的是,《重庆日报》在副刊的头条发表了我写的散文《渴望理解》后,文中的主角遭到了所在单位同事的反感,他们找到报社、找到副刊部主任万龙生纠缠,责问万老师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给万老师带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麻烦,万龙生老师没有责怪我,而是鼓励我说:“继续写下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没有错。”
万龙生老师是一名学富五车的诗人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在一次散文学会的聚会上,他为我写了一首诗,并慷慨激昂地现场朗诵。其中有两句我至今记忆犹新:“日竞锱珠利,夜来书雅文。”——这是对我的赞美,更是对我的期望。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巴一散文选》在散文学会老师的帮助下出版了。散文学会的老师们鼓励我说:“你的写作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你完全可以把眼光放得再高一些、再远一些。”他们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底气。
2002年第五期的《十月》上,发表了我的三万多字的长篇散文《故乡在晚风中》。2003年第一期的《当代》上,发表了我的长篇散文《漂在重庆》。《故乡在晚风中》获得了“老舍散文奖”。《漂在重庆》获得了“重庆文学奖”,并被收入中国散文学会主编的年度散文选,重庆电视台根据这篇散文拍摄了同名电视剧。
中国散文学会组织的首届“全国亲情散文大赛”,我的散文《爱上空姐》获得了“一等奖”。正是在这个颁奖大会上,我认识了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周明等老师们。从此以后,我和周明老师成了电话里的好朋友。在他的引荐下,我结识了一大批全国的著名散文家。
视野开阔了,我对自己比以前更有信心了。当我被录取到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的时候,恰恰在这个班里又认识了中国散文学会秘书长红孩先生。《大家》文学期刊要发表一组我的散文,责编电话里告诉我,一定要请一位散文评论家写一篇评论文章。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红孩时,他没有拒绝,而是很客气地告诉我说:“你的作品我熟悉,大多与你的故乡有关,以前我读过几篇,所以,让我给你写评论,你算找对人了。”红孩的话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差一点掉下来。真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散文学会的人都是那么友善,都是那么和蔼可亲。
在网上看到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冰心散文奖”征文启示后,我把我的一篇散文《心灵深处的特别鸣谢》发给了《中国散文报》。没想到《中国散文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出来,并获得了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奖。从济南领奖回来,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重庆晨报》纷纷前来采访我,一时间,让我应接不暇。
有一天晚上,邢秀玲大姐打电话给我,向我祝贺,并约我以散文学会的名义为我设宴庆功。遗憾的是,我在安徽正忙着生意上的事情,没能赶回去。电话里,我一直在向邢大姐致歉,邢大姐没有责怪我,而是笑呵呵地说:“你现在名气大了、成就大了,别忘了当初重庆散文学会对你的帮助就好了。”
邢大姐的话一直萦回在我的耳际,我心里酸疼极了。
是啊,这么多年,我参加过重庆散文学会的活动吗?我给予过重庆散文学会什么回报呢?
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人啊,要知道感恩,千万不能忘了在困难时期帮助过你的人。”
那么,我自己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