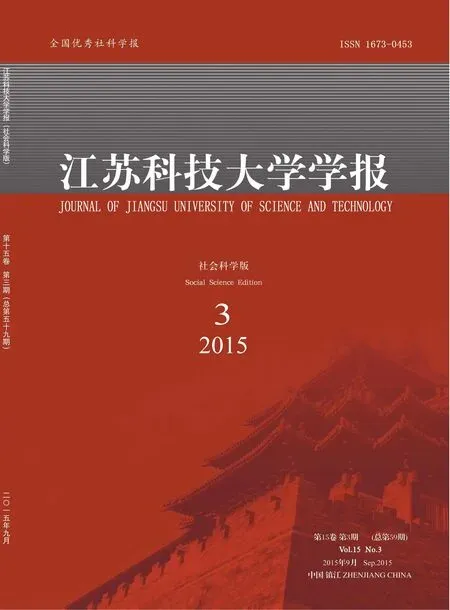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学视野下的文学观念与文学风貌
张永刚,单 辉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法律学院,江苏镇江 212003)
中国古典诗学视野下的文学观念与文学风貌
张永刚,单 辉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法律学院,江苏镇江 212003)
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经数千年,留给后世极为璀璨的文学遗产。综观百年来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国学界为了遵从西方权力话语而放弃民族话语,套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束缚了整个20世纪的文学研究。如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重新建构中国古典诗学学科体系?在宏观视野下,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解读文本,客观陈述和理论思辨结合,从心理学、哲学层面观照文学观念与文学风貌: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早在2 500年前已由孔子所揭橥,孔子道德化、政治化、哲学化的文学观念使后世文学作品包含了丰富内涵,呈现了“文以载道”“文质彬彬”“善美中和”等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风貌。
中国古典诗学;文学观念;文学风貌
中国古典诗学创作意识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演进过程。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同,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各类文学史著作都有意识或无意识体现了这一点。一直以来,在阐述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时,我们通常关注社会历史大环境对文学风貌的影响,而忽视文学产生的最深层次原因,即文学是作家心灵情感投影的产物。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它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由于忽略了对文人心灵的开掘,因此对文学的理解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透彻。在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文人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基本趋同,然而文学风貌迥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谈到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推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2]这些优秀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是各各不同的鲜活的文人之魂,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够超越时空界限而名垂千古。笔者将传统文学观念分为道德、政治、哲学三个层面。我国古人有所谓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3]1088三个层面是互为表里的,并不是独立于彼此之外的。但为了表述的需要,笔者将其与文学风貌的关系分别予以论之。
一、文学道德观念与文学风貌
我国古人非常重视道德的内在自律,崇尚有德之人。人们所认为的圣贤之人多是以道德为标准衡量的。传说中三皇五帝均为有德之君,备受后人称颂。孔子曾总结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舜有五臣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乎沟洫。”(《论语·泰伯》)[4]83-84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德的推崇可谓渊源已久。由于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所推崇的“惟德是依”思想便主宰了历代文人的头脑,在文学创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道德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肇端于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一)政治化的伦理——孔子及儒家的文学道德观念
儒家的所谓“内圣外王”,是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相表里的结果。孔子作为儒家的先师,倡道德教化之先河。孔门四科以“德行”为首,在谈及弟子的特长时,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4]110孔子以德行为四科之首并非偶然,是由孔子的政治观所决定的。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4]11。在孔子看来,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德治。因此,孔子所谓“德”已不是简单的伦理道德之“德”,而是进一步升华的产物。孔子对季康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4]129可见,孔子谈论德行,首先是从仕进的角度出发的。进而孔子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4]146(《论语·宪问》)的论点,这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孟子人化地理解儒家文学典籍,在回答公孙丑“何为知言”的问题时,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道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5]62
“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学的最大特征,亦是儒家思维的基本方式。由孔子的重人道,到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6]1915的天道观,及至宋儒张载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7]65张载主张穷理尽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完成人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其后,二程将天道归纳为理:“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二程遗书》卷22上)[8]138朱熹则提出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9]3377的理本论哲学思想。孔子而下,延续到朱熹,道德观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论题,其发展脉络也是非常清楚的。
(二)道势之争——文学道德观念的主旋律
文人的道德观念以儒家的道德观为内核,体现了对道德的不懈追求和维护,形成了卫道的立场和原道精神。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文人无疑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并不甘于寂寞。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4]82为了实现儒家理想,他们甚至不惜“舍生取义”。对于道统的维护成为历代文人处世的准则。孟子首先提出了“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5]303,荀子发出了“从道不从君”的呼吁,表明了道统至高的地位(《荀子·臣道》)[10]131。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却提出了“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韩非·人主》)[11]1102,从“势”的角度来反对道统。道与势的冲突,体现了文人在社会发生变革时期道德观念上的变化。但是在与“势”的抗衡中,“道”通常成了维护“势”的道德说教,于是文人所谓的“道”就给人一种假道学的感觉,以至于在历代都有很多文学作品批判封建的伪道学。“道”与“势”之争遂造就文学上“文”“道”之争的传统。
(三)文以载道——文学道德观念下的文学风貌
“文”“道”之争是文学史上永恒的话题,正如郭绍虞所说:“从前一般人的文学观似乎都以道为中心,在中国全部文学批评史上彻头彻尾,都不外文与道关系之讨论。”[12]170孔子最早的“述而不作”,试图恢复周礼隆盛的局面,可以说是遵守道统的先师。汉以前,道为文人立身之本,乐道而忘势成为主流。汉代大一统以后,文人感到了现实的巨大压力,“劝百而讽一”的汉赋成了统治阶级美化统治的政治范本。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文与道逐渐着上了文学本身的色彩。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道在圣人那里得到了统一。另外,刘勰指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13]68文道关系也就成了文章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倡导“文以明道”,对文与道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实际上是要在三代两汉古文基础上建立一种与“道”合一的新的文学语言和文体。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14]176北宋是文道关系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郭绍虞认为:“宋人风气好立门户以为党争,所以即于文论之分歧亦俨然有党派色彩。当时有洛、蜀二党互相攻讦,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苏轼为魁,而洛党正可为道学家的代表,蜀党亦正可为古文家的代表。盖在于此时,道学家建立他们的道统而古文家亦建立他们的文统。”[12]172南宋朱熹以后,理学成为官方的主要哲学形态,“文以载道”逐渐成了文学观念的主导。伴随着“文”与“道”关系的争论,文学风貌体现为文学形式和内容上的异同。汉大赋和六朝绮丽的文学是“文胜质”的体现。宋代以学问为诗,则是“文以载道”最为典型的代表。
二、文学政治观念与文学风貌
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的政治观念更是直接左右了文学创作的主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文人积极入世,其政治心态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然而也有不屑与俗世同流合污的行为。在不同时期,文人在政治观念上的变化,使他们的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一)学优则仕——孔子及儒家的文学政治观念
文学与政治似乎有解不开的结,这一渊源从孔子便已肇端。在孔门四科中,“政事”排在“德行”和“言语”之后,位列第三,足见孔子对政事的重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孔门四科,都是孔子从仕进角度予以考虑的。子夏提出的“学而优则仕”,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归纳和总结,也是对孔子社会政治理想的肯定。孔子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他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德治思想,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4]137孔子力图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脩》)[4]28不仅他自己积极入世,他还以其德治思想教育弟子:“政,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4]129“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4]136要求弟子从政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在他的教育下,很多弟子相继出仕,子路更是以身殉职。而当冉求违背孔子的思想帮助季氏积聚财富、祸起萧墙时,孔子愤而斥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4]115。对于德行较高的弟子,孔子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4]54可见,其“学优则仕”的政治观仍然是以德行为先导的,并且一直植根于后世文人的头脑之中。
(二)穷达之间——文学政治观念的主旋律
儒家热心于政治,开了后世文人积极入世之先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以说是对历代文人政治观念最为恰切的概括。然而,文人从政并不是一番坦途。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普遍采用镇压和怀柔两种手段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多数时候,文人无疑是政治的牺牲品。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用世而争鸣不已。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文人第一次深刻体验了政治的残酷性。韩非子文学有害于法治的思想悖逆了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韩非子·五蠹》)[11]1042,“是故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11]922。这就从文学功用上对文学进行了根本否定。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就了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由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文学与政治便逐渐趋向融合。对于文学的认识,其内核是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并且始终左右着历代的文学观念。对于文学的功用,由于政治的变化则出现了争执。文人在其地位上升与下降中寻求迎合政治的文学功用。
(三)文质之辩——文学政治观念下的文学风貌
当文学与政治逐渐趋向融合时,文学便走向了自觉的状态,文人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孔子的“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已经涉及到“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孔子的文学观念融合了儒家的人文教化政治理念,奠定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础。至于韩非则从政治上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做了完全否定。韩非在论“文”与“质”的关系时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韩非子·解老》)[11]278韩非对文做了否定,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政治观。后世遂围绕“文”与“质”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汉代“文质和谐”的文学观在先秦伦理政治文质观之后向文学性进了一步,体现了文学走向自觉的征兆。这是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联系的,文人的政治观念出现与政治的统一。魏晋时代,出现了“重质轻文”的倾向。“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形式主义成了当时的主流风气。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当时南方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南朝君主倡导形式主义文风相契合的。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文心雕龙·情采》)[13]274刘勰的这一文质观完成了从政治伦理化向文艺美学化的过渡,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陈子昂倡导“风雅”和“兴骨”,文质相融、情韵兼胜的创作理论开了盛唐气象的先声。中唐白居易弘扬儒家传统的政教诗学,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文质观[15]2792,深化了文质的范畴。至韩愈将道统论渗入了文质观:“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胜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柳冕《答荆南裴尚书》)[16]2372韩愈揭示了重质轻文的倾向,宋代程朱把这种道统文质论发挥到了极致。为历代所推崇的宏大的盛唐气象,是这一文学观念影响下的产物。由此,唐型文化也成为一种最为典型的政治文化。而与之相反,历代衰亡的末世之音多体现了文人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文学风貌。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强烈悲剧色彩。
三、文学哲学观念与文学风貌
立言不朽,是中国历代文人共同的理想,决定了文人的心态始终是积极的。但由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政治融合,导致文学观念带上某种功利化色彩,从而使文学观念的纯洁性打了折扣。
(一)善美中和——孔子及儒家的文学哲学观念
“文学”这一概念最早由孔子所提出,为孔门四科之一。孔子所说的“文学”,“应是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而非文章博学”[17],体现了早期文学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合生态。因此,孔子的文学观带上了伦理政治功用色彩。孔子评价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脩》)[4]33。孔子论《诗》以中和为美,他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脩》)[4]30孔子还评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4]11孔子的这些思想后来发展为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8]650“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与“中和之美”相联系的。《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达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8]691于民认为:“春秋末期主张美善统一、文质统一的观点,经孔子总结和发展之后,为儒家一些代表人物所继承,成为整个封建时期审美评价的主流。”[19]为孔子所揭橥的文学观念由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确立了文学观念的正统地位,影响着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
(二)立言不朽——文学哲学观念的主旋律
“立言不朽”至少是春秋就有的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3]1088,一直为后世文人所推崇。司马迁的垂文自见以求不朽,几乎是文人达成的普遍共识。如何使文章传世而不磨灭,汉人认为必须是迎合为政教服务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不朽。对于如汉赋那样文辞华艳、于世无补的作品,不能发挥政教的作用,难以达到不朽。王充《论衡·佚文》云:“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恩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20]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1]158这体现了文人高扬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所重视的文章是与政治教化相联系的,他说:“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21]159因此,他评价建安七子的文章,唯推徐干为一家之言,可以不朽:“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21]159曹丕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较为普遍的观点。如王粲在《荆州文学记官志》云:“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22]3能够达到不朽的作品必须是符合政教的作品,这成了封建时代文人的普遍共识,由此决定了文学观念上的功利性。
(三)中和之美——文学哲学观念下的文学风貌
“温柔敦厚”的诗教体现的是“中和之美”的文学观念,它渗透了历代文人所尊奉的中庸理学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论语·雍也》)[4]54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指出:“在中国美学史上达到了善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最根本和最广大的意义上达到美的境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23],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和哲学观在中国古典审美观念中必然表现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系统提出诗乐“中和之美”的是荀子,《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也。”[10]4在中和成为儒家政治美、道德美基础上,将其引入诗乐的审美范畴,给后世诗学观念以极大影响。董仲舒对“中和”有详尽的论述:“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道》)[24]这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提出了中和思想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盾,两难得而俱售也。”[13]266朱熹以心性体用论来阐释中和:“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似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汩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与张钦夫》)[9]1290元代戏曲家钟嗣成将中和之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录鬼簿》:“歌曲词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自有乐章以来,得乎名者止于此。”[25]这体现了中和之美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哲学观念都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学观念与文学风貌产生了深远影响。套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是难以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学观念与文学风貌作出准确阐释的。
[1] 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
[2] 袁世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35.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8]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1] 张觉.韩非子译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2]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 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
[14]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5] 朱金城.白居易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 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J].孔子研究,1998(2):19-25.
[18]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9] 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156.
[20]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15.
[2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2] 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4.
[24] 阎丽.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292.
[25] 钟嗣成.录鬼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04.
(责任编辑:喻世华)
Literature Concept and Styl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ZHANGYonggang,SHANHui
(School of hu manities and law,Zhenj iang College,Zhenj iang Jiangsu 212003,China)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leaving future generations a very bright literary heritage.Looking at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for hundred years,we find that Chinese scholars give up their ow n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order to co m ply with the discourse of western power.They apply concepts of m 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to establish their ow n disciplinary system,w hich affects the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20th century.How do we reexa mine the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construct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At the macro perspective,fro m a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by studying literature concepts and style and using the positivist approach to interpret texts with objective statement and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we think that Confucius reveal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early as 2,500 years ago and Confucian m oralized,politicized and philosophized literature concepts make later literary works contain rich connotation.Their literary style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Literature for m oral instruction”,“Gentleness”,“Goodness,Moderation,Beauty and Harm ony”is very different fro m that of the West.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literary concept;literary sty le
I026文献标示码:A
1673-0453(2015)03-0010-06
2015-06-22
张永刚(1977—),男,山东枣庄人,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