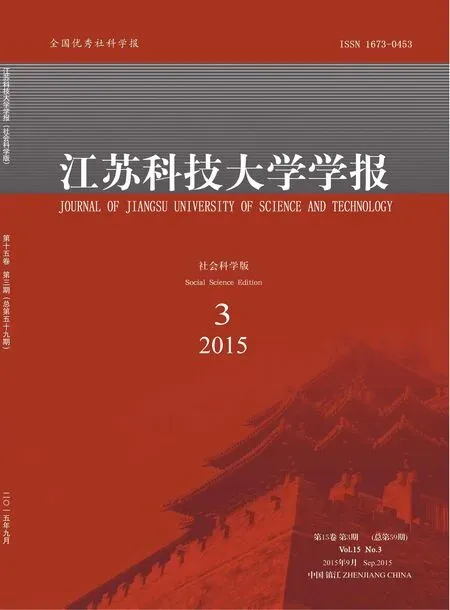对英汉作格句的顺应性考察
张小红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对英汉作格句的顺应性考察
张小红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言说并非都是意识参与的结果,有时言说者虽然作出了一定的言语行为,但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参与,甚至不清楚自己话语的内容、动机或意图等,而仅仅是一种下意识的顺应。顺应是交际需要,更是交际结果,是为了适应语境要求而作出的必要选择,不管这些选择的意识参与程度如何,也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最终结果都是快速消除语用紧迫感,解除语境压力。S受+V作是一种多层面隐喻,既是对人类知觉体验的隐喻,也是对人类本能的隐喻,更是对言说者个人语用紧迫感的隐喻。S受+V作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语境适应性,但很多情况下其生成却不是缘于某种语言策略,而仅仅只是一种下意识的顺应行为。
作格;下意识;顺应性;语用紧迫感
英语和汉语的作格句(S受+V作)有许多相似之处,最突出的是它们特殊的结构特征和信息序列特征。与及物句(S+V+O)相比,英、汉作格句(S受+V作)的结构通常只有两个组成部分,非常“轻便”,容易成为日常交际中顺应性言语选择对象。英、汉作格句的主语都是外致行为的作用对象,而不是实施者,象征着“受损”。如此的信息序列特征表明言说者有比较强烈的语用情感或语用紧迫感。
通常认为,言语的使用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意识或内心情感,语句的生成应该是意识活动的产物,并包涵一定的语言策略,但笔者认为,语言的使用并非都伴有较高的意识参与,有时仅仅是一种下意识的顺应行为。
一、作格化、顺应、下意识
“格”指语义结构中名词与关联动词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这种关系一旦确定就不会轻易变动。然而,如此稳定的关系并非只是通过名词的形态变化表现出来,而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附加成分、词序或介词等加以表现。作格是一个术语,原是对语言进行语法描写时使用的一种格标记。在作格语言中(如爱斯基摩语、巴斯克语、俄语等),一些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具有相同的格形式(即宾语和主语为同一个格),被称为“通格(absolutive)”,而及物动词的主语被认为属于作格,表示诱发了一个新过程。在宾格语言中,英、汉语中有些既可用于及物句又可用于不及物句并形式保持不变的动词被认为是作格动词,如“smash(摔)碎”、“break(破)坏”、“open(打)开”等,这些动词的主语虽然没有特殊的形式变化,但一般都指示新过程的发生并有动能释放。作格化(或作格过程)就是在句法层面上将受事宾语置于句首并主语化,例如,在英、汉及物句(S+V+O)作格化过程中,宾语O被提升至主语位置,其语义和句法地位被焦点化,动词V由及物变为不及物V作,原型事件由“延及”变成了“自启”,S+V+O最终演变为S受+V作。两个句型里的谓语动词虽被认为具有不同的语义功能,一个是及物动词V,一个是作格动词V作,但形式上V和V作没有任何差别。S受+V作预设:1)原型及物事件S+V+O中的O受到了V的作用;2)O启动了新过程(V作)。
顺应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不断选择、不断调节、相互适应的过程,语言形式的选择是以语用策略为基础的选择,既有连续性又有即时性等特点,显示出极强的顺应性。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1]59-61,为交际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本保证。顺应或顺应性选择除了方式选择之外,还可在语言的多个层面上同时发生,例如形式、语调、重音等。顺应不仅是形式的顺应,还有策略的顺应,“其运作过程既可以是完全有意识的,也可以是完全无意识的,中间会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细微差别”[2]。顺应既包括交际意图的顺应,还包括交际环境的顺应,更包括语言结构、形式的顺应,S+V+O演变为S受+V作就是顺应的结果,体现了语言本身具有的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S受+V作是一个被熟练使用的构式,顺应性极高,完全可能在无意识的参与下使用。因此,S受+V作的使用有时并不是运用某种语言策略的结果,而只是一种下意识言语顺应行为。
在心理学上,下意识指知觉意识范围之外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是有机体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原始反应,具有本能、被动等特征。意识常常压制本能的冲动,使其只能得到暂时的、象征性的缓解,而下意识却促使各种本能冲动得到释放或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存在犹如一座冰山,意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淹没在水下的大部分则是潜意识[3]。下文中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词在使用上无意义差别,只是缘于引自于不同著作文本。意识是本能的东西,暗中支配意识,是人类天性不加掩饰的自然显现,但“也有后天学得的类似自动化的一切方面”[4]。比如,当手被尖锐物刺到时,往往会应激性地缩回;当女生见到心仪的男生时,往往会有情不自禁的眼神、面部表情或肢体行为等。
二、S受+V作之语用功能
S受+V作是一个构式。在句法层面上,V作是S受的述谓,两者呈主谓关系。两者在语义层面上的关系比较复杂:显性上S受是V作的体现者,表示新过程的启动;隐性上S受是V作的受损者,表示S受承受了V作的作用。构式所表达的事件类型或行为类型是人类在认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某种经验框架,是一种极度抽象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构式是一种“预制结构”,易于整体或“自动化”使用。
S受+V作在语义上蕴涵了两个事件(动作行为+终点结果),但句法上只有一个动词。S受+V作是一个“最简方案”,常被用来把一个事件包含在另一个事件中,以便快速把信息加以综合并传给其他人。例如:
a.The glass smashed.
b.米饭糊了。
这两个例句拥有相同的结构(S受+V作),都是结果动词作谓语,施因动词被省略。因此,笔者认为,S受+V作是一个隐含施因动词的“双动”构式,虽然其施因动词在作格化过程中被结果动词“屏蔽”,但在句法上仍可以还原成“双动”形式:V因+V果,在语义上也还原为“动作行为+终点结果”的关联式。
c.The glass smashed(V果).→John smashed (V因+V果)the glass.→John did(V因)so mething,and the glass went(V果)into pieces.
d.The boat sank(V果).→Mark sank(V因+V果)the boat.→Mark shook(V因)his body,and the boat went(V果)under water.
通过例证可以发现,在“John smashed the glass”(S+V+O)中,谓语“smashed”只是施因,似乎没有结果,但仔细观察便知这里的“smashed”其实是施因动词与零形式动词(V0)的复合体(V因+V0),即V果已经被V因“屏蔽”变成了V0。尽管如此,V果还是留下了自己的语义痕迹。
c1.The glass smashed(V果).→John smashed(V因+V0)the glass.→John did(V因)so mething,and the glass went(V果)into pieces.
d1.The boat sank(V果).→Mark sank(V因+V0)the boat.→Mark shook(V因)his body,and the boat went(V果)under the water.
在上述例句中,汉语的还原路径大致一样,不同的是,汉语S+V+O中的结果动词没有被施因动词“屏蔽”,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即V果没有退化为V0,试比较:
e.米饭糊(V果)了。→小李煮(V因)糊(V果)了米饭。→小李煮(V因)东西,米饭糊(V果)了。
f.杯子碎(V果)了。→小王摔(V因)碎(V果)了杯子。→小李摔(V因)东西,杯子碎(V果)了。
观察以上例句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The glass smashed”和“John smashed the glass”两个句子中的“smashed”虽然形式一样,但功能大不相同,前者的“smashed”是结果动词,为不及物形式,而后者的“smashed”则是施因动词,为及物动词。
第二,S受+V作和S+V+O一样,它们的原型结构不是单动词构式,而是双动词的“动-结”构式,蕴涵了因果关系,差别是:S受+V作是一个施因动词虚化并被“屏蔽”的隐性“双动”构式,即V作是一个V因+V果的复合体,V因被虚化,V作=V0+V果(V因+V果)。S+V+O恰恰相反,是一个结果动词虚化并被“屏蔽”的隐性“双动”构式,V也是一个V因+V果的复合体,V果被虚化,V=V因+V0(V因+V果)。
c2.The glass smashed(V0+V果).→John smashed(V因+V0)the glass.→John did(V因)so mething,and the glass went(V果)into pieces.
d2.The boat sank(V0+V果).→Mark sank (V因+V0)the boat.→Mark shook(V因)his body,and the boat went(V果)under the water.
第三,S受+V作与S+V+O同为聚合性构式,原始功能相同,它们都可以把时空相邻的两个(或更多)客观事件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含因-果序的语言事件并有所突显。但是,它们的语义功能截然不同:S+V+O突显的是施因,并由施因预设结果;而S受+V作突显的是结果,并由结果预设施因。因此,从S+V+O到S受+V作的转变是一个构式转化为另一个构式的“嬗变”过程,也是一个功能和形式上得以自足的过程,其自足性来源于作格化。
从S+V+O到S受+V作的作格化过程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语篇层面的信息分布序列与信息出发点的关系。任何一个话语形式都有自己的信息出发点和信息序列特征,信息出发点就是话语主题。一般位于句首,是被确定的言说对象,是整个信息片段所关涉的焦点和开端,即以哪一个经验范畴作为谈论对象。一个语句一旦被确定为S受+V作形态,最先确定的就是其信息序列或信息框架:主题+述题。S受+V作的信息框架意味着其必然以受事而不是施事为信息出发点。在S+V+O中,S是旧信息,却占据出发点位置并成为句法上的主语,新信息O则出现在末端,为后续信息的补充和语篇的衔接提供了可能的连贯性和稳定性。S受+V作框架将S+V+O中的旧信息S屏蔽掉,将末端的新信息O提升至句首成为信息出发点,从S受和V作的句法关系看,两者之间形成主谓关系,S受为语句主语。如此一来,S受实现了句子主语和话语信息出发点的重合。
二是逻辑层面的中心参与者与作格的关系。逻辑主语是逻辑判断的对象和起点,表明言说者在开口之前有了足量的信息准备:1)确定某一对象的存在;2)确定该对象为逻辑判断支点;3)给该对象定名,为逻辑判断作载体。在S+V+O构式里,S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成为言说判断的起点。S+V+O是一个典型的“外延”型事件,内涵因-果关系,及物性高,具有“致使、改变”等性质,S在S+V+O因-果链中的角色是施因主体,表示致使或动力来源。S+V+O原型特征为[S←V]→O,核心是[S←V],S是中心参与者。
由于视角的变化,言说者逻辑判断的起点、核心自然不同,受“主题+述题”信息序列以及S受+V作语用功能(突出结果)的制约,S受+V作必须将结果前置。按照人类一般思维,施因在结果之前,例如S+V+O。但S受+V作则相反,结果出现在施因之前,句a里“the glass”在因-果链中是“果”的承担者,却出现在句首。被作格化处理后的“the glass”不再是被动受影响的参与者,而是变成了新过程的主体进入透视焦点。例句a突显了“the glass”在外力作用下释放出自己的动能,开启了新过程,成为中心参与者。而“John”是新过程的外在诱因,此时已退出判断焦点。
S受+V作是一个“核心”型事件,其原型结构为S←[O←V],以新过程[O←V]为核心,S已被“屏蔽”成为S0,S←[O←V]演变成S0←[O←V],O被提升为中心参与者并被作格化为S受。
作格化完成之后,S受既是逻辑层面上的判断对象和起点,又是语篇层面上的信息推理中心,S受的出现又激活了V作,实现了结构上和功能上的自足,直接“显示出作格经验范畴和信息语义价值在作格句中的参照关系和同一性”[5]。在句a中,被作格化的“the glass”受事性减弱,施事性增强,并获得了主语特征:第一,以作格形式出现在句首并充当主语;第二,对其后的谓语动词有约束;第三,排斥施事进入话题位置。语义上,事件结果得到突显,施因被虚化并最终脱离实际话语形式。语用上,说话人的交际动机得到强调,将最为关键的信息呈现在话语最前面。
在作格化过程中,构式的语用功能从S+V+O的命题表达为主转变到S受+V作的情感表达为主,“表义功能减弱,表情功能加强,并且与态度、情感和立场愈加相关”[6]。S受+V作突显了事件结果,使S+V+O中不显著的东西变得显著起来,便于将听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最关键”的话语信息上并激起对方情感共鸣,消除了说话人的语用压力和潜意识中的情感诉求。
三、S受+V作对知觉体验的顺应
我们的思想里早已有了类似因果、施受等“法则”,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有因才有果,有施才有受,因果、施受等法则似乎都是后者以前者为条件,其实未必尽然。例如,在现实中,我们可能突然感到一下刺痛,便开始查找原因,结果发现了一枚针,明白了是因针刺而痛,于是便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针-痛”(认知)顺序并成为思想的一部分,“针”为因,“痛”是果,即先因后果。但从实在的知觉体验看,“痛”首先被感知,先有“痛”,后才寻到“针”,即先感知结果,然后再溯源认知原因。由此可见,认知是经过意识整理、加工的知觉体验总和,与感知或知觉体验之间有距离。也就是说,感性的知觉体验不能直接与理性的认知意识划等号,也不能直接进入思想。
思想不是对现实的反映,也不是对知觉的反映,而是对认知的表征。思想的形成大都是在意识的参与下通过抽象、推理、综合等方式逐渐完成的,不过也有一部分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即下意识中形成了一些类似“针-痛”的认知顺序(“因”在先),并以此替代了“痛-针”感知顺序(“果”在先)。最常用的S+V+O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针-痛”思想的表征化,S和O之间通过V结成因果关系,是因-果序的隐喻,除非特殊的语言策略,S总是出现在O的前面。S+V+O隐喻了人类最一般的认知习惯:先因后果。但是从知觉过程看,先感知的往往是结果,人们总是认为有“太阳晒”才有“石头热”,但是真实的情景则是先感觉到“石头热”,再寻找“热”的原因。按照真实的感觉体验,“太阳晒”和“石头热”的语言信息序列应为O+V+S,没有O的出现,就不可能有V事件的成立。
与S+V+O相反,S受+V作的信息序列与人们的感知顺序贴合度很高,S受是主题对象(结果的承担者),接下来是V作(V果+V0),表示实际结果,没有施因。由此看来,S受+V作的首要功能就是通过聚合突出事件结果。它以事件结果的承担者S受作为信息出发点,必然会立刻激活后续的述谓信息——实际结果(V作)。结果(V作)的出现又预设了施因的存在,而无需更多的言语表达。如此信息序列象征着知觉的自然顺序:先果后因。
一个构式是一个认知图式,反映了人类的认知习惯及语用目的,“其间各个组成成分的次序、远近、多寡都是造成句式整体意义的重要因素”[7]。不过,交际者主体因素(包括情感、动机、乃至知觉体验等)对现实情状凸显的决定性自然也会对构式的形式和功能产生巨大影响。语言是概念法则的总和,但概念和法则并不总能引导我们对本体世界进行预设,因为它们往往是落后的东西。相比较而言,经验感受、直觉与本能则更早一步,是更需要得到表达的新东西。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石头热”,还需要寻找“太阳晒”吗?因此,句法结构与知觉体验之间也应该具有象似性,成为知觉体验的表征:最先感受到、最先想到的东西说在最前头。
S受+V作与人的一般体验规律保持一致,可以让听说者首先感觉到结果对象,如“the glass”,接下来是述谓“smashed”,补充主语的新信息,满足对方的信息需求。就构式本身而言,如果说S+V+O隐喻了人类的因-果认知范畴,S受+V作就是对果-因感知体验的隐喻,这样的信息顺序与人的知觉本能保持一致,无论是言说者还是听说者在使用过程中都无需太多意识的参与。
语言不是用来抽象的,也不是用来描述的,而是用来辅助认知的。在意识的参与下,语言必然趋同于认知,为认知服务,其形式、概念结构等必然与客观情状之间(认知的结果)存有“映照性相似”[8]。但语言也为知觉感受服务,相比认知、思维而言,知觉体验来得更早,更需要得到快速传递。因此,语言在许多方面必然与人的经验框架(如知觉顺序、情感需求等)相吻合。
四、S受+V作对本能需求的顺应
心理学认为,个人的自我感觉往往是脆弱和孤独的,人都有推人及已、自哀自怜的时候,且这种感受常常向外波及、延伸。当身处“受损”情状时,自然的反应(包括应激反应)就是同情并希望激起他人共鸣,同时伴有语用紧迫感。在“受损”语境中,同情、语用紧迫感与“刺痛-缩手”一样是一种本能,多为下意识行为。同情是自发的情感趋同,指当事人站在弱者立场上去感受,对弱者的同情就是自我怜悯或是自我保护本能的外射和延伸,本能的东西往往更有驱动力。
信息的突出程度往往与说话人的认知、情感需求有关,但也取决于直觉感受和心理本能,很多时候说话人最急于表达的往往是最急迫的东西:新信息、事件结果、最早被感受和体验的东西等。S受+V作的独特信息构成模式和交际功能使其无需太多意识加工便可“自动化”地运用,并把“最急迫”的东西前景化,以便快速引起对方注意,满足本能需求。
同情往往潜藏在意识之下,只有在特定的刺激下才不经意地冒出来,被不经意的行为所出卖。在“受损”情状中,可能是出于某种感觉或情欲,抑或是本能,言说者常常不以客观眼光审视事件,而是下意识中把自己“转化到事物里去”[9],推人及己,自我对象化。例如句a,“the glass”因外力而“smashed”,言说者本能地在其身上体验到了一系列“弱者的东西”。对“杯子破碎”的同情是一种下意识的情感涌动,是人的一种天性,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天性就在那里。“用弗洛伊德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自我虽然是基于意识的,但是自我也是无意识的。”[10]
句法的顺序反映了人类的认知习惯,更反映了人类特殊的语用目的和情感取向。因此,急于呈现的东西常常是说在前头。交际中,“受损”情状驱使你去做内心深处“最最想做的事”,并期待对方给予相应的情感回应和情感回报,言说者可能用颠覆常规和理性的表达方式,以尽快释放自己的语用紧迫感。例如,言说者没有选用及物式(S+V+O)“John smashed the glass”,或“双动”式(V因+V果)“John did so mething and the glass went into pieces”,而是“自动化”地运用了作格式(S受+V作)“The glass smashed”。其原因在于:S+V+O的中心参与者是S,但S仅是施因,“受损”情状中激发言说者同情的不是施因,而是“受损”的结果。与此相反,S受+V作的核心是[O←V],O是中心参与者,是结果的承担者,是言说者的同情对象,是“最最急于呈现的东西”。
g.Mary did so mething and caused the ball to m ove up and dow n violently and noisily.
Mary caused the ball to m ove up and dow n violently and noisily.
Mary m oved the ball up and dow n violently and noisily.
Mary bounced the ball violently and noisily.
Mary bounced the ball.
以上几个句子语义大体相同,表达了一个“受损”语境。其中,“the ball”为“受损”体,是言说者同情的对象,“Mary”只是一个施因的主体,不在言说者关注之列,最能够帮助言说者快速消除语用压力、把“受损”情状传递出去的方法无非就是把受损对象放在话语最前面,紧接其后就是结果。例如:
h.The ball bounced.
语言表达式不仅是认知、思想的隐喻,更是言说者情感和本能的隐喻,S受+V作作为一种“他化同情”的外在表征,是言说者下意识里的心境外射或情感流露,折射出说话人一种暂时的情感寄托或本能需求。
虽然我们认为“可以把语法形式看作是逻辑形式、纯思维形式的某种运用”[11],但我们也认为,在“受损”或是急迫语境中,对S受+V作的使用多源于蛰伏在潜意识中的同情本能,是言说者释放语用紧迫感的自然选择,是在言说者意识之外发生的言语行为,S受+V作结构本身就是对言说者本能需求的隐喻。
五、S受+V作是一种下意识的顺应
语用紧迫感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很多时候并不是言说者能够清楚意识到的。下意识是人天性中所固有的东西,是人对环境的一种自然反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在一定刺激的作用下,一系列的动作(或语言、文字等)便可以一个接一个地、自动地产生出来”[4]。下意识冲动总是力求得到满足而与意识相冲突,语用紧迫感常常以非常态方式得以释放。
Verschueren(1999)认为,语言的使用要从语境关系、语言结构、顺应的动态性、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等方面来描述和解释。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不是静态的,其结构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必然受到言说者在顺应交际过程中意识参与程度的影响。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人不仅要认识事物,还要评说事物。所谓评说,是指主体用一定的尺度或评判习惯去度量评价对象。在评说时,言说者的头脑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具有一定认识模型和评价尺度的。这里的“尺度”,就是认识主体的价值观念和大众认知心理(亦称百科知识)。“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不光是有意识的,还有潜意识的评价。”[3]130潜意识评说,即我们在观察、认识事物(件)过程中,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运用某种尺度对该事物(件)作出自己的评说。在评说时,我们可能不清楚为什么运用了这个而不是别的尺度,也不清楚是什么尺度或标准,更不清楚自己的脑子里如何存有这样的尺度。尺度的形成可能更多地源于大众认知心理,但其形成、存留及如何起作用等这些问题对于言说者个人来说可能都是模糊不清的。然而这些东西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并形成种种思维定势,自发地、自动地起作用并制约认知。评说有时并不需要意识参与或特别的语言编码,人们只是“自动化”地运用了早已存于脑中的“尺度”和语言构式。“人类几乎所有的思维都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的认知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们对经验进行概念化。”[12]
S受+V作是一种高度“自动化”的信息构建,它不属于语言策略,而是一种已被熟练掌握并自动化运用的“预制构建”,常常被人们拿来评说事件(物),以验证自己头脑里的“尺度”。相比较而言,语言策略是能够被意识控制的东西,是经过意识加工的东西,是人们在意识支配之下对客观情状进行抽象、概括、分析、判断等一系列思维整理的结果,例如:
i.杯子易碎。
j.杯子,碎了。
k.杯子被打碎了。
l.碎了,杯子。
句i只有一个动词,但它并不是一个现实事件,而是一个由高度的主体意志构建的可能世界,不蕴涵外在的致使因素。这不是一个普通的P+V概念,而是理性判断的产物,虽然结构上也是S+V,但没有结果,更不是两个动作行为的聚合。句j是一种刻意突显的方式,强调评说的具体对象或起点。句k也是一种语言策略,有意识地突出了受事参与者的主体信息和事件结果,句l与句j、k同为强调句,但是强调评说的起点却是事件的结果,而不是主体。以上几个例句本质上都是在较为强烈的意识参与下生成的,与“杯子碎了”有区别。
在日常交际中,有些东西(尤其是那些令人吃惊、不如意的东西)最容易激发人的同情心和语用紧迫感,这些东西往往未被言说者清醒意识到,但却被下意识所发现和捕获,下意识能捕捉到一般意识无法捕捉到的东西并提前作出反应,例如当事人对即将到来的东西感到悲哀、怜惜,或是兴奋、窃喜等。这些不易被意识察觉的东西却早早地被下意识捕捉到,将这些“被早早地捕捉到”的信息尽快地传递出去必然是言说者下意识里的催促和需求,从而使本能欲望得到释放或满足。在这种情状中,言说者的语用压力顿生,言说行为可能变得仓促甚至无序,但简单、高效,易于快速释放压力,策略的东西根本来不及起作用。例如在“杯碎”情状里,杯子“受损”触及到了言说者的同情本能,使其不知不觉中动了感情,作出评述以博得语用回报,但评述行为本身、评述尺度或认知趋向等都可能是在无意之中起作用的,“句式结构折射出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把握,是作为用语言的形式来认知和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结果,这一结果一旦形成,又成为后来人们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世界的工具框架”[13]。
S受+V作既是一种“框架”,更是一种“结果”,无论是从语言结构、意识参与程度,还是从适应性来说,S受+V作都是对“受损”语境的一种最好顺应方式。
综上所述,言说行为并不都是意识参与的结果,有时言说者虽然有了一定的言语行为,但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参与,甚至不清楚自己话语的内容、动机或意图等,而仅仅只是下意识中的语境顺应,如“Hello!”“Hi!”“你好!”“吃过了?”等。
顺应是一种交际,其内容和形式都随语境和言说者情感状况而定。语用顺应和语言选择相辅相成,选择是手段,顺应是目的和结果,“不管这些选择和顺应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1]55-56,最终的结果都是解除语境压力,消除语用紧迫感。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S受+V作都有着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情、表义功能,是一种多层面的隐喻。这种隐喻既是对人类知觉体验的隐喻,也是对人类本能的隐喻,更是对言说者个人语用紧迫感的隐喻。S受+V作是一种高度的形式变异,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语境顺应性,其简洁的结构和集约的内涵保证了语言使用者能自动地甚至是在无意识的参与中排除其他语言选项。
[1] VERSCHEU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Arnold,1999.
[2] 耶夫·维索尔伦.语用学诠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12-213.
[3] 张浩.论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J].东岳论坛,2007 (4):126-130.
[4] 周志晓.“从自我出发”与“下意识”浅论[J].戏剧艺术,1988(2):22-31.
[5] 彭宣维.作格关系、语态类别和信息推进——一项以阶段性加工为基础的认知研究[J].外语研究,2007(3):41-48.
[6] 杨佑文,管琼.语言的主观性与人称指示语[J].外语学刊,2015(3):46-52.
[7] 张伯江.施事和受事的语义语用特征及其在句式中的实现[D].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
[8] 王寅.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1-6.
[9]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33.
[10] 王天林.无意识的意识本性[J].心理学探新,2008 (2):11-15.
[11] 赵秋野.俄罗斯哲学家施别特对洪堡特语言意识观的阐释[J].俄罗斯文艺,2012(2):97-104.
[12] FAUCONNIERG,MARKT.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 m plexities[M].New York:Basic Books,2002:33.
[13] 徐盛桓.试论英语双及物构块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2):81-87.
(责任编辑:郭红明)
Seeing Adaptability of Ergativit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ZHANGXiao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6,China)
Speaking is not all the result of awareness participation.Although so metimes the speaker performs a certain verbal behavior,he/she is not very conscious of w hat the content,m otivation or intention of his/her utterance because the utterance,for lack of conscious awareness,is but a kind of adaptation in the subconscious.Adaptation is not only co m m unicative need,but m ore co m m unicative result,always necessary to meet the context requirements,and so regardless of w hatever awareness or reason,the final outco me of adaptation is the quick elimination of the prag matic urgency to lift the context pressure.Spatient+Vergativeis a kind of m ulti-level metaphor not only for hu man experence,for hu man instinct,but also for the speaker′s prag matic urgency.Spatient+Vergativeis highly flexible and context adaptive,therefore the generation of w hich is m ore often not a language strategy,but sim ply a kind of adaptive behavior in the subconscious.
ergativity;subconscious;adaptability;prag matic urgency
H0-05文献标示码:A
1673-0453(2015)03-0037-07
2015-08-19
张小红(1966—),男,安徽明光人,安徽农业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研究。